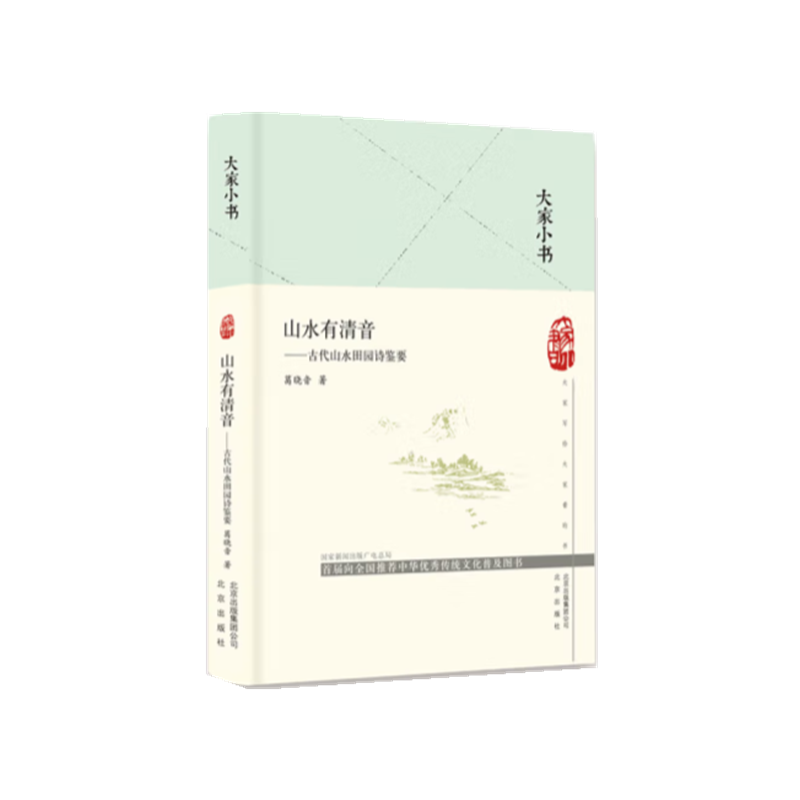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27.00
折扣购买: 山水有清音——古代山水田园诗鉴要
ISBN: 97872001454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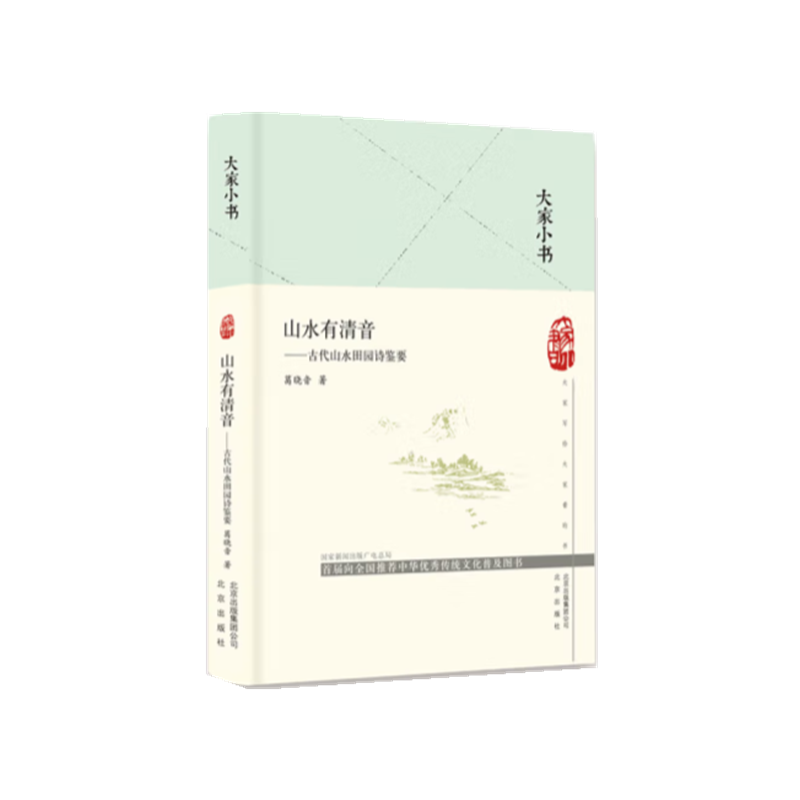
葛晓音,女,1946年生于上海,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获北大中文系中古典文学硕士学位后留系任教。1989年起任北大中文系教授。曾任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主要著作有《八代诗史》《汉唐文学的嬗变》《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唐宋散文》《中国名胜与历史文化》《古诗艺术探微》《山水有清音——古代山水田园诗鉴要》等。
山石 山石犖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蹋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贞元八年(792)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后贬阳山(今广东阳山)令。唐宪宗时升为刑部侍郎,因上表谏阻皇帝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最后官至吏部尚书。韩愈主张尊儒排佛、反对藩镇割据,并倡导古文运动,是唐代著名的大儒和古文家,散文成就极高。 韩愈博学多才,古文滔滔雄辩,以写作散文的才力和学问来写诗,就形成了韩诗的一个重要特点:以文为诗。所谓“以文为诗”,并没有确切的定义,只是古代诗话中的一种印象式的评论,大体指诗人采用或吸收散文表达的一些手法和特点来写诗,比如在诗里发议论,或者采用文章的布局章法等等。以文为诗的表现方式会产生一些弊端,例如描写过分细致,平铺直叙,缺乏诗歌的跳跃性,不够含蓄有味等等。但是也会扩大诗歌的表现力。成功与否要看具体作品,不能一概而论。山水记游诗是适宜于吸收散文手法的一种题材。中唐和宋代的一些诗人力图使诗歌能像散文一样具体详实、有头有尾地表现出较长时间的游览过程,自由地抒发议论,虽然写出了不少缺乏诗味的押韵之文,但是也有一些成功的作品,韩愈的《山石》就是其中的一例。 《山石》大约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韩愈当时任节度推官。七月在洛阳,与两三个友人到洛北惠林寺去钓鱼,当夜宿于寺中,次日归去,有感而作此诗。从表面看,这诗犹如一篇平铺直叙、文笔简妙的游记。然而一句一景、移步换形,层层展开黄昏、入夜、黎明等各个时分的不同画面,贯注着游人从中领悟的人生乐趣。一所荒山古寺,经诗人用浓淡相间的色彩点染之后,不但处处呈现出幽美的境界,而且渗透着诗人的特殊个性。 开头四句写诗人黄昏时进入山寺的过程:“山石犖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前句写沿着小路在高低不平的山石中穿行的经过,后句写到达山寺的时间以及黄昏蝙蝠乱飞的情景。开门见山地点出山寺环境的荒凉僻静,黄昏中的山色、寺景随着交代到寺的路径和时间步步展现。而且一起调便见出诗人崚嶒的骨相:“犖确”两字形容山石的棱角不平,却也能令人联想到韩愈很不随和的性格。韩愈一生刚直不阿,不肯趋附权贵。苏东坡曾说过:“犖确何人似退之,意行无路欲从谁。”就是用这首诗的第一句来比喻韩愈的性格,但也确实看出了《山石》取景及其格调与诗人性格之间的内在关系,可说是韩愈的知音。这两句选景取山石蝙蝠,遣词用僻字拗调,以怪景硬语导入幽境,倍增新奇之感。 接着在升堂坐阶的过程中就势捕捉住乍到寺中的第一眼印象:“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支子”即栀子花。用“大”和“肥”这两个极俗之字形容芭蕉、栀子吸足新雨之后的饱满水灵,也是一种反传统的手法,但这里用得十分恰当,因为刚刚坐定,天色又暗,不能细细鉴赏,只能得出一个花木都长得很壮的粗略印象,所以用俗字比雅词更能传神地表现诗人久居世俗、偶出尘外的清新感受。 接着诗人被寺僧引到佛殿里观看壁画:“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寺僧说画和以火照画都与前面的叙事步步紧接,文意没有一点中断,因而自然暗示出天色由昏变黑、游人自外入内,丝毫不露转换的痕迹。“稀”字一语双关,不仅赞美古迹的珍奇为世所稀有,也写出了古旧的壁画在烛光下影影绰绰的图像,使以火照画这幕情景本身就显现出一种秾丽而略带神秘的情调。 看完壁画,就该吃晚饭睡觉了:“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铺床拂席,是僧人为诗人留宿寺中做准备,连同设置羹饭等一系列动作,平直琐细,像散文一样铺叙,似乎是诗里可以省略的情节。但是写得亲切朴素,寺僧的殷勤和寺中生活的清苦也可由此见出,而且传达出诗人自得其乐的神情,所以语言虽然平淡却兴味十足。 躺下以后,诗人却睡不着:“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入岭光入扉。”渐渐不闻虫声,月光照进门内,是已到夜深的情景。这里只是从静卧之人的听觉和视觉去写时间的流转,而山寺深夜的静美意境、诗人一夜不眠的复杂思绪,都历历分明。 紧接着是从夜深到天亮离寺的过程:“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天明离寺,信步走去,由于晨雾迷漫,不见道路,上上下下在云雾之中到处走遍。这两句写空气的迷濛清润,与夜间的澄澈清朗各臻其美。古人有“烟霏雨散”句,此处用“穷烟霏”写平明真景,又照应黄昏雨后的兴象,何等自然现成。由于诗歌一开头就是上山到寺的情景,没有细写周围的景物,因此正好借天明以后下山的过程,补足了山景:“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山色烂漫为远望,松枥十围为近观。“山红涧碧”用概括的颜色写出满山花叶繁盛,溪涧水流清澈的美景。“十围”指十人拉起手来才能合抱的树干直径,一路走去常可见到这样高大原始的林木,更可见山中的深幽。这两句写出景物的远近层次,同时在景色转换之间也暗示了云开雾敛的天气变化。正如苏东坡所说:“宿云解驳晨光漏,独见山红涧碧时。”前面既然说满山烟霏,那么要看见山红水碧,必然是云雾收敛,晨光泄漏之时,远处的景色才能尽收眼底。 “当流赤足蹋涧石,水声激激风生衣”两句对渡涧的情景作了一个特写,借此与题目和开头的“山石”呼应:赤脚踏在山涧中的石头上,水声激激清其耳,山风吹衣入其怀,耳目为之全新,身心任其荡涤,是何等惬意!诗人在世俗中蒙受的尘垢,可藉此冲洗一净,所以自然引出以下的人生感叹:“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人若能够在如此美好的大自然中自由自在,不受官场的羁束,就足以快乐地渡过一生了。所以诗人不禁反思自己和二三好友,为什么到老还不肯回归自然呢?这段感想出自为景物触发的真情,成为全诗的点睛之笔。《论语》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结句由此化出,暗示想要在此归隐的意思,更见韩愈的儒者本色。这里虽已点透诗人从暂游山寺所悟出的人生乐趣,但背后还有一层不屑久居幕下的苦恼、渴望摆脱他人羁束的意蕴可供回味。 这首诗以游记首尾完整、层层深入、篇末结出感想的记叙手法为纲,以诗歌直寻兴会、融情于景、触目生趣的传统表现方式为本,画面层次丰富,色调绚丽清爽。虽然整个过程写得寸步不遗,但是处处流露出对山寺环境的清新感悟。因此是一篇以文为诗的成功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