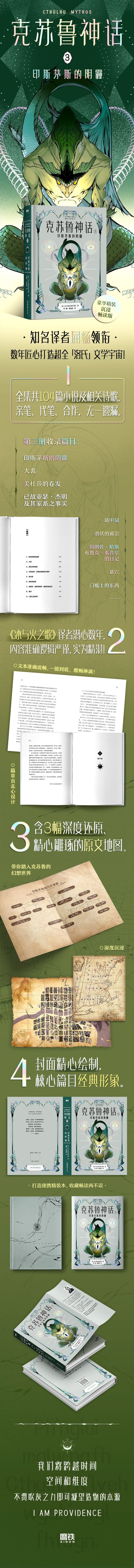出版社: 中国友谊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41.70
折扣购买: 克苏鲁神话.3·印斯茅斯的阴霾
ISBN: 9787505758421

"作者 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 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1890年8月20日-1937年3月15日。 美国恐怖、科幻与奇幻小说作家。作为“克苏鲁神话”的文化创造者,洛夫克拉夫特被看作是20世纪影响力极大的奇幻恐怖小说大师之一。 译者 屈畅,重庆人,毕业于四川大学。《冰与火之歌》系列译者,《巨龙的颂歌——世界奇幻史》作者, “史诗图书”工作室创立人,从事幻想文学的译介和出版工作。 邹运旗,北京求学,重庆定居。钟爱科幻、奇幻、恐怖、悬疑等类型文学。曾为自由译者、《科幻世界》杂志编辑,现就职于“史诗图书”。译有《神的九十亿个名字》等书。"
\\\"印斯茅斯的阴霾 (一) 1927年到1928年的冬天,联邦政府对马萨诸塞州古老海港印斯茅斯展开了奇怪的秘密调查。外界直到来年2月才有所耳闻,那时当局突然大肆搜捕,并在做好充分预案的前提下,有计划地焚毁和爆破了镇内荒废的海滨地带大批摇摇欲坠、饱受虫蛀、理论上无人居住的房屋。鉴于禁酒令期间时有流血冲突发生,习以为常的大众并未放在心上。 敏锐的新闻爱好者就不同了,此次行动投入力量之巨、逮捕犯人之多、处置方式又秘而不宣,这些都令他们倍感惊诧。对外报道并未涉及审判,连明确的指控都没有,事后在全国各地的普通监狱也找不到相关囚犯。有些声明含糊提及“疫病”和“集中营”,稍后又有传言说犯人被分散关押在陆海军监狱,但均无法证实。经此一役,印斯茅斯几乎沦为空城,最近才稍有复苏迹象。 许多自由主义团体对此口诛笔伐,迎接他们的是官方漫长的闭门谈话,他们中的代表长途跋涉走访了某些监狱与集中营,回来便集体失声、噤若寒蝉了。报刊记者更难对付,但最终也大多选择与政府合作,仅有一家小报——一家风格过于浮夸以致可信度大打折扣的小报——声称有艘深水潜艇朝魔鬼礁外的海底深渊发射了鱼雷。这条新闻是在水兵们常去的地方偶然打听到的,听上去颇为牵强,毕竟低矮的黑色礁石距印斯茅斯港足有一英里半之远。 周边乡野村镇的人们私下议论纷纷,对外却三缄其口。近一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在谈论日薄西山、几近废弃的印斯茅斯,恐怕很难有什么东西比他们多年来流传与暗示的故事更疯狂、丑恶了。然而许多经历教会了他们谨慎,事到如今也没必要对其额外施压——他们了解的真相毕竟有限,印斯茅斯地处广阔的盐碱沼泽,外加荒凉贫瘠、人口稀少,与内陆的交流本就不多。 至于我本人,最终还是决定打破禁忌,讲一讲此事的来龙去脉。我相信官方解决了问题,在这个时间点上,略微暗示惶恐的搜捕队队员们在印斯茅斯的发现,除了让公众起一身鸡皮疙瘩,并不会带来什么实际损害,或许还能引出对物证的其他解释。说到底,我也不了解全貌,且有许多理由希望此事真能到此为止——同局外人相比,我的牵扯过多,由此产生的种种杂念正驱使我做出过激举动。 1927年7月16日清晨,我发疯般逃离印斯茅斯,随后惊恐万状地请求政府展开调查并采取行动,由此带动事件见诸报端。当其热度高涨、悬而未决之际,我宁可保持沉默;如今时过境迁、尘埃落定,公众失去了兴趣与好奇,我却生出古怪而强烈的冲动,渴望不动声色地道出在那个名声不佳、阴霾笼罩、死神与亵渎怪物盘踞的海港度过的惊心动魄的数小时。原因无他,纯粹是想通过讲述来恢复镇定、回归本心,相信自己并非被癔病般的梦魇幻影压垮的头一人,并在今后面对可怕的选择时保持清醒。 我前往印斯茅斯时对它一无所知——迄今为止也没再去过——甚至前一天才听说这个地名。我为庆祝成年在新英格兰旅行观光、考察文物和寻根问祖,本打算由古老的纽伯里港直达阿卡姆,后者是我母亲的祖籍所在。由于没有私人汽车,我只能乘火车、电车和公交车,一路寻找最省钱的路线。在纽伯里港,有人说去阿卡姆得乘火车,而我在火车站售票处抱怨票价太高,这才引出印斯茅斯的话题。那位售票员身材结实,一脸精明,明显不是本地口音,他对我的精打细算深表体谅,进而提供了一条不寻常的建议。 “或许,你可以搭那路老公交。”他话里有些犹豫,“这儿的人一般不坐它,因为它会途经讨厌的印斯茅斯——你大概听说过此地。一个叫乔·萨金特的印斯茅斯人负责运营,但在这儿根本拉不着客,估计在阿卡姆也一样,鬼知道为啥还能通车,兴许是因为便宜吧。你在广场上就能找着——在哈蒙德药店门口——没改时间的话,早十点和晚七点各一趟。那辆老爷车一向只有两三个印斯茅斯本地客,反正我没坐过。” 这是我首度听说阴霾笼罩的印斯茅斯,然而任何一座没出现在通用地图和最新旅游指南上的小镇都能勾起我的好奇,售票员欲言又止的奇怪态度更是火上浇油。在我看来,能让附近居民如此反感的镇子,总该有些值得探究的特点,既是顺路,倒也不妨稍作逗留。于是我向售票员深入打听,对此他有些谨慎,口气也透出些许鄙夷: “印斯茅斯?唔,那个马努塞特河口的古怪镇子,以前差不多算是座城——1812年战争前港口相当繁盛,但近百余年间完蛋了。现在没有火车去那里,波缅线压根儿不从那里过,从罗利延伸的支线也停运好些年了。 “那地方除了捕鱼捞虾没啥营生,现在的空房没准儿比活人还多,外界基本都上这儿、阿卡姆和伊普斯威奇做买卖。镇子里以前还有几家工坊,如今统统关门,只剩一家黄金精炼厂半死不活地硬撑着。 “说起那家精炼厂,以前倒有点名头,东家马什老爷子是个大财主咧。但这怪老头基本上足不出户,据说晚年患上皮肤病,要不就是残废了,没法抛头露面。生意是他爷爷奥贝德·马什船长创办的,他娘好像是外国佬,有人说是南洋岛民。五十年前,他娶了个伊普斯威奇姑娘,当时差点儿没炸锅,因为附近没人想跟印斯茅斯沾亲带故。其实哪,马什老爷子的子孙后代跟别人也没两样,有人指给我看过——不过现在想想,好久没见着那些年长的子女了,我更没见过老爷子本人。 “为啥大伙不待见印斯茅斯?哎,年轻人,这些说法你也别太往心里去,这儿的人很保守,一旦种下什么念头就不放松。最近一百年,他们大概一直在议论——悄悄议论——印斯茅斯,我猜他们实际上怕得要死。有些传闻能让人笑掉大牙,比如说老船长跟魔鬼做交易,把许多地狱的小恶鬼带进印斯茅斯啦;又如有人声称1845年前后在码头附近同一地点撞见过恶魔崇拜和恐怖的献祭仪式。身为佛蒙特州的潘顿人,我不信这些鬼扯。 “但你最好听听老人家怎么描述海上那块黑色礁石——他们管它叫魔鬼礁,平素高出水面一大截,涨潮时也不会淹过太多,但算不上个岛。传说大群魔鬼时而来礁石上躺着,或在礁石顶部的洞穴群窜进窜出。那块礁石崎岖不平,离海岸有一英里多远,过去印斯茅斯有船只来往时,船员们为避开它,最终宁愿绕个大圈。 “我指的是外地船员,而他们厌恶马什老船长的一大原因,就是认为他会趁夜晚退潮登上魔鬼礁。或许他真的干过,礁石的奇特构造值得一看,上头兴许还真有海盗的宝藏,但船员们相信他是去跟魔鬼做交易。坦白说,我认为其实是老船长把那块礁石的名声搞臭了。 “这些都是1846年大瘟疫前的事了。瘟疫令印斯茅斯的人口锐减一多半,始终没查清来源,也许是船只从中国或其他什么地方带来的外国病。当时情况很糟,发生了暴乱,我相信许多不堪入耳的细节没传到镇外。最后印斯茅斯就成了这副德行,元气大伤,只剩下三四百号人苟延残喘。 “说到底,这儿的人对印斯茅斯人有种族歧视——我对此深表理解,我自己也很讨厌印斯茅斯,这辈子都不打算过去。跟你聊了几句,我听出你是打西边来的,但你也应该知道咱们新英格兰船去过非洲、亚洲、南洋及世界各地其他许多奇怪的港口,时常带回奇怪的人种。你可能听过,有个塞勒姆人娶了中国老婆回家,而鳕鱼角附近住着一大帮斐济岛民。 “印斯茅斯人同样不简单。沼泽和溪流几乎把那里与内陆隔开,虽然不清楚前因后果,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马什老船长曾有三艘船跑远洋,肯定带回过来历不明的怪人,所以印斯茅斯人的长相才变得这么怪——怎么说呢,看见就发毛,你坐上萨金特的车就明白了。他们大多长着奇怪的窄脑门、扁鼻子,玻璃般的眼泡朝外鼓凸,好像永远闭不上。他们的皮肤也不对劲,粗糙得像结了痂,脖子两边皱皱巴巴的全是皱纹。还有,他们年纪轻轻就秃了,岁数越大越难看——哎,说实话,我没见过他们当中年纪特别大的,八成照镜就能把自己吓死!连动物都讨厌他们,汽车出现之前,他们经常惹得马匹闹事。 “在这儿、阿卡姆和伊普斯威奇,没人跟印斯茅斯人来往,而无论是进城办事还是对付去他们地盘捕鱼的外地渔民,他们同样非常冷漠。也罢,鱼就爱往印斯茅斯跑,别地儿见不着——但你要自个儿跑去打鱼,就知道他们会怎么撵人喽!火车支线停运后,他们起初是步行到罗利再坐火车来这儿,现在则坐那路公交。 “对了,印斯茅斯有家‘吉尔曼旅馆’,但肯定很掉价,我不推荐。你最好在这儿过夜,搭明早十点的车去印斯茅斯,再赶晚八点的夜班车去阿卡姆。几年前有个工厂巡检员住过那家旅馆,碰到不少糟心事。尽管大部分房间是空的,有些房间却传来奇怪的说话声,吓得他直打哆嗦——他认为自己听到了外国话,可怕之处在于说话声很不正常,很像扑腾的水声。那晚他没敢脱衣睡觉,苦熬到天亮赶紧走人,说话声也差不多一宿没停。 “那位老兄——对了,他叫凯西——回来大发牢骚,抱怨印斯茅斯人如何戒心重重,好像时刻监视着他。他发现马什的精炼厂设在马努塞特河下游瀑布边的老工坊里,跟传闻中一样古怪。厂子的账册稀里糊涂,没有明确的交易记录。要知道,金子的来路一直是个谜,马什家族似乎没买过原材料,但多年前确实用船运出过大批金锭。 “以前还有传闻,船员和精炼厂工人会偷偷出售怪模怪样的外国首饰,马什家的女人们也戴过一两次。有人猜那种珠宝是奥贝德老船长从异教徒的港口换来的,身为航海家,当年他经常批量订购玻璃珠和小饰品去跟外国土著做交易;也有人至今依然坚信他在魔鬼礁找到了海盗的宝藏。有意思的是,老船长死掉六十年了,内战以来也没有像样的大船从印斯茅斯出过海,可马什家还在不停订购那些小玩意儿——听说主要还是玻璃和橡胶制的便宜货——仅仅数量有所减少。兴许印斯茅斯人自己喜欢,天知道他们是不是变得跟南洋的食人生番和几内亚蛮子一样坏了。 “1846年大瘟疫肯定带走了那地方的优良血统,无论如何,现在的印斯茅斯人有问题,马什家族等有钱人也强不到哪儿去。刚才说过,虽然那里的街道保持完整,但镇民应该不满四百,南方人管这号人叫‘白垃圾’——无法无天,奸诈狡猾,尽干些见不得光的勾当。他们倒总能打到鱼和龙虾,一货车一货车地拉出来卖,邪门儿了,为啥鱼就爱往那里跑,其他地方见不着咧? “没人清楚印斯茅斯人的情况,公立学校和人口普查员为此伤透脑筋。你可以想象,到处打听的陌生人在印斯茅斯有多不受欢迎。我老听说商人或官员失踪,谣传还有人被送进丹佛斯精神病院——肯定是他们干的好事,把人给活活吓疯了。 “所以喽,我要是你,就绝不会在那里过夜。我说了,我没去过也不打算去那里,但估摸着大白天旅行应该没问题,没这儿的人说的那么严重。若只是顺道逛逛,参观老古董,印斯茅斯还凑合。” 那天傍晚,我花了些时间在纽伯里港公共图书馆查资料。此前我在商店、餐厅、修车铺和消防站打听印斯茅斯时,发现本地人比那位售票员描述的更难开金口,似乎本能地抗拒这一话题,而我也没太多工夫软磨硬泡;况且他们隐隐有些怀疑我,似乎对印斯茅斯感兴趣本身就不正常。后来我在基督教青年会住下,办事员也不赞成我前往那个阴郁堕落的镇子,图书馆员同样如此——显然,在有教养的人们眼里,印斯茅斯乃是文明衰退的典型例证。 图书馆书架上的多卷本《埃塞克斯县志》对该镇描述不多,只提到它建于1643年,独立战争前以造船业闻名,19世纪初的海运兴旺发达,此后又利用马努塞特河的优势形成一个小型工业中心。但书中极少涉及1846年的瘟疫与暴乱,似乎把那当成本县的历史污点。 印斯茅斯衰落期的材料固然稀少,重要性却毋庸置疑。内战后,小镇的工厂只剩马什的精炼公司,除开传统渔业,金锭交易成了当地唯一重要的买卖。随着鱼价一跌再跌和大企业加入竞争,捕鱼收益越来越少,好在印斯茅斯港周围的渔获从来不缺。那里很少有外国移民,某些遮遮掩掩的证据表明,曾有一些波兰人和葡萄牙人做过尝试,但被当地人毫不客气地赶走了。 最有意思的是,县志还简略提到似与印斯茅斯相关的奇怪首饰。显然,全县人民对那些东西印象深刻,以至阿卡姆的密斯卡托尼克大学博物馆和纽伯里港历史协会的陈列室都有样品展出。纵然零星的描述乏味又平淡,字里行间却有些古怪的暗示撩拨着我,使我心头涌起微妙难言、无法释怀的暗流。尽管天色已晚,我还是决定申请参观,据说那是一件比例奇特的大型三重冕。 我带着图书馆的介绍函,拜访住在附近的历史协会负责人安娜·蒂尔顿小姐。幸好没到深夜,简单说明来意后,好心的老小姐就把我领进业已关闭的协会陈列室。那里的藏品琳琅满目,但我无暇欣赏其他,直奔角落展柜里那件被电灯照得闪闪发亮的奇异饰品。 紫色天鹅绒衬垫上的三重冕超凡脱俗、光辉夺目,充满异域风情又令人浮想联翩,再粗枝大叶的观众也会为之屏住呼吸。时至今日,我依然很难用语言描述它。诚如县志记载,它明显是种头冠,然而前端太高、周边太宽又不规则,就像为畸形的椭圆脑壳定制的。它的材质似以黄金为主,光泽却又白又淡,大概掺了同样华丽但我分辨不出的其他金属,熔炼成不可思议的合金。它的保存状况近乎完美,装饰设计不落窠臼,表面以无比优雅与娴熟的技法镂刻或浇铸出层次分明的高凸浮雕,其中既有单纯的几何线条,亦有直观的海洋生物——我所见到的三重冕意蕴深远、引人入胜,哪怕花上几个钟头研究也值得。 我越看越入迷,痴迷中又隐含着一丝难以界定或阐释的不安。一开始,我归咎为三重冕过于另类的神韵,因我见过的艺术品要么烙上了某个民族或国家的风格,要么是刻意挑战大众认知的现代主义尝试,但那头冠独树一帜、成熟到几近完美的技法与我见闻过的范例——不论西方还是东方,古典还是现代——都大相径庭,仿佛来自另一颗星球。 我很快又意识到,不安感或许存在同样强烈的第二个源头,也就是三重冕上构图与数学元素的古怪意象。所有装饰都隐喻着时空的遥远奥秘与无从想象的深渊,单调的海洋浮雕因之变得险恶起来。浮雕中那些半鱼半蛙、怪诞恶毒、难以言表的可憎怪物,似乎唤醒了人类的细胞和组织深处最古老原始的记忆,投射出萦绕不去的丑怪幻影,教我时而感到,每根描绘它们的渎神线条都在彰显彻底的异端与非人的邪恶。 据蒂尔顿小姐所言,别看三重冕雍容华贵,得来却全不费工夫。1873年,一名印斯茅斯醉汉以可笑的价格将它抵押给政府街某家当铺,随后死于斗殴,历史协会直接从当铺老板手中得到头冠,并立刻举办了与之相称的展览。它被标注为疑似出自东印度或印度支那,坦白讲只是猜测罢了。 对于三重冕的真正来源,又为何出现在新英格兰,蒂尔顿小姐比较各种假说之后,倾向认为其属于奥贝德·马什老船长得到的海盗的异域赃物。马什家族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开出高价试图赎回,即便遭历史协会反复拒绝,至今也没有放弃,这从侧面印证了此观点。 好心的小姐领我离开时明确表示,马什家族的财富来自海盗宝藏是本地有识之士的共识。纵然她并未去过阴霾笼罩的印斯茅斯,但那里无可辩驳地正与文明社会渐行渐远,活该受到排斥。她还向我保证,传闻中的恶魔崇拜并非捕风捉影,一个罕见的秘密教团已在那里发展壮大,霸占了所有正统教堂。 据她所言,该教团名为“大衮秘教”,毋庸置疑是个卑劣的异教组织,一个世纪前由东方传入。当时印斯茅斯的渔业本已濒临枯竭,却突然反弹并长盛不衰,教团自然笼络到大批头脑简单的百姓,很快成为镇上的最强势力,甚至取代共济会,将后者设在新教会绿地旁的总部老共济会堂也夺了过去。 总之,虔诚的蒂尔顿小姐完全有理由远离那个堕落衰败的古镇,但我的探索意愿却不减反增。抛开建筑与历史,那里的人种状况似乎也很有趣,回到青年会的小房间,我兴奋得彻夜难眠。\\\" "★全集共104篇小说及相关诗歌,洛夫克拉夫特亲笔、代笔、合作篇目,无一遗漏。其中某些作品,你也许从未读过! ★《冰与火之歌》译者屈畅,潜心数年,字斟句酌,文本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力求至臻! ★译者屈畅,以主题性对洛氏作品进行选择和排列,让读者能清晰地看到洛氏作品的总体脉络和有机联系,仿佛在读一个前所未有的长篇! ★含3幅仔细考证、细心设计制作的精美地图,以拉页形式装订,带你步入克苏鲁的世界,沉浸式畅读! ★封面精心绘制核心篇目《疯狂山脉》经典场景,打造便携精装本,收藏畅读两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