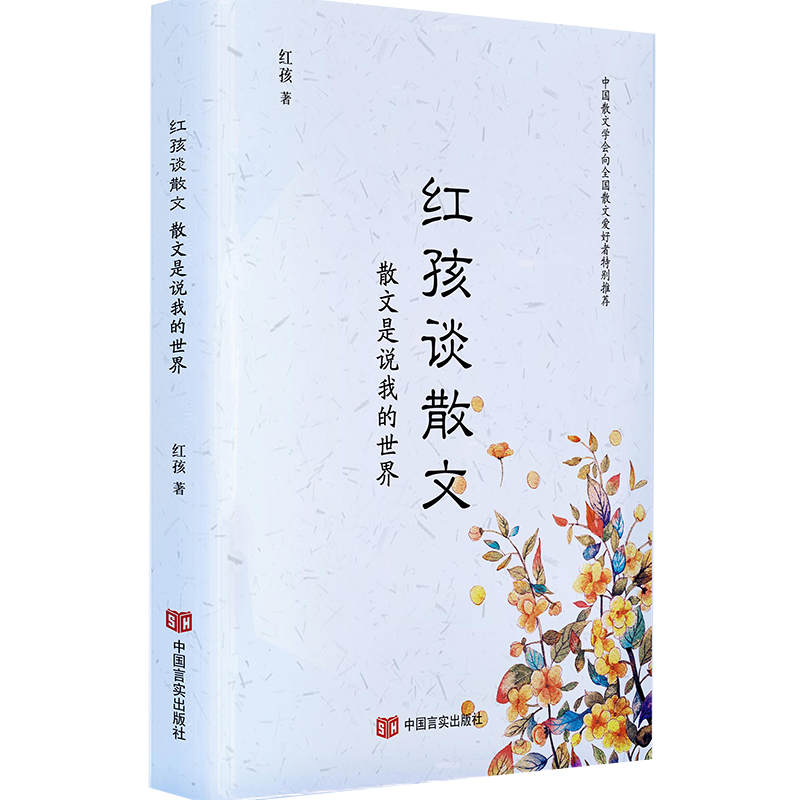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言实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46.80
折扣购买: 红孩谈散文(散文是说我的世界)(精)
ISBN: 9787517129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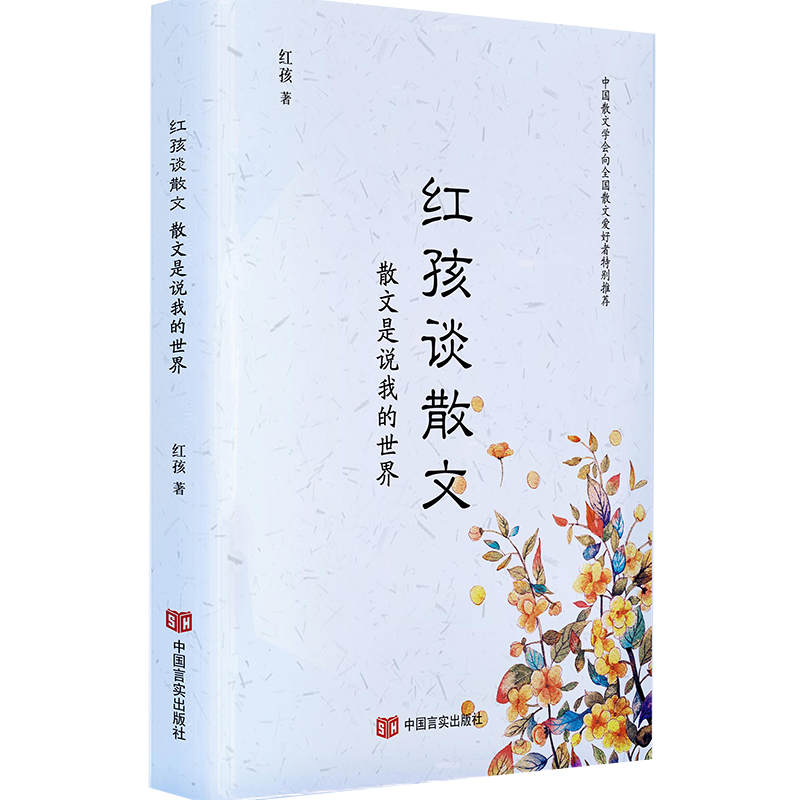
红孩,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委员,作家、文学评论家。已出版长篇小说《爱情脊背》,短篇小说集《城市的海绵》,散文集《阅读真实的年代》《东渡东渡》《理想的云朵有多高》,诗集《笛声从芦苇中吹来》,文艺评论集《拍案文坛》《铁凝精品散文赏析》等10余部,约300万字。曾获冰心散文奖理论奖,报人散文奖,文艺评论获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现供职文化部中国文化报社,主编文学副刊。
美的本质在于审美 ——罗光辉散文印象 当下的文学,已经越来越光怪陆离。尽管市场经济如火如荼,但心仪文学的人仍旧挤满前行的小路。每次到各地采风、座谈、办讲座,听到的问到的最多的就是文学到底是何物。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理解不同,其答案也就不同。 我的回答是:文学是发现美和审美的过程。 是的,文学首先是能不断地发现美。美是无处不在的,它是具体的,物质的,也可以是抽象的,精神的,这些只有通过人的思想情感才能产生。在文学诸多样式中,散文来得最敏感。这就难怪有人喜欢将散文理解成美文。当然,美的东西也不都是喜剧,有的恰恰是悲剧。散文中的悲剧往往蕴涵着大美。譬如冰心的《小桔灯》、朱自清的《背影》。 我还想到刚刚读过的罗光辉的《看陈独秀墓》和《再看陈独秀墓》。陈氏作为中共最早的创始人和一大至五大的最高领导人,其身前身后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关于他的生前,人们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基本上都有所了解,但对于他的死后,几乎很少有人问津。至于他的墓地在哪里,就更无人知晓。一个偶然的机会,作者到安徽安庆出差,无意中得知在不远的大龙山里矗立着陈独秀墓。说是矗立,也是勉强的,因为那墓实在不够规模,“一下车,我就看见一个不壮观,也不复杂,面积又不大的墓地静静地耽于林丛间。缓步走上陈独秀墓前约有百余米的甬道,甬道尽头的墓廓微微高出我的视线,墓上面长满了草,但看墓并不需要怎样去仰视”。对于陈独秀为什么不需要仰视,这肯定源于他所犯的错误,这是有定论的。我们中国的事就是这样,很多的人和事都亘古不变地沿袭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然而,人又是有思想的,对好多事终归有自己的判断。面对杂草丛生的陈独秀墓,作者不由感慨道:“他的人生我觉得比这墓地复杂得多。”特别是接下来的描写:“我绕墓地又转了两圈,好像总想看出哪怕随便一点什么来也好。这时,我发现墓地两侧还有八棵桂花树,树上桂花不见了,自然,香气也早已溢散。香气溢散,但桂树还在,季节还在,墓地还在。在墓的前面我还发现有一些烟花纸屑,还有用松杉扎成的似花圈又不是花圈的东西。我问朋友:‘还有人来墓地扫墓?’他说:‘有。他还有家人,还有乡亲。’我再看了看墓,又望了望蓝天,我知道,这山的下面,睡着一个复杂的魂灵。”读至此,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者都会与作者的感悟产生共鸣。五年后,当作者再次来到陈独秀墓,其看到的景象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站在墓上,我思绪万千,变了,的确不一样了!浮现在青烟绿霭中的,是扩修了的墓园,与原来墓顶裸露,一片黄土朝天,杂草疯长,象征盖棺而未论定的墓地相比,壮观多了,牢固多了。墓是圆顶,起码有我两个身高,直径有六七米以上,通体用汉白玉砌成,四周是石阶、石栏,材料都是上等白石,占地达一千多平方米,石碑也显高大,从甬道上看墓,要微微仰视了,但在碑上刻着的仍是那‘陈独秀之墓’五个大字,仍没有任何文字介绍。‘这只是第一期工程,’陪同我的友人介绍说,‘据说还有二期,三期,规划中,要修成一座很壮观的陵园。’”见此,作者不禁又发了一通感慨: 墓地的变化,是人世荣枯的投影。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个大起大落、毁誉交加的复杂人物,总要等时间老人剔伪存真,删繁就简。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完成他最后的造型。以后的陵园会是什么样?除材料变化面积扩大以外,墓碑上会不会增加他祖父的预言“不成龙,便成蛇”——应该说,作者的第二次感慨是对第一次感慨的升华,思维独特,大胆而不失偏颇。 作为一名军旅作家,因为职业不同,我和罗光辉不是很熟悉。但通过以上两篇散文,我对他猛然间高看了很多。许多读者不会理解,军队不同于老百姓的地方,首先是要讲组织纪律性的,这是职业军人的共性。只有在此前提下,你才能讲你自己的个性。由此,也似乎在证明,我们部队的思想工作越来越朝着人性化不断进行改进。这既是军队的进步,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 当然,罗光辉在散文中能有如此的真知灼见,除了来源于他多年从事政治工作积累的理论素养,还源自于他平日对生活的发现与感悟。我们的生活由每一天构成,每一天又由很多具体的琐碎的俗物组成。一个优秀的作家,一定要当生活的有心人,不断地从俗常的事物中发现亮色。这种亮色,就是形成文学的基本要素。我向来反对作家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也反对作家装腔作势地去考古掉书袋做假学问。我曾说,散文和诗歌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散文既然说我,那么要说什么呢?我以为,要说的是我的发现,我的感悟,这种感悟是一种美,艺术的美,是作家自己的审美。在这一点上,罗光辉显然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我在其创作的《到心仪的地方去升华生活》《泉州的文友们》《那天,泰山顶上无雨》《随纳米儿看动物世界》等大量篇什中,都有精彩的发现。有些感悟如同警语,常能让人掩卷之后深深地思考。 去年,在第三届冰心散文奖颁奖结束后,有好多记者采访我,关于当前散文创作我回答了许多问题。当采访快结束时,一位中学女教师对我说:您刚才讲的都好,我都记录了。但我有一个建议,您能让我提吗?我说,只要对散文创作有益,您只管提。女教师说,当前报刊上的散文越写越长,一点都不节制。我们的学生不爱读,读不懂。您是中国散文学会领导,散文理论家,请您代表我们呼吁一下,为了孩子们,请作家们学会写短文章,写千字文!女教师的提议,如同醍醐灌顶,我听后内心感到很震动。在如今一味强调自我、追求个性的时代,我们的作家们谁考虑过给孩子们写作呢? 我所以写这些,主要想说:罗光辉的散文大都是千字文,很适合在校学生和生活忙碌的人们阅读。我相信,只要你认真读,在读后你一定会有惊喜,那是一种发现后的惊喜! 二○○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红孩谈散文:散文是说我的世界》是红孩的一部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散文评论集。从时间跨度上,梳理了近二十余年散文界的创作现象,结合散文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风格和主流态势,对相关的散文创作者及其作品进行了系统评述。红孩根据其散文创作理念——散文是说我的世界,认为散文是“我”在场的艺术,是以我手写我心的文学创作,要形成自己独有的气质和风格,同时要在合理基础上勇于创新,寻求自我的突破,从而促进散文的发展。这是一部专业性和普及性兼具的散文评论集,适合各个层次的散文写作者研读或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