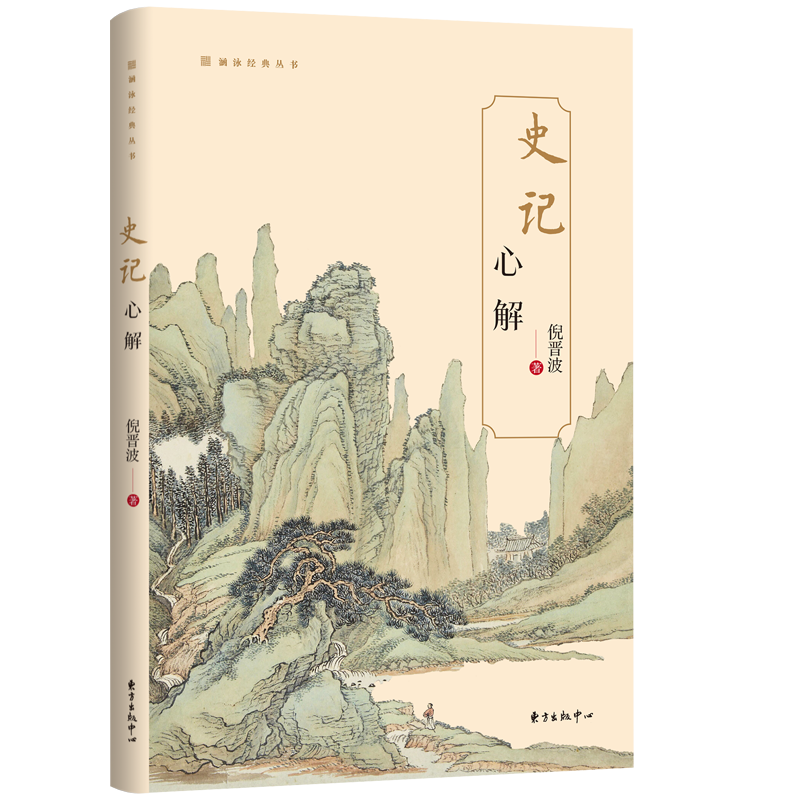
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原售价: 52.00
折扣价: 36.92
折扣购买: 《史记》心解
ISBN: 97875473174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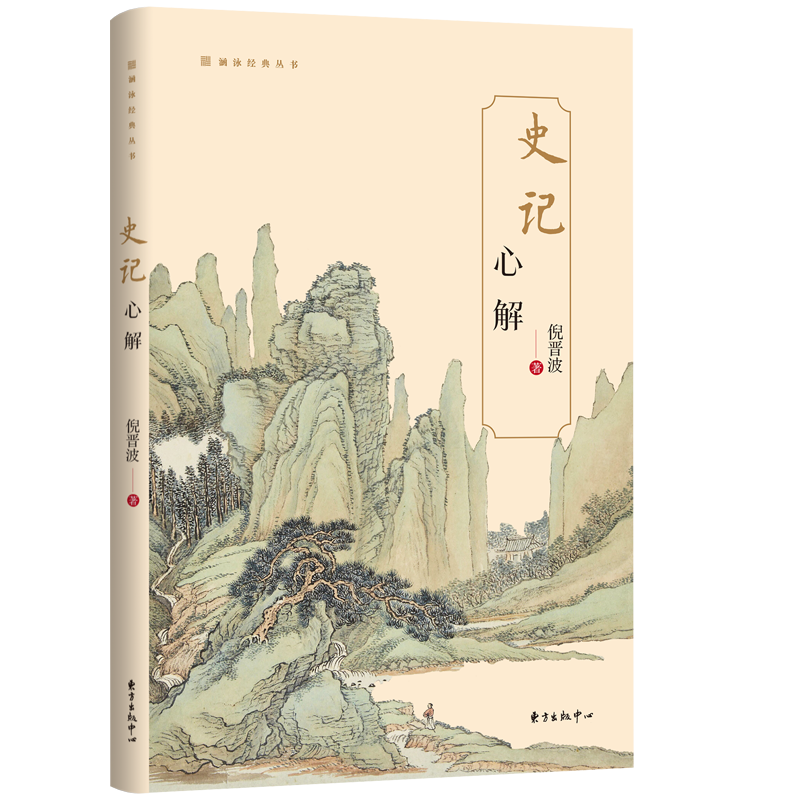
倪晋波,文学博士,中国古典文学教师。从事先秦两汉文学、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文学等领域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文化视野下的东周秦文学》(09CZW019)、《清代郡邑诗话研究》(17BZW059),出版专著《出土文献与秦国文学》(文物出版社,2015)等。
就历史个体、社会类群和中华民族三种心理的内在联系而言,社会类群心理其实是历史个体的共性集合,主要显影于其语言、行为、情绪等外在形态;而民族心理则是历史个体和社会类群的历时抽象,主要造就于类群心相的超时空积淀,这既是一个主体选择、接受的过程,更是一个历史选汰、凝积的过程。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的哲思,提炼特定群体的心理共相,勾画数千年时空迁延中的民族之魂,其逻辑起点是省察历史个体的浮沉悲喜。所以,在读者层面,把握个体人物的心理就可以顺流而观,凭河窥海。 事实上,在漫长的《史记》接受史上,早有读者和学者在其“史例开三代,词华重六经”的史、文价值之外,认知到其心灵书写的价值。这其中,尤以清代康乾年间“菉猗女史”李晚芳所著的《读史管见》最为特别。李晚芳基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在《读书摘微》一文中指责司马迁“立心褊蔽,未闻圣人之大道”“挟一不平之意据于中,虽未必借立言为泄发,而灵台未净,则系累偏僻之私,往往吐露于字里行间而不自检,故其书肆而不纯,谐而多怨”;又批评《报任安书》“怼君者十之六七,忿朝臣朋友者十之二三,全无一言反己内咎。所谓自是而不知其过者,非欤?其褊蔽也甚矣”;更指斥太史公“操是心而修国史,大本已失,故《平准》《封禅》尽属谤书。……如是而欲上继知我罪我之心法,愚未敢轻信也”。不过,上述论断或许并非李晚芳的初心。《读史摘微》写于康熙庚寅桂月上浣,即康熙四十九年(1710)八月上旬,李晚芳时年19周岁;次年嫁于梁永登。《读史管见·自序》早于《读史摘微》写就,时在康熙丁亥阳月朔日,即康熙四十六年(1707)十月初一,且序文显示该书当时已完结,李晚芳时年16周岁。前后三年之间,从二八少女到成年女子,认知趋于保守正统,并非不可理解。通观《读史管见》一书,可见李晚芳对司马迁和《史记》实际上是推崇备至。《三代世表序·总评》:“寥寥短幅不过百三十余字,亦具如此章法。如是结构、立论措辞,不离孔子家法,宜《史记》继麟经,而千古不磨也!”无论如何,《读史管见》是李晚芳出自心性、衡诸心意之作,虽有迂执回护之弊,如不愿承认太史公对刘邦、汉武帝有批评之意,但总体而言,该书长于揣摩《史记》人物及司马迁的内心世界,洞烛幽微,识见特出,致有“展卷而惊、望为河汉”之叹。降及于今,时贤先进对《史记》人物和太史公心理的探赜索微,更是屡见新篇,颇具启迪。如,李长之先生的著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长之先生以捭阖中西的理论视界驱使郁烈流芳的诗性文笔,将司马迁的时代看作“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的时代,太史公是“那一个浪漫世纪的最伟大的雕像”和“浪漫的自然主义的大诗人”,《史记》则是中国“无比的史诗性的纪程碑”。如此情调高扬而激荡人心的歌颂奠定了氏著在《史记》心灵书写抉发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因此,基于《史记》心灵世界的构成逻辑和历史认知等原因,本书不拟以《史记》个体人物心理的玩索为鹄的,而以其为基石,管窥斯书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类群人物心理,并及太史公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