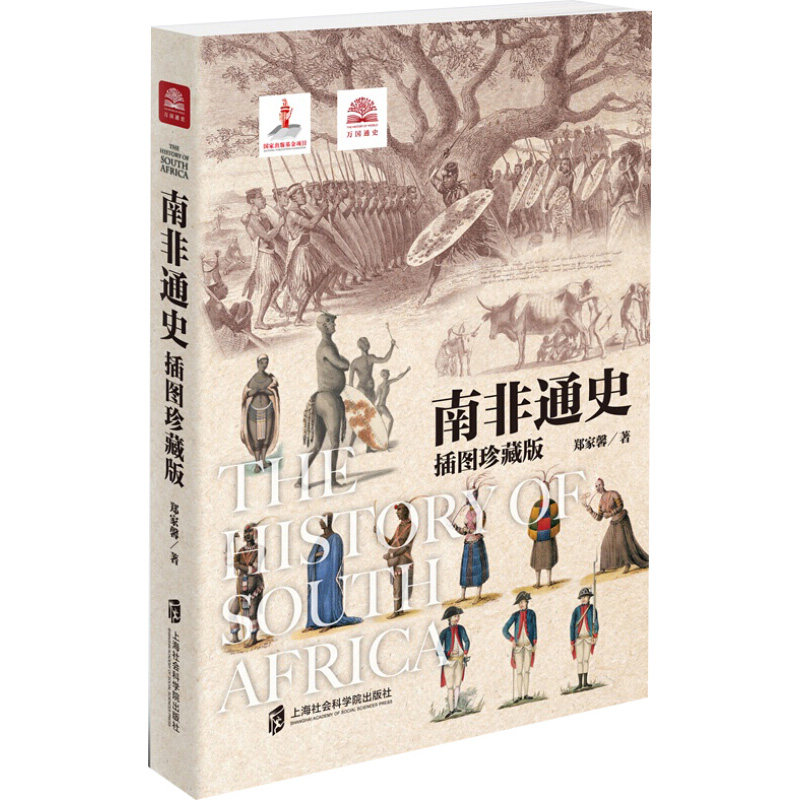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社科院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47.60
折扣购买: 南非通史(插图珍藏版)
ISBN: 97875520165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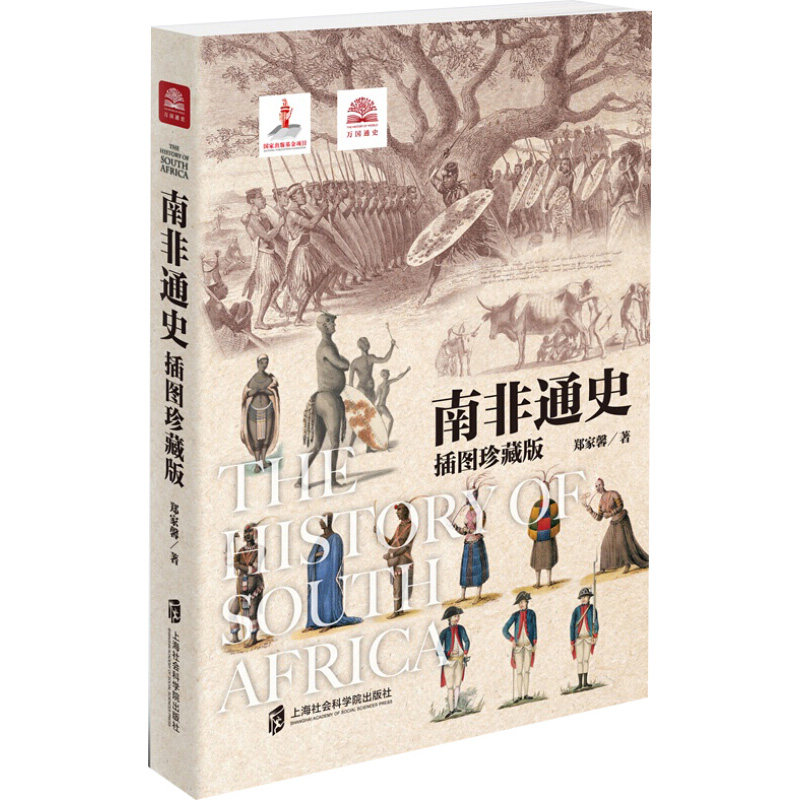
郑家馨(1934—2017),福建省福州市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亚非拉史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多年从事非洲史和殖民主义史的教学和研究,著有《世界历史(亚非拉部分)》、《南非史》,曾主编《非洲通史·近代卷》、《殖民地史·非洲卷》、《世界文明史》等。
第七章 祖鲁王国的崛起 一、 北恩戈尼人诸部落统一的有利条件 得天独厚的祖鲁兰 北恩戈尼人栖居的纳塔尔是南非得天独厚的富庶地区。它地处南非的东高原斜坡地带,其北部地表低平,河谷开阔;南部地区崎岖狭窄,河流动辄形成峡谷,水势湍急。全区雨量丰富,常年温差不大。由于地形复杂多变,在不大范围内就含有甜维尔区、酸维尔区和混交禾草区等多种类型草原。维尔(veld)为“草原”之意,特指既未耕种过又无密林的开阔地。甜维尔(Sweetveld)区生长着全年甚至干旱时期都有营养的禾草如红草,适于饲养牲畜。酸维尔(Sourveld)区的禾草在生长的早期富含营养,但生长3个月以后所含蛋白质和矿物质急剧减少,木质素和纤维素含量升高,牲畜吃了不好消化,因此不爱吃。祖鲁牧人擅长放牧。他们让牲畜先吃酸维尔区的细嫩牧草,3个月后进入甜维尔区,牛羊吃得腰肥体壮,繁殖率很高。祖鲁人的畜牛业特别兴旺发达,祖鲁语中有100多个专有名词,分别表示不同品种、毛色和角形的牛。 除了适牧以外,比起高原斜坡带的其他地区,祖鲁兰又是适宜农耕之地,既温暖多雨,水源条件优越,又无危害人畜的萃萃蝇,是理想的发展农牧经济的地带。居住在祖鲁兰的恩戈尼人主要部落有恩德万德韦、恩瓜内、姆塞思瓦和夸比。这些黑人部落善于利用自然条件,充分发展农牧混合经济。16—17世纪,从东海岸葡萄牙海难者手中引进高产的美洲玉米以后,更增强了祖鲁兰雨量充沛地区的农业潜力,遇上好年成,玉米加上非洲蜀黍可使谷物产量倍增。以祖鲁人为代表的北恩戈尼人人口迅速增加。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北恩戈尼人的炼铁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铁制工具甚多。专业铁匠技术严格由家族传承。他们也善炼铜,喜好用铜制作各种装饰品。另有专事生产草篮、草席的工匠。木雕工艺也得到发展,生产的牛奶盘、木制长柄勺、羹匙、枕头等远销各地。手工业分工初具规模。恩戈尼人可用来交换的产品数量和品种比其邻居科伊桑人多得多。这促进了商品经济迅猛发展,使地区财富急遽增多。 靠近德拉戈阿湾的南班图诸部落,兼得地理之利,长期控制德拉戈阿湾贸易。这里在1794年以前由聪加人控制,其后控制权曾短期转入马普托人之手。居住在主要通道之一的蓬戈拉河西岸的恩瓜内人和恩德万德韦人,也力图控制此类贸易。于是,争夺长途贸易控制权成为刺激南恩戈尼人各部落建立强大军事力量的动力。乌姆福洛济河下游的姆塞思瓦部落的酋长丁吉斯瓦约在1809年前曾多次到德拉戈阿湾一带旅行,眼见贸易繁盛和欧商咄咄逼人的情景,深感加强武力控制贸易通道的重要。他在1809年即位后组织商队运输象牙、牲畜和毛皮向葡萄牙出口,他曾贩运100头公牛和大批象牙,到德拉戈阿湾去换取串珠和毛毯。诸种有利因素使北恩戈尼人酋长能够有效维持其对象牙、毛皮贸易的垄断地位,获得巨利,从而壮大其经济实力。 18世纪末生态环境的变化改变了祖鲁兰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政治实力的变动。德拉戈阿湾的象牙贸易因大象被滥杀而骤减,牲畜出口猛增。贸易上对牲畜需求的增加(葡属莫桑比克港口同样是印度洋帆船的供给站),以及牛群是社会和家庭财富标志的传统,刺激着北恩戈尼人想方设法扩大畜群的规模。 生态环境变化促进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过程。恩瓜内、恩德万德韦和姆塞思瓦诸部落的中心地均位于雨量丰沛、土壤肥沃的分水岭地带,靠近甜维尔和酸维尔地区,全年均可放牧,饲养牛群最多。但是,各部落出现的长期过分放牧的现象,一度破坏祖鲁兰的生态平衡,特别是甜维尔地区受到的破坏最大。这些优良牧场一旦植被覆盖面减少,表土流失,就会滋生牲畜不爱吃的灌木刺林。根据树木年轮研究,18世纪90年代纳塔尔地区的降水跌至历史最低点,引发了1801—1802年的大灾荒。祖鲁兰各部落酋长竞相向所剩无几的牧场储备资源扩张,占领新资源扩张土地的行动引起了激烈的部落战争(迪法肯战争的前奏),战争减少了人口,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和人口膨胀所产生的严重问题。 18世纪末,此地的非洲人开始了部落广泛联合、从部落过渡到民族的过程,有的通过和平途径,有的通过武力征服。游牧经济在南非自然条件下本来很难形成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但在南非南纬30°以北地区,可靠的农业生产和不断扩大的畜群却提供了形成国家的有利条件。 大约在16世纪中叶,北恩戈尼人的恩瓜内黑人部落已居住在蓬戈拉河下游两岸平坦的沼泽地带(今莫桑比克南界内),当时叫伦吉尼人,其创造者称德拉米尼一世。伦吉尼部落成为聪加人的滕布王国的一部分。从北伦吉尼部落分出来的新氏族往南迁徙,渡姆库泽河进入纳塔尔。新氏族恩瓜内后来又分成德拉米尼和恩德万德韦两个氏族。而留在北方的伦吉尼部落属其中的伦加氏族,从中又分出赫卢比和斯威兹两部。大约在1720—1730年,赫卢比继承其父伦加为酋长后,可能因在滕布内战中失地,遂率伦加氏族延林波波河丘陵南迁,定居于蓬戈拉河南岸,成为恩德万德韦的臣属。后来,伦加氏族分别由赫卢比及其兄弟德拉米尼三世率领。德拉米尼三世率领的氏族定居于蓬戈拉河上游南岸(后来的斯威士兰国南界)那片十分适宜农牧混合经济的地带。一直到德拉米尼三世之子恩戈瓦尼三世即位后,他才率众从南岸回渡北岸。无论如何,斯威士人终于定居在蓬戈拉河上游北岸这片适宜农牧混合经济的肥沃地带了。恩戈瓦尼三世(约1750—1770年在位)充分利用有利的自然条件发展生产,奠定了斯威士民族的融合基础,建立了斯威士兰王国。斯威士人自称恩瓜内人,就是从几个自称为(巴卡)恩戈瓦尼家族的名称沿袭而来的。恩瓜内人不断扩张领土范围,逐渐征服或吞并蓬戈拉河上游北岸的几个小酋长国,包括其中的苏陀人酋长国,因此,恩瓜内人文化中也糅进了属于苏陀—茨瓦纳语系的苏陀人文化成分。有意思的是,北恩戈尼人实行严格的族外婚制,而同样属于恩戈尼语系的恩瓜内人却宁愿实行姑表和舅表婚制,斯威士人中 皇太后的崇高地位与其说是恩戈尼人的传统,毋宁说是苏陀人遗风。 两强之对峙—恩德万德韦和姆塞思瓦 定居于蓬戈拉河南岸的恩德万德韦人力量强大,雄踞一方。18世纪90年代,亚卡酋长传位于其子兹威德。兹威德精明强干,他乘德拉戈阿湾附近的滕布王国衰亡及其继承国马普托王国力量不济之机,控制了沿海和高地之间的东西方贸易商道,聚敛财富,征服了当地酋长国库马洛、恩瓜勒尼、布塞勒齐等,威势大振。远至纳塔尔北部和斯威士南部的许多酋长国和王国赫卢比、恩瓜内等,都不得不向他称臣纳贡。 在恩德万德韦人的统治下,一些臣属国如索尚加的加扎国和兹旺曾达巴的恩克万曾尼国仍保持自治地位。 位于乌姆福洛济河下游的姆塞思瓦酋长国,境内多河谷低地,既有适于农耕的丘陵地带,也有滋生大量猎物(尤其是大象)的低地。18世纪中叶以后,德拉戈阿湾的猎象业向乌姆福洛济河低地扩展,姆塞思瓦酋长国控制了低地的各个要道,从而既垄断了猎象活动,又控制了地方贸易。18世纪90年代,丁吉斯瓦约同其酋长父亲乔伯闹翻,愤而出走,游历各地。关于此段游历,恩戈尼民间故事有许多传说。有说他曾到过开普殖民地,回乡时骑马挎枪,引人注目。这些都缺乏可信的证据,但他见多识广,眼光远大却是可信的。1809年他倦游思归时,其父已传位于其弟马韦韦。丁吉斯瓦约夺回酋长宝座后,知人善用,勇于革新,在他统治期间,国力迅速增强。他与马普托王国结盟,进一步控制了北方贸易;并向西扩张,将祖鲁、布塞勒齐等酋长国均置于其控制之下。 19世纪初,在北恩戈尼人部落战争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部落联合和集中的现象。昔日一个酋长国击败另一个酋长国,一般并不吞并后者,而只让其认输,而后撤兵。如今,恩德万德韦人和姆塞思瓦人一改前例,不断通过战争征服和吞并别国,扩大疆土,为统一造势。 同龄兵团制度的出现 为适应这种拓疆扩土统一军队的需求,他们率先建立起一种同龄兵团的军事制度,打破部落界限,按年龄等级将各部落男青年混编在兵团中。这种同龄兵团制度几乎同时出现在班图黑人几个不同民族(恩戈尼人、苏陀人、茨瓦纳人)中,这一现象说明它是适应内外环境压力的产物。 南班图黑人早就盛行割礼入会的习俗。这种颇具神秘色彩的习俗演进为部落的政治生活赖以存在的基础,其实质是建立一种身份依附制度。酋长们为了便于控制各自部落的同一年龄段的青年,每当酋长的一个儿子施行割礼时,部落中同年龄的青年便一起去施行割礼。这些青年便自然成为酋长之子未来扈从的核心和最亲近的伙伴,一生效忠于他们的首领。实行多妻制的酋长一般子嗣众多,部落的青年便按年龄段参加割礼,分属于酋长诸子,自然形成若干个年龄集团。 到19世纪初,随着部落的广泛联合,沿袭已久的割礼制度同部落联合、集中趋势及其带来的频繁的战争生活发生了严重冲突。割礼仪式繁复冗长,年轻小伙子集中关闭一地,在四五个月内受到严酷的肉体折磨,筋疲力尽。敌对部落常乘对方在割礼期间无力自卫而发动突袭。此外这种入会仪式使部落的同龄青年只忠于年轻的酋长继承人,十分不利于部落的合并和统一国家的形成。改革这种过时的、弊端丛生的旧制度已势在必行。 北恩戈尼人的同龄兵团制度废除了传统的割礼和入会仪式,而以加入同龄兵团、服役、参加战斗作为少年步入社会的标志。按祖鲁人的程序,允许他们戴头圈(一种成年的光荣标志)。同龄兵团不再以部落划界线,而以同一年龄段作为标准。被征服部落的同龄青年也以平等地位编入各年龄段兵团。兵团成员只对国王或最高酋长效忠,而与原属部落酋长脱离隶属关系。各同龄兵团的给养完全仰靠王室领地的收成或战利品。例如,由属于国王或最高首领所有的牛群供给其肉食和奶制品;谷物供应则靠各领地大批妇女的农耕所获或靠国王向各个家族征募的剩余劳动力所生产的粮食。国王或首领依靠垄断贸易或征战来聚敛财富和扩大畜群。战士的给养与军事行动的成败息息相关。这种新军事制度有利于促使来自各部落的战士形成共同的民族感情和对首领(国王)效忠的信念。北恩戈尼人的四大酋长国恩德万德韦、恩瓜内、姆塞思瓦和后来居上的祖鲁小酋长国都将该制度作为联合部落以逐步形成国家的重要手段。 二、 四大酋长国争战中祖鲁王国国势后来居上 斯威士兰王国脱颖而出 争夺土地和控制商道的斗争频频发生。恩瓜内人与恩德万德韦人为争夺蓬戈拉河南岸的盛产玉米地带而爆发战争。兹威德率恩德万德韦军队侵入恩瓜内领土,打败索布扎的军队,几乎消灭了恩瓜内酋长国。1815年刚即位的索布扎率残众退往北方。此后,兹威德接二连三的攻击迫使索布扎躲进群山岩洞中避难,最后不得不退让至后来的斯威士兰中心地带—因科马蒂河沿岸,并在此建国。索布扎初败不馁,勤于学习,知人善用,善于吸收各方长处,他既仿效丁吉斯瓦约同龄兵团制度,也采用归附于他的苏陀人的一些政治制度,如国王与太后的两宫分权制、个人扈从制等,建立起一套较为灵活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制度。中央在加强集权的同时,允许各地臣民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参加国民会议)。索布扎组织的同龄兵团征服了当地讲恩戈尼语和讲苏陀语的小酋长国马塞科、佩迪等,奠定了斯威士兰王国疆土。 在强邻窥伺下,为巩固新王国的政权,索布扎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1817年他娶兹威德之女为正妻,避免与强邻恩德万德韦再次发生冲突。后来他同更强大的祖鲁王国交往时,也同样谨小慎微,避免冲突。依靠外交途径,避免同潜在的强大敌国发生冲突,成为斯威士兰王国的立国之道。此后历代君主也将此道奉为圭臬。但对弱邻,它毫不犹豫地发动进攻。到1820年左右,斯威士兰进入和平建国时期,索布扎迁都于乌苏河谷地的诺克万,仿照祖鲁人的军事原则进一步加强同龄兵团。其四邻成为它的进贡国,包括位于高维尔地区的佩迪国、低维尔地区的聪加酋长国和中维尔地区的恩戈尼人诸酋长国。①索布扎在位21年(1815—1836),把斯威士兰建成一个巩固的较强大的王国。 祖鲁小酋长国在纷争中获得机会 在祖鲁兰南方,姆塞思瓦酋长国的土王丁吉斯瓦约首先要对付的是强大的夸比酋长国。夸比人统治着姆赫拉图泽河之间的地盘,在库兹瓦约统治时期国势日强,控制了整个恩戈耶地区,迫使其主要对手塞列人和图利人移居图盖拉河以南,其威势远及恩戈耶以西地区,祖鲁小酋长国也在其卵翼之下。1815年夸比大酋长憎恶崛起于乌姆福洛济河间的姆塞思瓦国日益侵入其权力范围,遂故意庇护刚被丁吉斯瓦约赶下台的 其弟马韦韦。丁吉斯瓦约借用马普托王国的火枪兵,击败并吞并夸比酋长国,统一了乌姆福洛济河流域,祖鲁人从此成为它名副其实的附属国。因此,姆塞思瓦一跃成为南方最强大的国家。 恩德万德韦人自从把恩瓜内人赶到因科马蒂河以北,称雄蓬戈拉河以南地区后,逐渐往南向乌姆福洛济河甜维尔地区扩展,与姆塞思瓦人发生冲突。由于姆塞思瓦人有马普托王国火枪兵的支持,兹威德始终未能切断姆塞思瓦与马普托之间沿海平原的商道。1817年北恩戈尼人的两雄发生全面冲突,双方都动员了主力。初期丁吉斯瓦约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直逼兹威德首府。1818年冬,双方在首府附近的姆齐山丘进行决战,均布下了著名的公牛角阵。①会战前夕,丁吉斯瓦约带一小批随从爬上一座小山俯瞰战场,观察地形。不幸陷入计 谋多端的兹威德设下的埋伏,被擒处死。姆塞思瓦军队临阵痛失主帅,陷入混乱。兹威德不战而胜,把姆塞思瓦人赶过乌姆福洛济河,几乎逼近图盖拉河。 恰卡的才干和历史机遇 历史给姆塞思瓦军队中一位普通指挥官恰卡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恰卡出身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氏族—祖鲁。其父森赞康纳是位只管辖2 000人的小酋长。童年时期,恰卡因父母的婚变而寄居于母方氏族兰吉尼。寄人篱下的牧童生活和坎坷的境遇使他炼就了坚强勇猛的性格。他身材魁梧(身高1.9米以上),胆略过人。1803年,成年后的他离开本部落投奔姆塞思瓦酋长国,1809年应召入伍。他勇敢善战,卓具指挥才能,屡建战功,深得丁吉斯瓦约的赏识,获得“勇士”称号,升任指挥官。1816年恰卡父亲森赞康纳亡故,其庶子西古贾纳继位为酋长,恰卡借得丁吉斯瓦约的一支军队杀回部落,从其异母兄弟手中夺回酋长宝座。恰卡以本氏族青年为主,建立一支剽悍善战的军队。毗邻部 落慑于其武力纷纷归附。一年之内,恰卡统辖的地盘从100平方英里扩大到400平方英里,军队由500人增至2 000人,并兼并了6个部落。丁吉斯瓦约将恰卡所统辖的祖鲁军队提升为姆塞思瓦禁卫军。1818年年初丁吉斯瓦约被俘遭戮后,姆塞思瓦国群龙无首,失地大半,濒于瓦解。恰卡斩杀新酋长,取而代之,任命亲信为姆塞思瓦各级指挥官,重建权力中枢。 兹威德乘恰卡立足未稳,兴兵讨伐。1818年4月兹威德率1万大军侵入乌姆福洛济河南岸。恰卡指挥祖鲁5 000名精兵,在格夸科列山丘击败恩德万德韦军队,但自己的军队也是伤亡严重。这一战役使恰卡声威大振,成为姆塞思瓦公认的国王。他乘胜出兵攻打夸比,吞并这个祖鲁人的前宗主国。由此,祖鲁王国疆域往北扩至乌姆福洛济河,西抵恩康得拉森林,面积达7 000平方英里,共辖30个部落。1818年年末,兹威德派全部人马约1.8万人再犯祖鲁。面对优势敌军,恰卡率军先行撤退,烧毁沿途粮草,实行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断以小股部队夜袭侵扰敌军。当恩德万德韦军队孤军深入到图盖拉河时,因粮草不济发生饥荒,被迫仓促退兵,抢渡姆拉图彻河。以逸待劳的恰卡抓住战机,率精兵半渡而击,疲惫不堪的敌军溃散四逃。恰卡乘胜追击,摧毁了恩德万德韦的后方基地。兹威德仅以身免,率众远逃北方。 战胜北方残敌之后,恰卡又向富饶的图盖拉谷地和东海之滨扩展,征服了姆博、恩科洛西、列塞、图利等酋长国。祖鲁王国的版图扩大到1.15万平方英里(近3万平方公里),北至蓬戈拉河,南至图盖拉河,西抵德拉肯斯山,兵员总数跃增至5万人,是当时南部非洲空前强大的军队。恰卡部队连年出征,击败一个又一个酋长国和王国,100多个部落被并入祖鲁王国。在这片原来星罗棋布分散着北恩戈尼人众多酋长国的地带,崛起了一个统一的王国,辖区内的数十万居民都被(欧洲人)称为祖鲁人。恰卡应运而起的军事行动促进了南非 北半部一个新民族的形成。 图文并茂,非洲史大家郑家馨教授十年磨一剑,为您揭示金砖国家南非波澜壮阔的前世今生! 本书不仅文笔生动、史料可靠,并且配有近两百幅精美的历史图片,很多图片都是第一次出现在图书中。打破了以往读者对南非刻板的印象,呈现出一幅多彩多姿、生机勃勃的南非图景,为读者展现了一个非洲大国别开生面的进化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