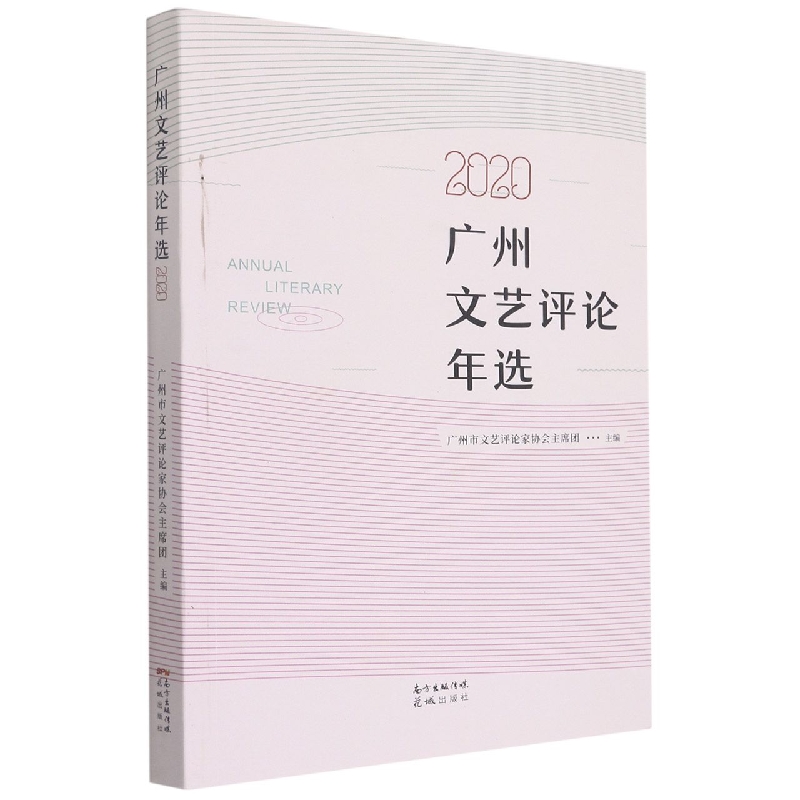
出版社: 花城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7.20
折扣购买: 广州文艺评论年选(2020)
ISBN: 97875360953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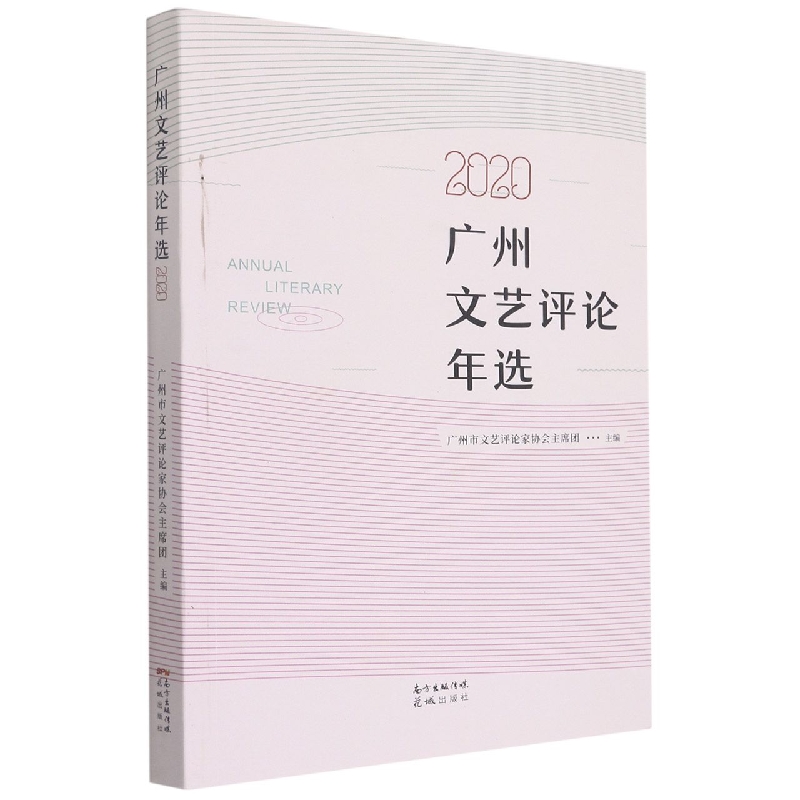
论中国文艺批评标准的正偏结构 林岗 如果将中国固有的批评传统视为一个整体,可以看到 ,在这个整体里用以衡量、批评作品的标准显然存在一个正 偏结构。从古至今,批评的关注点都聚焦于分辨、考究何者 为正、何者是偏,哪些是值得弘扬的主流趣味,哪些是可以 给予存身之地的旁流趣味。文艺批评即立足于正与偏的分梳 、辨别和判定。在这个批评传统里,正和偏之间通常不是对 立的,而更多是不同、差异、主次的关系。每一个时代,被 批评确立为主流“正者”的文艺作品都处于正面价值的位置 ,并因此得到弘扬,而次要的“偏者”当然就处在主流之外 的偏旁。对于具体作品,批评者或有争议和龃龉,但要之批 评作为整体,其孜孜不倦的努力、耿耿在怀的辨正识偏却是 贯穿性的,超越具体的时代场景而成为恒久的传统。经过一 番分辨、考究确定下来的正者和偏者各自占据的位次不可更 改。或许有的批评家过于执着个别趣味,将本来处于偏次位 置的作品悄悄提升到正者的位置,但事后这种扶正的“偷袭 ”总被证明无效。正与偏不可相互代替,其位序不可淆乱, 这个中国固有的批评传统值得我们一番解会。 一 最早体现这个批评传统的词是“雅”与“俗”。今天 ,我们有时过于执着雅俗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分意味 ,以文体和体裁定雅俗这个后起之义又另当别论。雅俗的本 然意味是:雅者,正也;俗者,偏也。因为是正,故位居上 等,衍为阳春白雪;因为是偏,故位居下流,衍为下里巴人 。批评标准所论的“雅俗”包含了严肃的伦理意味,不是纯 粹的文学艺术形式之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一 个故事,是古代文献确凿记载的第一个关于诗和音乐批评的 故事。吴国公子季札往聘鲁国,顺便观周乐以及诸侯国乐。 鲁国当然尽力接待,“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季 札观后评论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观过周乐,鲁国又为季札演郑乐。“为之歌郑,曰:‘ 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季札的批评 标准很清楚,他并未完全否定郑乐的艺术成就,无论对周乐 还是郑乐,第一个评价都叹道“美哉”。但他认为“二南” 是王化的始基,虽未尽善尽美,却灌注着勤而不怨的精神。 而细究下去,季札对郑乐“美哉”的评价,更多是对鲁国乐 工精湛演出的褒扬,对其诗句则微词颇多。什么是“其细已 甚”?为什么“细”就导致“民弗堪也”?季札的逻辑是什 么?杨伯峻的注释给我们提供了理解的线索。他说:“此论 诗辞,所言多男女间琐碎之事,有关政治极少。……风化如 此,政情可见,故民不能忍受。”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第三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61—1162页。以今天的 眼光看,“男女间琐碎之事”同样可以谱写成不朽的文学, 这几乎是常识。但是季札对之并不认可,中国固有的批评传 统对之也不认可。这不认可又不是蛮说,而是自有它的一番 道理。 “二南”雅正而郑风低俗,这个定评意味着“二南” 的音乐文辞典雅而入于主流,郑风的文辞低俗而流于闾里曲 巷。因为前者可以顺理成章地归入由文王、武王开创的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