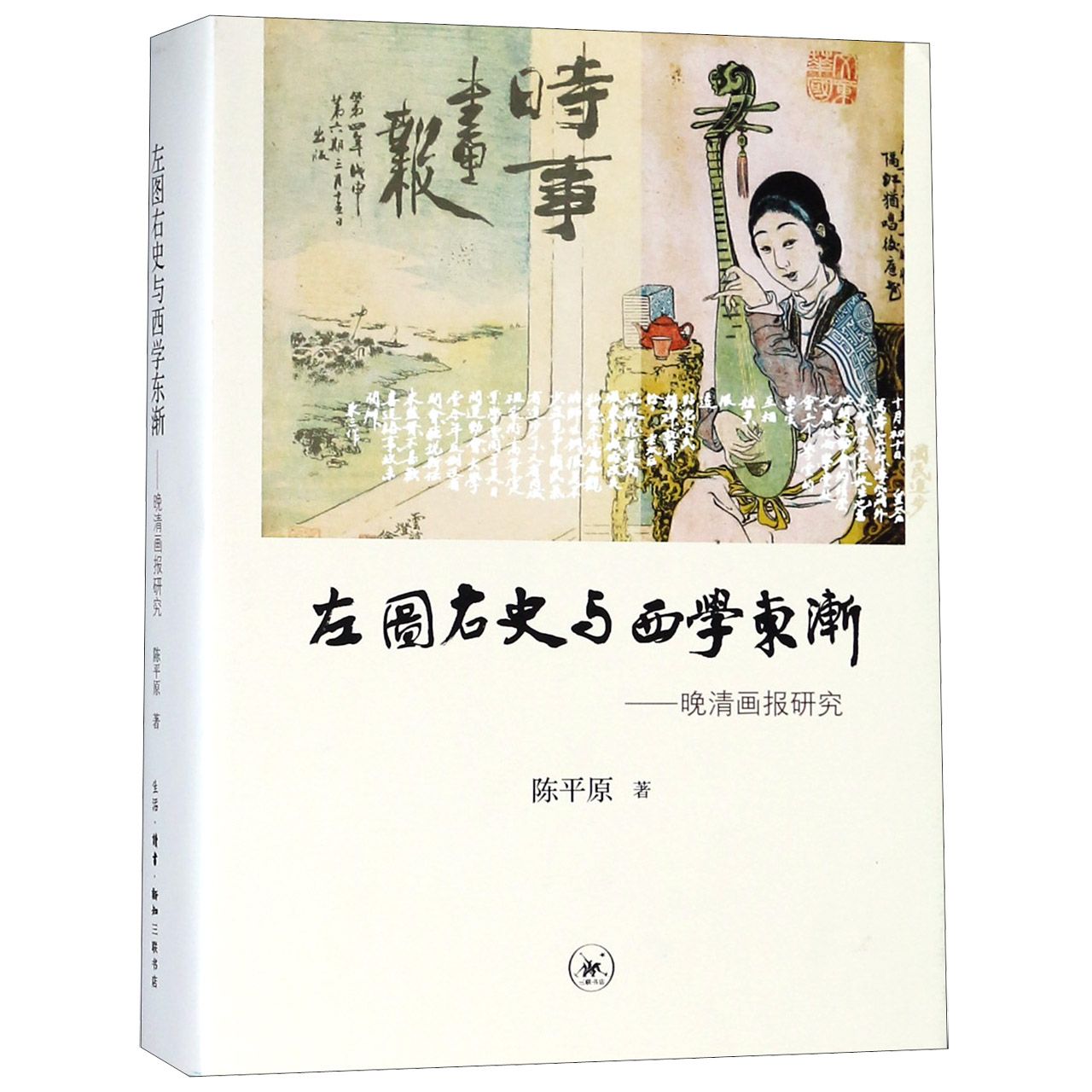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62.48
折扣购买: 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精)
ISBN: 97871080618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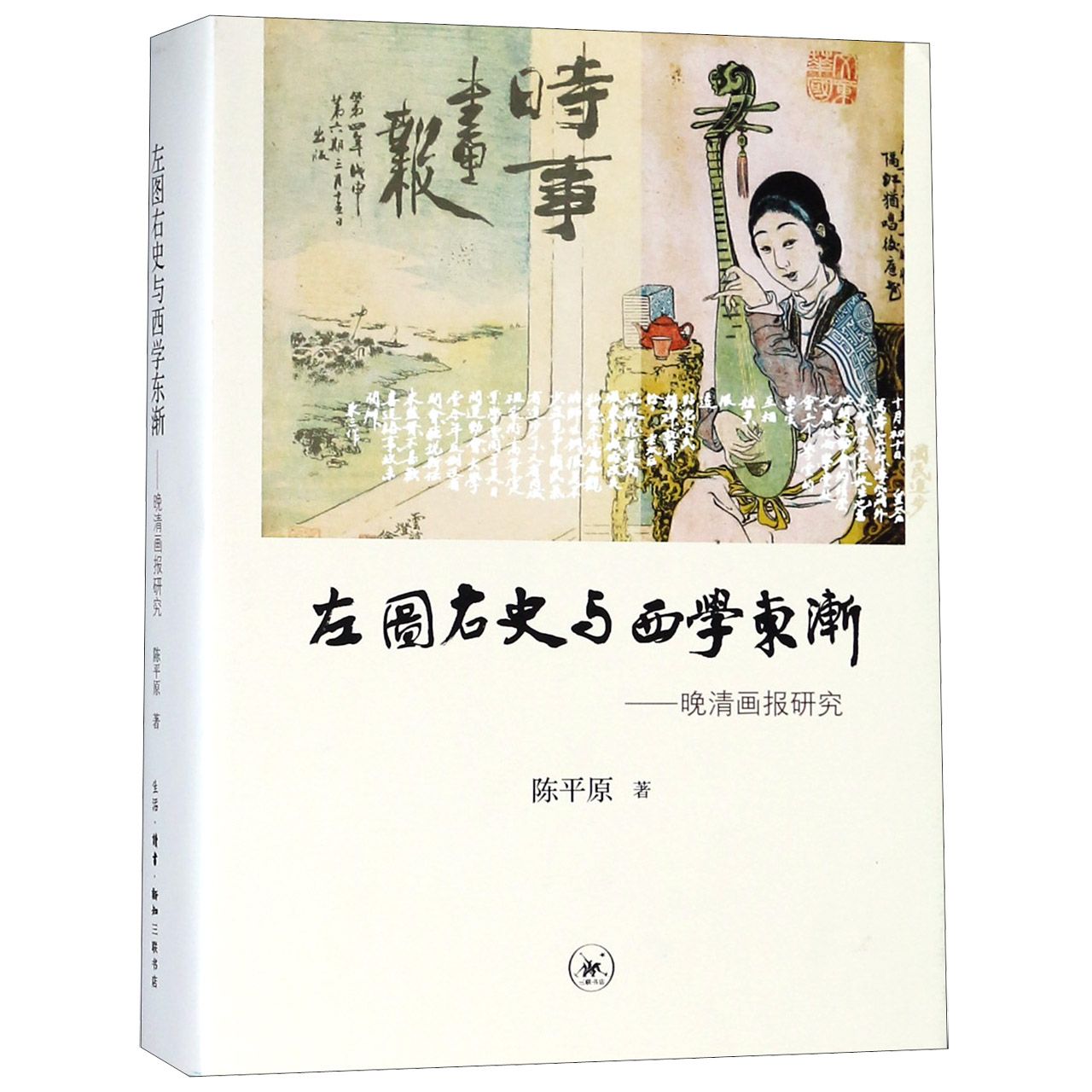
陈平原,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系主任)、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
迥异于晚清其他画报,《时事画报》等基本上不考虑商业利益,也非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而是旗帜鲜明地鼓吹革命。这里所说的“革命”,不是梁启超式温文尔雅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而是孙中山那样以推翻清廷、创建民国为目标的暴力政治。上述六位画报人,都是热血青年[辛亥年黄花岗起义时,这六位画报人,最大的34岁(何剑士),最小的22岁(高奇峰)。],但介入实际政治的程度不同。陈垣虽在1913年初“以革命报人身份正式当选众议院议员”,但在晚清,基本上是以笔为枪,“读书不忘爱国”[参见刘乃和《陈垣年谱》10—2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张荣芳、曾庆瑛《陈垣》23—29页,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年。]。这与陈树人“我本艺林人,自幼成画痴”、“革命思潮起,波澜要助推。我遂走香江,笔政初主持。大义著攘胡,文字力鼓吹”的自述比较接近[ 陈树人:《寄怀高剑父一百韵》,《战尘集》41—4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陈树人《寒绿吟草》(上海:和平社,1929)卷首刊陈大年撰《作者小传》,文中有曰:“以清政不纲,决心鼓吹革命,绘事之外,历主香港《广东日报》、《有所谓报》、《时事画报》笔政。时中山先生方从欧美赴日本,道经香港,格例不克登岸,树人偕陈少白、黄世仲等秘密登船谒之。中山先生告以拟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树人即欣然就船上加盟,时乙巳岁,同盟会尚未正式成立也。”]。高剑父更为积极主动,1906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组织“支那暗杀团”[参见大华烈士(简又文)《革命画师高剑父》,《人间世》32期,1935年7月20日;郑彼岸、何博《暗杀团在广东光复前夕的活动》,《广东辛亥革命史料》81—8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黄花岗之役,“举义时,高氏任支队长,但因为事先同志以拈生死阄分配任务,高氏拿到‘生阄’,所以担任外围接济及运输军械的工作,没有直接参加攻击”[ 参见陈芗普《高剑父的绘画艺术》32页,台北:台北市立美术馆,1991年。]。大凡谈及高剑父历史功绩,都会刻意强调其早期的革命生涯[ 参见陈芗普《高剑父的绘画艺术》27—33页;蔡星仪《高剑父》23—3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王丹《岭南画派大师——高剑父》26—4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我更倾向于认为,高剑父早年的政治热情,与其日后努力倡导“新国画运动”时之不屈不挠,二者之间确有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兄弟追随总理作政治革命以后,就感觉到我国国画,实有革命之必要。这三十年来,吹起号角,大声疾呼,要艺术革命,欲创一种中华民国的现代绘画。几十年来受尽同道之种种攻击,要打倒我,消灭我,要使我这派不能成功。做革命工作时受尽这痛苦;而艺术革命也竟有这劫运,在我国欲改革一件事,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见高剑父《我的现代国画观》29页,台南:德华出版社,1975年。]。至于本人追忆以及后世论述中出现的不少夸饰之辞,则难以取信[“近代中国丛书·先烈先贤传记丛刊”之《革命二画家——高剑父、潘达微合传》(臧冠华著,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采用小说笔法,多有夸饰之辞,不足为信。至于高剑父口述、学生笔记的《七十自述》(初刊1948年《真善美》,收入李伟铭辑录整理《高剑父诗文初编》344—346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过分夸大自家在辛亥革命中作用,编造了不少“辞官”的故事(参见黄大德《辛亥革命中的高剑父》,《南方都市报》2012年10月24日)。]。真正在“辛亥革命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是潘达微,尤其是其冒险为烈士收尸,并将其合葬于黄花岗[ 参见潘达微《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殡葬之情形》及黄大德《潘达微与黄花岗》第一章“舍身护忠骨,缔造黄花岗”,分别载政协广州市天河区委员会《天河文史》编委会编印《天河文史》第九期(2001年12月)《潘达微与黄花岗——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暨潘达微诞辰一百二十周年》132—135页、5—15页。],得到了革命派以及后世史家的一致褒扬[参见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87—88页,周光培主编《辛亥革命文献丛刊》第一册287页,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曹亚伯《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173—2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陆丹林、刘锡璋:《潘达微殓葬七十二烈士的经过》,《广东辛亥革命史料》60—6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纂《辛亥革命在广东》78页、127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时事画报》等创办于舆论环境相对宽松的广州(及香港)[同样创办于广州的《赏奇画报》则力求平稳,如季毓《赏奇画报缘起·释例》称:“本报审慎立言,凡干涉闺阃政界,不轻阑入。”季文载《赏奇画报》丙午年(1906)第一期。],主要编辑及作者又是如此年轻气盛、热血沸腾,难怪其政治色彩特别浓烈。单看高剑父所拟《本报约章》,似乎并无特别之处[ “本报仿东西洋各画报规则、办法,考物及纪事,俱用图画,一以开通群智、振发精神为宗旨。”高卓廷:《本报约章》,《时事画报》创刊号,1905年9月。];第一期围绕“反美拒约”做文章(《女界光明》、《华人受虐原因图说》、《蒋女士生祭曾少卿》等),也算比较稳健。可随着革命党人在各地举行起义,画报从一般的“觉世”与“讽世”,走向了直接鼓吹“革命”。以1907年为例,从《论近日政府对于拿获革党之政见》,到《黄冈乱事》【图7】,到《轰杀恩抚》,再到《祭国士文》[《论近日政府对于拿获革党之政见》,《时事画报》丁未年第六期,1907年4月;《黄冈乱事》,《时事画报》丁未年十一期,1907年6月;《轰杀恩抚》,《时事画报》丁未年十五期,1907年7月;《祭国士文》,《时事画报》丁未年十七期,1907年8月。],全都是站在清政府的对立面,或表彰“乱党”,或直接与朝廷唱反调。而年底刊出的《革命博物院》【图8】,介绍俄政府拟设专门收藏提倡革命之文书、檄文、相片、书籍等的“革命博物院”,然后大加发挥:“二十世纪,一革命之时代也。革命风潮,淹及全世界。革命之人之事既多,则革命之物亦伙。吾意天下之物,无博于此者。俄政府拟设此革命博物院,当视他博物院,广大千百倍,不然不足以示其博也。”[ 《革命博物院》,《时事画报》丁未年三十期,1907年12月。] 积极鼓吹“革命”的《时事画报》,对于“暗杀”情有独钟。从1906年初的“日日都话有暗杀,究竟为乜原因”的粤讴《暗杀》(亚钟),到1907年表彰俄国虚无党人的《女革命党》,再到1909年讲述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暗杀》[ 《暗杀》(亚钟),《时事画报》丙午年第四期,1906年3月;《女革命党》,《时事画报》丁未年十三期,1907年6月;《暗杀》,《时事画报》乙酉年十六期,1909年10月。],只要有暗杀事件发生,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时事画报》必定积极追踪报道。关注突发事件,这本是画报“新闻性”的体现;问题在于,除了讲述事情的经过,此画报往往低两格,发一番惊世骇俗的宏论——如此模仿“太史公曰”,足见其政治激情与书生本色。 讲完俄国虚无党人如何以木匠身份入宫,放置炸弹,谋炸俄皇,最后功亏一篑,接下来便是: 辑者曰:俄国之虚无党,诚足令人谭之而色变哉。我国暗杀之士,莫盛于战国秦初之间,史迁编《游侠传》,有慨于此等人物,良有深意也。俄之虚无党,诚非吾国人所可及。我国往者之游侠,类多以刃、以锥,而俄虚无党则炸药也。……然有此锥,有此炸,而专制酷烈之君主,少知所惕,则力士与木匠,亦足多矣哉。[ 《狠辣之党人》,《时事画报》丁未年第七期,1907年5月。] 至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无疑是当年最为激动人心的“特大新闻”。同样是讲完事情经过,再来一番热情洋溢的评议: 二十世纪世界,炸弹世界也。革命风潮,无国不有。我国为外潮所激荡,革党日盛一日,屡以起事,随即扑灭。殆所谓本国兵势,御外侮则不足,防内患则有余者乎。革党近乃一变其方针,为个人轰杀主义。虽大事难成,亦聊以快一时之意气欤!往日革党多空言家,今则竟有实行者。一般政界中人,安得不怵然惊也。[ 《轰杀恩抚》,《时事画报》丁未年十五期,1907年7月。] 这则《轰杀恩抚》【图9】,结束处嵌有“暗杀主义”印章。晚清志士之所以热衷暗杀,既受俄国虚无党人的刺激与启示,也是出于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考量,还有就是参与者多为热血青年,崇尚牺牲,希望借此“伸民气”,“铸国魂”[ 参见陈平原《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第四节“暗杀风潮之鼓吹”,《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224—2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辛亥革命成功后,《广州时事画报》刊出潘达微等《广州平民日报添招股份简章》,其中有一《平民报之历史》,称:“本报发刊于庚戌九月,为内地第一革命机关日报,以提倡大举暗杀为目的,发挥人道大同为宗旨。”[ 《平民报之历史》,《广州时事画报》壬子年第三期,1912年10月。]其实,不仅《平民报》如此,《时事画报》及其后续的《平民画报》,也都是见缝插针,明里暗里表彰实行暗杀的革命党人。 画报从属于新闻,不能故意抹杀或歪曲事实;可即便不直接发表评论,单是角度的选择以及版面的编排,也都能表达自家立场。如革命党人熊成基1908年冬发动安徽新军起义,事败逃匿,《时事画报》的报道表面上不偏不倚,讲述安徽、江苏两省如何连手缉捕“安庆叛首熊成基”,最后甚至还有一句“熊果获,亦两省政界之福也”——因徐锡麟案弄得各省官吏人心惶惶。可此图用特写的方式,刊出熊的小照,不也是一种无言的表彰【图10】[ 《党人踪迹》,《时事画报》乙酉年第一期,1909年2月。其实,熊成基此次并没被铺,而是逃往东京。1910年熊回国,在东北进行革命活动,谋炸清廷考察海军大臣载洵及萨镇冰,事败被捕,于2月27日就义。其狱中自书供词广为传颂:“我今日早死一日,我们自由之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这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时事画报》刊出报道《轰杀恩抚》、时论《妄哉徐锡麟,愚哉徐锡麟》、资料《徐锡麟之亲供》、图像《徐锡麟之真像》一样[ 《轰杀恩抚》及《妄哉徐锡麟,愚哉徐锡麟》,刊《时事画报》丁未年十五期,1907年7月;《徐锡麟之亲供》及《徐锡麟之真像》,刊《时事画报》丁未年十六期,1907年7月。],都是一种明贬暗褒。 对于潘达微等人来说,直接介入的“革命活动”,是广州辛亥“三·二九”起义。“黄花岗”于是成了寄托理想与情怀的重要标识。潘达微以《平民报》记者身份四处奔走,说服善堂出面为起义烈士收尸一事,当初报章上已有提及[ “有河南潘达微往江绅处陈请,愿帮同各善董料理检埋各事。当由江绅电商善堂,许其同往。各骸发胀,有棺小不能容者,均另易棺,统葬于大东门外之黄花冈。”见程存浩整理《广东最新绘图近事——革党潮》111页,香港出版社,2011年。];“辛亥五月出版”的《广东最新绘图近事——革党潮》,更是围绕埋葬烈士的黄花岗大做文章[ 《广东最新绘图近事——革党潮》中提及黄花岗的诗文有:棱的谐文《黄花冈赋》(222—224页)、帝民的谐文《黄花塚记》(224—225页)、缉公的板眼《黄花冈祭革党》(251—254页)、宋四郎的龙舟《黄花塚党魂游十殿》(263—273页)、宋四郎的粤讴《黄花塚》(274—275页)。]。同年闰六月十一日《平民画报》第三册上有一页彩画,下乃叙事性质之《焚攻督署》,上为潘达微(铁苍)所绘黄花岗:“七十二坟秋草遍,更无人表汉将军。此陈元孝先生句也,移题黄花岗,觉有韵味,读者以为何如?铁苍并志。”[ 铁苍所绘黄花岗图,载《平民画报》第三册,辛亥年闰六月十一日,1911年8月5日。]辛亥革命成功后,七十二烈士受到了新政府的大力表彰,黄花岗更是名扬天下。高奇峰所编《真相画报》第一期上,与之相关的图片及文章就有:《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广州黄花岗三烈士墓》、《七十二烈士纪功碑》、《民军追悼赵声》、《孙中山先生致祭黄花岗》(其一、其二)、《民军致祭黄花岗》、《广东海军将校及海军学生致祭黄花岗》、《广东海军全体致祭黄花岗》等[ 参见《真相画报》第一期,1912年6月。]。如此说来,提倡革命、参与革命而且见证革命之成功,是《时事画报》诸君作为画家兼新闻人的最大特色。 “左图右史”是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西学东渐”是近代中国的特定产物。当晚清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这两个元素也在画报这一“文化”载体中产生了碰撞,迸发出极富意味的文化张力。陈平原二十多年来东奔西走,努力搜寻资料,写成此书,堪称是晚清画报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通过这本书,将带你看懂图像,了解晚清,认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