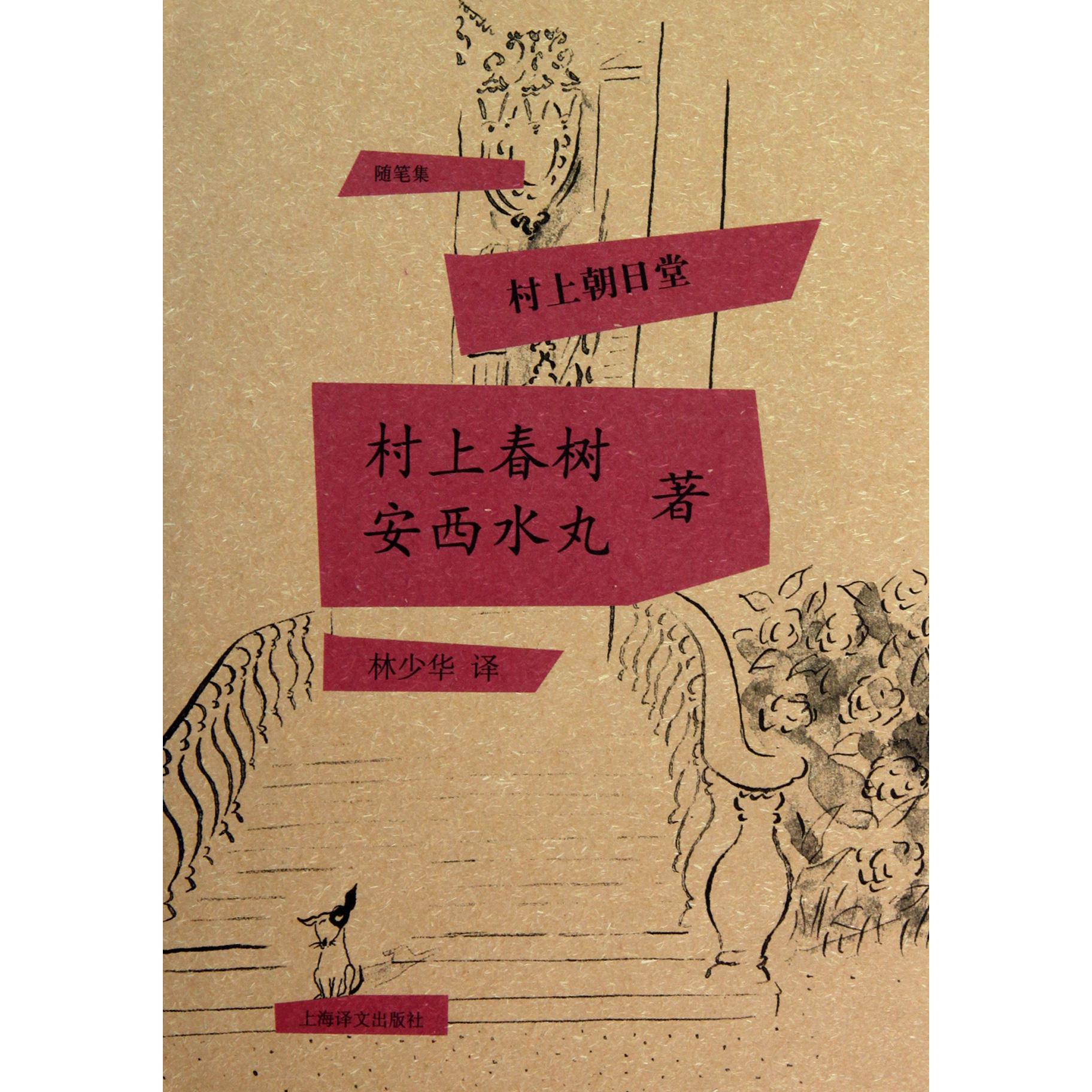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译文
原售价: 25.00
折扣价: 16.30
折扣购买: 村上朝日堂(精)
ISBN: 9787532752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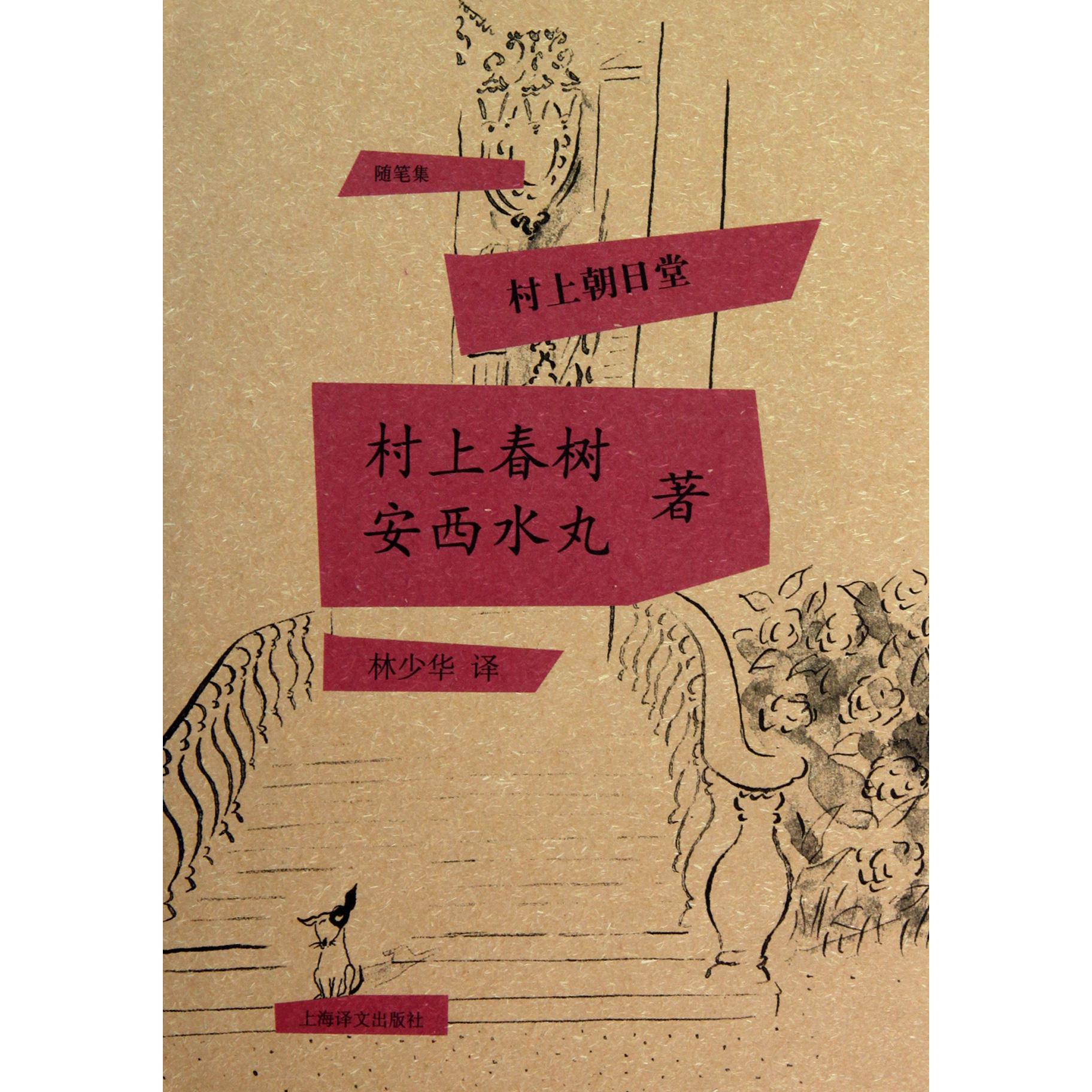
打工 学生时代——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打工的每小时平 均工钱差不多等于在酒吧喝一杯咖啡的平均价钱。具体说 来,六十年代末期为一百五十日元左右。记得一盒“hi-lite” 烟八十日元,一本少年画报一百日元。 我打工挣的钱都用来买唱片了。干一天可以买一张密纹 唱片。 如今咖啡三百日元而打工每小时五百日元,行情变了一 些,干一天能买两张唱片。 只看数字,似乎这十年来我们的生活好过了。但从生活 感觉来说,我不认为好过多少。过去家庭主妇很少做钟点 工,更没有高利贷催命。 数字这东西极为复杂。所以总理府统计局那地方不大可 信,GNP绝对莫名其妙。 如果把GNP那东西“通”一声放在新宿西口广场,想 摸谁都可以摸两下,那么我也可能相信。若不然,我才不相 信那没有实体的玩意儿。 在这方面,我认为竹村健一和田中角荣实在很伟大。 因为他们明知数字形迹可疑,却又信手拈来为己所用。那种 程度的数字,一本小手册足矣。 这个不说也罢。反正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学生时代打工 买来的唱片,一张张认真欣赏。总之,问题不在于数量多 少,而在于质量如何。 荞麦面馆的啤酒 一九八一年夏天从城区搬来郊外,最伤脑筋的是大白天 根本见不着有人东游西逛。住户大半是工薪阶层,无不早出 晚归。理所当然,白天街上只有主妇。我原则上只有早晚写 作,午后便在附近游游逛逛。游逛起来,感觉甚是奇妙—— 周围人都投以狐疑的眼光,好像自己干了坏事似的。 看来街上多数人把我看成了学生哥儿。散步之间,老太 婆问我是不是要租房子,出租车司机问我学习够辛苦的吧, 唱片出租店要我出示学生证。 虽说我一年到头一件夹克一双运动鞋,但毕竟三十三岁 了,无论如何也不该被人看成学生。在街上人眼里,想必大 白天就东游西逛的人都应该是学生。 在城区就绝对没这等事。中午在青山大街散步,时不时 碰见和我同样的人,尤其经常和插图画家安西水丸不期 而遇。 “安西君,干什么呢?” “啊,哪里,是啊,这个,没干什么的。” 便是如此情形。至于安西真是有闲之人还是忙而不形于 色,个中情由全然无从知晓。 一句话,城里莫名其妙的男女所在皆是,这些人大白天 就东游西逛。是好是坏我不清楚,但自在还是自在的。光是 在荞麦面馆吃午饭时要啤酒而对方不显出诧异神情,这点就 足以让人庆幸。因为荞麦面馆里喝的啤酒的确好味道。 三十年一次 我是Yakult Swallows棒球队的球迷,常去神宫球场。 球场相当不错,和后乐园的不一样,四周绿树成荫,感觉上 得以远离鸡飞狗咬的日常生活,慢慢悠悠看一场棒球赛。 或许是不习惯的关系,后乐园球场总好像让人心神不 定。Yakult夺冠那年由于有大学棒球比赛,神宫无法举办日 本职业棒球赛事,只好改在后乐园争战。 在神宫看不成固然遗憾之至,但反过来说,感觉倒也痛 快——“巨人队活该!”进后乐园一垒侧看球前后仅此 一回。 作为Yakult球迷来说,再没有一九七八年赛季更让人畅 快淋漓的了。 那年我住在离神宫球场走路五分钟远的地方,天天都去 看球。每当日落天黑灯火通明鼓声阵阵传来,我就再也按捺 不住,扔下工作跑去神宫。 说起来,那年Yakult打得实在痛快。船田迎战巨人队打 的最后一个本垒打、希尔顿的一垒前扑滑垒、决赛场上战神 松冈那个强有力的投球以及打进后乐园外场席最上边的本垒 打至今仍历历在目,每次想起心底都一点一点涌起幸福感。 声援三十年间仅夺冠一次的球队,可以像咀嚼鱿鱼干一 样把这仅有一次的胜利玩味十年之久。 今年Yakult战绩不佳,可以说输定了。没办法啊!但愿 Yakult在我有生之年——最好在二零零零年之前——再夺冠 一次,别无他求。 离婚 不知何故,最近接连遭遇离了婚的熟人。 这让我相当头疼。就是说,熟人久别重逢,话题本来不 多。一开始打听两旬工作如何和如今住哪儿,之后大体是问 “太太可好?” 这倒不是因为我很想了解对方太太的动向——别人的太 太怎么都无所谓——只是一种家常话,或类似时节性寒暄。 所以我所期待的无非是“啊,还过得去吧”一类回答。 而若这种时候道出“其实已经离了”,说的人怕不开心, 听到的我也不惬意。 对于离婚我没有任何成见。离婚话题的困惑在于自己全 然不知如何应对。 若是结婚或生子,道一声恭喜即可过关;倘是葬礼,说 一句“够你受的”也可了事。 但对于离婚就没有如此方便的说法了。离了或许大快人 心,但那别人是体会不出来的。说“这回舒心了吧’’未免不 负责任,说“哎呀羡慕之至”又不无轻薄,而若板起面孔一 口一个“这可是……”又破坏气氛。 百般无奈,遂说“噢,真的?唔唔唔……”对方也同 样:“是的哟,唔唔唔……”如此场景近来重复了三四回, 弄得我心力交瘁。 既然世间离婚者有增无已,那么在《婚葬祭礼手册》中 添加离婚一项也未尝不可嘛,我想。 夏天 夏天最让人欢喜。太阳火辣辣照射下来的夏日午后,穿 一条短裤边听摇滚边喝啤酒,简直美到天上去了。 夏天不到三个月就过去实在令人惋惜。真想求它至少持 续半年。 前不久看了阿什拉·K·洛·戈因的科幻小说《边境 的行星》,讲一颗很远很远的行星,星上一年,大约等于地 球六十年,就是说春天十五年夏天十五年秋天十五年冬天十 五年,甚是了得。 因此,这颗行星上有句谚语说“能看到两次春天就是幸 福之人”。总之就是说人人盼望长寿。 但长寿得看到两次冬天可就麻烦了,因为这颗行星上的 冬天极其严酷和黑暗。 假如我生在这颗星球,还是从夏天开始为好。少年时代 在夏天的阳光下东跑西颠,思春期和青春期在秋天老老实实 度过,而将壮年中年岁月连同严寒一起送走,春天转来时进 入老年。理想模式。 若碰巧长寿,再迎接一次夏天自然没得说的。死时最妙 的感觉是:噢,能在哪里听一听“沙滩男孩”该有多好啊! 但愿我能如此死去。 西纳特拉有一首老歌名叫《九月之歌》,大意是:五 月到九月太久太长,九月过后日落匆忙。秋意渐渐加深,树 木一片红黄,还有几多时光。 听起来——歌固然很好——让我黯然神伤。死的时候最 好赶在夏天。 P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