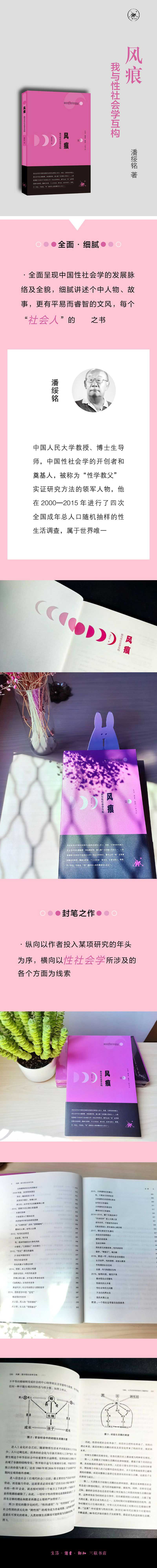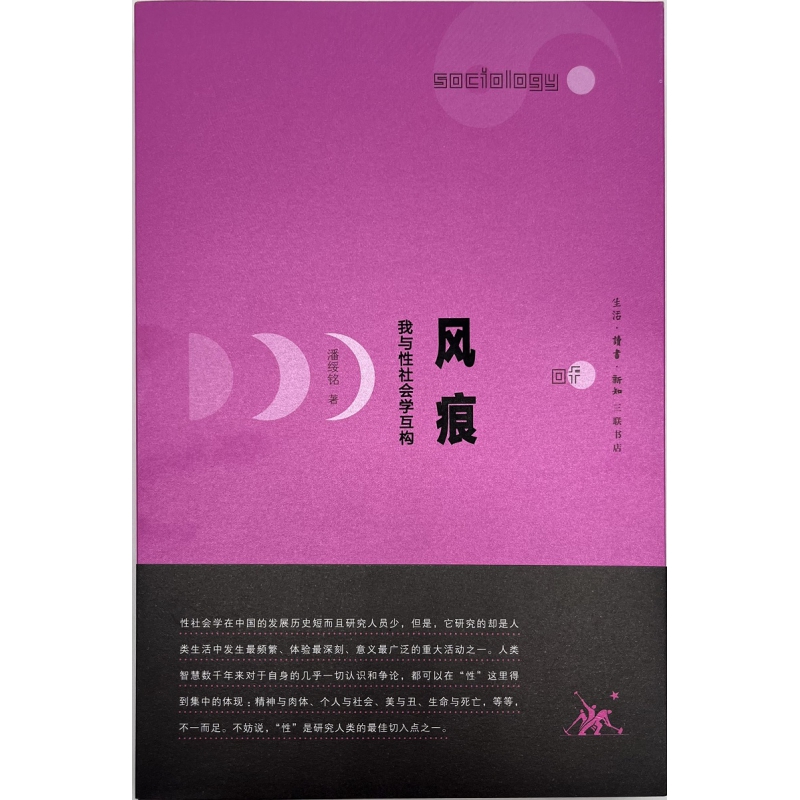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63.00
折扣价: 42.90
折扣购买: 风痕:我与性社会学互构
ISBN: 97871080758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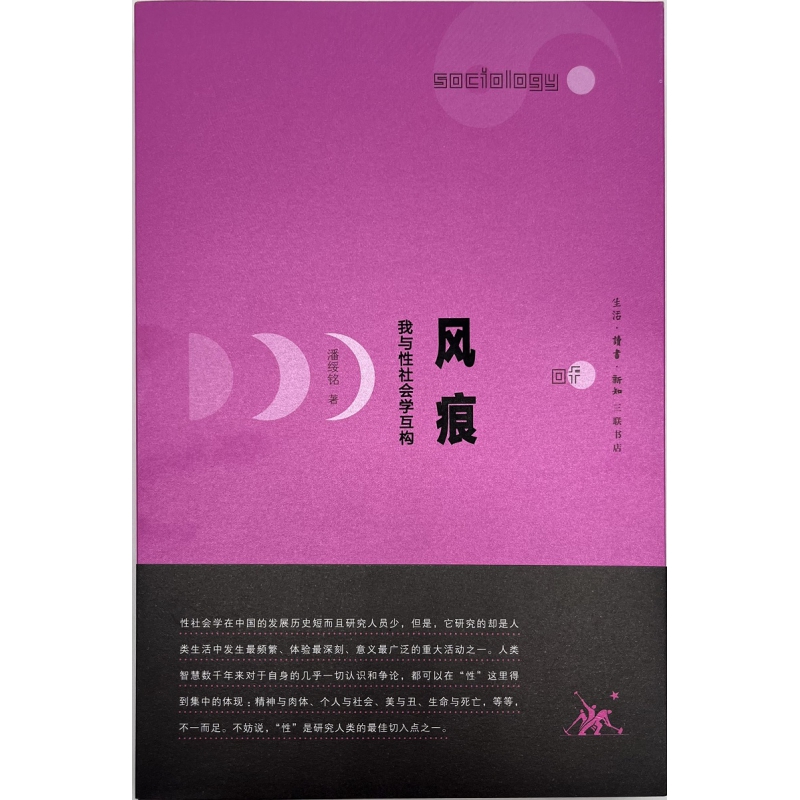
潘绥铭,1950年出生,北京人。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和该校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从1985年开始,他在中国创立并推广性社会学,奠定了其基本理论框架;创立了该学科的基本概念:初级生活圈、全性(sexuality)、性革命、性化、亲密消费、性风采、性福、无性婚姻、性的人权道德等,以及“有性无别”的新型多元性别理念,被同仁称为“性学教父”。 潘绥铭是实证研究方法的领军人物。在定量研究方面,他在2000—2015年进行了四次全国成年总人口随机抽样的性生活调查,属于世界唯一。在质性研究方面,他创立了“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论,落实于“相处调查法”“求异法”和“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等操作模式,以及社会调查的伦理原则。
2019,刨根问底,继往开来 基本假设必须重构 在全性方面,21世纪的中国情境,再也不是“落后”的,而是在许多方面领先全球。 从大环境来看。 首先,中国现在已经拥有更普遍的男女同工同酬,加上更多的夫妻双方就业,给男女平等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经济基础。 其次,中国从1985年到2015年有整整一代独生子女,全世界都没有过。结果,父母的经济负担和精力耗费就大幅度地减少,再加上非常实用的跨代养育,有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四个老人可能帮助独生子女的父母。可是在西方,只有不多的族裔或宗教信徒才会这样做,典型的中产阶级白人很少愿意。 其三,中国大多数男性的气质更加阴柔,夫妻关系更加倾向于“阴阳和合”,客观上有利于出现更加平等的性别关系和性关系。 从具体情况来看,目前中国人的性有以下特点。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的生殖与养育的次数最少,对于性生活的干扰也就最少。 由于严厉的生育管制,私生子女最少,对非婚性关系的制约也就最少。 由于汉族从来就没有任何教规严厉的宗教,性行为戒律最少,对于性的快乐主义的妨碍也就最少。 由于中国没有设立通奸罪,出轨的顾虑最少。 由于独生子女成为“小太阳”,性的家内规训最少,下一代的自由发展更加可能。 由于出现了“单性别成长”,男女交往的前期培训最少,造成“不恋”和“网恋”的增加。 由于中国没有反同性恋的教义和传统,多元性别的阻力最少。 中国没有肉体禁欲主义,没有“性即罪”的文化,没有“性技巧罪”,没有“性成瘾”的概念,这些都是性革命发生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目前的中国,没有任何成形的性哲学,因此情绪吞噬掉一切讨论与思考。 总而言之,在经历了40年之久的性革命与性化之后,在性的几乎一切主要方面,现今中国已经在世界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因此,以前那些“压抑”“封闭”“禁锢”的基本假设都不得不重新构建。这就不得不进行如下反思。 性研究的元矛盾 虽然性研究的人数和成果都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性本身就存在着一系列悖论,无论研究者多么努力,它们也无法消除,反而可能越研究越受阻。因此可以称其为“元”悖论。最主要的是下列两个。 性的生物悖论 性高潮违反了节约能量的客观要求。性高潮就是调动起并且消耗掉人类极大的身心能量。这不是缓慢的付出与疲劳,而是瞬间的迸发与消散。这违反了人类甚至是整个动物界的最基本的原则:尽可能节省能量。这就是个“元”悖论:性高潮带来的快乐与体能充沛的生存需要,往往呈现为非此即彼的相互冲突。 从性与生育的关系来看,人类女性的总和生育率a是相对恒定的,在18个子女上下。那么人类为什么还要进行远远超出必要次数的性交?这种生理机能,无论是由于怀孕概率太低还是出于追求性高潮,都在客观上形成了悖论。 再来看性与生命的关系。人类之性主要表现为勃起,从胎儿三个月一直到临终之际都始终存在。那么为什么只有在“性的活跃期”里才表现为“有性状态”,而且之后很久寿命才结束?其原因可能很多,但是都无法避免其成为一种悖论。 性与安全也存在着生物学意义上的悖论。性交,尤其是性高潮,必须专心致志、感觉集中,否则就会失败或功亏一篑。可是这也恰恰是人类最容易忽视外界威胁的时刻,很容易被乘虚而入,乃至危及生命。这就是一个悖论。 性似乎必然带来快乐,但是在性高潮中,生生死死这样天差地别的感受连接在同一个过程中,这就形成了悖论。 性与性别的关系更是一个元悖论。无论男女还是性少数,性行为其实就是任何形式的摩擦,因此是“有性无别”。可是人类同时又是“器官有别”。这个悖论安安静静地在人类历史中潜伏了百万年,直到最近才突然爆发,闹得天翻地覆。 总之,性的本尊原本就是一个充满悖论的矛盾体,只不过并不必然会产生现实的冲突而已。这每一条悖论,在现在的性研究中—不是我,也不是咱们中国,全世界的人研究来研究去—都没办法解释。所以它也反过来说明,没什么规律,没什么真理。 强人所难的性关系 人类之性,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快乐,还是迫使人们不得不去结成某种性关系(包括各种性少数),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这两种情况都可以生存下去,区别仅在于是否可能生殖—而这仅仅是一个副产品。 性,还要结成关系,我们以为自己是上帝?我们要结成性关系,这简直就是自找倒霉。在人类的任何一种性关系当中都可以看到下列情况。 感受之自私vs感情之无私:性的感受必须是自私的,否则很难达到性高潮,可是感情又必须是无私的,否则性关系很难维系。 个体差异vs快乐共享:在性方面,无论是要求什么、使用何种技巧还是如何感受,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我们的性快乐却必须共享,否则就会削弱性关系。 高潮唯一vs生活目标:性高潮是我们性生活的唯一目标,可是我们的性关系却往往有另外的目标,例如生育、互助、亲情等。在性生活中我们都必须感觉集中,可是日常生活中又有一大堆油盐酱醋在牵扯我们。 性本无别vs乐同烦异:对于性行为而言,我们跟谁做都无所谓,因为性的快乐是相同的。可是与不同的人做,却非常可能带来不同的烦恼,别说同性恋与异性恋不同,就是不同的夫妻也不同。 所以我们想结成一个性关系,这实在是太伟大了。因此,一部分处于中年左右的男人,就会退而求其次,去找小姐了,“一把一利索”,省得这些麻烦。在洁身自好的人里面,其实有的人不是因为遵守道德,而是因为不想轻易投入另外的情感。因为投入以后,可能有一大堆麻烦,哪怕一夜情变成两次,都有这种可能。 其实,所谓的性关系,不管具体是什么样,其实质就是削弱自我、顾及对方。凡是结了婚的人都知道,你结了婚以后,两口子一块出去参加朋友聚会,跟你一个人去绝对不一样。不用任何人提醒,你就会意识到你的妻子或丈夫的存在,你的言谈举止什么都跟你跑去闺密或死党那里去玩绝对不一样。因为你就是存在于这个夫妻关系之中的,已经没有一个独立的你了。 明白这一点,一切夫妻矛盾、婚外性关系、一夜情等都没什么可研究了,不就是独立的个性与制约的关系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吗?过去为了共同“过日子”,中国人牺牲了自己的个性,现在物极必反,为了张扬个性而不再循规蹈矩。这真的有什么可奇怪的吗?这算是一个问题吗?这难道需要去解决吗? 反对“生物因素取消论” 主体建构论最容易被混淆于“随心所欲论”:全性(sexuality)无论扩展到多么宽广的地步,毕竟还是需要有一个生物基础,那就是我们的肉体。 这个理念也是来自生活经历。2006年,我和彭涛、黄盈盈在墨西哥开会,一帮社会建构论者在那儿说得正热闹,一位医学界的人站起来说:你们这叫“生物因素取消论”!好像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认同什么性别就可以变成什么性别,今天变男同,明天变直女,后天变成酷儿。可是我们毕竟有一个肉体呀,这个肉体是由器官构成的。肉体在性别变来变去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如果没有作用,那么变性人为什么还要做手术来改变自己的身体? 当时没人理他,会议也照旧进行。那个人气跑了。过后想想,启发深深。我们性社会学当然坚决反对生物决定论,可是也必须反对生物因素取消论。例如,我们研究了那么多妇女问题,有没有人研究一下女性的肉体(包括身高、容貌、体型等)对于女性的社会地位,究竟有没有发挥作用?这种作用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程度大小之分? 在现今中国的生活实践中,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漂亮女性与不漂亮女性之间究竟存在哪些差别,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例如,“撩人妹”和“恐龙”、“大长腿”和“大象腿”、“波涛汹涌”和“飞机场”、“老刁婆”和“青春玉女”,这些差别都出现在女性之间,这不太可能是一个性别问题,而是一种阶级差别。这样的两种女性之间,难道就不存在斗争?作为一种身份的标签,这些分类究竟是怎么来的?仅仅是因为肉体的客观差异,还是其中渗透了其他的社会因素? 最典型的就是女性减肥,就是强制改造自己的身体。一方面,“盲从减肥”的人确实很多;另一方面,在那些体重指数真的不超标的女性当中,希望减肥的比例也确实很少。所以说,肉体的现实状况实际上仍然在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不能一股脑儿都归结为“男人的目光(造就)女人的身体”。 性少数:跳出阴阳的最大优势 任何一种性少数,根本就不属于阴阳这个范畴,也不需要追求合阴阳,这就是他/她们相对于异性恋的最大优势。因此他/她们完全可以寻找一个新的起点,一个中国没有的或者被忽视的起点,创立出许许多多中国本土没有的新理论,哪怕仅仅是新看法。 对于男同志而言,明清小说《弁而钗》里有“其七寸中,亦有淫窍”之说,认为这就是男男性行为的生物学依据。我没查到西方人写过这个。这当然可能不是真的,但是我们不仅要知道有这种说法,还应该去探究甚至去实验,无论结果如何,都可以推进我们的认知。 性少数的这个思维优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性少数理性与合法性的获得,只有两条路可走。 其一就是建立在“外延的变异”的基础之上,仅仅把多元性别视为二元对立的一种拓展,把性少数包含到性别这个传统概念之中去。 另外一条道路则是,从“内涵的异质”这个基点出发,寻找和论证一个终结式的命题:性少数究竟在性质上(而不仅仅是在取向与行为上)与传统的男女有哪些区别,其根据又是什么。 通俗地来讲就是一句话:任何一种性少数,他/她们还是男人或者女人吗?例如男同性恋这个概念就是第一条思路的产物,就是说,这些人虽然是同性恋,但仍然是男人。可是如果把男同性恋作为“第三性别”,那就是第二条思路,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男人了。 性少数需要边界吗?这是性少数这个概念必然带来的问题。 首先,性少数的外延有没有边界?多元性别究竟有多少种?是可以无限增加,还是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边界? 其次,从内涵上来看,每一种性少数之间,莫非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不是,那么是不是存在着内部边界,需不需要划分清楚这些边界呢? 按照酷儿理论来说,多元性别根本就不需要边界,任何一种独特的现象都可以作为多元中的一元。这在政治斗争中有它的好处,甚至是必须的。可是如果这样,人类就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分类,我们也就无法思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就会全部垮台。我们回到原始人,完全靠感性来行动,那样就好? 理性必然需要定义,定义必然需要边界。可是在现实生活中,那种无类别、不加划分的人类生存状况,却是最舒服、最令人向往的,而且被假设为必定是最平等和最自由的,也就是所谓的“返璞归真”。一切宗教都靠这个来吸引信徒,例如重返伊甸园的理想、死后上天堂的理想、下辈子更好的理想、得道升天的理想,统统都是这种主张。 可是,人类需要两种思维方式的共存:一切伟大的口号都是在说“应该怎么样”,人类在生活实践中却首先需要考虑“只能怎么样”。尤其在现今的中国,人们早就被更加精细、更加严格地分类、定义和命名,因此提倡“去类别的、无边界的多元化”固然很振奋人心,但是所有可操作性过低的口号,最终只能是自己消灭自己。 这就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两者都存在巨大的风险:前者过头就是疯狂,后者过头则是僵死。中国目前的性少数运动正处于这样一个关口,无论是圈里人还是支持者都需要认真地思考。 多元性别的两个基本命题 基本命题之一:阴阳哲学=异质同构,多元性别=异构同质。 阴阳哲学给我们提出一个启示:阴阳是异质同构的,阴与阳,性质是异的,但是它是共同构造在一起的。由此推论,多元性别就必须是同质异构。也就是说,一切性少数,其实仅仅是被社会给构建成不同的类别(异构),但是性质是相同的(同质)。这个性质就是人,是人权。 如果能够这样来思考,那么阴阳哲学与多元性别就不冲突,而是相反相成,就会有利于我们促进性少数的平等权利。 基本命题之二:阴阳哲学=过程协调,性别平等=起点还是结果。 阴阳哲学强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协调,以便达到中庸与和谐。它可以启发我们去反思:我们说的男女平等、多元性别平等,说的到底是结果的平等,还是起点的平等?还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实现的、阶段性的平等,也就是协调?这在社会学里已经争论了数十年,可是性研究领域还没有开始。 性社会学的元问题 人与人,如何被联结起来? 我们社会学研究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元课题”,没别的。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以往我们都有一个“元假设”:人类是群居动物,因此人与人之间是天然、自然、必然地被联结在一起,因此目前那种越来越多的“独处”现象是不良状态,需要想办法来解决。可是,如果我们逆向思考一下:倘若人类的天性就是要独处,只不过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联结起来集体劳动,那么现在生存问题不严重了,人类岂不是恰恰应该恢复个人独处的状态?例如,我们的元假设是人人都需要性,因此才会相互联结。可是现在“无性”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人工生殖、虚拟性爱、人工智能性爱普及之后,我们的元假设是不是还能成立?我们现在的一切研究成果,会不会被全盘颠覆? 呈现与解读,能做到吗? 我们研究性文化,先别去读西方著作,而是问自己下列两个“元问题”:我真的能如实呈现自己吗?我真的能理解任何一个别人吗? 第一个问题,至少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所谓如实呈现,应该是没有自我操纵和控制的。如果写成文字,那就是我自己的一种主体建构。这并不是故意撒谎,而是我虽然希望让你看到一个原始真实的我,但是我做不到。 第二个问题,真的理解别人,我能做到这一点吗?例如“夫妻假象”,就是两人很相爱,长相厮守一辈子,但是也会有一个互相的假象。这不是撒谎,是因为你爱他,你珍惜他,你知道他不喜欢这个,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把这个方面给遮掩住,不让他看到。结果,长此以往,对方也就以为你真的是这样了。 如此一来,我们性社会学所研究的一切个人或者文化现象,其实都是别人的表演。我们越是深入生活,越可能看到善意的假象。我们只不过是习惯成自然地在使用“社会现实”这样的话语,来支撑自己的学术合法性。总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你凭什么来研究社会、研究性? 性是可以理性分析的吗? 理性分析,就是能用概念、术语、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能够进行逻辑思维。可是人类之性只是一种最强烈的感性体验,绝大多数人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就造成一个悖论:每个人都说不清自己的性究竟是什么样的,我却大言不惭地论证中国人的性革命与性化。我不知道这在哲学上是否可以,但是作为经验研究的性社会学,这个鸿沟必须加以解释和化解。否则,“一切都只不过是认同”的思潮就会把我们带到不可知论的阴沟里面去。 性,可能有一个文化吗? 性,如此私密与个体化的性,可能有一种文化吗?人们又是如何形成与传播性文化的?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产生一种文化,我们都很容易理解,甚至“性关系的文化”也可以理解,因为大家都能看见它的种种表现。唯独“性的文化”莫名其妙。莫非人们互相参照着过性生活? 我这一辈子其实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最终在《性社会学》这本教材里专门写了“语汇,建构着我们的性”和“行为训练的构建”。其主要意思就是说,性文化不是直接传播的,而是靠着消除骂人话和“像样”的行为训练,才形塑出每个个体的具体的性行为方式,最终汇聚成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的性文化。 性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而且研究人员少,但是,它研究的却是人类生活中发生最频繁、体验最深刻、意义最广泛的重大活动之一。人类智慧数千年来对于自身的几乎一切认识和争论,都可以在“性”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美与丑、生命与死亡,等等,不一而足。不妨说,“性”是研究人类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然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大众对于性社会学普遍存在误解,就是把它混同于“黄”或者“求医问药”,即使在学术界,非本专业的师生也往往认为:性社会学很有意思,但是不重要,尤其是学术价值有限。本书所呈现的研究成果,能够促使大众知道这是一门学问,而且很有用。作者用这些在经典社会学领域中也顶天立地的创新成果,来推广性社会学的学术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