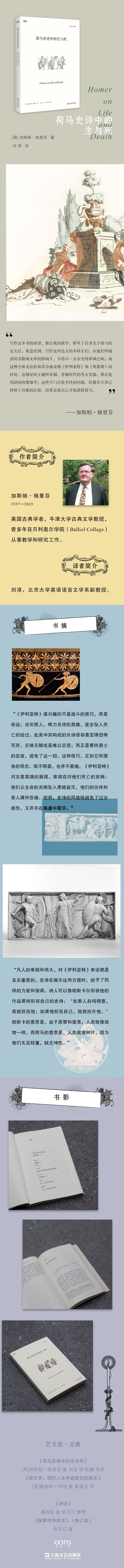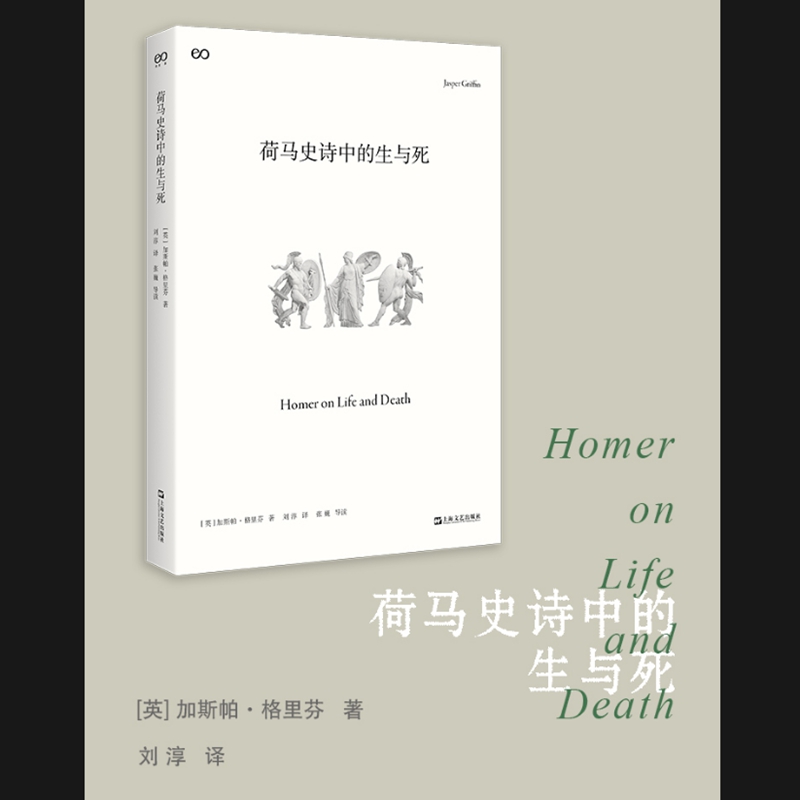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文艺
原售价: 62.00
折扣价: 40.30
折扣购买: 荷马史诗中的生与死
ISBN: 9787532189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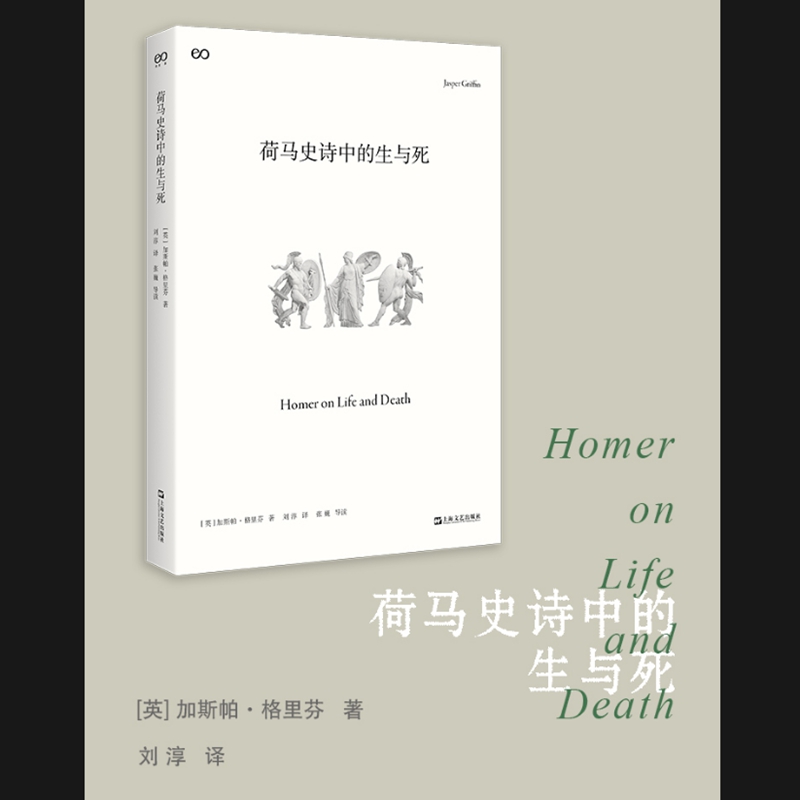
加斯帕?格里芬(Jasper Griffin,1937—2019),英国古典学者,牛津大学古典文学教授,曾多年在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刘淳,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张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格著正是“回归文学”潮流里的一部经典之作。原书以“荷马论生死”为名,意在引发读者如下疑问:荷马作为两部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叙事者,是否以及如何有所论说?读者又怎样一窥其论说之堂奥?荷马如若有所论说,也是见诸史诗这种特殊的诗歌表演形式,我们必须掌握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亲临史诗表演的现场。当年的史诗表演有如乐章,时而雄浑,时而低徊,令听众-观众或悲或喜,直击他们的心坎。(早期史诗的表演有此效果,柏拉图的《伊翁篇》可以为证。)因此,格著追求一种亲临现场的体验,而非钻入故纸堆的考据。他运用的方法,更为接近荷马史诗的表演同古代受众之间的关系(聆听、观赏与传习)。他称之为“aesthetic methods”,不过对此只是点到为止,并未加以申发,读者须在此种方法的实际操作里领会其实质。“aesthetic”一词源于希腊文的aesthesis,后者从其本义上而言,是“感知”,即“经由感性而认知的方式”,有别于“理性分析的认知方式”。此种认知方式近于吾国传统所言的“体悟”,故而格里芬笔下的“aesthetic methods”或可译作“体悟法”。(aesthesis的认知方式,最重要的后果是“审美观照”的生成,而俗常所谓的“审美”,并非aesthesis的出发点,倒是其结果)。格著运用此法,尤重对情感的领受并体知其中深意。如其所言,这种“诗评”方法远绍自古希腊人,可见于“大量关于荷马的希腊评注当中”,亦即古代学者抄录于文本页边或行间的评注,统称为scholia。至于现代学界,格里芬认为二战前后的德语地区荷马学者,最能得古代文学评论的“心法”之传,故而与他们最为意气相投。在全书的注脚里频频出现Hermann Fr?nkel, Wolfgang Schadewaldt, Walter F. Otto, Karl Reinhardt, Walter Marg等人的大名,作者与他们诚可谓心有戚戚焉。 …… 格著(尤其是第一和第二章)着力展示诗人的技艺与文学风格,背后其实隐伏着一条根本原则:文学特性乃是荷马史诗展示其生命体验的方式,前者取决于后者。评者的首要任务不是将文本拆解成未经组装的片段,而是要接契荷马史诗出乎其中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格里芬一言以蔽之为“英雄的生与死”。荷马论说的这一主旨在格著前两章已有所透露,譬如“《伊利亚特》的伟大主题是英雄的生与死”,或者,“在《伊利亚特》中这一最引人瞩目的人格上【指阿基琉斯——笔者按】,聚焦着史诗中的核心问题:英雄生与死的意义与重要性”,而后四章则集中从英雄与众神两方面详加阐明。首先提出的问题是:“何为英雄?”(第三和第四章)英雄生涯的决定性因素恰恰是“死亡”。这一观点可证之以两部史诗的主题。《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分别以一位最伟大的英雄为核心,前者可谓“英雄之死”的史诗,而后者不啻为“英雄之生”的史诗。在西方,《伊利亚特》虽然被誉为“战争史诗”之冠,甚至被直呼为“暴力之诗”(西蒙娜?薇依语),但在格里芬看来,“史诗对死亡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战斗的关注”。“死亡”的核心地位在《伊利亚特》的“序诗”里已然道出:“阿基琉斯的忿怒”带来的后果是“无数的苦难”,特别是许多战士的阵亡,让他们的亡灵去往冥府,而尸体则暴露野外,为野兽所凌虐(《伊利亚特》第1-5行)。从史诗“序诗”宣告并展开主题的功能来看,《伊利亚特》的故事以“阿基琉斯的忿怒”发端,以“赫克托耳的葬礼”终结,着眼点并非“特洛依战争”的本末,而是死亡以及与之相伴的苦难。“英雄之死”的主要脉络,尤见于史诗诗人将四位大英雄的死亡构筑成一个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并衬之以众多相对次要的武士之死)。这也是“阿基琉斯的忿怒”主题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阿基琉斯的挚友帕特罗克洛斯代友出战,杀死了支援特洛依一方的宙斯之子萨尔佩东(第十六卷),导致他自己命丧特洛依主将赫克托耳之手(同卷),并由此激起阿基琉斯复仇的滔天怒气(第十八卷),与赫克托耳单打独斗,将其杀死并凌辱尸首(第二十二卷),而阿基琉斯的大限之期在赫克托耳死后也会接踵而至。虽然《伊利亚特》并未述及阿基琉斯之死,但这个主题其实贯穿了整部史诗,尤其在史诗的后半部成为不时奏响的“主导动机”。阿基琉斯得知自己将会英年早逝,必须用“短暂的生命”来换取“不朽的荣光”,而且随着战事的推移,他对自己的死亡到来的准确时刻和具体情形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德国学者玛格(Walter Marg)曾把《伊利亚特》称作“死亡之诗”,格里芬认为,“把它称作生与死之诗更为恰当:史诗中描述的是生与死的对比和生死间的变换”。倘若我们把《奥德赛》也纳入考察范围,那么两部荷马史诗确乎以“死”与“生”为各自的关注焦点。《奥德赛》以“奥德修斯的归家”为主题,这位英雄归途迢递,历经艰险,总算劫后余生,返回故土并以巧智和勇力重新夺得王位,与家人团聚。不过,奥德修斯的生还与归家,若是没有“英雄之死”的映衬,便会黯然失色。这种“生与死”的互衬关系,深刻地体现在两部史诗的互文性当中(遗憾的是,格著对此面向鲜有关注)。奥德修斯与阿基琉斯构成两种不同的英雄典范,“奥德修斯的归家”与“阿基琉斯的忿怒”也讴歌了两种不同的英雄主义。事实上,《奥德赛》的史诗传统与《伊利亚特》的史诗传统形成了一种竞比的关系。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奥德修斯入冥府的经历(第十一卷),在那里遭遇其他阵亡的战友,特别是阿基琉斯的亡灵。阿基琉斯对他说道(第488—491行): 光荣的奥德修斯,请莫把死亡说得轻轻松松。 我宁愿做农奴,受他人役使, 即便他并无地产,家财微薄, 也不愿统领所有亡故者的魂灵。(笔者试译) 这番话并非由史诗诗人叙述,而是奥德修斯在自述其经历。我们不要忘记,这位狡黠的英雄善于编织谎言,所以不能轻信,认为阿基琉斯的亡灵果然有如此枉自菲薄的言论。事实上,奥德修斯(或是《奥德赛》的诗人)造作此语,很可能是让奥德修斯借“阿基琉斯”之口,抑“死”扬“生”,意在以《奥德赛》的传统与《伊利亚特》的传统争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是基于入冥府的体验,与阿基琉斯为代表的亡灵相谈所产生的对死亡的更深入的认知,促使奥德修斯勇于“英雄之生”,经受“无尽的哀痛”而绝不放弃一丝生还的希望。 古希腊以降,世人皆谓,《伊利亚特》出乎前而《奥德赛》继乎后。这种评断,不仅关涉两部史诗的创作年代,而且更重要地针对它们的经典地位;换言之,作为史诗,《伊利亚特》比《奥德赛》更胜一筹。基于此种评断,或许我们可以说,要肯定“英雄之生”(“英雄之生”也只有其饱尝苦难与艰辛的部分才值得肯定),就必须首先肯定“英雄之死”,故而“英雄之死”的史诗必居首位。从《伊利亚特》对“英雄之死”的肯定与颂扬,生成一幅本原性的悲剧世界图景:悲剧性为荷马英雄存在的基调,只有饱受苦难,直至经历终极的苦难——死亡——英雄才能证成自己;因此,死亡具有优先的存在意义,只有悲剧性的“英雄之死”才成就人类存在的最高意义。同样是《伊利亚特》的诗人(而非《奥德赛》的诗人),巧妙地用这幅世界图景把英雄“悲剧”的“两重观众”——内部和外部观众——联结起来,促成他们的视域融合。悲剧的内部观众乃是荷马的众神。格著的最后一部分(第五和第六章)致力于阐明荷马众神的特性。这些神明并非史诗使用的文学或修辞手法,亦不能还原为某种社会事实。他们强大有力,令人敬畏,史诗里的英雄对他们虔信有加。他们形态多样,每一尊都有鲜明的特征,但作为一个整体,“荷马诸神是为了展示荷马中凡人的本质而设计的”。与凡人相较,他们可谓美化了的、更强大的种族。凡人与神明的本质性差异在于“死亡”及与之相伴的“苦难”:众神免于真正的愁烦,以及凡人生命的有限性。英雄则介于凡人与众神之间:芸芸众生当中,英雄是最具有“神性”的凡人,故而英雄与众神得以彼此映照,两者的本质相互界定,相互衬托。《伊利亚特》的众神虽则有时也单独行动,对于个别的英雄有着特殊的关切(在《奥德赛》那里成为定则),但他们更经常地居于光明璀璨的奥林坡斯山上,从那里作为一个整体观望尘世发生的事件,特别是英雄的悲剧,有如神界的悲剧观众(见格著第六章“旁观的诸神与《伊利亚特》的宗教”)。英雄的行为、成就和苦难成为诸神热切关注的对象。这种神界观众的视域,也是史诗要传达给(表演当下和后世的)外部观众的视域。这些外部观众,正如史诗的内部观众(众神)那样,从更高的境界来观照“英雄之死”,也就是从天界崇高的视角,最终获得了悲剧的“审美直观”,得以收摄世界之整全与生命之真相。 阅读中译本的过程中,我的脑海里逐渐浮现出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出自《论语?先进》:孔门弟子仲由,性耿介好勇,有一次向老师问起服事“鬼神”的方法,被夫子反驳了一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仲由并不甘休,斗胆又问死后之事,夫子的回答如出一辙:“未知生,焉知死?”师徒间的这番问答虽然简赅,但孔门精神已跃然纸上。孔子重 “人事”而轻“鬼神”,以人生为本,事死如事生。他对于现实人生采取奋发有为的态度,但将“死”和“鬼神”视为“不可知”,对弟子的求知欲望予以当头棒喝。第二个场景出自柏拉图的《斐多篇》:临刑前的苏格拉底,在狱中与众弟子作别,神态自若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哲学讨论,话题是灵魂的不朽,苏格拉底对之予以详细论证,并以一篇道说“死后”灵魂命运的神话作结。苏格拉底对待“死亡”安之若素,恰恰因为他知之甚深。这个场景虽由柏拉图的妙笔所造,必定描摹了乃师的真面目。后来,柏拉图更是将“死后”的遭遇铺展成像《理想国》篇尾“埃尔的故事”那般洋洋洒洒的伟大神话。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这两位古希腊的哲学师徒,为何孜孜于探究“死亡”,认为“死亡”不仅“要知”,而且“可知”?读罢格里芬的名著,我更加确信,他们对待“死亡”的执着精神其来有自,早就伏根于荷马史诗“未知死,焉知生”的精神当中。从对比的视角来看,我以为这也是此书的中译本将会带给今日中国读者的最大启示。 ★ 《荷马史诗》是西方经典中的经典,是众多作家及各个领域学者的创作与思想资源 ★ 世界经典《荷马史诗》的绝佳导读,知名古典学者引领读者感受史诗的文学之美 ★ 豆瓣评分9.3,佳作佳译,译文受到众多读者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