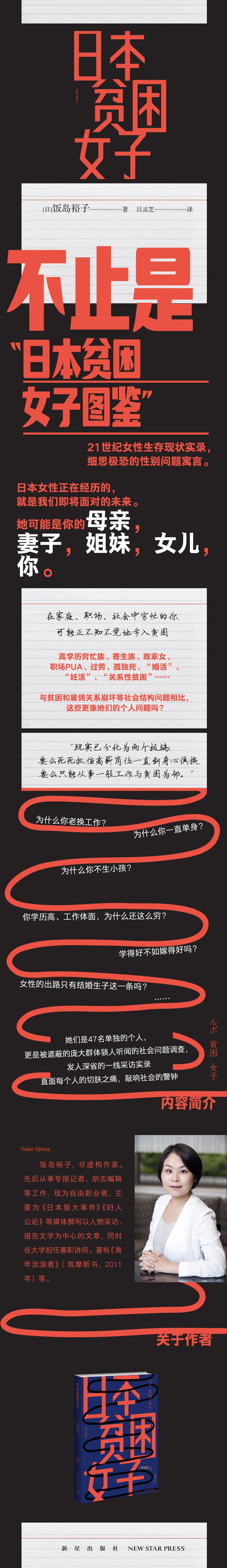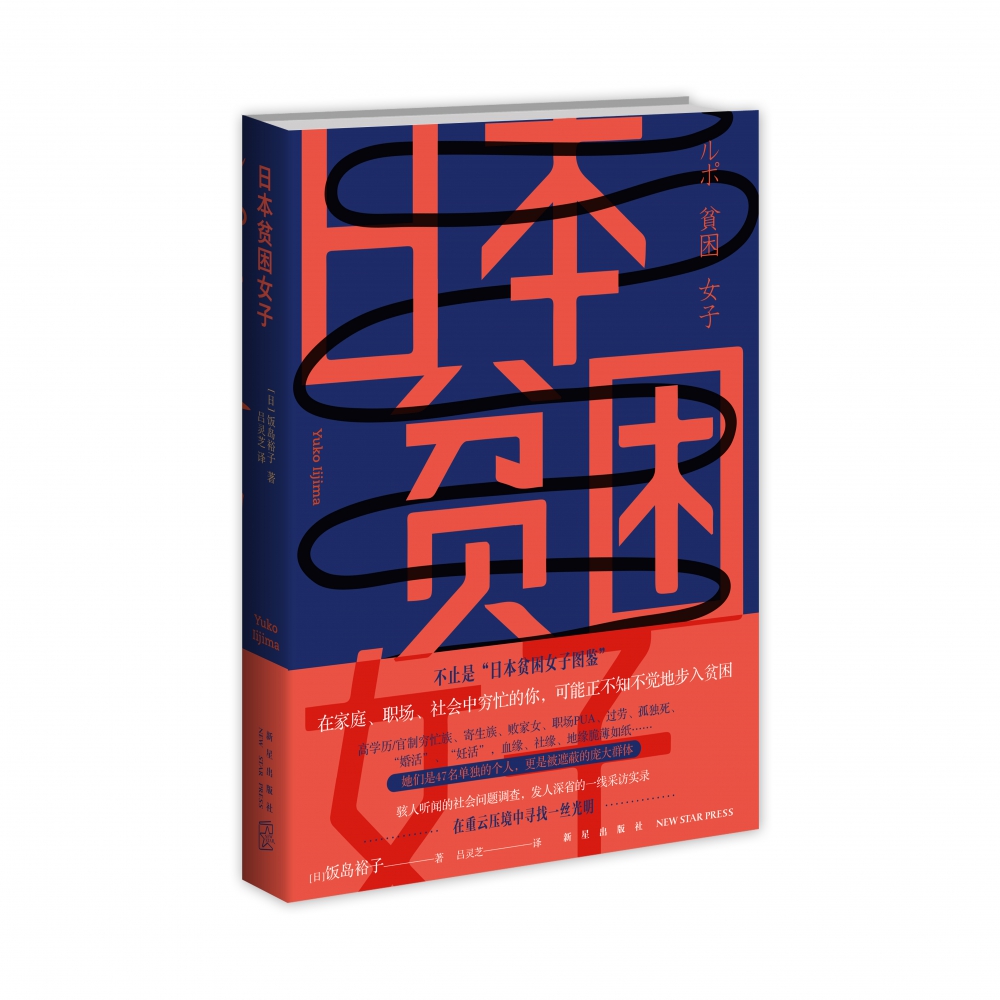
出版社: 新星
原售价: 42.00
折扣价: 26.90
折扣购买: 日本贫困女子
ISBN: 97875133440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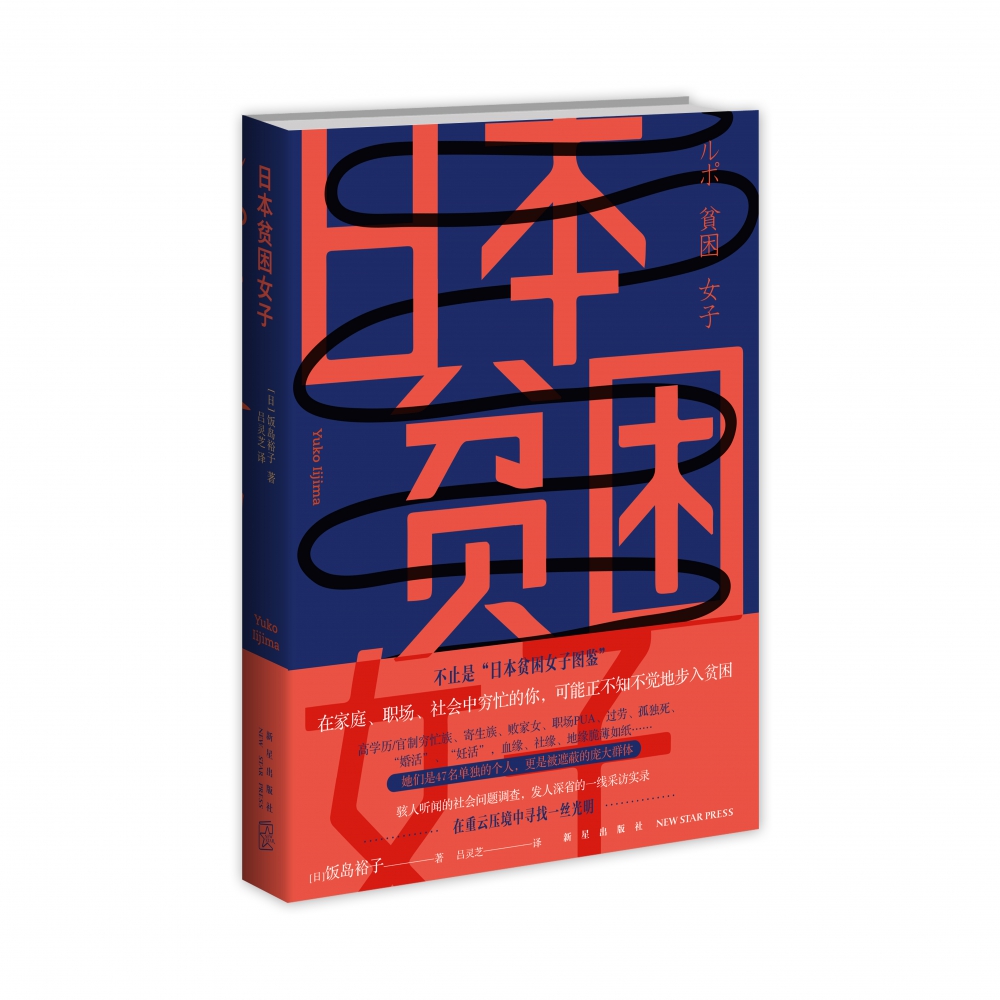
饭岛裕子,非虚构作家,出生于日本东京。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科硕士毕业,先后从事专报记者、杂志编辑等工作,现为自由职业者,主要为《日本版大事件》《妇人公论》等媒体撰写以人物采访、报告文学为中心的文章,同时在大学担任兼职讲师。著作有《青年流浪者》(筑摩新书,2011年),采访集有《99种小转机的做法》(《日本版大事件》编辑部编,大和书房,2010年)等
“穷充”背后的陷阱 我们已经分析了女性面临的困境,而且艰难的形式多种多样,很难用“贫困”一词一言以蔽之。 现在不同于泡沫时期,青年已经不属于可支配收入较高的人群。很早以前就有人指出,现在的青年不出国旅行,不买车,兴趣和爱好已经发生了改变。这点在女性杂志的特辑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月刊《日经女性》自1988年创刊以来便与专注时尚、美妆的普通女性杂志不同,致力于呈现各个时期女性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等。20世纪90年代的特辑多为“出人头地的工作法”“工作中常用的英语”等,专为试图在工作上有所突破的女性所设。然而近几年来,“节约方法”“存钱方法”的特辑却频频出现。比如2015年发售的12期中就有5期刊首特辑都在总结关于存钱的窍门。 如此看来,青年似乎并非在忍耐,而是在追求自得的充盈和每日的充实。 人们将有恋人、朋友和伙伴,现实生活很充实的人称为“现充”。一开始是为了揶揄沉迷网络世界的人,才对与之相反的人群如此称呼,后来这个说法便慢慢普及开来。这个词表明物质相对丰富的青年更追求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的充实感,但实际上,“现充”也遮蔽了贫困的现实状况。 铃木大介通过采访靠性服务赚取日薪勉强维生的女性,写成了著作《最贫困女子》(幻冬舍新书,2014年)。书中就有许多难以称为现充的“穷充”女子登场。铃木取材过程中见到了许多居住在地方、年收入仅100万日元左右,但是周围有许多朋友、每天开朗乐观的穷充女子,铃木不禁疑惑:“她们真的是‘最贫困女子吗’?”但是铃木也指出,她们大都无法摆脱贫困,且极可能将这种负面遗产留给后代。 电视总会把艺人在底层奋斗时因贫穷而历尽艰难的故事当成美谈,并且频繁提及。实际上不仅是艺人,大多数人也认为“年轻时应该尝尝贫困的滋味”。 2011年开播的综艺《幸福!贫民女孩》(日本电视台)直到现在仍人气十足。节目向观众展示了为了追梦而甘于贫困的女性,还分享了不花钱也能每天都快乐的秘诀。里面登场的女性可谓“穷忙族”的代表,她们不仅丝毫没有表现出贫困的苦恼,反倒正因为贫困,她们在逆境中保持坚强、不断追梦的身影才更加耀眼。 我采访的众多女性,尤其是独居女性,也都具有“穷忙族”的特质。有人说:“把菜叶晾干了做成菜干特别好吃。这种细致节俭的生活方式能让我得到治愈。”也有人说:“我会把百元店的商品加工成具有季节感的小饰品摆在家里。”“我在阳台种菜,顺便省了菜钱。”“因为狠不下心来放弃去迪士尼,所以每天只吃生鸡蛋拌饭,用省下的钱买迪士尼年卡。”“我会想尽办法凑钱买偶像的演唱会门票。”女性们提到了很多生活中的“穷充”故事。 在经济困难的境遇下,通过改变思维方式来过上积极向上的生活——这种看待问题的“穷充”视角极为重要。只有这样,事态才可能好转。与此同时,脱离“穷充”才是至关重要的课题。“穷充”的故事往往容易掩盖其背后的贫困,社会相关部门不能被迷惑,必须直面每个人的真实状况,并商讨相应的对策。 所谓贫困是什么? 一谈到青年女性的贫困,总会有人指出:“住在父母家的寄生族女性不算贫困。”每次我都反驳:“从家庭收入来看,她们的确不算贫困,但如果从本人的可支配收入来看,她们正是贫困的一员。”我邀请住在父母家的女性接受采访时,就有不少人回复我说:“我出不起车费,麻烦到离我家最近的车站来。” 还有人指出:“住在父母家、可支配收入极低的女性如果算作贫困,那么家庭主妇怎么算?”这个提问很有道理。我可以不怕误解地直言:“她们与贫困只有一线之隔。”无论丈夫收入多高,如果离婚后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可以依靠的家人,这些女性很有可能立刻陷入贫困。从单身母亲的贫困率居高不下就可以看出这点。 贫困究竟是什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单纯讨论所得的多寡,而是从是否有可以依赖的家人和朋友、是否有受教育的机会、是否身体健康能参与社会活动等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来判断。同时,“社会排斥”的概念也得到了普及。岩田正美认为,社会排斥不仅仅是当下的问题,而要把贫困放在整个人生历程中,同时,作者通过著作普及了“并非断点,而是连成一线”的社会排斥概念(《社会排斥》,有斐阁,2008年)。 和父母一起居住的女性或许暂时无衣食之忧,但是父母去世后,她们极有可能陷入贫困。另外,同样是无业状态,学历的高低和工作经验的有无也会极大地影响女性摆脱贫困的可能性。 在审视潜在的女性贫困时,有必要基于社会排斥的概念,将女性过去和未来的生存困难和工作困难也纳入视野,制定一个综合指标。 通过纳入社会排斥的视角,一些看不见的问题也会浮现出来,用贫困无法完全概括的复杂状况也能变得更加明晰。“住在父母家是否属于贫困?”“‘穷充’是否属于贫困?”这类问题也自然能得到解决。 雇佣的包容与脱离 青年单身女性的严峻处境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善的。虽然本书无法对此开出万能处方,但是针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变更这种宏观现状,以及包括当事人在内的我们能够做到的微观行动,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进行反思。 首先,雇佣方面。 目前,假设男性普通劳动者的薪资为100,那么女性普通劳动者的薪资就只有70.9,女性短时间劳动者的薪资则只有50.5(厚生劳动省《薪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2012年)。当前缩小男女薪资差距刻不容缓。 只要非正式雇佣人群和无业人群能获得稳定的工作和足以维持生活的薪资,就能解决物质性的贫困。可是,雇佣稳定的工作大都对学历、经验和年龄等有要求,就业对她们来说就十分困难。尤其对低学历的女性来说,这些要求对她们非常不利。 这个提议虽然有些唐突,但我认为,有必要撤销招聘时的学历要求。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对青年女性需求较高的是销售及待客等工作。待客需要的并非书本上的知识,而是亲和度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同时,由于销售和待客的工作多为非正式雇佣,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此外,还可以通过获取资质和培训来消除缺乏工作经验这一不利因素。然而贫困已经使她们的生活捉襟见肘了,很难再挤出时间和金钱接受再教育。 目前有求职者支援制度,让没有领取雇佣保险金资格的失业人员可以免费接受职业培训。相对正式雇佣,非正式雇佣者接受研修的机会较少,连教育培训也要自掏腰包。就算是非正式雇佣,也应该得到官方支援,让她们得到足以成为工作经验的教育培训。 虽说如此,综合上文可知,现实中并非只要得到正式雇佣就能解决问题,也有人在成为正式员工后难以忍受长时间的劳动和严苛的工作环境,反而刻意选择了非正式雇佣。因此,今后非正式雇佣率在很长时间内仍会居高不下。 或许,更为现实的目标不是得到正式雇佣,而是让非正式雇佣成为一种可以让人实现生活独立的工作方式。为此,必要条件首先是同工同酬。此外,为了同时从事多份工作的非正式雇佣女性和自由职业者,要实现年金一元化,并消除家庭形态带来的不平等对待,将社会保险改为以个人为单位。还有必要为很难得到体检机会的非正式雇佣和无业女性创造机会。 开通了“职业女性热线”的职业女性全国中心(ACW2)副代表伊藤绿女士长年倾听女性们的工作烦恼,为解决她们的问题不断奔走。 这个意见听起来可能比较极端。我们最近正在倡导“每周工作3天,让生活成为生活”。 自从《均等法》颁布以后,保护女性的规定被废除,使女性劳动时间与男性趋同,长时间劳动的风潮不断蔓延。 伊藤女士说:“1999年女性深夜劳动被解禁,从那以后,超时劳动就迅速蔓延,患病人数急剧增多。正式雇佣已经不再是正解,我们应该把目光转向与男性劳动时间差异化上。” 特别是女性人群,因为育儿和看护的需要,劳动条件遭到限制的比例较高。 人都会累,都会得病,都要休息,也都有不想工作的时候。只有让有血有肉的人们不勉强自己的工作,才称得上体面工作。 我们一方面要建成只要有意愿人人都能通过劳动自立的社会,另一方面也要保证人们遇到就业困难时不至于陷入不安和负面情绪,能够安心生活下去。 家庭的包容与脱离 日本是家庭包容性很强的国家。可是对女性来说,那可能会成为一把双刃剑。经济上无法独立的青年单身女性应该依赖家庭,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就算自己家已经如坐针毡,也有很多女性难以走出家门。 倘若工作不稳定,要维持每个月支付房租和水电费的独居生活自然会不安。在大城市,房租和押金等租房初期费用都非常高,许多人表示以前从未独居过,很难建立自信。 就算与家人的关系非常不好,还是有许多人选择咬牙忍耐,因为“只有这个选项”。家人因为担心女儿的将来,也容易将忧虑化作严苛,进而体现在话语和态度上。 另外,也有不少人正在遭受来自家人的暴力。抱着决死的心情逃出家门的女性不得不在公园过夜,或是到偶遇的男性家中留宿,无家可归。我遇到的这些女性后来都在支援组织的帮助下申请了生活保障,从此得以脱离原生家庭,但想必也存在只被解释为“未婚女儿离家出走”,最后被送还原生家庭的案例。 随之凸显出来的还有一个问题,即工作不稳定的女性一旦离家出走,就不得不依赖生活保障制度。这点从独居女性一旦失去工作就陷入贫困,不得不领取生活保障金的案例中也可看出。就算后来终于摆脱了低保状态,也要时刻生活在不安中,生怕将来遇到一点小事又会重蹈覆辙。未来的不确定进而化作精神压力,甚至使抑郁迟迟得不到改善。 如果能够得到房租补助、无息贷款和公营住宅等援助,或许就无须被迫领取生活保障金了。可是,现存的公营住宅几乎不允许除60岁以上高龄人士和残障人士以外的单身者入住。 2015年4月,《生活穷困者自立支援法》开始施行,只要满足条件,就能领取住宅补贴。可是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而工作一直不稳定的人又很难找到待遇好的正式工作,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此外,万不得已时可以寻求保护的庇护所和妇女保护设施的作用也极为重要。人们通常认为,只有遭受家暴的女性才会寻求庇护所帮助,但事实是所有女性都可以。这一信息也有必要广为传播。 尽管独居女性时常会担忧现在的生活不知能持续到何时,但是相比住在父母家、为家人关系所扰的女性而言,她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相对较高。 还有一些女性好不容易摆脱了家庭的束缚,总算能安心生活,她们却没有独立和自立的观念。 有人因为自己一把年纪了还不嫁人,没脸在父母家待下去。而且这也是日本独特的家庭包容性原则,即幼时随父,出嫁随夫。但实际上,她们只是受到了“男主外模式”的影响。 也有人认为,如果与家人关系好,就没必要非得离开父母家。在日本,单身者与父母同住率极高,欧美国家却一直将离开父母视作成年的必要条件。可是近年来,由于欧美各国的青年雇佣状况恶化,越来越多的青年在独立之后又返回父母家居住。由于家庭重复着闭合与展开的过程以包容孩子,有人将其称为“手风琴家庭”(Accordion Family)。 与父母同住的单身女性中,也有在家务和看护方面为父母所依赖的人,还有不少与家人同住的正面案例。 可是这里必须申明,“手风琴家庭”都具备了能伸能缩的经济实力,并且仅限于彼此关系良好的家庭。 “离家”与“留家”乍看是相反的选择,其根源却是一样的,那就是无论作何选择,都应该优先考虑当事人的意愿,摆脱“男主外模式”观念下的日本式家庭包容规则。 最近政府为解决少子化问题,设置了三代同住的减税措施。从配偶优惠政策中也能看出,直到现在,与何种属性的人同住仍是日本重要的生活模式。 但不管是谁,只要有离开家庭独立生存的意愿,政府就应该提供相应的支援机制;还应该建立一个无论和谁生活都不会陷入制度上的劣势,进而生活艰难、望而却步的社会制度。 “男主外模式”的崩坏与意识的偏移 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男主外模式”在终身雇佣制的崩溃和非正式雇佣的扩大中,已经如同风中烛火。 在男性从事长时间劳动,女性包揽家务、育儿、看护等劳动再生产的“男主外模式”中,能够当得起“家庭主妇”角色的,只有正式雇佣、收入较高,可充当收入顶梁柱的女性配偶。 从享受配偶优惠的女性比例可见,丈夫年收入越高,女性获得优惠的比例就越高,堪称讽刺。自然而然地,家庭年收入低的阶层无法依靠“男主外模式”,即男性一人工作无法维持一家生计的时候,妻子也必须出去工作。 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和贫困的蔓延,以青年人群为中心,越来越多的男性只得从事不稳定的工作。最近,希望成为家庭主妇的青年女性逐渐增多,但如今家庭主妇已经不是人人都做得起的了,只能对“家庭主妇”临渊羡鱼。 未来将成为丈夫的青年人群中,非正式雇佣者众多,就算是正式雇佣,也看不到加薪的希望,处在这种境地中的单身高龄女性无法依赖儿子,也不会想依赖儿子。随着未婚、晚婚的发展,父权的威仪极有可能已经不复存在。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的价值观也不会轻易改变。 本书一直强调女性的贫困很难被看到,而且当事人及其家人往往也意识不到贫困的危机。例如大学毕业以后一直打零工的女性在父母家过着不自由的生活,却声称自己很满足。还有高中退学后连续多年“家里蹲”的女性并没有感到不安,她的家人也从不抱怨。 没错,与其在所谓黑心企业工作,最后身心俱损,这些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她们完全有可能直接找到能够充当“收入来源”的男性并与之结婚,过上与贫困和生存困境无缘的人生。 可是,“从此,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全剧终”这样的结局真的好吗?这种生活持续下去的保障在哪里? 常有人说,女性拥有很多选择。橘木俊诏在前面提到的《女女格差》后记中写道:“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女性都有机会获得更多选择。”所谓选择,就是结婚、成为家庭主妇、生孩子、做全职或是兼职。随后她又总结道:“正因为女性的选择更多,人生更灵活,如果顺利,她们的满意度或许也会比男性更高。” 但我认为,这种“选择多”的想法可能是个陷阱。说到底,大多数选项都以“结婚”或“将来可能结婚”为前提,这种前提下的结婚还必须是进入“男主外模式”的婚姻,否则就无法当家庭主妇或是做兼职。 正因为选择多,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更轻松”,甚至连女性自己也深信不疑。 相比之下,越是深陷困境的女性,“选择”就越少。如果学历低,就只能从事非正式雇佣。因为没有丈夫,只能做全职。而且随着年龄增长,一度近乎无限的“选择”也会变得极为有限。即便想继续工作,如果丈夫不帮忙育儿,也只得辞职。想结婚生子,但是找不到对象。?? 我认为,女性摆脱贫困的一个方法,就是舍弃这种“多元选择”,即放弃以结婚为前提的观念,而是培养身为“户主”的意识。已婚女性也一样。当然,不仅是意识,税收和社会保障等以家庭为单位的政策也有必要改成以个人为单位。 上文已经论述过,由于计算贫困率时家庭收入也在参考范围内,只要不是独自居住,女性贫困问题就无法浮出水面。一旦被隐藏在家庭中,女性贫困甚至无法被看到。为了让其凸显出来,培养“户主”意识是重要的第一步。 超越贫困女子 我一直在犹豫,是否要将本书书名定为“贫困女子”。本书之意不在于探讨“住在父母家是否算贫困”,可是只要出现“贫困”这个词,就会引发根据可支配收入多寡等诸多条件的客观“筛选”。然而,女性的贫困很难定义,一旦使用了“贫困”一词,可能就会将周边人群排除在外。 正如第二章介绍,大多数举办女性就业支援讲座的组织在招募对象时都会使用“工作上有烦恼,生活上有困难的女性”这一描述。这些组织可能试图通过“工作烦恼与生活困难”,来发掘用“贫困”无法涵盖的、被隐藏的困难人群。 更进一步的,本书还试图将女性深陷工作与生活困难的现实归结为社会结构上的问题。 就业冰河期导致了就业困难、雇佣非正式化和过劳的蔓延,这种情况又使女性不得不依附于家庭,从而引发各种问题,使得“雇佣”和“家庭”的包容度到达了临界点。在工作与生活困难的背景之下,女性自己可能已经察觉到了这些问题。 此外,本书还指出了青年女性被紧紧追逼的背景之下,举全国之力应对少子化和促进女性活跃的趋势。只要走出家门就非常容易陷入贫困的境地始终没变过,但现在的青年女性却要在“一亿总活跃”的呼声中满足人们“工作并生儿育女”的要求。 或许有人认为,担心国家政策会影响到个人观念和婚育等私人领域的想法是杞人忧天。当然,现在也存在无论社会风向如何,依旧选择做“单身女王”的女性。但大多数接受采访的青年单身女性从未主动选择过非正式/单身/无子。从她们屡屡提及婚育压力、对将来的不安和无法为社会做贡献的焦虑这一现象中,足以看出这个事实。她们为无法工作并生儿育女而自责,情绪低落不已。那不仅仅是由雇佣和家庭关系引发的、自身有意识的生存困难,而是“像空气般无味透明的生存困难”。 身在社会之中,却感到像空气般无味透明的生存困难的人,恐怕不只是青年女性。 当今世界,没有在经济(参加工作并纳税)、社会(生儿育女,看护老人)等方面做出“活跃”(为国贡献)的人,都要被贴上“没用”的标签,被迫保持沉默。假设有人想在那个立场上表达“我的痛苦源于社会”,立刻就会遭到围攻。 在差距与割裂不断深化的同时,人们开始关注贫困问题。尤其是近几年,最为积极的政策可能就是解决儿童贫困问题。然而针对通常被认为属于“自身责任”的成人贫困,社会却表现出了严苛的倾向。例如一些市町村行政部门制定了极为严格的生活保障金使用限制,试图筛选出“值得拯救的穷人”。 第三章讲述了在职场遭到霸凌,或是压力过大导致抑郁症发作,换了好几份工作,最后不得不选择以残障身份,才终于能够安心工作的女性故事。归根结底,她是在成了“值得拯救的弱者”之后,才从自身责任的论调中解放了出来。 只要不被认同为“值得拯救的穷人、弱者”,就要被打上“没用”的烙印,被迫付出没完没了的努力。 然而,“值得拯救的穷人、弱者”这个观念非常危险,也极不稳定。人们为了得到这个价值观的认同,不得不暴露在众人的眼皮底下。举个例子。电视节目往往会对处于贫困状态的人进行持有物品检查,并做出“他有这个东西,所以不算贫困”的评价,或是批判一个领取生活保障金的人“竟然做这种事,太不要脸”。有时,连政治家都会站在这种批判的最前沿。 为了保持“值得拯救的穷人、弱者”立场,必须时刻低头乞怜。可是,就算不拿出“健康而文明的最低限度生活”这一《宪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每个人也都有生活的权利。对身陷困境的人提供救济而非怜悯,是国家必须履行的义务。 当今社会究竟是让谁过得更好的社会呢?给别人贴上“没用”的标签并大加批判的人,很可能自己的生存也有困难。 本书反复讲述了因过重劳动而疲惫不堪的人群,霸凌和职权骚扰横行的职场,以及若不拼命工作到身心俱损、若不表现出堪称过剩的活跃就无法被认同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无论他/她多么优秀,都很容易掉队。或许正是每天难以排解的疲劳和苦闷,才转化成了对他人的攻击。 可是,稳定雇佣的数量有限和青年求职困难都不是个人努力不足的缘故,而是社会结构的问题。为改善这种状态,国家究竟做了什么? 可以预见,政府将继续在解决少子化和促进女性活跃的旗号下推出各种政策。可是在正式员工薪资刷新历史纪录的背景之下,雇佣者中非正式雇佣者所占比也刷新了历史纪录。正如上文所述,在《女性活跃促进法》颁布那年,规定派遣劳动者可以无限期派遣的《劳动者派遣法修正案》也同时颁布。 我们恐怕不能忘记,表面看似福音的政策,换个角度看就有可能变成深化割裂、固化差距的始作俑者。 最后,我之所以定下“贫困女子”的标题,也是因为一切工作必须从让“连贫困都无法定义的女性”被大家看到。我认为,这同时也是让“像空气般无味透明的生存困难”被看到。连工作都没有、税都没纳过、婚也没结、孩子都没有??我们不能让这种“像空气般无味透明的生存困难”被归结到自身责任的闭环中。 在重云压境中寻找一线光明——我们不能放弃,要始终争取让每个人都不会感到生存困难 *21世纪女性生存现状实录。现实已分化为两个极端:要么死死抓住高薪岗位一直到身心俱损,要么只能从事一般工作与贫困为邻。 *细思恐极的性别问题寓言。日本女性正在经历的,就是我们即将面对的未来。她可能是你的母亲,妻子,姐妹,女儿,你。 *直面每个人的切肤之痛,敲响社会的警钟。在家庭、职场、社会中穷忙的你,可能正不知不觉地步入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