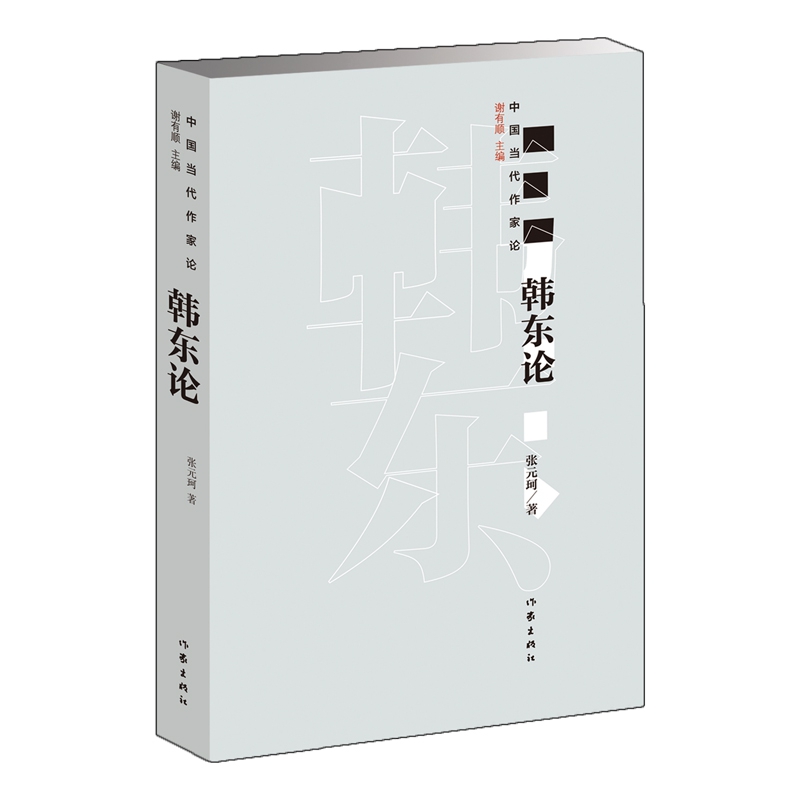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50.00
折扣价: 32.50
折扣购买: 韩东论
ISBN: 9787521204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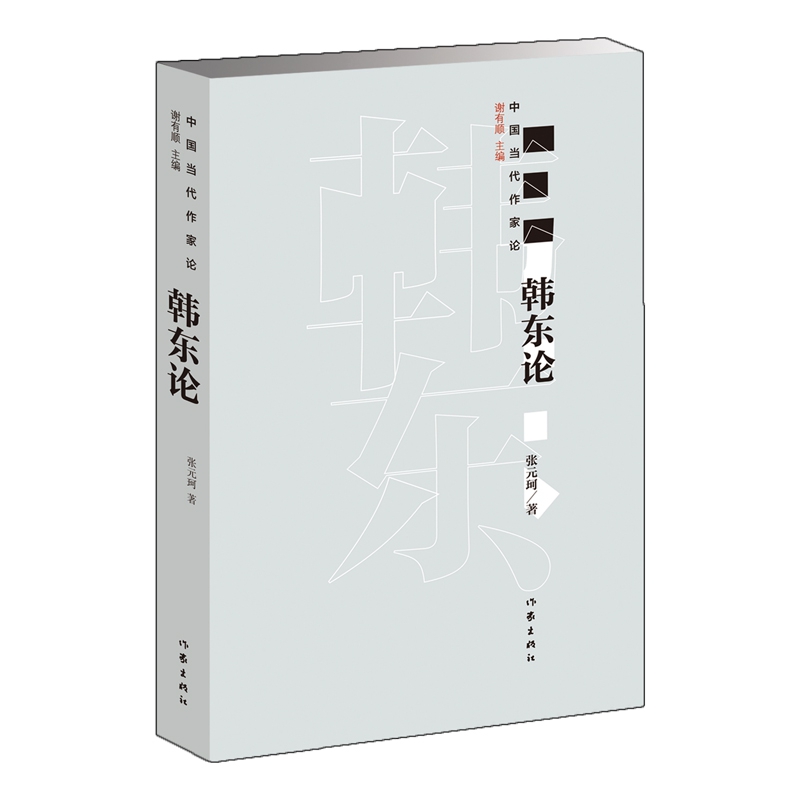
张元珂,1976年生,山东沂南人。文学博士,副研究员,南京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新文学作品版本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工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东岳论丛》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著有《新文学版本丛话》,编选《方方研究资料》,主编《现代作家研究》丛书(共八卷),参编大型丛书《中国现代文学馆经典书系·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一般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面上资助、中国作家协会重点资助课题各一项。现就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兼任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理事、临沂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所逐渐展开的“现代化”图景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有关共同体(国家、民族、集体)和个体(人、人性、人情)的乌托邦式想象,赋予“新时期文学”以异常宽广的实践空间。时至今日,其口号、理念与文学实践业已成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个让人怀念且将之当作珍贵历史遗产予以看待与继承的黄金时代。然而,尤须强调的是,在“新时期文学”源头,诗歌是先于小说、散文、戏剧等文体较早介入时代主潮并对时代问题做出有效呼应的急先锋。从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到“归来”诗人群的大量涌现,都可充分表征诗歌在“文革”结束后的三四年内所体现出的社会“晴雨表”地位。当有着两千余年诗歌传统的中国进入八十年代,创生不足百年的白话新诗再一次取代旧诗,不仅加入到了思想解放和文化创生的阵营,还以容纳中西、除旧创新之势,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诉求和发展蓝图,注入了独属于现代中国诗人的文化基因。他们由对“文革”极权的痛恨与反思,转而对民主、自由的呼唤与想象,既而内化为对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与表达,都在短短的几年间构成中国新诗的血肉肌理。“文革”结束后,一切百废待兴。在文学领域,北岛及其“今天派”接续地下文学流脉,以其带有个体反思与批判性的写作,拉开了“新时期文学”出场的序幕。而以舒婷、江河、顾城、梁小斌为代表的“朦胧诗”诗人光明正大地将大写的人推上前台,并以对爱情、自由、理想等宏大意识的书写和崇高情感的表达而风靡一时。虽也时常遭受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监控甚至惩罚,但诗歌在民间——以高校学生或社会诗歌爱好者自发组织的社团为主——宛若春草,疯狂生长,其发展态势无可遏制。诗歌与时代的血肉关联,诗歌与人性的交融,诗歌与日常的拥抱,在此后以韩东、于坚、杨黎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的实践中更是得到全面而深入的贯彻。他们为复兴“新时期文学”所做的贡献不容低估。历史呼唤诗人,时代需要诗歌;诗人顺应了历史,诗歌融入了时代。一切似乎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诗人也因此成为八十年代最为耀眼的文化符号之一。韩东就是在这样一种高亢的诗歌时代中脱颖而出的。 韩东在八十年代前期的出场、快速扬名,并以其诗歌写作奠定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既是“新时期文学”内在律强力规约与自动筛选的必然产物,也是天时(社会文化的大变革)、地利(身处西安、南京等中国文化中心,拥有便利的诗歌发表渠道)、人和(作家本人的文学天赋、哲学功底、对语言的敏感,以及对时代的聪敏体悟,等等)共同发力的结果。这位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的大学生较早接触北岛及《今天》并深受其影响,既而开始诗歌创作,发表了不少带有“今天派”风格的作品。这些诗歌虽大都为模仿之作,也不免空洞,但一经《青春》杂志发表,便在大学生群体中产生一定影响。因为那时能够在正规刊物上发表诗歌者尚寥寥无几,韩东因其哥哥李潮(时任《青春》编辑)而占得了优先发表作品的先机。但他真正给诗坛带来“地震”式影响力的,则是创作于1983年前后的以《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为代表的一组口语诗,以及顺势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创作理念。待1985年之后,他创作了大量的以日常性、口语化、个人化为主要特征的诗作,正式奠定了其在第三代诗人群中的重要地位。虽然在八十年代后半期标举知识分子精神的诗歌写作也活力正健,但毫无疑问,以反英雄、反传统、反崇高、反等级,要求回归语言与个体的“第三代诗人”的写作,也一样进入文学现场的核心地带。一边是高扬西式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写作,一边是韩东们归入日常与个体的身心表达,作为八十年代两个虽偶有交锋但终归按照各自道路正常发展的流派,都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贡献了崭新经验与美学范式,但从后来的文学发展态势看,后者的文学实践对后世的影响更大。不仅以马原、洪峰、余华、莫言、苏童为代表的当红作家创作的所谓“先锋小说”在其风格与精神谱系上直接继承了韩东们的部分经验(比如“纯文学”、去政治化、语言本体,等等),而且进入九十年代后以韩东、朱文、李冯、徐坤为代表的新生代小说家所从事的回归感性、肉体与日常的写作在其精神渊源、美学实践方面更是与之一脉相承。因此,韩东在八十年代的诗学理念、诗歌创作、出场方式,以及对推进“新时期文学”创生与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都是不可抹杀的。 美国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包括相互关联的四个基本要素:世界、作品、作者(艺术家)、读者(欣赏者)。这一有关文学的定义被世界各国文艺理论界所普遍接受。按照他的定义,作家仅仅是文学四要素之一,或者说,离开其他三要素,文学就不会生成。一般情况下,一位作家很难将四要素完美地结为一体,而总是在其中某一项或几项上难以达及理想效果。似乎只有像胡适、鲁迅这类文学天才方能具备有效整合四要素并能达及理想状态的能力。比如,胡适对自己《尝试集》从初版、再版、三版、四版不间断的修改行为(发挥作者惊人的创造力),对潜在读者的精准定位,对作品臻于经典的努力,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开展的一系列问询、研讨、出版等外部活动,堪称将“四要素”经由组合后发挥至极致的经典案例。可以说,《尝试集》的经典化是由胡适一人来操作完成的。我觉得,与胡适类似,韩东也是这样一位出色的文学活动家,其出色就在于,他也能够依靠自己的才华,动用一切艺术与非艺术的手段,将文学四要素的组合及互融互生效果达及最理想状态。无论在八十年代提出“诗到语言为止”,在九十年代围绕“民间写作”展开一系列争鸣,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提出“中国当代诗歌到现实汉语为止”,以及与杨黎、于坚、王家新、野夫、沈浩波、程永新、史元明、刘涛等学界各层次学者、作家、诗人所展开的针锋相对的文艺论争,还是在大学时参加云帆诗社活动,毕业后创办《老家》《他们》等民刊,在《芙蓉》《今天》《青春》等期刊开设专栏,推介作家,在“橡皮”“他们”等文学网站与众多网友的论战,以及后来围绕“他们”所展开的与众多同仁的文学交往,特别在二十世纪末与一帮新生代作家所开展的文学“断裂”活动,都可充分展现出作为文学活动家的韩东在组织社团活动、开展文学运动方面的先天能力与惊人才华。这些文学活动不止于活动,而总是涉及作家、作品、世界、读者及其复杂关系,其旨归最终指向文学,并由此而生成诸多文学热点、思潮或理论。比如,韩东有关“民间”的阐释、有关“断裂”的宣言、有关诗与真理的论析、有关“70后”诗人及诗歌的推介,等等,对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实践。因为韩东的文学活动总是与当代文化思潮互为关联,因此,考察、研究韩东的文学活动,将是本课题的重要内容之一。 韩东是新时期以来不多见的横跨多时期、多领域、多文类写作,并取得突出成绩的多面手。目前,韩东的文艺创作涉及诗歌、小说、散文、电影、话剧等领域。他经常在这五种艺术形式间来回调换,互审互视,自成一体,且成就卓然。首先,作为当代杰出诗人的代表,韩东不仅是“新时期文学”的引领者、创建者,也是自九十年代以来三十多年间新诗写作群体中最具持续力、最具诗学品质、写作最接近母语本体的代表诗人之一,其四十年不间断的诗歌创作历程,以及围绕汉语与诗歌之间的本体关系所做的一系列理论探索与实践,都值得学界予以全面、系统的研究。其次,作为当代优秀小说家的代表,他在短篇、中篇、长篇创作领域中的接续发力,不仅以其知青小说和情爱小说的持续创作拓展了当代小说的经验领域,并在质量和数量上确证了其在当代小说界的地位和影响力,还以其对小说智性品质的经营、关系诗学的建构、新式叙述语式的实践,以及对小说本体的理论探索(韩东称之为“虚构小说”),大大提高了当代汉语小说的品位与档次。再次,作为当代电影界的新锐导演、演员、编剧,他以“做作品”的理念所执导、饰演和编剧的电影作品,不仅为当代电影注入了诗人气质和异质要素,从而丰富当代中国电影样态,刷新观众观影体验,也为“作家电影”在中国电影界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艺术经验。最后,韩东在散文和剧本写作方面也大有可观。他将日常性、论辩性、哲理性引入散文,特别注重对理与智层面的开掘、表达,从而大大提高了散文写作的内在品格;他对学术体、文论体、随笔体、对话体、日记体、箴言体的多体实践,亦丰富了当代散文写作的文体形态;他对反抒情、冷幽默、代偿性、劝诫性等修辞向度的实践,也显示了其在当代散文创作中的别样风景。近年来,他陆续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舞台剧;近年来,他又尝试话剧创作,其在小说、电影、话剧界的跨体实践或曰实验,作为典范个案,也值得细加研究。总之,韩东出入于各种艺术领域,以自创的文艺理论为指导,以诗为经,以小说为纬,以散文为视界,以电影和剧本写作为补充,建构起了一个立体的、丰富而驳杂的、万花筒般的艺术世界。 文学的外部研究固然不可缺少,也相当重要,弃之,就有失去对现实与历史的发言的能力,就有失语之危险,任何一个有理想的文学研究者当时刻警惕这种危险,但我们从事的是文学研究,而非历史、哲学、社会学或其他什么学,故必须考虑文学的特质及其演进规律,必须有一个谁主谁次的位次考虑。以外部为主,内部为副,必然将文学研究导向非文学研究范畴,发展到极端,就会沦为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其他什么学的附庸。只有以内部研究为主,外部为副,方能避免迷失文学研究的主体性。鉴于此,我觉得,作品是从事文学研究最为核心的要素。因为只有作品才是对作家和历史的最好的也是最终的见证物,其他都是临时的易变的参照物或曰“中间物”。既然作品既是作家主体精神与相应的艺术形式互融互聚后的最终物化产品,也是人、事、物及其关系经由作家审美机制的严格筛选与精神熔铸后的历史遗留物,那么,文学史写作或文学批评也当以此为中心,即以作品为中心,对其内部美学要素予以及时、精准、系统阐释,既而参考作者、读者、世界三要素,以内外互证、彼此映照方式展开对作家论或文学史的写作。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作品一经生成,便脱离作者,进入阅读场,经受各种力量的筛选、考验,并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有益或无益的阐释。但作品实在是一个异常复杂、繁丰、立体的语义世界,故对作品的解读成了文学研究中最难以达及周全的环节。当然,凡是优秀的作品,必然承载了丰富的信息。作品的生命力依赖各时代各层次读者特别是专业读者的创造性阅读与阐释。本书将以对作品(文本)的解读为中心,以外部研究为辅助,不仅对韩东这样一位“新时期文学”孕育的作家做全面、系统研究,还对与韩东密切关联的“新时期文学”“九十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的标志性事件、特征及得失做学理性总结。 作为新诗艺的实践者,韩东除旧布新、开一代诗风的探索与实践,对“第三代诗人”的影响是内在而深远的。而且,其影响不仅限于诗歌界,还影响到了小说界,可以说,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新生代小说”是对以韩东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诗歌精神的延续。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二十世纪初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三大主义”,虽就其影响力而言,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不能与之比肩,但其“文学革命”的逻辑及推动“新时期文学”向前发展的客观效果则是极其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