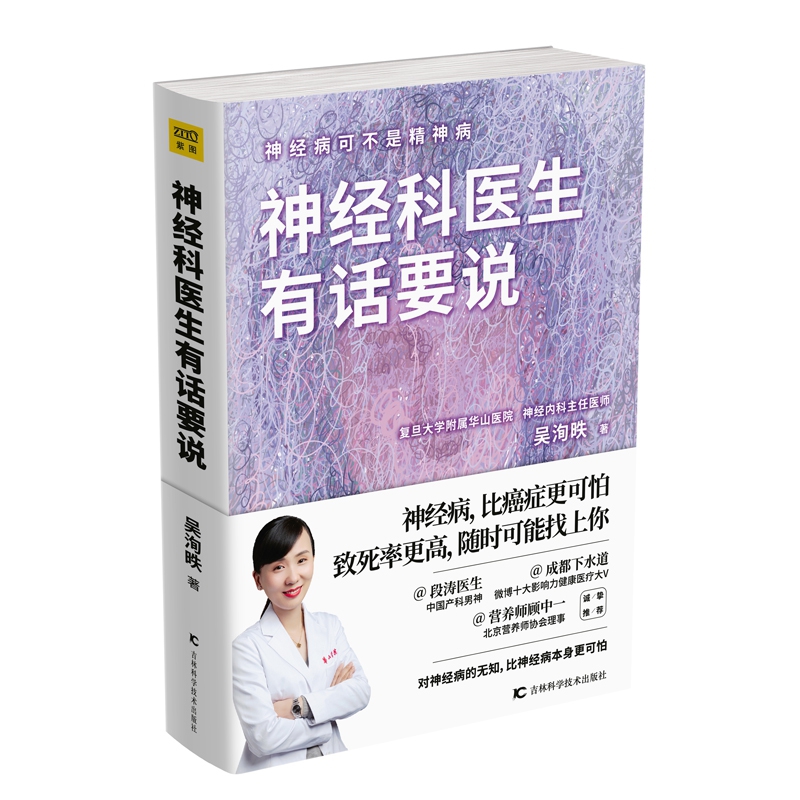
出版社: 吉林科技
原售价: 49.90
折扣价: 29.50
折扣购买: 神经科医生有话要说
ISBN: 97875578498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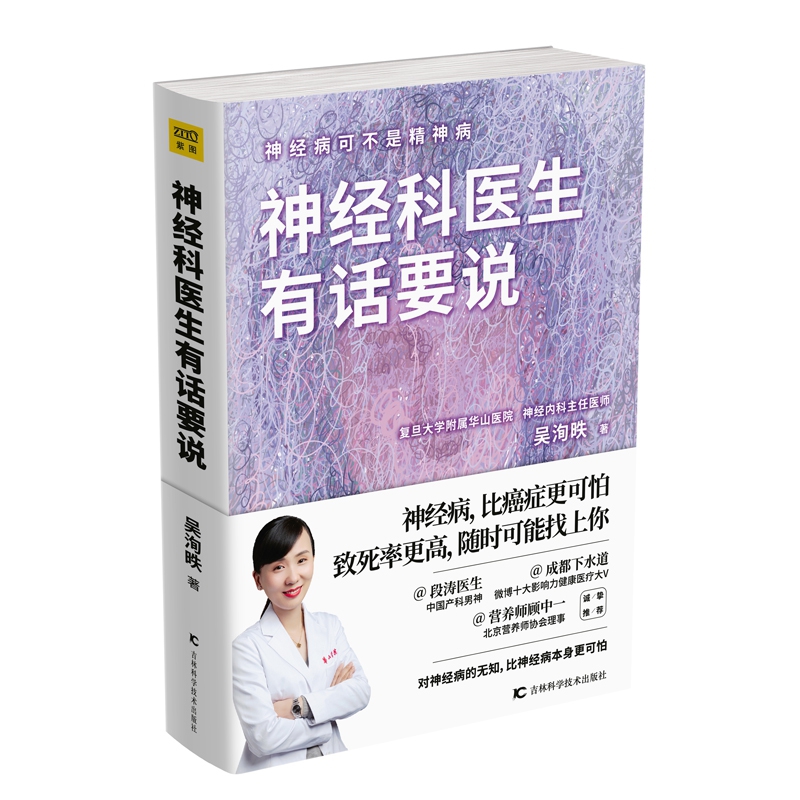
吴洵昳(网名Sherine医生洵)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抗癫痫协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电与癫痫学组委员,上海市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会员。承担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多项国家级与省部级科研基金项目。 她是一个有点儿文艺理想的专职医生,因为从事神经内科专业方向而获赠雅号“神仙姐姐”。具有射手座特有的豪迈奔放,兼备上海人专属的敏感细心。上班时专注于工作,业余时间崇尚生活。
★神经科到底看的是什么病 曾经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很牛的外科医生,就跟那部十分流行的美剧《实习医生格蕾》的女主角一样英姿飒爽、帅气逼人。 结果在进入医学院以后,我慢慢意识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会有差距的。我去外科轮转的时候,跟着带教老师上台,当时跟的第一台手术就是胰腺肿瘤切除手术。现在想来胰腺肿瘤是多大的手术啊,五六个小时就那么连续保持着一个姿势不动,站得我差点儿没背过气去! 直到轮转实习的最后一个月,我来到了神经内科,遇到了一位在我人生之路上起了巨大指导作用的老师。当得知我正在为保送研究生选择专业苦恼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至今都令我印象深刻的话——“你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为什么不考虑选择神经内科呢?难道你不知道‘华山神内’在全中国的影响力吗?”就是这句话彻底改变了我的从业初衷。 很多朋友第一次见我,在得知我的职业是医生以后,总会习惯性地问一句:“你是什么科的医生啊?看什么病?”以前,总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对我而言比较难回答,因为一般人似乎不太可能完全理解神经内科是干什么的。后来被追问的次数多了,再遇上此类问题,我总是一脸坏笑着答道:“我是神经科的,专门看神经病呗!”然后对方就会一脸诡异,故意拖长声音夸张地说:“噢……神经病啊……”然后我常会继续追问一句:“你知道神经科是看啥病的么?”然后得到的回答多半是不怀好意的讪笑:“神经病嘛!” 对,的确是神经病。 其实神经疾病与精神疾病之间确实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这两者都是由于神经系统出了问题,神经系统的中枢就像司令部(比如大脑)。我们业内有句玩笑话说:“脑子有问题,不是神经病就是精神病。”但神经疾病与精神疾病又大有不同,神经疾病多是大脑器质性的问题,也就是属于真的有病;而精神疾病则大多是大脑意识领域出了问题,也就是患者自己不认为自己有病,属于更高层面上的问题。这些也是后来我在多年的临床实践过程中,慢慢琢磨出来的道理。 关于“神经病学的范畴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我将在书中为大家逐一揭晓。 现在如果再有人问我是什么科的,我会昂起头大声地回答:“我是学习脑科的!”国外有本科普书《大脑的奥秘》,写得很炫,卖得也很火——咱就是看大脑的,这回够酷了吧! ★什么病容易夺去那些年轻、美丽的生命 那年我23岁,刚刚进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读研。 开始的几个星期,对于神经病学复杂的定向、定位、定性诊断完全摸不清思路,乃至被上级医生“夸奖”为“完全没有思路”。那时执业医师资格认定制度还没有出台,也还没有资格证书这种东西,研究生入科不久就要开始值班,3个月以后统一像被赶鸭子似的分配到急诊。真心不知道那时还属于“完全没有临床思路”的我,是怎么扛下那一夜夜漫长的急诊、夜班的。 有一天(记得那是我第一次病房值班)临下班前,组里的同事差不多都走光了,我正在和会诊回来的师姐夜巡病房、查看交班记录,值班室的呼叫器响了。夜班护士小易在呼叫器里说:“来了个病人。” 我问:“严重吗?” 小易回答:“还行,你自己过来看看吧!” 还没有独立收治病患经验的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刚从外面跑完一圈儿会诊回来的师姐。她擦了擦★神经科到底看的是什么病 曾经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很牛的外科医生,就跟那部十分流行的美剧《实习医生格蕾》的女主角一样英姿飒爽、帅气逼人。 结果在进入医学院以后,我慢慢意识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会有差距的。我去外科轮转的时候,跟着带教老师上台,当时跟的第一台手术就是胰腺肿瘤切除手术。现在想来胰腺肿瘤是多大的手术啊,五六个小时就那么连续保持着一个姿势不动,站得我差点儿没背过气去! 直到轮转实习的最后一个月,我来到了神经内科,遇到了一位在我人生之路上起了巨大指导作用的老师。当得知我正在为保送研究生选择专业苦恼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至今都令我印象深刻的话——“你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为什么不考虑选择神经内科呢?难道你不知道‘华山神内’在全中国的影响力吗?”就是这句话彻底改变了我的从业初衷。 很多朋友第一次见我,在得知我的职业是医生以后,总会习惯性地问一句:“你是什么科的医生啊?看什么病?”以前,总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对我而言比较难回答,因为一般人似乎不太可能完全理解神经内科是干什么的。后来被追问的次数多了,再遇上此类问题,我总是一脸坏笑着答道:“我是神经科的,专门看神经病呗!”然后对方就会一脸诡异,故意拖长声音夸张地说:“噢……神经病啊……”然后我常会继续追问一句:“你知道神经科是看啥病的么?”然后得到的回答多半是不怀好意的讪笑:“神经病嘛!” 对,的确是神经病。 其实神经疾病与精神疾病之间确实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这两者都是由于神经系统出了问题,神经系统的中枢就像司令部(比如大脑)。我们业内有句玩笑话说:“脑子有问题,不是神经病就是精神病。”但神经疾病与精神疾病又大有不同,神经疾病多是大脑器质性的问题,也就是属于真的有病;而精神疾病则大多是大脑意识领域出了问题,也就是患者自己不认为自己有病,属于更高层面上的问题。这些也是后来我在多年的临床实践过程中,慢慢琢磨出来的道理。 关于“神经病学的范畴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我将在书中为大家逐一揭晓。 现在如果再有人问我是什么科的,我会昂起头大声地回答:“我是学习脑科的!”国外有本科普书《大脑的奥秘》,写得很炫,卖得也很火——咱就是看大脑的,这回够酷了吧! ★什么病容易夺去那些年轻、美丽的生命 那年我23岁,刚刚进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读研。 开始的几个星期,对于神经病学复杂的定向、定位、定性诊断完全摸不清思路,乃至被上级医生“夸奖”为“完全没有思路”。那时执业医师资格认定制度还没有出台,也还没有资格证书这种东西,研究生入科不久就要开始值班,3个月以后统一像被赶鸭子似的分配到急诊。真心不知道那时还属于“完全没有临床思路”的我,是怎么扛下那一夜夜漫长的急诊、夜班的。 有一天(记得那是我第一次病房值班)临下班前,组里的同事差不多都走光了,我正在和会诊回来的师姐夜巡病房、查看交班记录,值班室的呼叫器响了。夜班护士小易在呼叫器里说:“来了个病人。” 我问:“严重吗?” 小易回答:“还行,你自己过来看看吧!” 还没有独立收治病患经验的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刚从外面跑完一圈儿会诊回来的师姐。她擦了擦★神经科到底看的是什么病 曾经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很牛的外科医生,就跟那部十分流行的美剧《实习医生格蕾》的女主角一样英姿飒爽、帅气逼人。 结果在进入医学院以后,我慢慢意识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会有差距的。我去外科轮转的时候,跟着带教老师上台,当时跟的第一台手术就是胰腺肿瘤切除手术。现在想来胰腺肿瘤是多大的手术啊,五六个小时就那么连续保持着一个姿势不动,站得我差点儿没背过气去! 直到轮转实习的最后一个月,我来到了神经内科,遇到了一位在我人生之路上起了巨大指导作用的老师。当得知我正在为保送研究生选择专业苦恼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至今都令我印象深刻的话——“你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为什么不考虑选择神经内科呢?难道你不知道‘华山神内’在全中国的影响力吗?”就是这句话彻底改变了我的从业初衷。 很多朋友第一次见我,在得知我的职业是医生以后,总会习惯性地问一句:“你是什么科的医生啊?看什么病?”以前,总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对我而言比较难回答,因为一般人似乎不太可能完全理解神经内科是干什么的。后来被追问的次数多了,再遇上此类问题,我总是一脸坏笑着答道:“我是神经科的,专门看神经病呗!”然后对方就会一脸诡异,故意拖长声音夸张地说:“噢……神经病啊……”然后我常会继续追问一句:“你知道神经科是看啥病的么?”然后得到的回答多半是不怀好意的讪笑:“神经病嘛!” 对,的确是神经病。 其实神经疾病与精神疾病之间确实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这两者都是由于神经系统出了问题,神经系统的中枢就像司令部(比如大脑)。我们业内有句玩笑话说:“脑子有问题,不是神经病就是精神病。”但神经疾病与精神疾病又大有不同,神经疾病多是大脑器质性的问题,也就是属于真的有病;而精神疾病则大多是大脑意识领域出了问题,也就是患者自己不认为自己有病,属于更高层面上的问题。这些也是后来我在多年的临床实践过程中,慢慢琢磨出来的道理。 关于“神经病学的范畴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我将在书中为大家逐一揭晓。 现在如果再有人问我是什么科的,我会昂起头大声地回答:“我是学习脑科的!”国外有本科普书《大脑的奥秘》,写得很炫,卖得也很火——咱就是看大脑的,这回够酷了吧! ★什么病容易夺去那些年轻、美丽的生命 那年我23岁,刚刚进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读研。 开始的几个星期,对于神经病学复杂的定向、定位、定性诊断完全摸不清思路,乃至被上级医生“夸奖”为“完全没有思路”。那时执业医师资格认定制度还没有出台,也还没有资格证书这种东西,研究生入科不久就要开始值班,3个月以后统一像被赶鸭子似的分配到急诊。真心不知道那时还属于“完全没有临床思路”的我,是怎么扛下那一夜夜漫长的急诊、夜班的。 有一天(记得那是我第一次病房值班)临下班前,组里的同事差不多都走光了,我正在和会诊回来的师姐夜巡病房、查看交班记录,值班室的呼叫器响了。夜班护士小易在呼叫器里说:“来了个病人。” 我问:“严重吗?” 小易回答:“还行,你自己过来看看吧!” 还没有独立收治病患经验的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刚从外面跑完一圈儿会诊回来的师姐。她擦了擦★神经科到底看的是什么病 曾经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很牛的外科医生,就跟那部十分流行的美剧《实习医生格蕾》的女主角一样英姿飒爽、帅气逼人。 结果在进入医学院以后,我慢慢意识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会有差距的。我去外科轮转的时候,跟着带教老师上台,当时跟的第一台手术就是胰腺肿瘤切除手术。现在想来胰腺肿瘤是多大的手术啊,五六个小时就那么连续保持着一个姿势不动,站得我差点儿没背过气去! 直到轮转实习的最后一个月,我来到了神经内科,遇到了一位在我人生之路上起了巨大指导作用的老师。当得知我正在为保送研究生选择专业苦恼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至今都令我印象深刻的话——“你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为什么不考虑选择神经内科呢?难道你不知道‘华山神内’在全中国的影响力吗?”就是这句话彻底改变了我的从业初衷。 很多朋友第一次见我,在得知我的职业是医生以后,总会习惯性地问一句:“你是什么科的医生啊?看什么病?”以前,总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对我而言比较难回答,因为一般人似乎不太可能完全理解神经内科是干什么的。后来被追问的次数多了,再遇上此类问题,我总是一脸坏笑着答道:“我是神经科的,专门看神经病呗!”然后对方就会一脸诡异,故意拖长声音夸张地说:“噢……神经病啊……”然后我常会继续追问一句:“你知道神经科是看啥病的么?”然后得到的回答多半是不怀好意的讪笑:“神经病嘛!” 对,的确是神经病。 其实神经疾病与精神疾病之间确实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这两者都是由于神经系统出了问题,神经系统的中枢就像司令部(比如大脑)。我们业内有句玩笑话说:“脑子有问题,不是神经病就是精神病。”但神经疾病与精神疾病又大有不同,神经疾病多是大脑器质性的问题,也就是属于真的有病;而精神疾病则大多是大脑意识领域出了问题,也就是患者自己不认为自己有病,属于更高层面上的问题。这些也是后来我在多年的临床实践过程中,慢慢琢磨出来的道理。 关于“神经病学的范畴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我将在书中为大家逐一揭晓。 现在如果再有人问我是什么科的,我会昂起头大声地回答:“我是学习脑科的!”国外有本科普书《大脑的奥秘》,写得很炫,卖得也很火——咱就是看大脑的,这回够酷了吧! ★什么病容易夺去那些年轻、美丽的生命 那年我23岁,刚刚进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读研。 开始的几个星期,对于神经病学复杂的定向、定位、定性诊断完全摸不清思路,乃至被上级医生“夸奖”为“完全没有思路”。那时执业医师资格认定制度还没有出台,也还没有资格证书这种东西,研究生入科不久就要开始值班,3个月以后统一像被赶鸭子似的分配到急诊。真心不知道那时还属于“完全没有临床思路”的我,是怎么扛下那一夜夜漫长的急诊、夜班的。 有一天(记得那是我第一次病房值班)临下班前,组里的同事差不多都走光了,我正在和会诊回来的师姐夜巡病房、查看交班记录,值班室的呼叫器响了。夜班护士小易在呼叫器里说:“来了个病人。” 我问:“严重吗?” 小易回答:“还行,你自己过来看看吧!” 还没有独立收治病患经验的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刚从外面跑完一圈儿会诊回来的师姐。她擦了擦脸颊边细小的汗珠,对我淡淡地说了句:“走吧。” 34号病床边坐着两个安静的年轻人——一个高瘦白净的男孩儿和一个文弱秀气的女孩儿。见我们走近,女孩儿把急诊室病历递了过来:“医生,他是病人。” 我看了一眼病历首页,上面写着年龄是28岁。职业一栏填着“中国科学院脑科学研究所博士”。看到这几个字,一股崇敬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中科院一直是我想象中高手林立、秩序井然的神圣宝地,“做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也是我从小时候起就常常挂在嘴边,却又遥不可及的崇高理想之一。 见师姐使了个“你先上”的眼色,我就开始询问男孩儿小亮(文中出现病人均为化名)的病情。女孩儿是小亮的女朋友,她说他前一阵刚刚做完实验研究,写完毕业论文。研究的结果很理想,论文也写得很漂亮,其中部分研究成果还引起了中科院领导的关注,并被推荐去申报了奖项。小亮也因此获得了导师的青睐,并被推荐毕业以后继续留在中科院脑科所工作。女孩儿是生物工程专业硕士毕业,也刚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工作,如果顺利,他们俩打算在不久之后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人生的航船正在扬帆,一切似乎都在顺利地进行着,未来在他们的憧憬之中慢慢变得明晰、美好起来。 可能是之前那段时间太拼命,在接连得到这么多好消息后,轻松下来的小亮反而激动得几天几夜都无法入睡。“那天是周末,他们所里还组织了球赛,”女孩儿说,“我让他歇歇别去了,结果他还是去了,他说自己是球队的主力。那天下午下了场大雨,估计他是淋坏了。” 淋雨回来的小亮觉得头痛,起初以为是感冒,吃了点儿药,并没有太在意。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小亮感觉头痛得更厉害了,眼睛看东西也出现了重影。一量体温,竟然烧到了39℃,然后就被女朋友逼着来看病。 一直以来小亮都十分优秀。他来自北方的一个小县城,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再到中科院,总是很努力,也一直都是父母和家人的骄傲。他的家境并不算富裕,父母用微薄的工资支持着他一路读到了博士。 “等我工作了,一定要好好孝敬我爸妈。”小亮笑着说。他的声音有些嘶哑,笑起来显得有点儿吃力,面颊部明显不对称。 “吃东西呛么?”我问。 “有点儿吧。”小亮说。 之后在师姐的指导下,我给他做了详细的体格检查,嘱咐小亮躺下休息,又安慰了两个年轻人几句,便打算和师姐一道回去写病历。 这时,女孩儿问我:“他的病要紧吗?” “没事儿,我们这儿的神经科是最好的,你要有信心。”我冲她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谢谢!”女孩儿笑了。 回到值班室已经是下午5点40分了,师姐开始忙活着打电话订外卖,说是第一次和我搭班,要请我吃饭。见我皱着眉、咬着笔杆在病历纸上胡乱写画着,师姐便问我对小亮病情的看法。我说:“貌似不太好办。” “怎么个不好办?” “视物模糊、面瘫、构音障碍,疑似出现病理反射,从体征上看范围很广,又全在脑干,整个发病过程很急,又发热又头痛,像是炎症。” 虽然是第一次分析这么棘手的病例,在师姐面前,我还是笃定而积极地表述了看法。 “分析得不错啊,”师姐乐了,“一会儿咱先吃饭,吃完了准备挑灯夜战!” “好!” 我们俩摊开送来的外卖开始狂吃,填饱肚子后又一起在灯下讨论着病例,直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查房时,上级脸颊边细小的汗珠,对我淡淡地说了句:“走吧。” 34号病床边坐着两个安静的年轻人——一个高瘦白净的男孩儿和一个文弱秀气的女孩儿。见我们走近,女孩儿把急诊室病历递了过来:“医生,他是病人。” 我看了一眼病历首页,上面写着年龄是28岁。职业一栏填着“中国科学院脑科学研究所博士”。看到这几个字,一股崇敬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中科院一直是我想象中高手林立、秩序井然的神圣宝地,“做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也是我从小时候起就常常挂在嘴边,却又遥不可及的崇高理想之一。 见师姐使了个“你先上”的眼色,我就开始询问男孩儿小亮(文中出现病人均为化名)的病情。女孩儿是小亮的女朋友,她说他前一阵刚刚做完实验研究,写完毕业论文。研究的结果很理想,论文也写得很漂亮,其中部分研究成果还引起了中科院领导的关注,并被推荐去申报了奖项。小亮也因此获得了导师的青睐,并被推荐毕业以后继续留在中科院脑科所工作。女孩儿是生物工程专业硕士毕业,也刚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工作,如果顺利,他们俩打算在不久之后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人生的航船正在扬帆,一切似乎都在顺利地进行着,未来在他们的憧憬之中慢慢变得明晰、美好起来。 可能是之前那段时间太拼命,在接连得到这么多好消息后,轻松下来的小亮反而激动得几天几夜都无法入睡。“那天是周末,他们所里还组织了球赛,”女孩儿说,“我让他歇歇别去了,结果他还是去了,他说自己是球队的主力。那天下午下了场大雨,估计他是淋坏了。” 淋雨回来的小亮觉得头痛,起初以为是感冒,吃了点儿药,并没有太在意。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小亮感觉头痛得更厉害了,眼睛看东西也出现了重影。一量体温,竟然烧到了39℃,然后就被女朋友逼着来看病。 一直以来小亮都十分优秀。他来自北方的一个小县城,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再到中科院,总是很努力,也一直都是父母和家人的骄傲。他的家境并不算富裕,父母用微薄的工资支持着他一路读到了博士。 “等我工作了,一定要好好孝敬我爸妈。”小亮笑着说。他的声音有些嘶哑,笑起来显得有点儿吃力,面颊部明显不对称。 “吃东西呛么?”我问。 “有点儿吧。”小亮说。 之后在师姐的指导下,我给他做了详细的体格检查,嘱咐小亮躺下休息,又安慰了两个年轻人几句,便打算和师姐一道回去写病历。 这时,女孩儿问我:“他的病要紧吗?” “没事儿,我们这儿的神经科是最好的,你要有信心。”我冲她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谢谢!”女孩儿笑了。 回到值班室已经是下午5点40分了,师姐开始忙活着打电话订外卖,说是第一次和我搭班,要请我吃饭。见我皱着眉、咬着笔杆在病历纸上胡乱写画着,师姐便问我对小亮病情的看法。我说:“貌似不太好办。” “怎么个不好办?” “视物模糊、面瘫、构音障碍,疑似出现病理反射,从体征上看范围很广,又全在脑干,整个发病过程很急,又发热又头痛,像是炎症。” 虽然是第一次分析这么棘手的病例,在师姐面前,我还是笃定而积极地表述了看法。 “分析得不错啊,”师姐乐了,“一会儿咱先吃饭,吃完了准备挑灯夜战!” “好!” 我们俩摊开送来的外卖开始狂吃,填饱肚子后又一起在灯下讨论着病例,直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查房时,上级脸颊边细小的汗珠,对我淡淡地说了句:“走吧。” 34号病床边坐着两个安静的年轻人——一个高瘦白净的男孩儿和一个文弱秀气的女孩儿。见我们走近,女孩儿把急诊室病历递了过来:“医生,他是病人。” 我看了一眼病历首页,上面写着年龄是28岁。职业一栏填着“中国科学院脑科学研究所博士”。看到这几个字,一股崇敬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中科院一直是我想象中高手林立、秩序井然的神圣宝地,“做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也是我从小时候起就常常挂在嘴边,却又遥不可及的崇高理想之一。 见师姐使了个“你先上”的眼色,我就开始询问男孩儿小亮(文中出现病人均为化名)的病情。女孩儿是小亮的女朋友,她说他前一阵刚刚做完实验研究,写完毕业论文。研究的结果很理想,论文也写得很漂亮,其中部分研究成果还引起了中科院领导的关注,并被推荐去申报了奖项。小亮也因此获得了导师的青睐,并被推荐毕业以后继续留在中科院脑科所工作。女孩儿是生物工程专业硕士毕业,也刚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工作,如果顺利,他们俩打算在不久之后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人生的航船正在扬帆,一切似乎都在顺利地进行着,未来在他们的憧憬之中慢慢变得明晰、美好起来。 可能是之前那段时间太拼命,在接连得到这么多好消息后,轻松下来的小亮反而激动得几天几夜都无法入睡。“那天是周末,他们所里还组织了球赛,”女孩儿说,“我让他歇歇别去了,结果他还是去了,他说自己是球队的主力。那天下午下了场大雨,估计他是淋坏了。” 淋雨回来的小亮觉得头痛,起初以为是感冒,吃了点儿药,并没有太在意。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小亮感觉头痛得更厉害了,眼睛看东西也出现了重影。一量体温,竟然烧到了39℃,然后就被女朋友逼着来看病。 一直以来小亮都十分优秀。他来自北方的一个小县城,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再到中科院,总是很努力,也一直都是父母和家人的骄傲。他的家境并不算富裕,父母用微薄的工资支持着他一路读到了博士。 “等我工作了,一定要好好孝敬我爸妈。”小亮笑着说。他的声音有些嘶哑,笑起来显得有点儿吃力,面颊部明显不对称。 “吃东西呛么?”我问。 “有点儿吧。”小亮说。 之后在师姐的指导下,我给他做了详细的体格检查,嘱咐小亮躺下休息,又安慰了两个年轻人几句,便打算和师姐一道回去写病历。 这时,女孩儿问我:“他的病要紧吗?” “没事儿,我们这儿的神经科是最好的,你要有信心。”我冲她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谢谢!”女孩儿笑了。 回到值班室已经是下午5点40分了,师姐开始忙活着打电话订外卖,说是第一次和我搭班,要请我吃饭。见我皱着眉、咬着笔杆在病历纸上胡乱写画着,师姐便问我对小亮病情的看法。我说:“貌似不太好办。” “怎么个不好办?” “视物模糊、面瘫、构音障碍,疑似出现病理反射,从体征上看范围很广,又全在脑干,整个发病过程很急,又发热又头痛,像是炎症。” 虽然是第一次分析这么棘手的病例,在师姐面前,我还是笃定而积极地表述了看法。 “分析得不错啊,”师姐乐了,“一会儿咱先吃饭,吃完了准备挑灯夜战!” “好!” 我们俩摊开送来的外卖开始狂吃,填饱肚子后又一起在灯下讨论着病例,直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查房时,上级脸颊边细小的汗珠,对我淡淡地说了句:“走吧。” 34号病床边坐着两个安静的年轻人——一个高瘦白净的男孩儿和一个文弱秀气的女孩儿。见我们走近,女孩儿把急诊室病历递了过来:“医生,他是病人。” 我看了一眼病历首页,上面写着年龄是28岁。职业一栏填着“中国科学院脑科学研究所博士”。看到这几个字,一股崇敬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中科院一直是我想象中高手林立、秩序井然的神圣宝地,“做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也是我从小时候起就常常挂在嘴边,却又遥不可及的崇高理想之一。 见师姐使了个“你先上”的眼色,我就开始询问男孩儿小亮(文中出现病人均为化名)的病情。女孩儿是小亮的女朋友,她说他前一阵刚刚做完实验研究,写完毕业论文。研究的结果很理想,论文也写得很漂亮,其中部分研究成果还引起了中科院领导的关注,并被推荐去申报了奖项。小亮也因此获得了导师的青睐,并被推荐毕业以后继续留在中科院脑科所工作。女孩儿是生物工程专业硕士毕业,也刚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工作,如果顺利,他们俩打算在不久之后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人生的航船正在扬帆,一切似乎都在顺利地进行着,未来在他们的憧憬之中慢慢变得明晰、美好起来。 可能是之前那段时间太拼命,在接连得到这么多好消息后,轻松下来的小亮反而激动得几天几夜都无法入睡。“那天是周末,他们所里还组织了球赛,”女孩儿说,“我让他歇歇别去了,结果他还是去了,他说自己是球队的主力。那天下午下了场大雨,估计他是淋坏了。” 淋雨回来的小亮觉得头痛,起初以为是感冒,吃了点儿药,并没有太在意。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小亮感觉头痛得更厉害了,眼睛看东西也出现了重影。一量体温,竟然烧到了39℃,然后就被女朋友逼着来看病。 一直以来小亮都十分优秀。他来自北方的一个小县城,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再到中科院,总是很努力,也一直都是父母和家人的骄傲。他的家境并不算富裕,父母用微薄的工资支持着他一路读到了博士。 “等我工作了,一定要好好孝敬我爸妈。”小亮笑着说。他的声音有些嘶哑,笑起来显得有点儿吃力,面颊部明显不对称。 “吃东西呛么?”我问。 “有点儿吧。”小亮说。 之后在师姐的指导下,我给他做了详细的体格检查,嘱咐小亮躺下休息,又安慰了两个年轻人几句,便打算和师姐一道回去写病历。 这时,女孩儿问我:“他的病要紧吗?” “没事儿,我们这儿的神经科是最好的,你要有信心。”我冲她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谢谢!”女孩儿笑了。 回到值班室已经是下午5点40分了,师姐开始忙活着打电话订外卖,说是第一次和我搭班,要请我吃饭。见我皱着眉、咬着笔杆在病历纸上胡乱写画着,师姐便问我对小亮病情的看法。我说:“貌似不太好办。” “怎么个不好办?” “视物模糊、面瘫、构音障碍,疑似出现病理反射,从体征上看范围很广,又全在脑干,整个发病过程很急,又发热又头痛,像是炎症。” 虽然是第一次分析这么棘手的病例,在师姐面前,我还是笃定而积极地表述了看法。 “分析得不错啊,”师姐乐了,“一会儿咱先吃饭,吃完了准备挑灯夜战!” “好!” 我们俩摊开送来的外卖开始狂吃,填饱肚子后又一起在灯下讨论着病例,直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查房时,上级医生为小亮定下了脑干脑炎的初步诊断。听到我景仰的主治医生黄老师说出和我在病历里相似的定位、定性诊断结果,我高兴地冲师姐眨了眨眼。现在的我属于略有思路,而不再是完全没有思路了。 治疗方面,黄老师打算给小亮用小剂量的激素,再辅以丙种球蛋白冲击疗法。查房结束后,黄老师让我和病人及家属谈谈丙种球蛋白的问题。 我对女孩儿说:“丙种球蛋白很贵。” 她问:“要多少钱?效果好吗?” “一个疗程2万左右吧!丙种球蛋白的效果,会因个人体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我实事求是地说,“激素马上就可以用,但是你最好先问问他爸妈的意见。” 下午查房,女孩儿拉我到一边儿说:“小亮爸妈说了,只要能治好他的病,花多少钱都行。” “好,明天就给他用药。”我说。 她轻轻说了声“好的”,末了又说:“你们要是有啥好药都给他用上吧,他爸妈就这么一个儿子,再穷也会救他的。” 后面几天,也许是丙种球蛋白和激素加脱水剂起了点儿作用,小亮的头痛和发热症状有了些缓解。但是头颅MRI(磁共振成像)结果显示,脑干上有些许异常信号。 “没错,应该是脑干脑炎。”黄老师胸有成竹。 我悄悄来到34号病床边,问小亮感觉怎样。 “好点儿了。”他笑着说。但是我觉得他的笑容似乎更僵硬了些。 “好好休息。”我安慰他说。 第五天早上查房,小亮说眼睛不舒服,我为他做了体格检查,发现他的眼球固定了。下午他女朋友跑来说,小亮感觉胸闷,透不过气。血气分析提示氧分压下降,师姐说:“复查个片子吧!” 复查结果显示脑干上高信号的东西变多了,如点点雪花一般。 “会不会是渗血?”我问。 黄老师嘱咐:“明天把激素停了吧!” 那天夜班的护士又是小易,我嘱咐她,要是小亮有什么变化,及时发消息给我。晚上11点多钟,小易给我发来了短信:“小亮突然血氧饱和度下降,意识不清,已插管。” 第六天查房的时候,小亮已经插着气管昏迷不醒了。女孩儿眼圈红红地说:“昨天晚上一下子就不好了。”望着病床上戴着呼吸机,胸廓随着机器频率规律起伏着的小亮,望着他那苍白的脸,我也很难过,但又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面前这个无助的女孩儿。 “告诉他父母了吗?”我问。 “嗯,他们下午应该就会赶来的。”她哽咽着说。 当天下午6点,小亮的父母赶了来,我向他们仔细说明了病情。这对老实本分的老人抹着眼泪说:“医生,你们看吧,该咋样就咋样,俺们也不懂。”那时我忽然觉得,之前我对小亮女朋友说的“没事,我们这儿的神经科是最好的”那句话,好像说得太乐观,也太早了。 后来,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作为一名身处临床一线的医生,永远都不要对你经手病人的病情进展表现得过于自信,而应当时刻注意各种潜藏的、可能的风险。 又过了几日,已经做了气管切开的小亮体温仍然在一路飙升,各种抗生素好像在他身上都失去了效果。小亮的父母话不多,一直都很沉默。 黄老师分析:“脑干脑炎往往要比普通的脑炎更加凶险。脑干体积虽然小,但却是整个大脑的中枢司令部,容不得半点儿差池。” 这让我想起大学邻班的一个男生小赵,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小伙子,和小亮一样努力,成绩优异。他是我们年级的学生会干事,总是很热心地为同学们服务。毕业前夕,学校组织文艺会演,他去帮忙搭建场医生为小亮定下了脑干脑炎的初步诊断。听到我景仰的主治医生黄老师说出和我在病历里相似的定位、定性诊断结果,我高兴地冲师姐眨了眨眼。现在的我属于略有思路,而不再是完全没有思路了。 治疗方面,黄老师打算给小亮用小剂量的激素,再辅以丙种球蛋白冲击疗法。查房结束后,黄老师让我和病人及家属谈谈丙种球蛋白的问题。 我对女孩儿说:“丙种球蛋白很贵。” 她问:“要多少钱?效果好吗?” “一个疗程2万左右吧!丙种球蛋白的效果,会因个人体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我实事求是地说,“激素马上就可以用,但是你最好先问问他爸妈的意见。” 下午查房,女孩儿拉我到一边儿说:“小亮爸妈说了,只要能治好他的病,花多少钱都行。” “好,明天就给他用药。”我说。 她轻轻说了声“好的”,末了又说:“你们要是有啥好药都给他用上吧,他爸妈就这么一个儿子,再穷也会救他的。” 后面几天,也许是丙种球蛋白和激素加脱水剂起了点儿作用,小亮的头痛和发热症状有了些缓解。但是头颅MRI(磁共振成像)结果显示,脑干上有些许异常信号。 “没错,应该是脑干脑炎。”黄老师胸有成竹。 我悄悄来到34号病床边,问小亮感觉怎样。 “好点儿了。”他笑着说。但是我觉得他的笑容似乎更僵硬了些。 “好好休息。”我安慰他说。 第五天早上查房,小亮说眼睛不舒服,我为他做了体格检查,发现他的眼球固定了。下午他女朋友跑来说,小亮感觉胸闷,透不过气。血气分析提示氧分压下降,师姐说:“复查个片子吧!” 复查结果显示脑干上高信号的东西变多了,如点点雪花一般。 “会不会是渗血?”我问。 黄老师嘱咐:“明天把激素停了吧!” 那天夜班的护士又是小易,我嘱咐她,要是小亮有什么变化,及时发消息给我。晚上11点多钟,小易给我发来了短信:“小亮突然血氧饱和度下降,意识不清,已插管。” 第六天查房的时候,小亮已经插着气管昏迷不醒了。女孩儿眼圈红红地说:“昨天晚上一下子就不好了。”望着病床上戴着呼吸机,胸廓随着机器频率规律起伏着的小亮,望着他那苍白的脸,我也很难过,但又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面前这个无助的女孩儿。 “告诉他父母了吗?”我问。 “嗯,他们下午应该就会赶来的。”她哽咽着说。 当天下午6点,小亮的父母赶了来,我向他们仔细说明了病情。这对老实本分的老人抹着眼泪说:“医生,你们看吧,该咋样就咋样,俺们也不懂。”那时我忽然觉得,之前我对小亮女朋友说的“没事,我们这儿的神经科是最好的”那句话,好像说得太乐观,也太早了。 后来,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作为一名身处临床一线的医生,永远都不要对你经手病人的病情进展表现得过于自信,而应当时刻注意各种潜藏的、可能的风险。 又过了几日,已经做了气管切开的小亮体温仍然在一路飙升,各种抗生素好像在他身上都失去了效果。小亮的父母话不多,一直都很沉默。 黄老师分析:“脑干脑炎往往要比普通的脑炎更加凶险。脑干体积虽然小,但却是整个大脑的中枢司令部,容不得半点儿差池。” 这让我想起大学邻班的一个男生小赵,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小伙子,和小亮一样努力,成绩优异。他是我们年级的学生会干事,总是很热心地为同学们服务。毕业前夕,学校组织文艺会演,他去帮忙搭建场医生为小亮定下了脑干脑炎的初步诊断。听到我景仰的主治医生黄老师说出和我在病历里相似的定位、定性诊断结果,我高兴地冲师姐眨了眨眼。现在的我属于略有思路,而不再是完全没有思路了。 治疗方面,黄老师打算给小亮用小剂量的激素,再辅以丙种球蛋白冲击疗法。查房结束后,黄老师让我和病人及家属谈谈丙种球蛋白的问题。 我对女孩儿说:“丙种球蛋白很贵。” 她问:“要多少钱?效果好吗?” “一个疗程2万左右吧!丙种球蛋白的效果,会因个人体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我实事求是地说,“激素马上就可以用,但是你最好先问问他爸妈的意见。” 下午查房,女孩儿拉我到一边儿说:“小亮爸妈说了,只要能治好他的病,花多少钱都行。” “好,明天就给他用药。”我说。 她轻轻说了声“好的”,末了又说:“你们要是有啥好药都给他用上吧,他爸妈就这么一个儿子,再穷也会救他的。” 后面几天,也许是丙种球蛋白和激素加脱水剂起了点儿作用,小亮的头痛和发热症状有了些缓解。但是头颅MRI(磁共振成像)结果显示,脑干上有些许异常信号。 “没错,应该是脑干脑炎。”黄老师胸有成竹。 我悄悄来到34号病床边,问小亮感觉怎样。 “好点儿了。”他笑着说。但是我觉得他的笑容似乎更僵硬了些。 “好好休息。”我安慰他说。 第五天早上查房,小亮说眼睛不舒服,我为他做了体格检查,发现他的眼球固定了。下午他女朋友跑来说,小亮感觉胸闷,透不过气。血气分析提示氧分压下降,师姐说:“复查个片子吧!” 复查结果显示脑干上高信号的东西变多了,如点点雪花一般。 “会不会是渗血?”我问。 黄老师嘱咐:“明天把激素停了吧!” 那天夜班的护士又是小易,我嘱咐她,要是小亮有什么变化,及时发消息给我。晚上11点多钟,小易给我发来了短信:“小亮突然血氧饱和度下降,意识不清,已插管。” 第六天查房的时候,小亮已经插着气管昏迷不醒了。女孩儿眼圈红红地说:“昨天晚上一下子就不好了。”望着病床上戴着呼吸机,胸廓随着机器频率规律起伏着的小亮,望着他那苍白的脸,我也很难过,但又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面前这个无助的女孩儿。 “告诉他父母了吗?”我问。 “嗯,他们下午应该就会赶来的。”她哽咽着说。 当天下午6点,小亮的父母赶了来,我向他们仔细说明了病情。这对老实本分的老人抹着眼泪说:“医生,你们看吧,该咋样就咋样,俺们也不懂。”那时我忽然觉得,之前我对小亮女朋友说的“没事,我们这儿的神经科是最好的”那句话,好像说得太乐观,也太早了。 后来,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作为一名身处临床一线的医生,永远都不要对你经手病人的病情进展表现得过于自信,而应当时刻注意各种潜藏的、可能的风险。 又过了几日,已经做了气管切开的小亮体温仍然在一路飙升,各种抗生素好像在他身上都失去了效果。小亮的父母话不多,一直都很沉默。 黄老师分析:“脑干脑炎往往要比普通的脑炎更加凶险。脑干体积虽然小,但却是整个大脑的中枢司令部,容不得半点儿差池。” 这让我想起大学邻班的一个男生小赵,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小伙子,和小亮一样努力,成绩优异。他是我们年级的学生会干事,总是很热心地为同学们服务。毕业前夕,学校组织文艺会演,他去帮忙搭建场医生为小亮定下了脑干脑炎的初步诊断。听到我景仰的主治医生黄老师说出和我在病历里相似的定位、定性诊断结果,我高兴地冲师姐眨了眨眼。现在的我属于略有思路,而不再是完全没有思路了。 治疗方面,黄老师打算给小亮用小剂量的激素,再辅以丙种球蛋白冲击疗法。查房结束后,黄老师让我和病人及家属谈谈丙种球蛋白的问题。 我对女孩儿说:“丙种球蛋白很贵。” 她问:“要多少钱?效果好吗?” “一个疗程2万左右吧!丙种球蛋白的效果,会因个人体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我实事求是地说,“激素马上就可以用,但是你最好先问问他爸妈的意见。” 下午查房,女孩儿拉我到一边儿说:“小亮爸妈说了,只要能治好他的病,花多少钱都行。” “好,明天就给他用药。”我说。 她轻轻说了声“好的”,末了又说:“你们要是有啥好药都给他用上吧,他爸妈就这么一个儿子,再穷也会救他的。” 后面几天,也许是丙种球蛋白和激素加脱水剂起了点儿作用,小亮的头痛和发热症状有了些缓解。但是头颅MRI(磁共振成像)结果显示,脑干上有些许异常信号。 “没错,应该是脑干脑炎。”黄老师胸有成竹。 我悄悄来到34号病床边,问小亮感觉怎样。 “好点儿了。”他笑着说。但是我觉得他的笑容似乎更僵硬了些。 “好好休息。”我安慰他说。 第五天早上查房,小亮说眼睛不舒服,我为他做了体格检查,发现他的眼球固定了。下午他女朋友跑来说,小亮感觉胸闷,透不过气。血气分析提示氧分压下降,师姐说:“复查个片子吧!” 复查结果显示脑干上高信号的东西变多了,如点点雪花一般。 “会不会是渗血?”我问。 黄老师嘱咐:“明天把激素停了吧!” 那天夜班的护士又是小易,我嘱咐她,要是小亮有什么变化,及时发消息给我。晚上11点多钟,小易给我发来了短信:“小亮突然血氧饱和度下降,意识不清,已插管。” 第六天查房的时候,小亮已经插着气管昏迷不醒了。女孩儿眼圈红红地说:“昨天晚上一下子就不好了。”望着病床上戴着呼吸机,胸廓随着机器频率规律起伏着的小亮,望着他那苍白的脸,我也很难过,但又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面前这个无助的女孩儿。 “告诉他父母了吗?”我问。 “嗯,他们下午应该就会赶来的。”她哽咽着说。 当天下午6点,小亮的父母赶了来,我向他们仔细说明了病情。这对老实本分的老人抹着眼泪说:“医生,你们看吧,该咋样就咋样,俺们也不懂。”那时我忽然觉得,之前我对小亮女朋友说的“没事,我们这儿的神经科是最好的”那句话,好像说得太乐观,也太早了。 后来,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作为一名身处临床一线的医生,永远都不要对你经手病人的病情进展表现得过于自信,而应当时刻注意各种潜藏的、可能的风险。 又过了几日,已经做了气管切开的小亮体温仍然在一路飙升,各种抗生素好像在他身上都失去了效果。小亮的父母话不多,一直都很沉默。 黄老师分析:“脑干脑炎往往要比普通的脑炎更加凶险。脑干体积虽然小,但却是整个大脑的中枢司令部,容不得半点儿差池。” 这让我想起大学邻班的一个男生小赵,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小伙子,和小亮一样努力,成绩优异。他是我们年级的学生会干事,总是很热心地为同学们服务。毕业前夕,学校组织文艺会演,他去帮忙搭建场地,却不小心从新搭的舞台架上摔了下来。当时,他是后脑勺先着地,据说拍了片子显示的是“脑干挫裂伤”。虽然他当即就被送去中山医院抢救,但是没过几天就去世了。 追悼会上,他妈妈好几次哭得昏了过去。我们看着他平日里帅气、白净,如今却水肿不堪的面庞,也都泣不成声。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同龄人的葬礼,而且是曾经那样熟悉的、在我的生活里真实存在过的人。这让我深刻感受到了比参加老年人葬礼来得更加真切的悲痛。 从那时起,我就深刻地明白了“脑干”这个词汇所代表的意义有多重大。看着眼前毫无反应的小亮,再一次证实了“脑干病变”是一个多么严肃而残酷的词汇。 小亮最终还是没能挺过去,在又坚持了几日以后的一个凌晨,他那颗年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母亲和女朋友泣不成声,而他的老父亲在一边默不作声。沉默半晌,他抬头询问黄老师关于小亮的病因以及他的去世,有没有一个最终明确的定论。 黄老师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问小亮的父亲愿不愿意做尸检。如果愿意,神经病理科主任同意亲自给小亮做局部脑组织的病理解剖。由于小亮的病情比较特殊,要想知道他的脑组织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只有病理结果可以为最终的诊断提供依据。若干年前的医患关系不像现在这般势如水火,我记得小亮老实本分的父母商量以后,签字同意了黄老师的尸检建议。 于是第二天,我和师姐跟着黄老师一起去到了神经病理室。我们默默地站成一排,在那里安静地看着解剖教研室请来的老师先做解剖。他用戴着手套的双手小心翼翼地取出小亮的脑组织,再由病理科主任仔细地做薄层切片。解剖专用手术刀一层层地切割着那白花花的脑叶,一直切到脑干的部位开始显现出大片的暗红色出血点。从左侧脑桥至延髓锥体部位,广泛呈现出连续出血性坏死病灶。 “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病理科主任回头对黄老师说。 黄老师点了下头说:“继续做石蜡包埋和染色固定吧!” 听着他们的对话,我感觉我的心随着手术刀的起落变得越来越沉重。那一刀刀仿佛是切在我的心上一般,脑海里不停地思考着同一个问题:这难道真的就是那个年轻博士的脑子么?潜意识里我很难将眼前这堆毫无生命力的组织结构,与那个曾经鲜活的男孩儿的身影联系在一起。 这样想着,我感觉自己的眼眶湿润了。说实话,我打心眼儿里不能接受我的患者在前途一片光明的花样年华里,生命就这样猝然终止了。我偷偷看了一眼师姐,发现她的眼角也是湿湿的。后来小亮的遗体被送去火化,他的父母自始至终也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病例,就这样永远地、深刻地镌进了我的记忆里。 小亮属于典型的“凤凰男”,是家里的独子,是那个并不富裕的家庭获得幸福快乐的唯一希望。且不说培育一个优秀的孩子所需要付出的艰辛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苦痛,他父母那样的年纪也早已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不可能再生一个孩子来弥补丧子之痛。那么,小亮父母的晚年将由谁来照料?老两口又将如何摆脱老年丧子的痛苦? 记得当年参加完小赵同学的追悼会以后,我听说他妈妈后来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与妄想症。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家里门铃一响,她便欢天喜地,以为是她儿子回来了。每次都是小赵的爸爸拿了儿子的死亡证明书出来,她才肯相信她儿子是真的走了——免不了又是失声痛哭。地,却不小心从新搭的舞台架上摔了下来。当时,他是后脑勺先着地,据说拍了片子显示的是“脑干挫裂伤”。虽然他当即就被送去中山医院抢救,但是没过几天就去世了。 追悼会上,他妈妈好几次哭得昏了过去。我们看着他平日里帅气、白净,如今却水肿不堪的面庞,也都泣不成声。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同龄人的葬礼,而且是曾经那样熟悉的、在我的生活里真实存在过的人。这让我深刻感受到了比参加老年人葬礼来得更加真切的悲痛。 从那时起,我就深刻地明白了“脑干”这个词汇所代表的意义有多重大。看着眼前毫无反应的小亮,再一次证实了“脑干病变”是一个多么严肃而残酷的词汇。 小亮最终还是没能挺过去,在又坚持了几日以后的一个凌晨,他那颗年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母亲和女朋友泣不成声,而他的老父亲在一边默不作声。沉默半晌,他抬头询问黄老师关于小亮的病因以及他的去世,有没有一个最终明确的定论。 黄老师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问小亮的父亲愿不愿意做尸检。如果愿意,神经病理科主任同意亲自给小亮做局部脑组织的病理解剖。由于小亮的病情比较特殊,要想知道他的脑组织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只有病理结果可以为最终的诊断提供依据。若干年前的医患关系不像现在这般势如水火,我记得小亮老实本分的父母商量以后,签字同意了黄老师的尸检建议。 于是第二天,我和师姐跟着黄老师一起去到了神经病理室。我们默默地站成一排,在那里安静地看着解剖教研室请来的老师先做解剖。他用戴着手套的双手小心翼翼地取出小亮的脑组织,再由病理科主任仔细地做薄层切片。解剖专用手术刀一层层地切割着那白花花的脑叶,一直切到脑干的部位开始显现出大片的暗红色出血点。从左侧脑桥至延髓锥体部位,广泛呈现出连续出血性坏死病灶。 “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病理科主任回头对黄老师说。 黄老师点了下头说:“继续做石蜡包埋和染色固定吧!” 听着他们的对话,我感觉我的心随着手术刀的起落变得越来越沉重。那一刀刀仿佛是切在我的心上一般,脑海里不停地思考着同一个问题:这难道真的就是那个年轻博士的脑子么?潜意识里我很难将眼前这堆毫无生命力的组织结构,与那个曾经鲜活的男孩儿的身影联系在一起。 这样想着,我感觉自己的眼眶湿润了。说实话,我打心眼儿里不能接受我的患者在前途一片光明的花样年华里,生命就这样猝然终止了。我偷偷看了一眼师姐,发现她的眼角也是湿湿的。后来小亮的遗体被送去火化,他的父母自始至终也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病例,就这样永远地、深刻地镌进了我的记忆里。 小亮属于典型的“凤凰男”,是家里的独子,是那个并不富裕的家庭获得幸福快乐的唯一希望。且不说培育一个优秀的孩子所需要付出的艰辛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苦痛,他父母那样的年纪也早已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不可能再生一个孩子来弥补丧子之痛。那么,小亮父母的晚年将由谁来照料?老两口又将如何摆脱老年丧子的痛苦? 记得当年参加完小赵同学的追悼会以后,我听说他妈妈后来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与妄想症。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家里门铃一响,她便欢天喜地,以为是她儿子回来了。每次都是小赵的爸爸拿了儿子的死亡证明书出来,她才肯相信她儿子是真的走了——免不了又是失声痛哭。地,却不小心从新搭的舞台架上摔了下来。当时,他是后脑勺先着地,据说拍了片子显示的是“脑干挫裂伤”。虽然他当即就被送去中山医院抢救,但是没过几天就去世了。 追悼会上,他妈妈好几次哭得昏了过去。我们看着他平日里帅气、白净,如今却水肿不堪的面庞,也都泣不成声。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同龄人的葬礼,而且是曾经那样熟悉的、在我的生活里真实存在过的人。这让我深刻感受到了比参加老年人葬礼来得更加真切的悲痛。 从那时起,我就深刻地明白了“脑干”这个词汇所代表的意义有多重大。看着眼前毫无反应的小亮,再一次证实了“脑干病变”是一个多么严肃而残酷的词汇。 小亮最终还是没能挺过去,在又坚持了几日以后的一个凌晨,他那颗年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母亲和女朋友泣不成声,而他的老父亲在一边默不作声。沉默半晌,他抬头询问黄老师关于小亮的病因以及他的去世,有没有一个最终明确的定论。 黄老师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问小亮的父亲愿不愿意做尸检。如果愿意,神经病理科主任同意亲自给小亮做局部脑组织的病理解剖。由于小亮的病情比较特殊,要想知道他的脑组织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只有病理结果可以为最终的诊断提供依据。若干年前的医患关系不像现在这般势如水火,我记得小亮老实本分的父母商量以后,签字同意了黄老师的尸检建议。 于是第二天,我和师姐跟着黄老师一起去到了神经病理室。我们默默地站成一排,在那里安静地看着解剖教研室请来的老师先做解剖。他用戴着手套的双手小心翼翼地取出小亮的脑组织,再由病理科主任仔细地做薄层切片。解剖专用手术刀一层层地切割着那白花花的脑叶,一直切到脑干的部位开始显现出大片的暗红色出血点。从左侧脑桥至延髓锥体部位,广泛呈现出连续出血性坏死病灶。 “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病理科主任回头对黄老师说。 黄老师点了下头说:“继续做石蜡包埋和染色固定吧!” 听着他们的对话,我感觉我的心随着手术刀的起落变得越来越沉重。那一刀刀仿佛是切在我的心上一般,脑海里不停地思考着同一个问题:这难道真的就是那个年轻博士的脑子么?潜意识里我很难将眼前这堆毫无生命力的组织结构,与那个曾经鲜活的男孩儿的身影联系在一起。 这样想着,我感觉自己的眼眶湿润了。说实话,我打心眼儿里不能接受我的患者在前途一片光明的花样年华里,生命就这样猝然终止了。我偷偷看了一眼师姐,发现她的眼角也是湿湿的。后来小亮的遗体被送去火化,他的父母自始至终也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病例,就这样永远地、深刻地镌进了我的记忆里。 小亮属于典型的“凤凰男”,是家里的独子,是那个并不富裕的家庭获得幸福快乐的唯一希望。且不说培育一个优秀的孩子所需要付出的艰辛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苦痛,他父母那样的年纪也早已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不可能再生一个孩子来弥补丧子之痛。那么,小亮父母的晚年将由谁来照料?老两口又将如何摆脱老年丧子的痛苦? 记得当年参加完小赵同学的追悼会以后,我听说他妈妈后来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与妄想症。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家里门铃一响,她便欢天喜地,以为是她儿子回来了。每次都是小赵的爸爸拿了儿子的死亡证明书出来,她才肯相信她儿子是真的走了——免不了又是失声痛哭。地,却不小心从新搭的舞台架上摔了下来。当时,他是后脑勺先着地,据说拍了片子显示的是“脑干挫裂伤”。虽然他当即就被送去中山医院抢救,但是没过几天就去世了。 追悼会上,他妈妈好几次哭得昏了过去。我们看着他平日里帅气、白净,如今却水肿不堪的面庞,也都泣不成声。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同龄人的葬礼,而且是曾经那样熟悉的、在我的生活里真实存在过的人。这让我深刻感受到了比参加老年人葬礼来得更加真切的悲痛。 从那时起,我就深刻地明白了“脑干”这个词汇所代表的意义有多重大。看着眼前毫无反应的小亮,再一次证实了“脑干病变”是一个多么严肃而残酷的词汇。 小亮最终还是没能挺过去,在又坚持了几日以后的一个凌晨,他那颗年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母亲和女朋友泣不成声,而他的老父亲在一边默不作声。沉默半晌,他抬头询问黄老师关于小亮的病因以及他的去世,有没有一个最终明确的定论。 黄老师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问小亮的父亲愿不愿意做尸检。如果愿意,神经病理科主任同意亲自给小亮做局部脑组织的病理解剖。由于小亮的病情比较特殊,要想知道他的脑组织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只有病理结果可以为最终的诊断提供依据。若干年前的医患关系不像现在这般势如水火,我记得小亮老实本分的父母商量以后,签字同意了黄老师的尸检建议。 于是第二天,我和师姐跟着黄老师一起去到了神经病理室。我们默默地站成一排,在那里安静地看着解剖教研室请来的老师先做解剖。他用戴着手套的双手小心翼翼地取出小亮的脑组织,再由病理科主任仔细地做薄层切片。解剖专用手术刀一层层地切割着那白花花的脑叶,一直切到脑干的部位开始显现出大片的暗红色出血点。从左侧脑桥至延髓锥体部位,广泛呈现出连续出血性坏死病灶。 “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病理科主任回头对黄老师说。 黄老师点了下头说:“继续做石蜡包埋和染色固定吧!” 听着他们的对话,我感觉我的心随着手术刀的起落变得越来越沉重。那一刀刀仿佛是切在我的心上一般,脑海里不停地思考着同一个问题:这难道真的就是那个年轻博士的脑子么?潜意识里我很难将眼前这堆毫无生命力的组织结构,与那个曾经鲜活的男孩儿的身影联系在一起。 这样想着,我感觉自己的眼眶湿润了。说实话,我打心眼儿里不能接受我的患者在前途一片光明的花样年华里,生命就这样猝然终止了。我偷偷看了一眼师姐,发现她的眼角也是湿湿的。后来小亮的遗体被送去火化,他的父母自始至终也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病例,就这样永远地、深刻地镌进了我的记忆里。 小亮属于典型的“凤凰男”,是家里的独子,是那个并不富裕的家庭获得幸福快乐的唯一希望。且不说培育一个优秀的孩子所需要付出的艰辛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苦痛,他父母那样的年纪也早已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不可能再生一个孩子来弥补丧子之痛。那么,小亮父母的晚年将由谁来照料?老两口又将如何摆脱老年丧子的痛苦? 记得当年参加完小赵同学的追悼会以后,我听说他妈妈后来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与妄想症。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家里门铃一响,她便欢天喜地,以为是她儿子回来了。每次都是小赵的爸爸拿了儿子的死亡证明书出来,她才肯相信她儿子是真的走了——免不了又是失声痛哭。 这样的故事很残酷,也很真实,真实地提醒着所有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过想要的生活,借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活在当下就好”。但医生的视角大多比较保守,在我看来,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活着,我们肩负更多的,是家人的关爱、家庭的责任和社会的使命。一旦你身上发生了什么,对于整个家庭的摧毁力往往是致命的,并且是无法弥补的。这也是所有独生子女家庭享受轻松的同时,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 记得在小亮的状况不太好了以后,隔壁床位的病人家属曾经议论过小亮的女朋友。在他们看来,小亮走得那么干脆,对于女孩儿来说反倒是件好事。在女孩儿妈妈过来看望小亮时,有一位老太太甚至直截了当地对她说:“还好你女儿没有跟他领证哦……”潜台词就是:“万一领了证,合法了,他一走,你女儿就变成了寡妇;他们俩没有领证,只是男女朋友,这样没关系,至少你女儿未婚……” 女孩儿的妈妈没有说话,但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出她是赞成老太太的话的。这不是说为了女儿,她变得残忍了,而是在面对这样的生死选择时,她必须自私。如果小亮保住一条命,但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我相信她一样会劝女儿和他分手。道理很简单,因为她也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而不是一辈子背着“包袱”过日子。 直到现在,每每想起小亮,我总是会语重心长地劝诫我的师弟们和患者们:“千万不能去淋雨,也千万不要过度疲劳。”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我只劝师弟呢?因为男生在这方面大多比较马虎随意些,不太懂得照顾与爱惜自己。感冒是诱因,疲劳是催化剂。神经科的很多疾病,不论是脑炎、多发性硬化还是脊髓炎、脑血管畸形破裂等,都与这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上述中枢神经疾病又犹如杀手一般,最易侵犯与剥夺那些年轻、美丽的生命。 因此,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要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事业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失去了健康,也就意味着你丧失了奋斗的根本。 2011年,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一名25岁的女硕士,因为长期工作强度大、免疫力低下,引发了急性脑膜炎(这一事件曾经轰动一时),在外院治疗病情恶化后转至我们医院,最终因为发生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抢救无效去世。这个病例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年轻人是应当去努力拼搏,但是在拼搏的过程中,要懂得分辨身体发出的各种警示信号。如果我们忽视了身体提出的抗议,造成过度负荷,最终就有可能导致悲剧的发生。 2011年4月22日,我在微博里为那个女孩儿写了下面这段话: 都说女孩子像花,可是要成长为他人所欣赏的“优雅知性之花”,背后付出的却是巨大的代价!鲜花很美丽,但也极易凋零,所以女孩子一定要善待自己。如果她们不幸在本应怒放的年龄凋谢了,留给身边人的只有长久的悲恸与永远也无法磨灭的回忆。 ★年轻人也是会中风的 在所有的神经科急症里,脑血管意外的发生率相当高。 一提起脑血管疾病,普通人总会把它当作一种老年性疾病,认为这类疾病大多和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头儿、老太太有关,就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脂血症等基础性疾病,往往是老年群体发生脑血管意外的重要危险诱因。 这些属于一般人的认知。在此,我要郑重提醒大家注意:年轻人也是会中风的! 这样的故事很残酷,也很真实,真实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