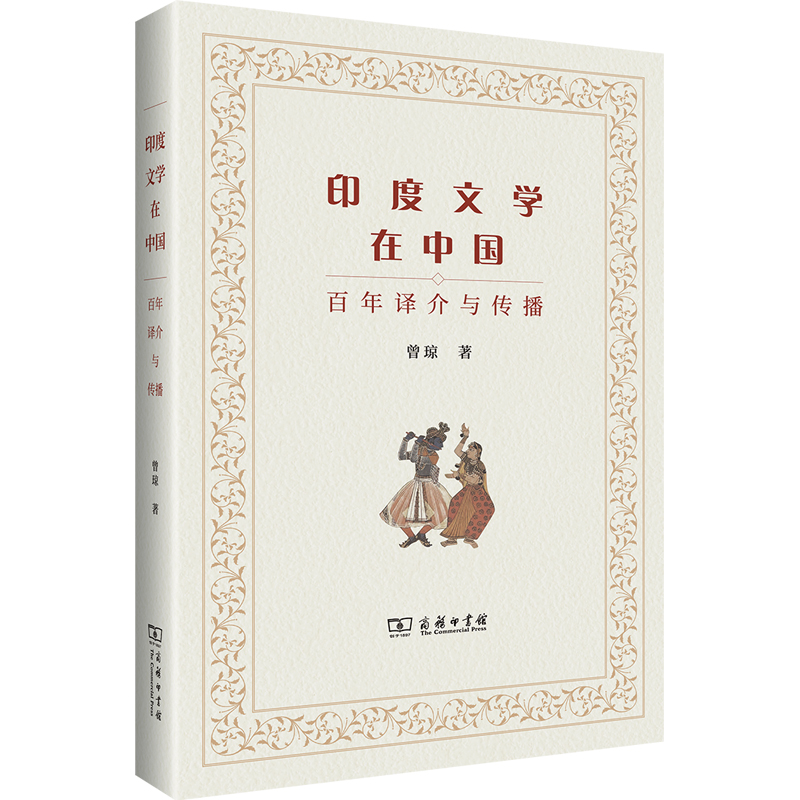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158.00
折扣价: 118.50
折扣购买: 印度文学在中国:百年译介与传播
ISBN: 9787100205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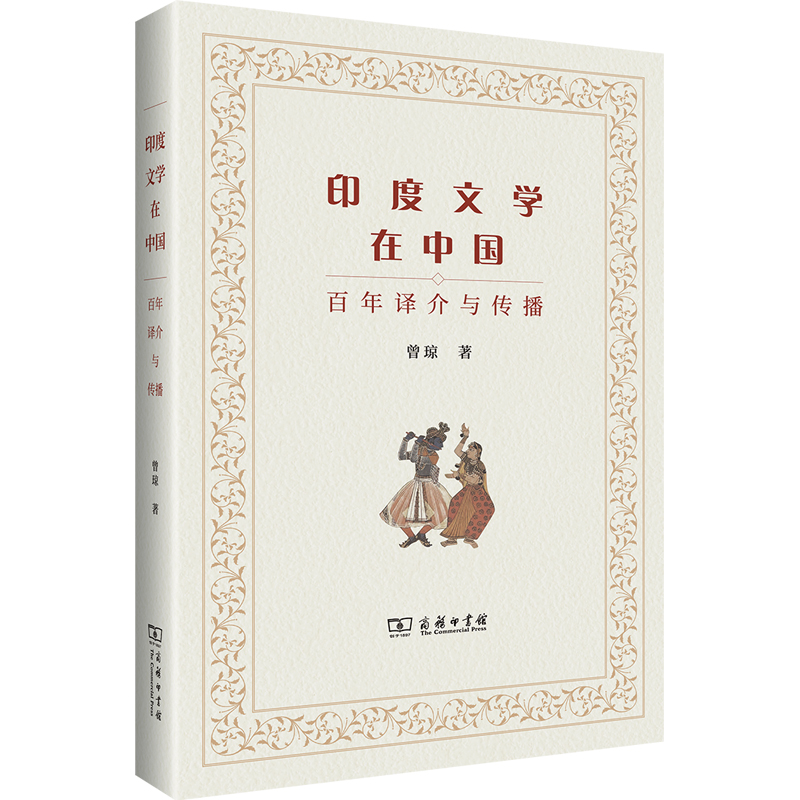
曾琼,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南亚语种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印度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东方文学、中印文学比较研究、泰戈尔研究。出版学术专(译)著4部,在海内外累计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参编教材多部。
第四章 第三节 一、冰心是中国的泰戈尔式作家 我用“中国的泰戈尔式作家”来形容冰心,是想指出泰戈尔在印度文化生活与印度文学中所起的杰出作用,特别是泰戈尔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文学巨匠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不想在这一点上大加发挥,只是概括地指出几点。我觉得泰戈尔之所以伟大,在于其两大特点。第一,他一方面尽情吸纳西方文明的优点,又敏锐地觉察出西方文明的严重缺陷。他的这种敏锐是因为他辩证地继承了东方文明,特别是印度文明几千年积累的广博精深的智慧。第二,他热爱人类,相信精神的力量是最伟大的。文学写作对他来说是对社会和人类的服务、奉献,不是斗争;文学是滋补饮料,不是武器(更不是“投枪”);文学重在安慰、镇定、启发,不是咒骂、刺激、挖苦、打倒(不是“打落水狗”)。泰戈尔对西方文明的透彻了解是与他同时代的胡适、林语堂、陈独秀等人无法相比的。可是他并不“一边倒”,而是站得高,看得远。他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对西方文明所做的评论,现在仍然能为全世界所接受与学习,这是值得肯定和深思的。泰戈尔强调应该重视印度文化和东方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与特质,并非一种保守主义,而是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时,他清醒地看到了其中的不足,并深刻认识到了东方文明的价值,因而他以高远的目光和超乎时代的认识,提倡应该捍卫印度传统和东方传统。 当然,我不是说冰心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或者在中国文学上的成就可以和泰戈尔在印度的地位和成就相提并论。冰心并不是“中国的泰戈尔”。在这一点上,应该看到,冰心是中国男尊女卑历史上得到新潮流解放的第一代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中还属于“必须保护”的类型,不可能达到泰戈尔那样受人普遍敬仰的程度。但是,冰心能够在20世纪20年代就以女性作家的身份在男权世界的思想界与文学界中和其他名人平起平坐,已经是了不起的,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另外,促使中国真正接受泰戈尔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扩大到中国思想界与文学界中,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展起到了良性作用的正是一位女性——冰心,这也是空前的。 冰心在文学创作和思想上对泰戈尔的接受,有其必然的原因。就20世纪初期的整个文学和文化氛围来说,对外国文学文化的学习是当时的一种文化潮流。在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作品被大量译介到中国来,这是冰心能够阅读到泰戈尔的作品并接受其思想影响的外部机缘。就冰心个人来说,她对泰戈尔的接受,还有更为深刻的内在原因。 冰心童年时代的成长环境是她接受泰戈尔思想的基础。对于冰心所受泰戈尔的影响,茅盾曾经指出,要了解和分析冰心思想的成因,固然应该看到她受到了基督教教义和泰戈尔哲学的影响,但这种因素只占了一半的比重。因为一种思想要产生影响,就必然需要有其条件。茅盾以“种子”和“土壤”作比喻,指出外来思想这颗种子如果要生根发芽,就必须有适合它的土壤。而茅盾认为的适合的土壤,就是一个人小时候的成长和生活环境。冰心成长于诗书礼仪之家,父母对她宠爱有加,她与弟弟年龄差距虽然较大,但关系却很好,她自幼在海边长大,对海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些都为她接受泰戈尔的“爱”的思想奠定了适宜的基础。例如,在她的诗歌中,海的形象经常出现,她对自然的爱,往往寄托在对海的描述与赞美之中。冰心在自传中还写道,由于童年生活的影响,“我喜欢空阔高远的环境,我不怕寂寞,不怕静独,我愿意常将自己消失在空旷辽阔之中。因此一到了野外,就如同回到了故乡,我不喜城居,怕应酬,我没有城市的嗜好”。她的这种对于独处的喜爱,对于自然和静谧的喜爱,是她能理解并接受泰戈尔“无限”与“有限”思想的重要原因。此外,冰心对基督教的了解,对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的熟悉,使她对宗教具有一种开放的态度,因此对于泰戈尔所带来的印度教的观念,她也并不排斥,并能加以吸收利用。对此香港学者梁锡华曾撰文指出冰心的宗教思想“既是耶、是佛、是印,也是非耶、非佛、非印”。 在《文学家的造就》一文中,冰心认为一个人要成为文学家,必须具备以下一些条件:家庭中要有文学的氛围;出生在风景美好的地方;生于中产之家;多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与自然接近;多研究哲学社会学,少于纷繁的社会交际;多做旅行。考察冰心和泰戈尔的身世,我们便会发现,两人都符合冰心所列的这八个条件,这便为两人之间的契合打下了基础。她对泰戈尔的忠诚可以从翻译《吉檀迦利》的例子看出。冰心从1946年开始翻译,到1955年诗集全译本出版,历经了近十年时间。这十年正是冰心人生中起伏不宁的一个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冰心的生活就已经开始变得动荡不安。其间她全家几经迁徙,从北京到昆明,从昆明到呈贡,又从呈贡到重庆。1946年随丈夫吴文藻赴日本,她与家人又不得不再次分离。不但如此,在这段时间内她还经历了丧父、丧弟、丧友之痛,生活上也日渐困窘,在到了重庆之后有段时间甚至不得不捉笔卖文以求得生活之资。但她始终抽出时间不断修改《吉檀迦利》的译稿。如果把冰心的这段时间内的生活轨迹与泰戈尔创作《吉檀迦利》期间的生活经历进行比照,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竟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泰戈尔在创作那些其后变成英文的《吉檀迦利》的孟加拉语诗歌之时,正步入“知天命”之年,经历了丧妻、丧父、丧女、丧友的痛苦,也遭遇了来自外界的误解和攻击,同时还不得不为了他在和平乡所创办的学校的运行而费心劳力。诗人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曾说过:“对诗人的理解和地理位置的变化无关。它和年龄有关。”在这一点上,冰心和泰戈尔的类似经历可以成为我们比较两位诗人的指南。 二、冰心在诗歌创作中与泰戈尔的交响 作为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获得高度肯定与赞赏的女诗人,冰心的诗名与《繁星》《春水》两部诗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两部诗集于1922年和1923年先后出版,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繁星》《春水》之后,阿英曾这样评价冰心:“她——谢婉莹,毫无问题的,是新文艺运动中的一位最初的,最有力的,最典型的女性的诗人、作者。”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由胡适所标举的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新文学的要求与呼声是当时文坛的主流,中国文学创作领域内各种文学体裁均不同程度受到了这一运动的影响,诗歌领域中的“小诗”便是在此时出现的。所谓“小诗”,指的是它篇幅短,一般多为“一至四行”,以“简洁含蓄”的方式表现“零碎思想”。“小诗”的兴起与周作人的推动密切相关,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的《论小诗》(1922)一文中提出“小诗”有两个文学来源:其一是中国文学里“古已有之”,小诗是中国“诗的老树抽了新芽”;其二是“中国现代的小诗的发达,很受外国的影响,是一个明了的事实”。周作人认为这种“外国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于日本的小诗和泰戈尔的诗歌,并在《论小诗》一文中援引了冰心的诗歌《繁星》来证明泰戈尔诗歌对“小诗”的影响。事实上,冰心在《繁星》的序言中便已坦承了泰戈尔对这部诗集的影响:“一九一九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R. Tagore)的《迷途之鸟》(Stray Birds),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1959年,年近六十的冰心在重提自己这两部诗集的创作时,再次确认了她当时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由此可见,《飞鸟集》为冰心创作《繁星》《春水》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文学形式的范例,冰心的这两部诗集在文体上的确是模仿《飞鸟集》的产物。“小诗”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并不长,而冰心的《繁星》与《春水》则可看作是这一形式的典范。朱自清认为,从这两部诗集之后,到宗白华的《流云》小诗集问世,“小诗渐渐完事,新诗跟着也中衰”。在出版这两部诗集之前,冰心在当时文坛的形象基本是一位崭露头角的小说新秀;在这两部诗集之后,冰心获得了诗人的身份,开启了她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领域。在此之后,她“才开始大胆地写些新诗”。因此也可以说,是泰戈尔引领冰心走上了现代诗歌创作的道路。 这种引领,不但体现在诗歌的形式上,也体现在诗歌的风格和内容上。周作人在《论小诗》中提出,小诗由于所受的日本与印度的影响不同而分为冥想与享乐两个流派,冥想派直接受到泰戈尔诗歌尤其是《飞鸟集》的影响,冰心的《繁星》是其代表。在《繁星》中的不少诗歌上都可以看到《飞鸟集》的影子。如《繁星》六: 镜子—— 对面照着, 反而觉得不自然, 不如翻转过去好。 与《飞鸟集》二八: 啊,美呀,在爱中找你自己吧,不要到你镜子的谄谀中去找呀。 这两首诗的题材、旨趣都十分相似。又如《繁星》一一六: 海波不住的问着岩石, 岩石永久沉默着不曾回答; 然而它这沉默, 已经过百千万回的思索。 与《飞鸟集》一二: “海水呀,你说的是什么?” “是永恒的疑问。” “天空呀,你回答的话是什么?” “是永恒的沉默。” 可以看出,冰心这首小诗是受到了泰戈尔诗歌的启发,它是对后者的一种演绎和推衍。这样的例子在《繁星》中并不少见,乃至《繁星》这部诗集的名字,也可以说不无《飞鸟集》的影响。 冰心在文学创作中经常使用的一些词汇和意象,乃至部分诗歌的结构,都受到了泰戈尔很大的影响。以在她的诗和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无限”一词为例,斯洛伐克学者马利安·高利克(Marian Galik)在《青年冰心(1919—1923):冰心与〈圣经〉、冰心与泰戈尔的关系研究》(1993)一文中指出,青年冰心在创作中经常使用“无限”“无涯”等概念,其作品中多次出现关于“无限”与“有限”的讨论,这主要是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他的这一论点应当是可信的。冰心在1920年写作了《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一文,当时她刚刚读完泰戈尔的传记和一些作品,在这篇文章的开始,冰心便使用了“无限”:“泰戈尔!美丽庄严的泰戈尔!当我越过‘无限之生’的一条界线——一生——的时候,你也已经超过了这条界线,为人类放了无限的光明了。”又如冰心在1923年赴美途中所作的《纸船》,泰戈尔在《新月集》中也有一首同名诗。冰心《纸船》的整体情感与泰戈尔的《纸船》并不一样,冰心写的是游子对母亲和故乡的思念,泰戈尔写的是一个儿童对被了解的渴望,但两首诗的主体意象却是一样的,都写到了纸船、以纸船承载的情感以及梦。从结构上看,两首诗都从投放纸船开始,都以睡梦结束,同样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首诗,可以认为是冰心对泰戈尔的一次成功的模仿与突破。 泰戈尔在文学上对冰心的影响,还体现在冰心对泰戈尔的翻译上。冰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翻译东方文学的先驱和主力军之一,她翻译过泰戈尔的十余部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冰心对泰戈尔的翻译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吉檀迦利》是冰心翻译出版的最早的一本泰戈尔的诗集。冰心的这个译本也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最受欢迎、影响最大的《吉檀迦利》译本。关于《吉檀迦利》的翻译,冰心自己曾写道:“至于我自喜爱,而又极愿和读者共同享受,而翻译出来的书,只有两本,那就是《先知》和《吉檀迦利》!”由此可见她翻译《吉檀迦利》是缘于对这部作品的深切的喜爱和认同。事实上,如果考察冰心的创作年表,我们会发现,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冰心所创作的诗歌、小说都在慢慢减少,她创作生涯的后半期作品以散文、随笔为主,从这一点来看,对于冰心来说,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译介行为,它实际上是对其自身的文学创作的消减的一种补偿,尤其是那些她所喜爱和推崇的译介作品,就更是如此。 ? 王向远:印度文学在中国·序言 《印度文学在中国:百年译介与传播》中的“百年”,指的是20世纪。从东汉时代以来的中印上千年文化交流史上看,在宋代以后六七百年的沉寂后,20世纪的一百年,中国迎来了译介印度文学的转型期和复兴期。曾琼的这部著作将整个20世纪作为一个整体,从纵向上把握不同阶段印度文学译介传播的不同特点,寻求和总结其中的一些规律性现象,尤其是对民国时期中国的印度文学译介与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视,强化了此前被忽视的一些现象与环节,也影响启发了相关领域的深入探索,如深圳大学王春景教授近年来对民国时期中印文学交流,特别是印度游记的发掘与研究,实与曾琼的研究相互呼应、相得益彰。 ………… 这部书是研究中国东方学、印度学的学术史的,同时它本身也是中国的东方学、印度学学术史的一部分。有了曾琼这部书,再加上早几年出版的郁龙余、刘朝华著《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2015年)、郁龙余等著《印度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2016年)等,这方面的相对完整的知识领域就基本上建构起来了。这是读者的眼福,也是中国东方学、印度学之幸。 ——王向远 ? 全书内容的说明 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文学交流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翻译以及对译介作品的研究,是文学交流和传播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也是能直接体现文学交流、传播状况的一个指标。因此,文学传播史的研究对象,必然涵盖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本书的主题“印度文学在中国:百年译介与传播”,其研究的时间跨度主要为20世纪,前后均稍有延展;研究内容为印度文学的汉译、研究和传播,及其在学术界引起的回响,并尝试兼及在大众中引起的反响。 ? 新世纪之交的特点:印度电影和旅印游记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印度文学和文化在我国的传播又出现了新的特点。其一是传播媒体的多样化,其中又以印度电影为集中代表。电影是电影文学的一种具体化表现,尤其印度电影往往与印度传统文学作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神话、经典作品往往成为印度电影故事的精神来源和改编蓝本。因此,鉴于印度电影近年来在我国大众文化传播领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书将印度电影也纳入了考察范围。其二是随着国人越来越多地出游印度,各类印度游记成为印度文化在中国传播的新媒介,因此本书也将20世纪的印度游记纳入考察范围,以观察印度文学文化在我国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 郑振铎译笔优美清丽 郑振铎译《飞鸟集》,译笔优美清丽,生动活泼,又不失典雅大方。例如:“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第6首)“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第35首)“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第57首)“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第82首)在这样诗性的句子中,不通孟加拉文和英文的读者,也仿佛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泰戈尔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笔。读者与泰戈尔的文学作品,甚至与印度的文学都会结下一段美妙的“文学因缘”。 ? 季羡林翻译出版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全译本 我国的《罗摩衍那》翻译在20世纪80年代似乎忽然登上了一个高峰。从1980年至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和发行了由季羡林先生从梵文直接翻译的《罗摩衍那》全集,至此,我国拥有了《罗摩衍那》的全译本。这套全译本共七卷八册,长达九万余行,它的翻译和出版,是现当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桩重大事件,也是我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填补了我国外国文学名著翻译上的一项重大空白。据季先生的回忆,他对《罗摩衍那》的翻译开始于1973年,前后十年,历经了精神上的困苦、学术上的探索,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对这部皇皇大作的翻译。译著出版时季先生已年近七十,并刚刚经历了可以说人生最为低沉、黑暗的时期,这部七卷本的《罗摩衍那》,代表的是季先生对学术、对生命的坚持和希望。 ? 冰心译《吉檀迦利》获得了极大成功 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冰心翻译的《吉檀迦利》全译本,这是第一个真正在我国读者中广泛流行的译本。冰心从青年时期就崇拜泰戈尔,她自己又是诗人、作家,因此尽管她译的《吉檀迦利》有一些误译或错译之处,整个译本却获得了艺术上的极大成功。冰心译本在译文中保留并强化了英文版的节奏感,遣词用句精准独到。由于深知泰戈尔对词语使用的娴熟和英文版《吉檀迦利》本身言辞的优美,在翻译过程中,冰心对字、词的选用是颇费心思的,关于这一点,她自己曾说:“为了要尽情传达出作者这‘歌鸟’般的飞跃鸣啭的心情,使译者在中国的诗歌词汇的丛林中,奔走了好长的道路!”……《吉檀迦利》冰心译本本身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汉语文本,它具有不依附于英文原文的、属于汉语原创诗歌的文学美,它不仅仅是翻译,更是一部翻译文学的经典,它自身也成为汉语诗歌财富的一部分。冰心的《吉檀迦利》也是目前流传最为广泛、得到读者和研究者共同承认的最具权威性的版本。 ? 冰心的诗歌创作受到泰戈尔影响 周作人在《论小诗》中提出,小诗由于所受的日本与印度的影响不同而分为冥想与享乐两个流派,冥想派直接受到泰戈尔诗歌尤其是《飞鸟集》的影响,冰心的《繁星》是其代表。在《繁星》中的不少诗歌上都可以看到《飞鸟集》的影子。如《繁星》六: 镜子—— 对面照着, 反而觉得不自然, 不如翻转过去好。 与《飞鸟集》二八: 啊,美呀,在爱中找你自己吧,不要到你镜子的谄谀中去找呀。 这两首诗的题材、旨趣都十分相似。又如《繁星》一一六: 海波不住的问着岩石, 岩石永久沉默着不曾回答; 然而它这沉默, 已经过百千万回的思索。 与《飞鸟集》一二: “海水呀,你说的是什么?” “是永恒的疑问。” “天空呀,你回答的话是什么?” “是永恒的沉默。” 可以看出,冰心这首小诗是受到了泰戈尔诗歌的启发,它是对后者的一种演绎和推衍。这样的例子在《繁星》中并不少见,乃至《繁星》这部诗集的名字,也可以说不无《飞鸟集》的影响。 ? 印度民间文学翻概况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编译和出版的印度民间故事有20余种,其中极少数译自苏联的译本,大部分译自印度本国的作品。从译介的数量来看,20世纪50年代是第一个小高潮,有五部作品;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明显的高峰期,涌现了十数部译作;之后对印度民间文学的翻译逐渐减少。从译介过来的作品看,各作品集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和重复,译作既有译自印度出版的英文编译本的作品,也有译自梵语、巴利文等古老语言的作品,其中不乏一些在印度十分经典和流行的版本。在这些译作中,有两部值得格外注意:一部是《五卷书》,另一部是《故事海》。 ?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印度文艺理论研究的标志性事件 1949年到2009年间,我国的印度文艺理论译介与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渐成熟的过程。其中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分别是1980年由金克木翻译的《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的出版、1993年黄宝生著《印度古典诗学》的付梓、1997年倪培耕著《印度味论诗学》的出版、2006年郁龙余著《中国印度诗学比较》的出版和2008年黄宝生编译的《梵语诗学论著汇编》问世。 ? 印度文学与印度电影的关联 印度电影与印度文学有密切的联系,印度神话是印度文艺作品主要的灵感源泉之一,尤其两大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中的神话故事一直是印度文学和艺术取之不竭的灵感来源。神话传说是印度民族集体无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在印度当代的影视作品中有各种表现。 ………… 印度文学影响印度影视作品最直接的代表是《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的超长电视剧,如印度Star Plus公司2013年出品了二百六十七集版《摩诃婆罗多》。其变形作品则不一而足,除了《猴神老哥》之外,远的如《印度超人》(2006),近的有上下两部的《巴霍巴利王》。对印度神话不了解的观众觉得这些作品神乎其神,极尽夸张。但深谙印度神话传说的人则能充分理解其中各种情节,并由此看到印度观众对此类影视作品极其欣赏的深层心理原因。 ? 印度女性题材电影的突破 印度一些现实题材的电影也与印度的传统文化、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女性题材为例,印度是一个传统的国家,宗教与个人生活渗透捆绑,由此伦理规范的制约也变得不可动摇。在这样的习俗约束下,女性的生存状态一直令人担忧,很难得到改善,像西方国家女性那样走上街头为自己的权益奔走呐喊是她们可望而不可即的。 当代诸多印度电影对女性现实问题有所反映,其中《摔跤吧!爸爸》《护垫侠》《印式英语》《神秘巨星》《厕所英雄》等都是撼动人心的佳作,各从不同角度和立场为印度女性群体发声。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引导性作用不仅能娱乐大众,更将整个印度社会逐渐带入反思历程。 《摔跤吧!爸爸》中两个女孩儿通过父亲的严格训练最终摆脱了过早嫁作他人妇的命运,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模式;《护垫侠》中的妻子遇到了一个为她设身处地着想的好丈夫,不但解决了她的问题,还将整个印度女性的卫生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印式英语》中的贤妻良母最终受不了丈夫与孩子的嘲讽而励志学好英语,终于重新赢得身边人的尊重;《神秘巨星》凭借女儿的勇气和母亲的坚毅最终造就了大小两位名副其实的“巨星”;《厕所英雄》则是用妻子的坚持和丈夫的支持来敦促在村庄设立公共卫生间,为自己和他人带来了切实的方便和利益,也为女性的安全和隐私赢得了应有的关注度和相应的保障。 ? 印度老电影广受中国观众喜爱 印度电影在我国的传播,最初起源于20世纪中期。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是中印双方文化交流协议的签订,它为印度电影在我国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两亩地》《大篷车》《流浪者》等一系列印度电影传入我国电影市场后,观影人数众多,赢得了广泛而热烈的好评,使得国人对印度文化形成了深刻的认识。 ? 印度电影观照现实问题的人文关怀引发共鸣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本土大片大多不涉及中国社会问题。但印度电影并未刻意回避社会现实问题,甚至对现实问题表现出了较高的重视程度,对“贫民窟”等社会现象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与刻画,并且还有进一步的升华。与印度电影相比,中国电影在这方面做得是不够的。由于中印两国具有诸多共通点,导致两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类似问题,并且还存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冲突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印度电影更能符合中国观众的观影需求,同时还能激发中国观众的精神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将印度电影看作一面镜子,虽然它与我们有一定的距离,其反映的结果并不是完全准确,但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中观察到自身。 ? 旅印游记中对印度消极现象的描写 没有什么字眼比脏乱差更加频繁地出现在(旅印游记)文本中。印度奇慢的行政效率是这种脏乱差的重要体现之一。……印度的火车总是误点,印度人的时间观念并不可靠。这些负面的描述都是近代没落印度形象的延续,透露出行游者的不解与困惑。余秋雨惊异于印度人的无所事事:这些人“三成摆摊,一成乞讨,剩下的六成闲站着。闲人热衷于凑热闹,摆摊的人则毫无秩序可言,使得本来拥挤的街道更加密密麻麻”。在众多游记对印度的描述中,作者的观念与情感也在脏乱差这些词汇所构成的词语群、语汇网、语义场中最大限度地表现了出来。西川在《游荡与闲谈》附录中谈及自己上当受骗的经历时说:“作为一个外国人,不论你来自东方还是西方,你都必须小心花钱,否则你就得花1400卢比去买一尊价格应该在300卢比的铜制湿婆像,花50美元租一条价格在50卢比的船去游览恒河。”于坚则在《印度记》中形容印度的电车像幽灵一般,似乎从未清洗过,污垢像漆一样闪着光。乘客人人都有飞身一跃的本领。其实不只是西川和于坚,众多的旅行者都在游记中记录了他们跟印度小贩斗智斗勇的过程和莫名其妙被骗的扫兴经历。他们把这种不诚实的行为归结为印度的贫穷。 众多行旅者笔下的印度乡村残败狭窄,排水沟里流淌着绿色黏液,牲畜和人挤在堆满了垃圾和食物的肮脏的泥巴屋子中,苍蝇成群,气味难闻。这种从现代角度看来匪夷所思的场景带给了他们失落和愤怒的感情。这种失落在见到印度人独特的如厕习惯之后达到顶峰。西川写道:“我见到过一个拉屎的女孩的黑屁股。我沿路走来,她看见我,从地上站起,裙子自然垂下,遮住了该遮的一切。我走过她,走出十几步,回头看,她又蹲了下来。” ? 印度人的露天厕所观念 印度人对于使用大自然这一天然厕所的坦然和自得往往令外国人感到惊异。现代印度依然是一个被厕所问题严重困扰的国度。为确保印度达到无露天排便行为的标准,印度政府2014年推出了“清洁印度”运动(Swachh Bharat),誓言五年内在全国范围内消除露天方便。但这一运动的成效却并不令人满意,政府斥巨资修建的许多厕所或因缺失无法使用,或因为生活习惯被弃用。就像印度呈现给世界的各种复杂形象一样,它在厕所问题上也表现出多重矛盾:一方面厕所数量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现成的厕所却很少人使用;一方面政府希望取缔延续千年的旱厕和人力淘粪工,另一方面种姓制度的限制使得淘粪工只能安于淘粪。 在部分印度人的观念中,随地大小便其实是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而传统西式的厕所将人憋在火柴盒大小的房间里,使人不得不置身臭气当中。如果在露天的环境中,则可以在解决生理问题的同时仰望天空进行冥想。除此之外,他们的印式厕所环保洁净,不浪费树木。这种观念也可视作印度独特“洁净观”的投射。 本书全面介绍了一百多年来印度文学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传播情况,资料丰富。全书资料丰富,文献扎实,引用准确,结构合理,是一本系统、全面介绍20世纪以来印度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译介情况的参考书。 本书最后两章以印度电影和旅印游记为主题,内容生动,体贴生活,是了解印度社会、印度文化的好帮手,可以帮助中国读者近距离认识印度,形成“印度印象”。 本书利用图表对印度文学和电影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做了分门别类的汇总,是实用性强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