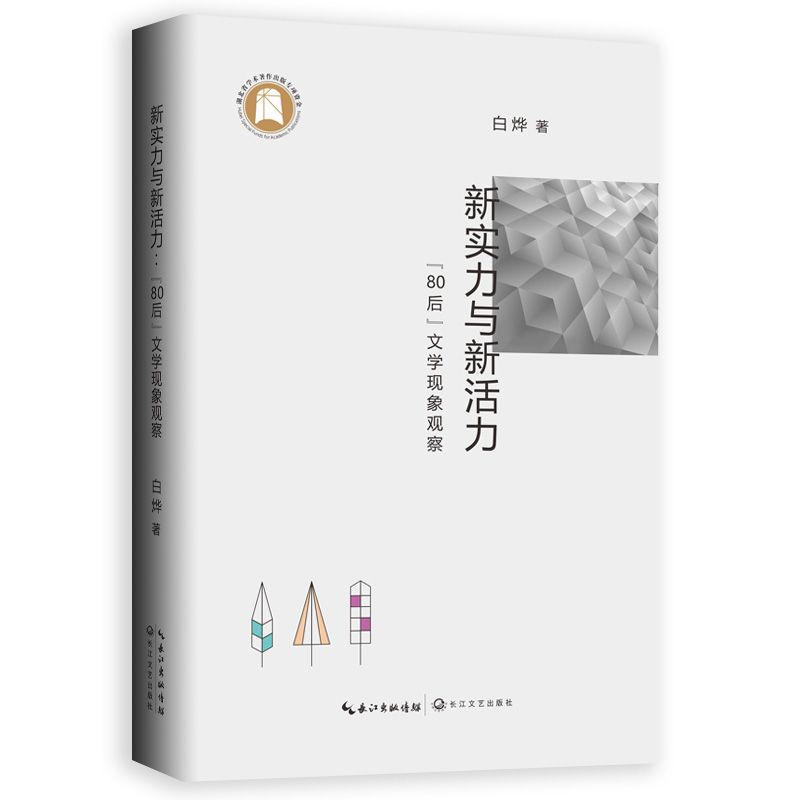
出版社: 长江文艺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28.80
折扣购买: 新实力与新活力(80后文学现象观察)
ISBN: 97875702098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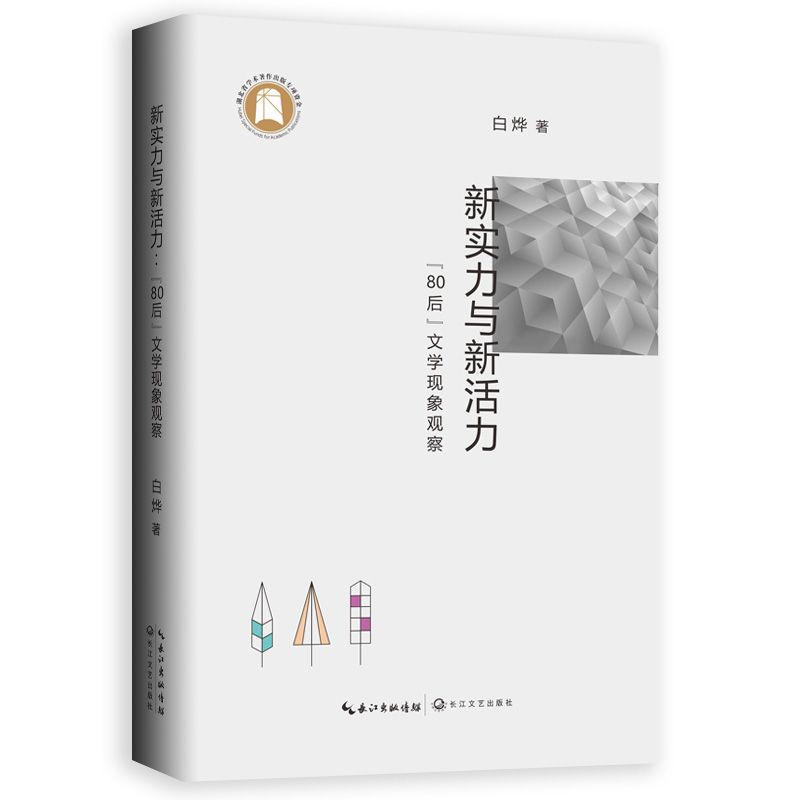
白烨,陕西黄陵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 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学术专长为作家作品评论与宏观走向考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和作家作品评论方面,撰著三百多万字,已出版《文学观念的新变》《文学新潮与文学新人》《文学论争二十年》等文学批评著作。其中,《文坛新观察》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另主持或主编有多种文学选本和年度文学现状概观著述。
少年写作纵横谈——与作家格非的对话 《北京青年报》编者按: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作者为主的少年写作群体正甚嚣尘上,在市场上来势汹涌。大量文学新人甚至低龄儿童都在加入文学、出版的大军,似乎呈现了出版的多元化格局。作家格非和评论家白烨显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在市场的多元化表象下,其实潜藏了文化选择的单一性,值得忧虑的是表象多元下的内在芜杂,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诸多问题。格非刚刚任“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归来,白烨是一直关注文坛现状的资深文学评论家,且听两位的相关看法。 一、少年写作在严格意义上说是准文学 白烨:我觉得这些年的少年写作,或者叫中学生、小学生写作现象越来越突出。这个现象里不是有很多人为因素的话,也许还可以复制下去。但是这几年,确实有其他因素的介入,所以这种现象比较令人忧虑,代表性的像韩寒,韩寒的《三重门》印了几十万册,然后又出了一本散文集,又印了几十万,在今年1月份的第二本长篇小说印量也是30万册,靠作品本身的话,30万册非常不容易,但是这种数量之后包含很多的因素。这个现象比较令人忧虑的是,可能给创作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正在写作的青少年有很大的影响,对整个文坛的影响也有消极的一面。从总体上讲,文学这个行当,应当说还要讲阅历,并不是说越年轻越聪明凭一点写作技巧、凭一点基础马上就能写得很好,我觉得真正的文学还是要看阅历、讲经验的。 格非:这个问题跟商业写作,跟出版业,跟我们整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意识是相关的。写作的低层化、低龄化,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学校的教育体制,父母如果说是给小孩子进行一笔投资,他希望很快收回这笔投资,他的这种投资心态,使写作越来越成为一种投资行为。比如说这次“新概念”大赛,我是评委,就是这帮孩子,很多人,我在上海的时候跟他们接触,他们带有非常强的功利目的,通过写作能够上名牌大学,能够加分,目的非常清楚,这就违背了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写作意义的初衷。好的作文确实比较少,我不否认这是社会发展当中带来的,这个实用的动机可以说是全国上下都非常厉害,从普通老百姓到大学教授,我们没有办法苛求那帮孩子,因为他们的生长环境就是充满了竞争,充满生存压力和充分的对未来的忧患这样一种意识,所以写作带有很多功利性。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忧虑的是,出版业也在推波助澜。因为我经常去逛书店,逛书店的时候我就很郁闷,中国每年出版那么多书干吗?从我个人来讲有很多书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大家在拼命地出,追求销量,它有一个庞大的商业利润,出版社在不断地制造选题和轰动效应,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一般来说,作家的作品还没有开始,出版商就开始考虑了,什么样的书是有市场的,所谓的市场预期,所谓的想象空间。 我们现在的文化本身自觉地培养了一批美国迷、日本迷、韩国迷,他们的生活方式从里到外全是这样一种时尚,比如说喜欢看好莱坞大片,喜欢喝可乐,喜欢开奔驰车。这就很容易造成一群从文化上依赖西方的孩子。 白烨:我觉得这应该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在一种社会、经济的过渡状态中,就是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怎么样能够坚守本土文化,使得本土文化能够在跟世界文化进行对话的同时不失去自己。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的文化批评不够,尤其是流行文化批评不够。刚才格非说到出版界,尤其商业运作对少男少女写作的推波助澜作用,我非常有同感。这几年出版业是有功又有过的,功是这几年出版数量和品种都很多,出了很多很好的书。另一方面也通过商业运作的方式把市场搞得很乱,我个人觉得我们出版行当的有一些人在选题的水平上不高,尤其是文化责任感或者叫社会责任感不够。反过来说,少男少女写作,如果它自然而然地去发展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加上很多商业的东西在里边之后,这个东西就变了味走了形,比如说现在韩寒像是一个文坛上的神话,宣传成名迅速致富,这种东西,它确实会带来很多很消极的影响。严格意义上讲,包括以韩寒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学生的写作是一种准文学,或者说是初级阶段的文学,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主要还是讲灵感讲技巧的东西,还不是有充分的生活积累、生活体验、生活感受的东西,因为我们讲文学的时候就是用语言创造形象,用形象来反映现实,那么这里头肯定是要有很多阅历,少男少女这一块如果它是文学的话,那也是准文学,就不必把这一下子炒得很热很火,好像文学方向在这儿。 二、游离于文学的“炒作”并不可取 格非:这种写作很热闹,但是对我来说,毫无印象。比如说韩寒的东西我是从来没有看过,我不便对他的作品发表什么看法。很多作家本身他想赚点钱,这没什么不好,但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面对写作的心态,这个很重要。我看到“新概念”作文,一个问题是他们失去了真实的心态。我认为这样是不可能产生好作品的,就是说你在写作的时候,你不具备任何表达真实的勇气。他就想怎么样写好,怎么样吸引别人,怎么巧,怎么别出心裁。上次我听到王蒙在会上的一个发言,我非常同意。他说我感觉到那帮孩子有一个很大的缺憾,他们的语言很好,文采很好,但是他们在文章当中应该是天真烂漫的,青春期嘛,他们有各种关怀,但是没有反映出来。他们谈的问题都非常空,谈很多写作的策略,怎么样引起评委的关注等,他们就把很多的心血都放在这种方面去。 白烨:像韩寒他们这样一种写作,尤其是对其他人的写作会产生一种什么影响?我觉得对格非这样的已经在文学上有相当的造诣和定力的没影响,倒是对另外一些人有影响,就是对那些文坛上还不太知名,正要往出冒,还没有冒出来的一群人,比如说像是70年代,包括特点年龄差不多的一些人,会对他们有些影响。它会带来一种焦虑,让很多人觉得我们不赶紧写的话,后头的人就追上来了。80年代的这拨儿,光我知道的,不光是韩寒一个,包括像北京、上海,另外还有一些在国外留学的中学生,就是十六七岁这样的孩子写的一些作品。我看了以后,觉得他们确实有才气,语言比较好,但是从我的这种观点来看,跟他们此前的70年代、60年代这些比的话,那确实是无法比的。从这方面看,代表性的韩寒,他的获得是大于他的实力的,就是说他得到的比他应该得到的多得多,这种是炒作所赋予他们的文学之外的东西,而且这些当然要产生负影响。 格非:在国外,文学在不同层次上面对不同读者,但在中国这一点恰恰界限不清。出版界的人有意无意地造成误导,比如说我推出一本书,知道它不好,但是销量很大,就会把它包装成中国最伟大最优秀的、代表中国水平的作品,这样在舆论上带来一个不科学不真实的引导,这个我觉得是错误的。因为你要知道,媒体代表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权力。现在很多知识分子转向搞传媒,为什么?传媒的力量太大了,它可以影响读者。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传媒在很大的程度上要负责任,应该反省自己了,应该有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比如大学生,他们就是读这些小说长大的,对他们能没有影响吗?当然影响很大了,他们就认为这些作品是最好的作品,他们不屑于读鲁迅,不屑于读卡夫卡、福楼拜。所以我们在评价畅销书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客观一点,很多批评家都是专家,出版家也是专家,他们在说一些违心的话,这种本身对中国的青少年教育确实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我觉得这个问题必须提出来。 三、真正的写作要有自己的定力 白烨:这确实是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批评家和出版社形成一条流水线运作的方式,其实我觉得更值得忧虑的是批评的媒体化,而不是媒体的批评。批评家现在基本上是出版物的广告人,或者说叫广告文案,现在跟60年代比,有一个很大区别,80年代出版还没有商业化,批评家就是专心致志地盯着作家和新的作品去写评论,现在谁再专心致志地花几年工夫去研究一部作品、研究一个作家就会看起来很傻,现在大家都忙着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然后要发言、吃饭、写文章,作为批评家来说,我自己也经常在反省,这些比媒体批评的问题更值得关注。 格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在这个商品社会的时候,他们会认为这个商品时代是一个永久的时代,会认为以后的事情就是大家赶快挣钱,出名须趁早。这样使很多人处在一个恐惧当中,觉得我再不奋进就完了。但是从一个人的历史观来看,人类社会已经发展进入了多少不同的时期很难说得清楚,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大的眼光来看待文学的话,很可能就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失去了应有的定力,也就是判断力。所以我就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这个在未来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怎么变化取决于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我们有些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很可能在未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在我们整理当代记忆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一些价值准则,这个我觉得都需要社会各种不同的声音能够发表,但是我们现在很糟糕的一个现实是,比较好的文学,它在主流的文学上不占优势,这个权力的分配不是很平均。 白烨:它甚至在出版物这一块也不占主流,就是说商业造成的表面多元化下面其实是非常单一的选择。 格非:现在这个表现越来越清楚,至少占主导的地位是这样的。它在逻辑上讲是多元化的,对每个人都敞开,但是问题是市场挑选什么,它从来不禁止你不能写作,但是市场它对你熟视无睹,它不看你,你就马上消失,因为你生存不下去,所以市场的东西很可怕。对市场化我们不做反思的话,这个多元化是无从谈起的,现在很多人认为市场化就是多元化,这是绝对错误的,这个观点根本不能成立。 四、作家不应漠视市场,要学会“为我所用” 白烨:你说的要反思市场这个观点非常重要,我们从经济到文化都过于相信市场和依赖市场,而对市场本身没有做分析,没有想到我们如何利用市场、把握市场,让市场为我所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做得确实太不够了,在图书市场,尤其是在文学出版,如果大家都去迁就市场的话我觉得就岌岌可危了。有一个问题就是读者需要引导,市场需要培育。 格非:所以我主张作家应该主动来应对市场化,作家一般是两种态度,一种是迎合,另一种是排斥,这两种办法我认为都是不对的。一个作家如果对市场视而不见,完全对市场冷漠,既然市场对我不重视,我也不会去管它,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自甘消失的观点。应该有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个市场。当然我觉得作家的使命感你不能放弃。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文学的认知,像是比赛,有新的就有旧的,新的一定比旧的好,旧的一定有弊病,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东西。中国的老百姓都喜欢新的东西,都喜欢追求新的生活方式,什么与国际接轨了就是好的,这个意识在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当中非常普遍。他们迫不及待地盼望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就是这个现象背后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这种现象就会不断自我复制。出版商用这个来炒作,就是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市场化的过程中,大家一下子全都乱了阵脚。社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衡量成功,你是不是成功人士,你能挣多少钱,那么这就要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对每个人的心理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白烨:这些问题的出现不光是一种写作现象,它实际上也是一种运作效果,或者是一种消费现象。我个人看法,作者无错,炒作者有过,因为我觉得包括像韩寒,他那种非常带有另类色彩的意义,一种写作姿态,被炒得那么火,提得那么多,对他个人肯定是有影响的。图书出版这几年越来越追求最大的利润,至于做什么书,那是手段,目的在钱。我个人认为出版这个行当不光是一个经济效益或者是商业行为,它本身是一种文化行为,而这个文化行为就应当讲两个效益,既讲经济效益,还要讲社会效益,不能光讲经济效益。虽然是两个效益,但是讲社会效益是软的,讲经济效益是硬的,目前是这样一个现象。所以从这个迹象来看,我个人对这一点表示忧虑。 格非:我们现在这个市场本身处于初级阶段,刚刚打开,所以我们着急也没有用。莫言在清华讲,我辛辛苦苦写一本书,撑死了一万册,那帮小孩一出手就是八九十万册,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多管,至少我个人可以肯定,我也不是说对金钱没有兴趣,我也是很有兴趣,但是你得拿到这个钱,而且我觉得除了金钱的兴趣外,还有更大的兴趣,比如说乐趣,比如说写作当中我跟读者的交流,比如说我自己的写作带给我的这种快乐,我觉得这个可能比金钱更大一点。 一次关于“80后”文学的多维、立体、全面的呈现,一次长达十余年的追踪式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