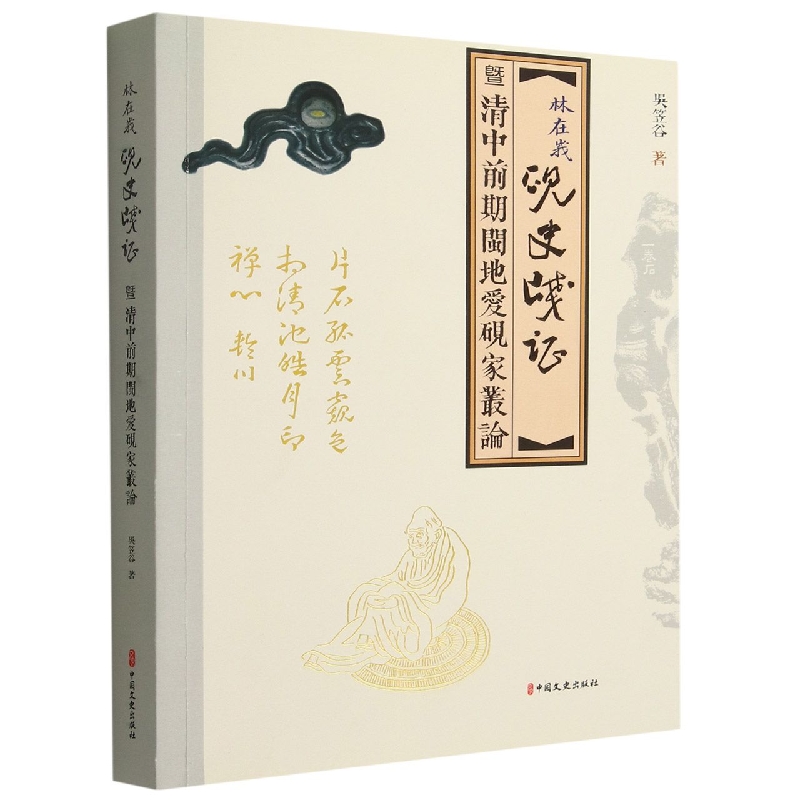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文史
原售价: 198.00
折扣价: 120.80
折扣购买: 林在峨砚史笺证(曁清中前期闽地爱砚家丛论)
ISBN: 97875205384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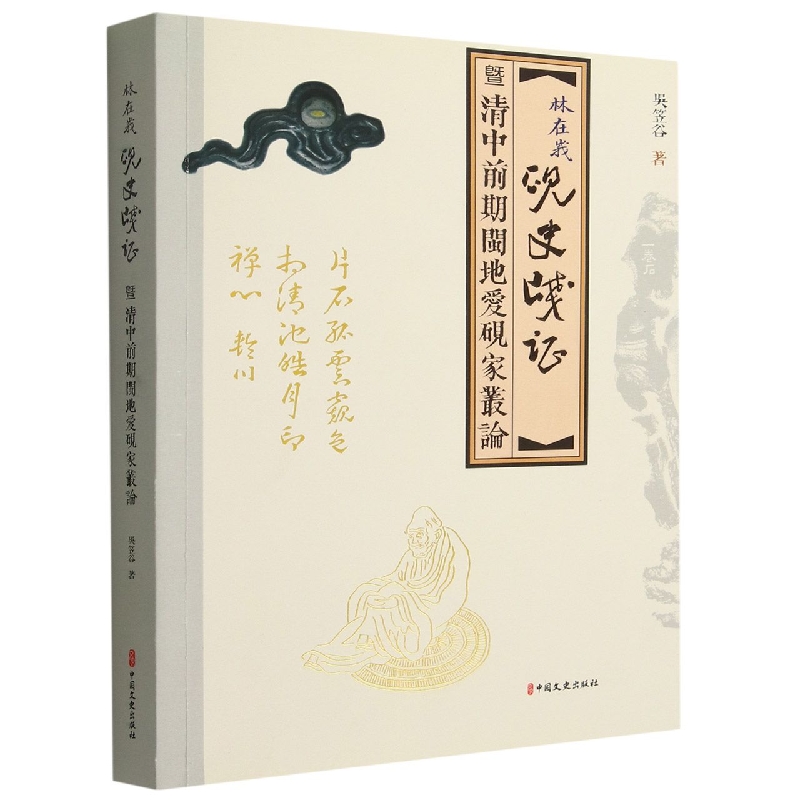
吴笠谷,安徽歙县人,现居北京。1994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现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砚文化委员会主任,中央文旅管理干部学院、国家开放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客座教授,合肥工业大学和湘潭大学特聘硕士生导师,中央电视台《一槌定音》栏目特邀鉴定专家,韩国秋史学会特聘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获得者。 先后应邀在韩国秋史博物馆、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个人作品展。作品被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馆、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韩国总统府、韩国秋史博物馆收藏。 首倡确立“砚学”专门学。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砚学专著《赝砚考》《名砚辨》,以及韩国版专集《吴笠谷制砚、藏砚及书画艺术》。被誉为当代学者型制砚家代表人物。
自序:寄情图史片石间 故纸留与后人看 观堂先生王国维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宋元戏曲史序》)换言之,文化,本质上是时代的附庸,依傍于人文环境、时代浪潮而兴衰、沉浮。今世是一个极其推崇“传统文化”的时代,但由于历史断层而导致的时代局限性,也是一个与传统文化,尤其与传统主流文化——“雅文化”貌合神离的时代。当代砚文化所处的尴尬境地,其深层原因也正在于此(拙著《名砚辨》的“自序”《论当代砚文化式微之成因及复兴的机缘》对此问题已有详述)。 所谓“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古调之所以不弹,多因曲高和寡,不合时宜。但是,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人坐冷板凳,致力于做一些小众化的冷僻学问。这或许更契合做学问的本质——寂寞之道。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钱锺书致郑朝宗信精选》,见《郑朝宗纪念文集》)此为正说;可视为正话反说的,则有清人项廷纪所言:“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忆云词?甲稿序》)人非圣贤,贤如东坡居士尚有“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之说,何况碌碌苟世之普罗大众?所以,“无益之事”可能更有益于人的天性与本心需求,经史子集“名山事业”中,集部“杂著”类闲书或许更能适人意、慰人心。 清人钻故纸堆,兴考据学,避文字祸固为习说要因,而金石考据之迷人处,一如行山阴道上,光风霁月之境,令人目不暇接。本人历年来搜藏古砚,深究砚学,于个中佳处亦颇有体味。而今世有待挖掘研究的砚学古文献可谓繁多——林在峨《砚史》即是其中一片瑰丽的珍璞。 为林氏《砚史》作笺注的初心,首先是感触于林氏及清中前期闽地爱砚家群体个人遭际之多厄。诸人中,无论官至一品者,还是沉沦下僚者,大多结局不佳。以致于多人的诗文稿皆未付梓刊刻,甚至抄本也已失传。其中砚名、诗名最盛的黄任,七考进士不第,只以举人身份出任县令,且三年即被罢归,晚年困窘,名砚尽散,连藏砚室“十砚轩”也转售他人。林在峨本人更是怀才不遇,虽才名动公卿,被大学士赵国麟目为国士,但科名仅止于监生。晚年流寓吴地,客死他乡,所著诗文集《陶舫集》也未刊刻行世(稿本似亦失传)。一生功业,唯有几枚遗砚、一部《砚史》稿本传世。而作为一个带有区域特性的爱砚群体,闽地诸人砚学的整体成就,在有清一代却堪称卓然大观。因此,总体盖棺论定该群体,可谓宦业三流、文学二流、砚学一流。读诸人砚铭,考诸人行迹,直令人掩卷叹息,感慨系之。 其次,是感动于诸人对砚的笃爱。典型如该群体领袖人物黄任、余甸,尤其黄任,不仅“有研癖,每典衣缩食以求”,且“以耽砚劾归”——被同僚告密其主持开坑时私藏美石,从而被罢归。因黄氏嗜砚名高,后世遂演绎出“千金买婢”“蓄尼养砚”等野说美谈。余甸罢官归里,时与黄任赏砚制铭消闲遣兴。因其题铭辞佳字美,时人持砚求题者众。闽地玩砚风气之盛,实由此滥觞而来。林在峨虽曾参与纂修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但总其一生,多属在野文人、艺人。其与砚结缘之深,乃如高邮文人续缙题《砚史》跋文所言: 或曰:“士当嗜其远者、大者。砚石虽美,犹卷石耳,何必积思蓄精,专事乎是?”呜呼!士达则善天下,穷则寄情图史水木竹石间,古之人皆然。轮川真识穷达之宜者也。 林氏可谓倾心于卷石之美,慰心在名砚之中,从而独善其身了。 上述种种况味,皆于我心有戚戚焉。故不吝笔墨,对该群体中各家其人、其艺、其砚、其事,皆作一碑传式的评注。 就学术研究层面而言,林氏《砚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砚文化史,而是一部辑录清中前期时人砚铭砚诗的书稿,但其内容多出于国学经典,能给后人撰写铭砚以诸多启示与借鉴。古人云“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其实艺亦可以言志,器亦可以载道。“言志”与“载道”正是名人砚、铭文砚的特性,亦是林在峨《砚史》之人文价值所在。此外,书中所收诸砚,大多据实物或砚拓注明铭辞、款识的字体及用印,有些还附有拓跋,这为后人按图索骥考证闽中诸人遗砚及部分时人藏砚提供了极大便利,堪称一部砚学要典。因此,对我而言,通过笺注此书并对诸家生平的梳理钩沉,不仅在砚学研究上获益良多,而且深感砚之聚散离合,与世事之盛衰,人生之沉浮,亦多有共通之处。从而对“不为物役”收藏观也有更深刻的自省与体悟。 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完稿交出版社时,书名原为《清中前期闽地玩砚群体述评暨林在峨〈砚史〉笺证》。但对书名中“玩砚群体”的定义颇为纠结,曾拟用“藏砚群体”,但闽中诸人不仅藏砚,也题铭,黄任、林在峨还兼擅刻铭,与一般收而藏之的“收藏家”有所不同,定位“藏砚家”难以彰显诸人的砚学综合素养。而“玩”字,本身也含有一定贬义成分(比如“褻玩”),且“玩砚”这词流行也较晚近,偏于俚浅,比如著名的“东坡玩砚”只是近现代人的称法,古称“东坡爱砚”,是古典绘画、工艺题材中著名的文人雅士“四爱”“八爱”之一。砚界有所谓“美人爱鉴(镜),文人爱砚”“武人爱剑,文人爱砚”之说。前者化用于明人陈继儒《妮古录》中语(原文: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后者出处难考,与林氏《砚史》卷一余甸“首选砚”铭云“武人剑,文人砚”、卷八余甸诗云“武人爱剑文人研(砚),启发清言有好题”意思相同。综上所述,可见“爱砚”是古人对藏砚最常见的称谓(其次尚有“赏砚”),所以,日本国藏砚界,亦称藏砚家为“爱砚家”。 所谓“礼失而求诸于野”,古汉语中的梵文舶来词很多,近现代汉语中的日文舶来词更是不胜枚举。有鉴于此,个人认为,“爱砚家”显然比“藏砚家”词义涵盖面更广,含义更丰富、全面,也更适用于通称闽中爱砚家群体,所以原定书名中的“玩砚群体”改为现名“爱砚家”(因已付排,正文中的“玩砚群体”字样未作改动)。 最后想说的是,名砚鉴藏,尤其砚学研究,须有一定的旧学(国学)准入门槛。古时“文人爱砚”,其爱砚群体的主流是文人士大夫,所以古时“砚学”近乎“显学”。由于当代爱砚群体其社会身份、传统学养有所不同,导致审美取向、收藏观念有所异变,但砚学、砚文化作为传统主流文化——“雅文化”之一脉,自有其内在的、穿透时空的生命力。桐城诗人方世举为林氏《砚史》所题诗云: 文人大抵砚为田,小史标名亦胜缘。 石若能言应笑语,也同学士上凌烟。 ——或许,后来的爱砚家,当能从林在峨《砚史》以及本人的诠释中找到更多的共鸣…… 吴笠谷 壬寅霜降后四日于北京西二环斫云楼 砚学、砚文化作为传统主流文化——“雅文化”之一脉,自有其内在的、穿透时空的生命力。桐城诗人方世举为林氏《砚史》所题诗云: 文人大抵砚为田,小史标名亦胜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