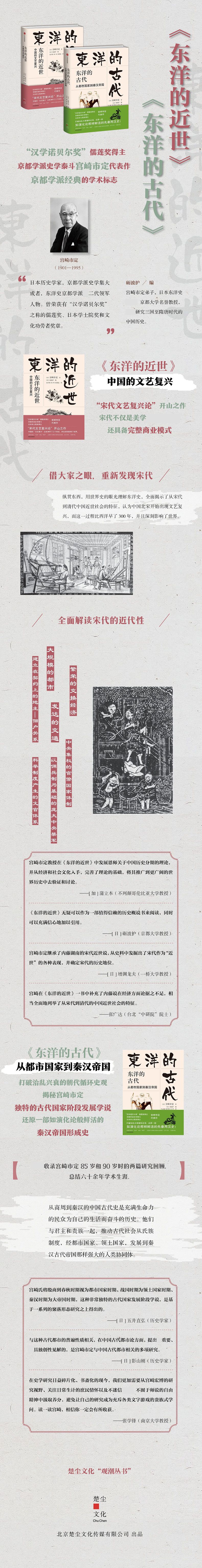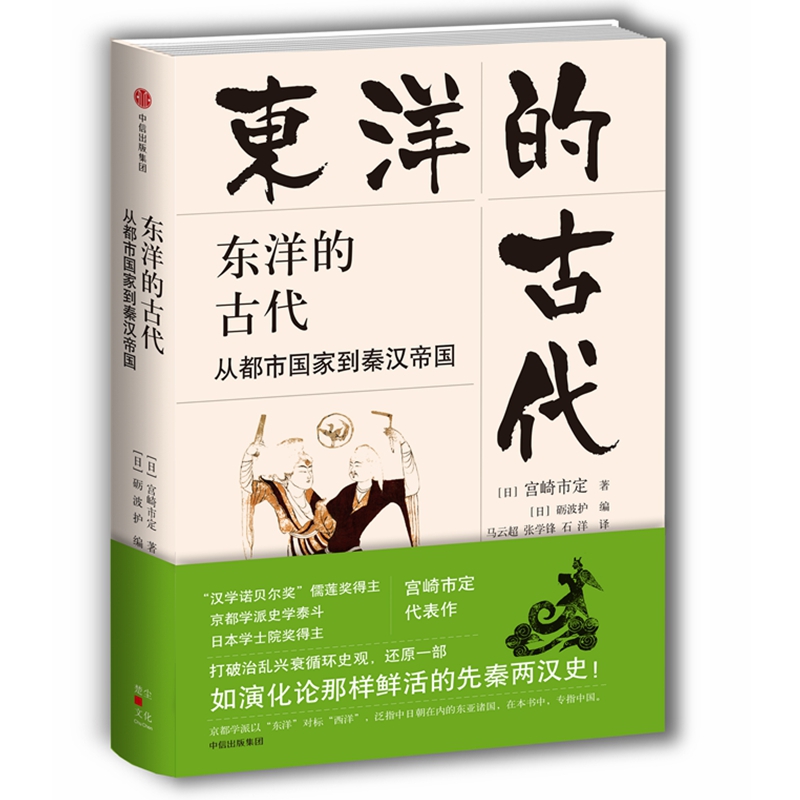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东洋的古代(从都市国家到秦汉帝国)(精)
ISBN: 97875086894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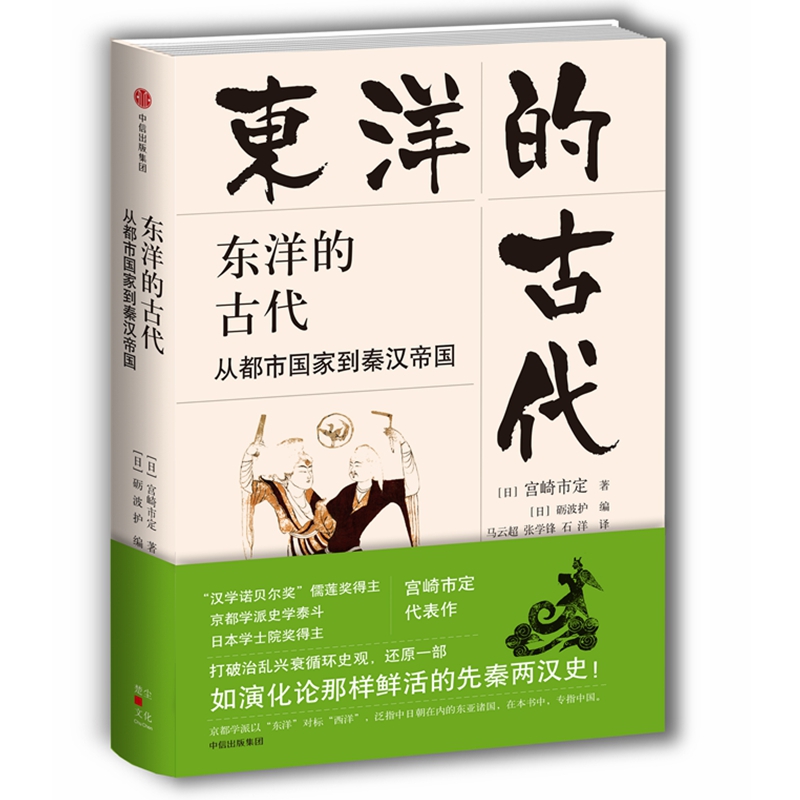
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历史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东洋史京都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先后任京都大学教授,巴黎大学、哈佛大学、汉堡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曾荣获有“汉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日本学士院奖和文化功劳者奖章。代表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科举》《东洋的近世》等。 砺波护,日本东洋史专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专门研究三国至隋唐时代的中国历史。代表作有《隋唐佛教国家》《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等。
春秋时期的都市国家 大凡都市国家都具有保守和进步的双面性。一方面,保守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它们以从前的氏族制为基础,以祭祀为中心,力图将长久以来的族人结合体维持下去,这样就必然会固守既有的阶级差别。另一方面,都市国家的进步性又十分明显,这种进步性建立在都市国家市民自觉的基础上,他们把氏族制作为过去了的东西加以抛弃,跨越氏族制的旧形骸,以崭新的都市国家新生活为理想,力图建立起与从前完全不同的社会。支持前者的是有权势的上层人物,推进后者的是下层的庶民。 周民族具有与罗马相同的氏族制度。罗马是由三百个氏族(Gens)集合起来建立的国家,各个氏族又分为若干个家族(Familia)。因此,罗马的贵族除了个人的名字本名(Praenomen)外,还有表示氏族的名字族名(Nomen)和表示家族的名字姓氏(Cognomen),合起来共有三个名字,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便是如此。一般情况下,男子用个人的名字和家族的名字,女子与此不同,仅用氏族的名字,如普布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Scipio)的妹妹则称科尔内利乌斯(Cornelia)。中国的姓相当于罗马的氏族,氏则相当于罗马的家族。所以,周的贵族也有三个名字,男子通常用个人的名字和氏的名字,女子与此不同,仅称姓。周、鲁、卫等国的君主各以国名为氏,而他们的姓则均为姬。因此,这些国家的女子都称“姬”,此后“姬”就逐渐成为泛称贵族女子的普通名词了。男子与此不同,如鲁僖公叫鲁申,即用了氏和个人的名字,而不称姬姓。同姓之间有不通婚的习惯。如果是姬姓,就要避开姬姓而与姜姓、姞姓等异姓联姻。“姓”这个字本身,以及姬、姜、姞等表示姓的字,多从“女”字旁,曾经有一些人提出这是母系氏族制度的遗风等说法,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无疑是由于女子称姓的缘故。庶民可能是被征服民族的后裔,正与罗马人一样,他们没有姓只有氏。 同姓集会或社交的场所是宗庙,集会的机会是对祖先的祭祀。这种集会是不让异姓参与的,带有很强的封闭性。当然,如果是君主的祭祀,则异姓的臣下也要参加,但他们只能处于末席。当时所用的祭器便是遗留至今的众多青铜器,祭祀的仪式就是“礼”。祭祀的过程中要献上牺牲,取牺牲的血来涂祭器,这便是“釁”。青铜器的表面雕刻着烦琐的饕餮纹、雷纹等装饰纹样,这能使“釁”的效果更加突出。有时则把战争中捕获的俘虏作为牺牲,把他们的血涂在祭器上。想到这里,便觉得青铜器所发出的孔雀翎般的蓝光并不是什么使人舒服的东西。 在这种氛围下举行的同姓集会或社交情景也大致可以想象。为了在集会时不致因席次等问题发生争吵,于是规定了上下的等级,这便是宗法。 除了封闭性的宗庙祭祀社交外,也有开放性的市民社交,这种社交是以市为中心展开的。不用说,市是布满店肆的特定的商业区,但它又不仅仅是事务性的买卖场所,同时也是娱乐、赶热闹等市民的社交场所和休憩场所。当然,有关春秋时期市的记载很少,但由于市的繁荣一直持续到后代,战国到汉代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变,因此我们可以依据后代市的记载来描述春秋时期的基本情形。战国时燕国的市上,荆轲令友操琴,且歌且泣。可见,市是市民凑集,各显技艺,尽情欢乐的娱乐场所。 市虽然带有很强的庶民性,但当时的贵族阶级并不像后世那样与庶民完全悬隔,依然保留着作为市民的一分子而与市民平等的一面。齐国大臣晏平仲说自家离市近,很方便,这位俭朴的大臣也过着“待市而食”的庶民生活。就是齐国的君主桓公,也曾在窗下与造车的老车匠谈过话,这般浓烈的庶民气息,在后世是不可想象的。这种以都市为中心、带有古代市民特征的开放性生活,一直持续到了汉代。 任何地方都一样,学问首先伴随着祭祀发展起来。祭祀不是单纯的仪式,而是所谓的“祭事”,当然也包含政治在内。祭祀伴随着占卜,占卜产生了文字,文字也被刻在宗庙的祭器上,而掌管占卜、文字和记录的就是“史”。 占卜的方法,从烧炙龟甲兽骨据其开裂情况判断吉凶,发展到后来成为据蓍草是奇数还是偶数来判断吉凶的筮。信手取来的蓍草,在数数的同时,每两根交叉叠放在一起,排列成“×××”的形状,这种形状就是后来的“爻”字。最后剩下的若是偶数便是凶,因此“凶”字作偶数的两根蓍草残留在箱函中的形状。若剩下的是奇数便是吉,“吉”字的上部是“×”和“一”,其义在于“一”,“一”与“壹”同,“壹”的古音读作“吉”。 在学、教、校、黉等有关学问和教育的文字里都含有“爻”字,这是值得注意的。这证实了掌管爻,即掌管卜筮的史,同时也掌管着知识,与之相关的知识传授便是教育。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學”(学)字,字的上部是“ ”,做双手操爻状,下部是“ ”,做台下有孩子观看状。总起来说就是,孩子看着大人在台上操弄着爻,并向他学习,这便是“學”。若用“见”来代替“子”,则成为“覺”字,也就是记忆的意思。孩子的学习成绩提不高,就从旁用棍棒敲打,这样在“學”字旁加上表示手持棍棒的“攴”,便成“斅”,简化后即成为“教”字。 文字和学问从封闭性的宗庙逐渐走向半开放,在“史”举办的私塾里面向大众。在有着屋顶“亠”的木构建筑物里排列爻的地方,这便是“校”。在众多的“史”中,作为伟大教育家活跃在教学舞台上的是孔子。孔子的教育理念是:所谓学,既不是博识,也不是技术,而是人格的完善。 在希腊,学问的活动更是扩展到了市,苏格拉底在市的广场上揪住年轻人对谈就是个例子。但是在中国,学问虽然从宗庙走向私塾,呈现出开放的势态,但却没有扩展到市。这是因为中国的都市国家寿命太短,历史很快就进入领土国家的时代,出现了强大的王权及宫廷社交,学问再度被收回到宫廷这一封闭性的社会里去了。民主主义是与市共同成长的,学问没有扩展到市,这是中国的不幸。 但是,在中国,学问向市扩展的趋势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战国末年,秦国吕不韦延揽宾客,作《吕氏春秋》,书成之后将之公布于咸阳市上,有能改正一字者赏千金,这也说明书在市上被人阅读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司马楚之在西汉长安城的东市开肆占卦,宋忠和贾谊曾到那里去访学,与他讨论先王的圣人之道。东汉王充在洛阳的市里站着读书治学。但是,学问向市的扩展已经错过最好的时机,庶民性的学问还没来得及建立,便被宫廷的学问压倒了。 同样的现象在文字的发展上也可以看得到。无论什么地方,文字都是先以绘画文字、象形文字的形式发生的,掌管文字的人都是宗教人员或祭司。嗣后,文字渐渐向庶民开放,文字一旦到了庶民手里,便产生了表音文字。但是,象形文字也不是一步就能跨入到表音文字,其间有一个中间阶段。布雷斯特德(JamesHenry Breasted) 的《古代史》(Ancient Times,Boston,1916)第43 页介绍了下面这组埃及文字: 右起第一个图像表示人,第二个把手放在口边,表示吃。这两个是象形文字。其余的三个,从右上起依次表示ch、q、r 的音符,是作为表音文字使用的,它们配合母音拼读,就表示出贫困、饥饿等意思。这组文字意在结合象形和音符两个部分来表示明确的意思。而音符部分被充分使用以后,单用音符也就能表达意思了。这些表音符号经过再次整理规范,就形成表音文字的字母,而右边的象形文字部分就脱落消失了。 中国的汉字大多数是由偏和旁组成的。偏是象形的部分,用它来表示某一限定范围内的字意;旁是发音符号,用音来表示某一限定范围内的字音。依靠这两个限定,就产生出了具有明确字意的文字。若用汉字来表示上面介绍的那组埃及文字,这便是“饿”字。“饿”“蛾”“鹅”,发音全都是“我”,但这不是虫子的“我”,也不是鸟儿的“我”,而是与饮食有关的“我”,所以用“食(饣)”加以限定。另一方面,在有关“食”的语言中有饭、饴、饱等许多概念,但这里并不是指这些概念,而是指有着“我”这个读音的那个“食”的概念,所以加上“我”旁,以表示关于食的概念中的一个特定的意思。因此,大部分汉字既不是纯粹的象形文字,也不是纯粹的表音文字,而是两者兼备。把汉字的性质理解为从象形文字向表音文字发展的过渡形式,是比较合乎历史事实的。若问汉字的发展为什么会中途停顿下来,那么我的回答就是,它还没有完全彻底地转化为庶民的文字。 ★打破治乱兴衰的朝代循环史观,还原一部如演化论般鲜活的秦汉帝国形成史! ★“汉学诺贝尔”儒莲奖得主、史学泰斗宫崎市定学术代表作,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经典的学术标志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坐标系。 ★殷商到春秋为都市国家时期,战国为领土国家时期,秦汉为大帝国时期,揭秘宫崎市定独特的古代国家阶段发展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