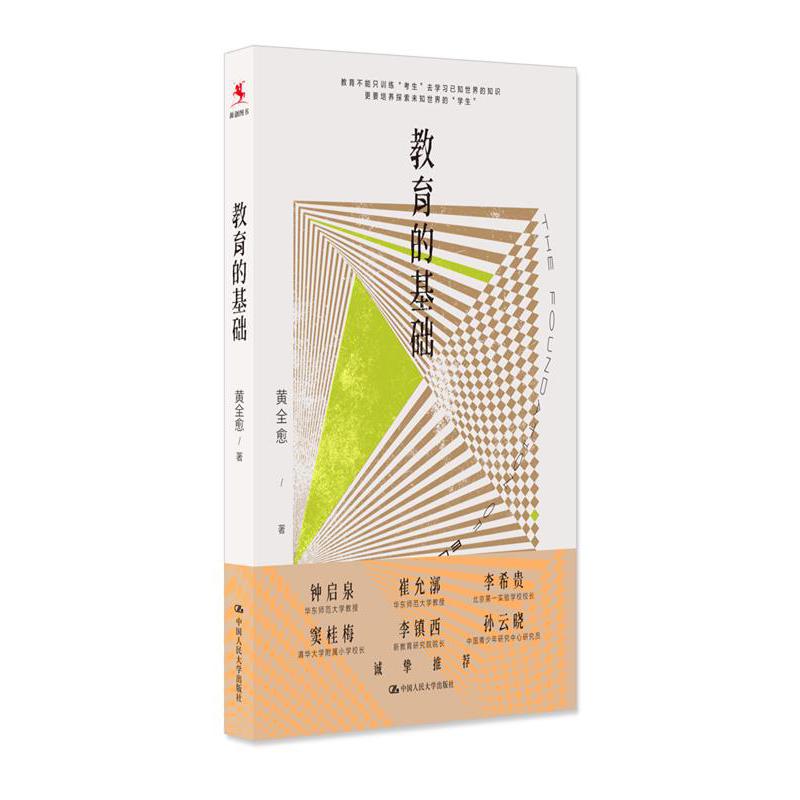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5.60
折扣购买: 教育的基础
ISBN: 9787300320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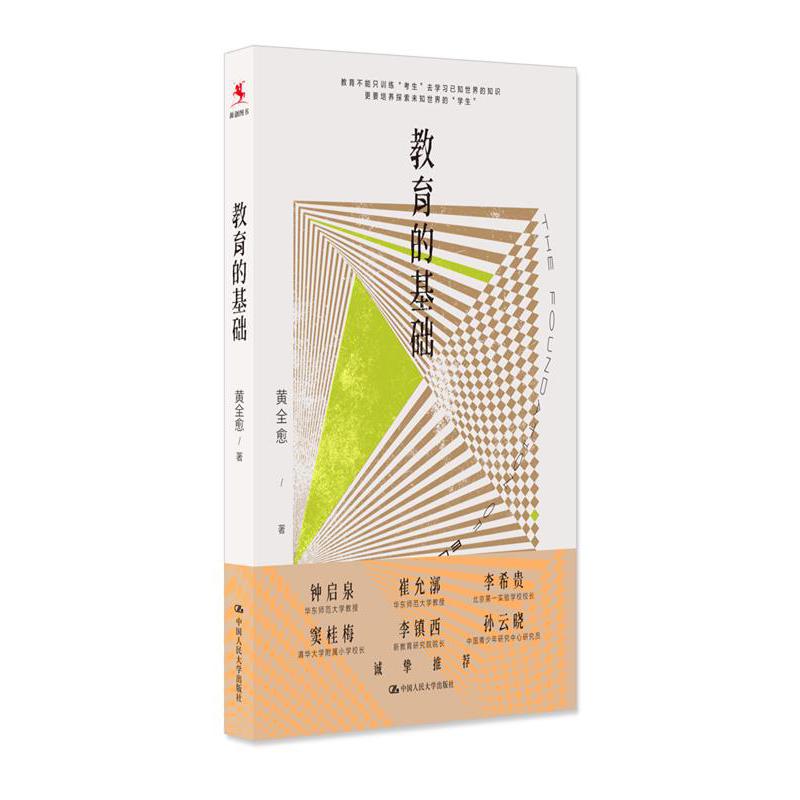
黄全愈,旅美教育学家。先后担任美国迈阿密大学亚洲、亚—美学科部主任,孔子学院院长,中山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老教授协会基教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被迈阿密大学授予“(学术)重大影响奖”,并被提名为杰出教授。 黄全愈是中美教育和文化比较专家,他长期致力于中美教育和文化交流。其作品《混血虎》曾荣登《纽约时报》《出版家周刊》推荐书单。所著中美教育比较系列,在中国教育界不断引起强烈反响,其中,《素质教育在美国》被誉为“20世纪中国的《爱弥儿》”。
自 序
我儿子来美国时刚5岁,那时还懵懵懂懂,上幼儿园会说的第一句英语是“厕所在哪儿”——怕“急”起来找不到北!
说实在的,别说孩子,我们自己在哪儿、教育在哪儿,都有点儿找不到北……
小学一年级,几乎每天,儿子一进门,就很有点儿得意地嚷嚷当天的“杰作”:“今天,老师问‘2+5等于几’,大家用十个手指头还没算利索,我就抢答‘等于21÷3’。小朋友个个蒙圈,老师也蒙圈了——愣愣地看着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和蒙圈的小朋友们。”……
那时,我嫌美国基础教育太小儿科,孩子啥都不懂,整天就知道傻玩……说出来你都不敢相信:学习从1数到100,要数整整一个星期(其实,“数字”与“数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多大人都没弄明白,直接拿数字替换数量)。小皇帝不急,老爸急啊,不带这样浪费孩子生命的!趁着图书馆处理旧书,就给儿子买了一整套数学课本,一美元一本砖头般厚重的教材,一整套得开车拉回家。不过,物有所值,课本编得非常简明易懂。我让儿子每天自学四页,这不,他把同班同学(包括我博导的孩子)甩了七八十条街(后来尝到苦果,这是后话)。
既然儿子把所有的孩子,包括我博导的孩子都甩得不见踪影,那我还来这里苦哈哈地学什么呢?这个新版“龟兔赛跑”,到底谁是龟?谁又是兔?我是越想越困惑。
小学二年级,某天,儿子一进门就叫嚷,要到图书馆找资料,说是对研究蓝鲸很感兴趣,学校要求写“科研论文”……
我瞠目结舌——怀疑人生足足三秒钟,不是我这种博士研究生才做“研究”吗?8岁小屁孩儿也叫嚷做“科研”?!
后来,“蒙圈”一个接一个……
某日,我坐在课堂里,听我最佩服的博导(我打心眼里佩服的人屈指可数——他能使我从似懂非懂的混沌状态升华到豁然开朗的“悟”的境界)在不落窠臼、鞭辟入里、一剑封喉地剖析、抨击美国教育的社会文化背景,犹如庖丁解牛:“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
我猛然有点儿蒙,又有点儿悟。不禁自问:这位导师严谨深刻、洞见犀利、一箭穿心、深入浅出的“謋然已解”功力是从哪里来的?他也是读的当地小学吗?他也曾花整整一周从1数到100吗?他小学一年级时也不懂2+5=21÷3吗?他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吗?他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他是怎么走出小学的混混沌沌,成为大名鼎鼎的教授的?小儿科的沙滩似的基础教育,怎么能承载高耸入云的科技摩天大厦?
我思考了很久很久,也反思了很多很多。
我豁然自醒:难道不是美国的基础教育小儿科,而是我对美国基础教育的理解太小儿科?
…………
半个世纪前,我插队时的生产队长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我说(知青)老弟啊,这只桶能装多少水,就看最短的那块桶板!”
朴质而深邃的水桶理论!
后来,远渡重洋来“洋插队”,导师说:“选修对您的祖国最有用的专业!”
我一直以为,中国的基础教育世界第一,之所以没有世界一流大学,问题出在高等教育……于是,我选择了“高等教育管理”专业。
导师那天的“庖丁解牛”,让我惕然且謋然地意识到:虽然美国的高等教育也值得好好研究,但更迷惑人、更困惑人、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更值得研究的,竟然是我从来就看不上眼的“一塌糊涂”的美国基础教育!
何为基础?
一个人要上跃,就必须先下蹲,牢牢地脚踏“实地”——基础!
一栋大厦能有多宏伟,能否高耸入云,取决于它的基础有多敦多厚,而不是它的屋顶有多尖多美。
解开“死结”,犹如打通任督二脉!于是,我把研究方向改为“跨文化的概念比较与分析”。
经过多年研究,我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二三四”素质教育核心理论体系。
“一”指多元教育的归元一体化——返本归元的终极目的,是具备能引爆人生“核裂变”的十大素质,去实现个人的自我完善。
“二”指教育的“双核理论”。权威的书评刊物《纽约时报书评》,曾头版头条隆重推出长篇评论,指出我的英文专著《混血虎》(The Hybrid Tiger: Secrets of the Extraordinary Success of Asian-American Kids)详细比较和分析了中美教育核心价值观的异同,解答了困惑美国人多年的问题:为什么亚裔只占美国人口的4.43%,尽管以哈佛为首的名校对亚裔设置了隐性录取上限(哈佛的上限一般是18%—20%,自2015年60多个亚裔团体状告哈佛后,2022年亚裔生录取率达到27.8%,2023年达到29.9%,为史上最高),但美国前20名顶尖大学仍录取了约20%的亚裔生?这一比例约为人口比例的5倍。此外,亚裔是人均获硕士、博士学位最多的族裔,家庭平均年收入全美最高。我用“双核理论”驳斥偏激的“虎妈”(蔡美儿):只有吸纳中美教育的精髓,才能产生虎虎生威的“混血虎”。比如,有“少年诺贝尔奖”之称的美国雷杰纳隆科学奖,2021年40位获奖选手,有16名华裔,占比40%。
同时,我又提出一个十分发人深省的扎心问题(国内某出版社社长誉为“美国亚裔教育的‘钱学森之问’”):虽然美国前20名大学的“龙虎榜”上亚裔生约占20%,但为何美国最牛、最尖端的20%——诺贝尔奖得主、大科学家、大教授、大律师、大企业家等,亚裔占比与20%相去甚远?
华裔以到脸书(Facebook)争得一个高薪职位为荣,扎克伯格则从哈佛跳出互联网的“局”,去设计一个脸书的“局”给我们玩。现在,他更是搞了一个“元宇宙”给人们去玩。
我儿子从一个懵懵懂懂、只会问“厕所在哪儿”的小屁孩儿,成为世界知名律所派到法庭上唇枪舌剑的最年轻的出庭律师与持股合伙人,并荣获美国Law360(一家法律新闻与分析权威媒体)2021年度“40岁以下出庭律师新星”荣誉;2022年6月21日,美国《商业内幕》报道了我儿子与其他14位美国年轻的出庭律师,因在审判、仲裁和上诉中表现优异,被评为2022年度“40岁以下出庭律师新星”的消息(两度获得殊荣,而且是华裔);7月他又被选为全美各界23位值得关注的亚裔领袖。看起来挺成功,但格局不大,都是赢在局内,都是在人家设计好的法律框架和条文下玩游戏,从未想过到局外去当那顶尖的20%——去设计、制定法律条文,让别人去玩。
这不是“凡尔赛”,真是我的家庭教育给儿子带来的局限。故曰:“成”也中式家教,“败”也中式家教也。
“三”指“三脚架理论”,给教育的“四位一体”(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设定各自的位置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点成一面,再由此形成三只支撑脚,承载教育的终极受体——人的自我教育,类似照相机的“三脚架”。
亚裔生为什么优秀?图解“三脚架理论”,就一目了然。请参阅本书《美国孩子的毛遂自荐,让我“怀疑人生”》一文,在此不赘述。
“四”指我的“四区理论”,从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去阐释人如何从第1区进入第4区,从而完成自我教育过程。“四区理论”既分析了人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行为的形成过程,也剖析了“我们是怎么用正确答案把孩子教傻的”这样一个极其严肃且发人深省的问题。
甚感欣慰的是,我在深入透视美国令人迷惑的教育现象的同时,又有对美国教育理论从底层到核心的深度思考,并条分缕析地剖析了生我养我那片土地上令人焦虑的教育。
在形成自己的素质教育理论的同时,我重新反思:何为基础教育的“基础”?
理论可能有些枯燥、无趣,但这本书的行文会尽量有料、有趣、有品——把“有料”融进“有趣”中,使之“有品”。
换言之,保持“举重若轻”的风格——把理论的干货融合进有趣的故事中,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豁然开朗,同时又有莫名的沉重。
实际上,这本书也是我的《素质教育在美国》系列与《混血虎》,以及我儿子青少年时出版的《我在美国读初中》和《我在美国读高中》(学生版《素质教育在美国》)的精华荟萃。请看部分文章的标题:
“问题化学习”应该是把“?”看作鱼钩的学习
创造性是“教”出来的吗
泄露“天机”——名校毕业也需要的10种核心素质
什么才是“土猪”人生最关键的考卷
“神童教育”的“神”在哪里
STEM是中国教育的希望吗
素质教育是个伪命题吗
敢于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何为体育的“育”
从走课制里能“走”出什么
国家强大的根源不在大学,而在基础教育
…………
因为篇幅原因,报纸、杂志刊发的文章可能有删减,而本书收集的基本是全稿,并且有些必要的、与时俱进的注释。
本书中的文章是针对不同的议题分开撰写的,有些辩驳性的文章又必须引用自己已有的某些论点或论据进行辩驳,因此,很难避免某些重复,但本书已尽力修改。
本书看似合集,但由于主线谈的是基础教育,也可以看作既比较中美教育又聚焦基础教育的专著。
其实,这还是合集的画风——把散见于众多平台的文章,为读者“一网打尽”,让读者“尽收眼底”。
许多人认为中美之间“卡脖子”的是科技,其实,真正“卡脖子”的是教育!试问:科技从何而来?来自教育!
为什么起跑领先的孩子,后来却落后了?为什么我儿子及其他亚裔孩子原来甩美国孩子七八十条街,到高中却被追上了?这就是要害——基础教育的“基础”(正是我数十年的研究内容,也是本书的主题)。我反复深思“为什么”:为什么世界前100名大学中的大多数在美国“排排坐,吃果果”?为什么美国截至2021年获得了333枚诺贝尔科学奖?为什么数学基础教育一路被吊打的美国,至2021年,仅哈佛(含校友、在职人员、兼职人员等)就获得了18枚国际最高数学奖——菲尔兹奖,普林斯顿也获得了16枚?……
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样的基础教育承载了这些结果?
这是我们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中国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某些方面的差距仍不容忽视。
许多人提倡“科技兴国”;其实,应该倡导“科教兴国”——以“教”为本的“科教兴国”。
中国科技公司的领头羊之一华为的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先生,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他认为,国家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
其实,基础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因而,国家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基础教育的竞争。
能把“人口大国”变为“人才大国”的,唯有实施素质教育的基础教育!
只有坚持“双减”,改革应试教育,推行素质教育,才能改变一代人以考为本的学习方式和思维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人才的素质,推动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
精彩书摘
创造性是“教”出来的吗
钱颖一教授最近的好文《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理念与实践》,论述了被视为未来孩子必须具备的核心素质4C中的2C(critical thinking和creative thinking)。其中不乏令人击节之处,但学术需碰撞才出火花。
我认为,创造性是教不出来的,因为教违背了教育规律,越教孩子越没创造性。
一、为什么创造性不能教
我曾有一位叫达琳的在职硕士生,是位小学美术老师。她到昆明做短期交流时,很多中国老师问她“在美国的课堂上,怎样教孩子的创造性”,并再三要求她示范。这位美国小学老师感到很困惑:创造性怎么能“教”呢?!无论怎么解释,疑者恒疑。
或信或疑,牵扯到三个问题:什么是创造性?技能等于创造性吗?创造性是怎么来的?
创造必须满足两个“有”的条件:一是“前所未有”,即“创”;二是“无中生有”,即“造”。要做到“前所未有”,就必须打破常规;要做到“无中生有”,就必须在打破常规的基础上产生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没有“创”,顶多是旧饭新炒;没有“造”,就只能是胡思乱想。
钱教授说:“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然而,这个“首先”却有争议。
钱教授设计了一个公式:创造性思维=知识×好奇心和想象力×价值取向。
若公式成立,顺序似应倒过来:知识不应是“首先”,而应放在末位。人类的很多创造都源于对已知知识的无视,或说正因为对知识的无知,才能引爆创造性的第一朵火花——好奇心。越有知,越不好奇,越不敢越雷池。谁敢问“蚯蚓没有脚怎么爬行”?唯孩子无知,才好奇,才有去“知”的欲望——做研究的第一个动力。
另外,好奇心、想象力不应是“和”的关系,因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创造的过程中各具不同的功能。
同时,“创”“造”是一对矛盾。“创”的天敌是知识、常规、经验、理智、习惯、正确、成功……总之,过去的一切都可能是障碍。而“造”恰恰需要在“创”打破一切的基础上,去“无中生有”。知识属“造”,应排在末位。
最后,钱教授提到了在创造中价值取向的作用,如短期功利、长期功利、非功利的效用。功利是创造的重要动力,但他最推崇的“非功利”,也可以是不利于创造的、与世无争的躺平主义。而一些于创造来说不可或缺的非智力因素(百折不挠的探索毅力、力排众议的独立性、舍得一身剐的冒险精神等)却遗憾地缺席了公式。正所谓“敢想敢干”,思维(如想象)也需要勇气。许多人在创造中落荒而逃,就是因为哪怕在思维中也缺了不可或缺的非智力因素。
钱教授设计的是“创造性思维”公式,而我深以为,思维是内在的行为,行为是外在的思维,创造性思维是创造过程中的思维活动。离开创造性行为去谈创造性思维,恐成敢想不敢干,只“创”不“造”——只想“前所未有”,不敢“无中生有”。因此,我觉得,设计“创造性行为”公式似乎更有实际意义。若然,简单的乘法难以厘清好奇心、想象力、知识、其他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等的复杂关系。
钱教授认为:“创造力的核心是‘新’,发现新规律,发明新产品,运用新方法,解释或解决新问题。”
我认为,光是“新”不行,还得“造”出有现实意义的东西。用新方法解决老大难的“旧问题”,或用“旧方法”(知识)解决新问题,甚至用“旧知识”解决悬而未决的“旧问题”,都是创造。脸书用已知的网络“旧知识”解决交友难的“旧问题”,不是创造吗?突破某些知识和技能,进而造出有现实意义的新东西,就是创造!若能改变千篇一律的麦当劳食谱,开创出可口并利于健康的新麦当劳,亦为创造!是否“造”出了“新结果”,才是创造的关键。另外,创新性和创造性不同,创新性讲究“创”或“新”,不一定含“造”。
总之,人的创造性是指能打破常规去产生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的人之特性。
创造性等于技能吗?
技能指“能够掌握运用的某些专门技术”,如绘画、开车等。
再看“教”的定义:把知识或技能传授给他人。
现有的知识和技能是已知的东西,如绘画的知识和技能,可从A传到B,再由B传到C;同时,其他人也可重复获得。
而创造性为什么不能教?
1.已知的、现有的,可以教;而创造是未知的、“无中生有”的,怎么教?
2.创造是“前所未有”、不可重复的,可重复的是技能。
3.创造性不能传给他人。正像老师的智力不能传给学生一样,创造性是潜伏在人的生理和心理层面的特质,无法从A传到B。
创造性既然不可教,那能不能训练呢?
训练是“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受训者具有某种技能”。
由于许多“教”的内容无对错之分,因此多是点到为止。是齐白石的画好,还是徐悲鸿的好?见仁见智。把知识“传”给学生即可,学生可接受,可不接受(许多老师的“教”过界为变相的“训练”,在此不论)。而“训练”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强迫性。例如,军训要求整齐划一,麦当劳训练员工要求操作统一。
有条条框框、有强迫性、有限制性的训练,与不拘一格、强调破局、强调独特的创造性格格不入。创造性不是技能,而是潜伏在人的生理和心理层面的特质,教不出来,更遑论训练!
创造性(思维)只能培养——从小到大,经年累月地培养!
潜伏在人的生理和心理层面的创造性像种子一样,需要土壤、气候、灌溉、施肥,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创造性不能教,教违背教育规律,越教孩子越没创造性!
教育者的使命是营造利于培养学生创造性的环境和氛围。
二、中国的梅西都在培训班做奥数吗
有人说,最烦人的是足球;有人说,最迷惑人的是教育。
烦人是因为“恐韩”——中国男足总是被吊打;迷惑人是因为中国孩子年年获奥林匹克竞赛奖,但只开花不结果——在诺贝尔奖的终点落后。
不管是烦人还是迷惑人,都跟一个概念——创造性有关。
创造性是怎么来的?到底是训练还是培养出来的?人们不是老爱拿足球说事吗?君不见,正是这个在教育中“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使得我们选来选去就是选不出11个能冲出亚洲的足球明星。
有人说,中国男足沦落,皆因中国的梅西都在培训班做奥数。中国男足画风不堪,也有许多人认为,皆因球员没文化。若然,只需选11个博士,或给11个球员恶补文化即可。然而,以我从小踢球的经验来看,成绩好的往往球踢得烂,球踢得好的往往成绩烂。试想一下眯着双眼的“韦神”(韦东奕)踢点球,耸着双肩的范志毅或满身刺青的张琳芃“之乎者也”的模样是什么画风!兔牙小罗有文化吗?梅西又有啥文化?
若不是文化问题,症结又何在?
中国男足只训练球员的技能,不培养球员的创造性!
在中国,培养球员创造性的教练寸步难行。米卢被说是骗子、水货,原因有二。一是他的训练太“小儿科”,从来就没有练技能,只会让球员嬉戏玩球。但他这个“小儿科”奇迹般地把五个国家的足球队带进世界杯!因“小儿科”与神奇的结果反差太大,有人就想到了玄学、特异功能什么的。不过,如果到美国中小学看看,你就会发现怎么都是些“小儿科”的东西,学生坐无坐相,净在嘻嘻哈哈地玩……然而,美国获得了众多诺贝尔科学奖,其发达的科技就是源于这种“小儿科”。
“骗子说”的第二个原因,别说球迷、记者、教练,就连队员自己都成了丈二和尚:到底从米卢那儿学了啥!实际上,“小儿科”有学问!学问还挺深,包括重知识(技能)传授还是重能力培养、重学还是重用、重执行还是重创造、重外在的教还是重内在的悟……下面试着从“学多悟少”和“学少悟多”的关系,来揭开米卢“小儿科”的“卢”山真面目。
在中国上课,一节课学下来,什么大一小一、带括号的一、不带括号的一……可谓学得多矣。但这些大一小一都是老师传授的“二手货”——知识和技能。在美国学习,我总感到是学少悟多。老师多是营造一个培养环境,让学生参与创造(包括创造自己),因此,学生内心不断地“悟”出自己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并不是老师“教”的,更不是老师“交”给我的。
假如要我指出我的素质教育思想中,哪些是我的老师的东西,可谈的确实不多。因为他们只提供平台,营造环境和氛围,剩下的就看我怎么在这个空间里“悟”出自己创造性的东西了。
当年,张无忌跟张三丰学太极剑,赵敏带着阿大、阿二、阿三一伙人在门外等着决一死战。老张问:还记得多少招?小张曰:差不多全忘了!旁人全蒙圈了……
小张的诀窍就是无招胜有招。
米卢只是营造“玩”球的氛围,让队员从中“悟”(创造)出自己的东西!
我们总是逼队员“招供”:“到底从米卢那儿学了啥?”都已内化为自己的“招”了,根本没有了米卢的印记。因此,也难怪他的队员时至今日还对“到底从米卢那儿学了啥”语焉不详。
这就是训练和培养的实质区别。
即使训练14亿人,也出不了11个球星;而乌拉圭培养几十万孩子,却涌现出无数有创造性的球星。
“暴力鸟”保利尼奥司职中场,但进球比前锋还多。我们总是感到困惑:为什么他总能出现在进球的最佳位置?其实,踢球的技能可以训练,而像“暴力鸟”能预判十步的足球意识,以及在瞬息万变和电光石火间创造性地运用足球技能的能力,这种中国男足球员最欠缺的灵性和悟性,是训练不出来的,只能培养。
同理,中国男足模式训练出来的运动员改当教练,难以拥有在瞬息万变和电光石火间预判球赛变化的穿透力与解析力——阅读比赛的能力,难以根据双方几十个运动员的特点,创造性地搭配出能产生化学反应的变阵。这种教练所需要的创造性,更是训练不出来的!
三、创造性思维与批判性思维的分分合合
不敢苟同钱教授说的“创造性思维(creative thinking)教育则是一个在关注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内更加受到重视的话题。在大学中,致力于本科通识教育的人更加关注批判性思维教育。在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企业、政府中,关注创新的人则更加关注创造性思维教育”。
首先,创造性思维始于婴幼儿时期。孩子把帽子、勺子扔到地下,妈妈捡起来,孩子又扔……这就是孩子在探索世界,在思考怎样与外界互动,怎样吸引妈妈的注意力。这可看作创造性思维的萌芽。也就是说,从好奇、想象、独立、质疑等开始,孩子就进行着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到大学才“关注”,为时晚矣!
其次,不宜把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截然区隔开。创造性思维包含批判性思维,是批判性思维的高级阶段。也可以说,批判性更多体现在创造性的“创”上。当然,批判性思维也可单独培养。
例如,美国某学区K-12的语言艺术课(类似于国内语文课),开篇的“童子功”,就是培养孩子的批判性阅读和批判性聆听的能力与习惯。
所谓“批判性”,是指可以用怀疑的眼光去审视一切,但不能盲目地批判一切。批判性阅读和批判性聆听是“质疑—分析—审辨”的思维过程,是在阅读和聆听中“悟”的过程,是发现自己的答案的过程。不仅要求从阅读和聆听中学东西,更重要的是在阅读和聆听中进行分析与思考,“悟”出自己的东西(包括:①自己全新或部分新的东西;②部分接受或部分反对对方的东西;③全盘接受或全盘反对对方的东西)。当批判性阅读和批判性聆听成为一种习惯时,阅读和聆听就变成一个深度思考、主动学习、自我提升的过程。
钱教授说,提出疑问后,“能够用有说服力的论证和推理给出解释和判断,包括新的、与众不同的解释和判断”。我们常常误以为,“批判性”在于反对、有异议或新意。其实,批判性思维强调的是独立思考、不盲从、有主见。换言之,经过质,独立思考,思辨分析,即便最后全盘接受对方的观点,也是批判性思维。可惜钱教授并未旗帜鲜明地点破,并不是一定要对立,才是批判性思维。
钱教授洞察到中国学生创造性思维发育的缺陷,在大学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实属难能可贵。但课程设置在时间(纵向)和空间(横向)上有瑕疵。作为一项教育改革建议,“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大学教育的必要环节”,仅提及高等教育,只字不提基础教育,会让人误以为,批判性思维能力不需从小培养,只要在大学设此课程就可以解决问题。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是有时间轴的,它需要从小培养,到大学才培养,因缺少基础教育甚至学前教育的“基础”,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是亡羊补牢,聊胜于无——实则难以“大器晚成”!钱教授说,批判性思维“要体现在所有课程和所有培养环节中”。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但国内大学皆有围墙,教育要植根于社会和生活,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就应该没有课本,没有教室,没有围墙,因为“课程”就是生活。这就是空间(横向)的瑕疵。
总之,创造性(思维)不能教,更无法训练,只能培养。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不宜截然区隔开,要在有分有合中突出创造性思维的主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