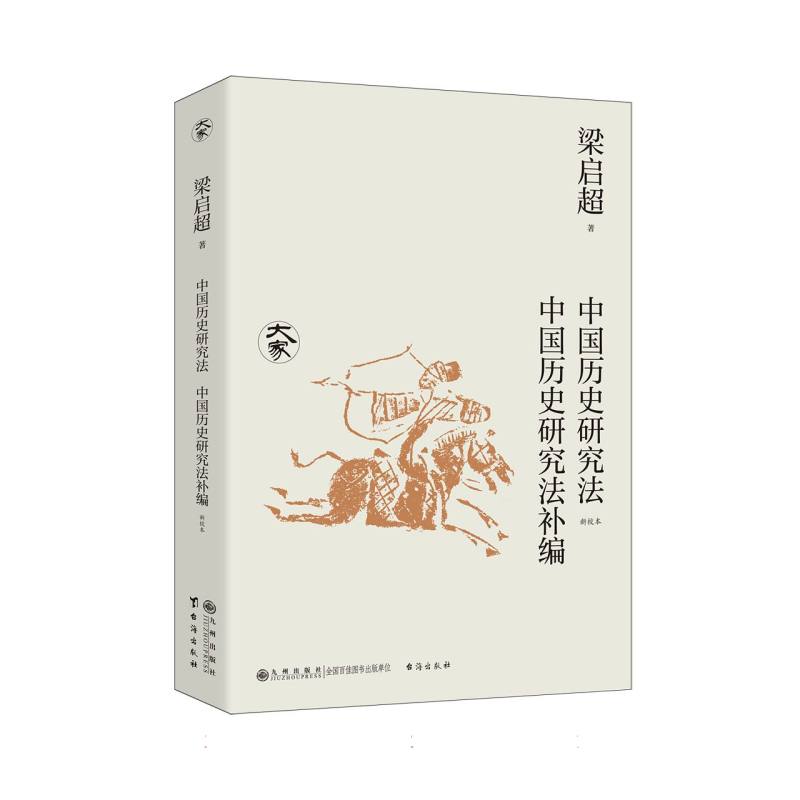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44.64
折扣购买: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新校本)
ISBN: 97875225275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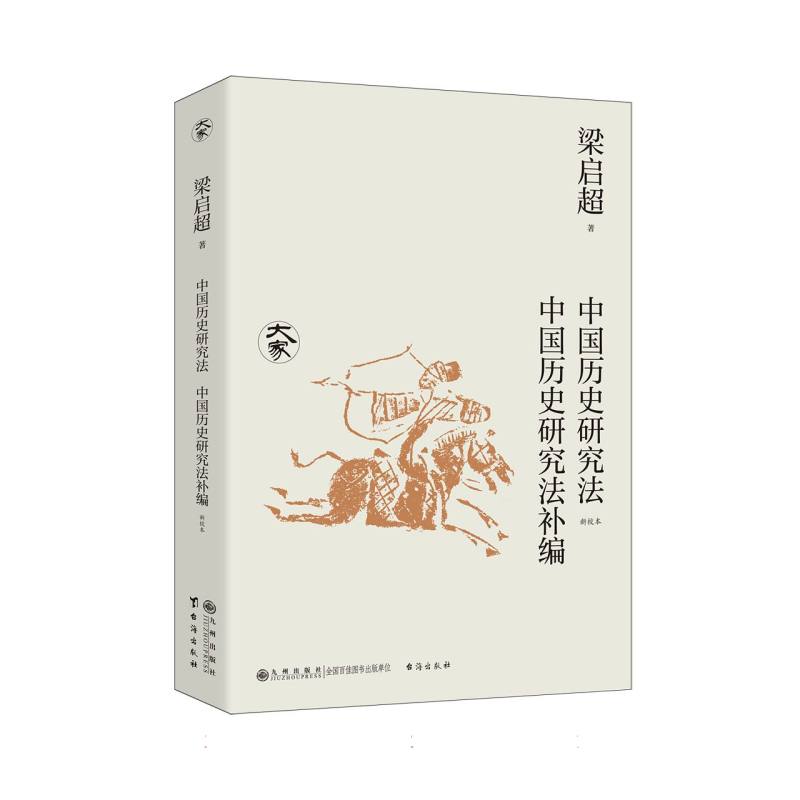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是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也是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其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代表作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等。
中国历史研究法 自序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今虽仅见其进,未见其止,顾所成就则既斐然矣。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启超不自揆,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迁延不以问诸世。客岁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凡十万言。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吾之稿本,将悉以各学校之巡回讲演成之。其第二卷为《五千年史势鸟瞰》,以今春在北京清华学校讲焉。第三卷以下以时代为次,更俟续布也。顾兹事体大,原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力,况学殖浅薄如启超者,重以讲堂匆匆开演,讲义随讲随布,曾未获稍加研勘,则其纰缪舛误矛盾漏略之多,又岂俟论。区区此稿,本宜坚??????之,以俟他日之改定。既而覆思吾研究之结果,虽未必有价值,其或者因吾之研究以引起世人之研究焉,因世人之研究以是正吾之研究焉,则其所得不已多耶?故贸然刊布,而字之曰《史稿》。孟子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吾之此书,非敢有以与人也,将以取诸人而已。愿读者鉴兹微尚,痛予别裁,或纠其大端之谬,或绳其小节之疏,或著论箴驳,或通函诲责,俾得自知其失而自改之,由稿本蜕变以成定本,则片言之锡,皆吾师也。 十一年一月十八日,启超自述。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绪论 此次所讲的“历史研究法”,与几年前所讲的“历史研究法”迥然不同。一则因为本人性情,已经讲过的东西不愿再讲;再则用旧的著作做讲演稿,有什么意思。诸君不要以为此次所讲的就是前次讲过的!我那旧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只可供参考而已。此次讲演实为旧作的一种补充。凡《中国历史研究法》书中已经说过的,此次都不详细再讲。所以本篇可名之为《补中国历史研究法》或《广中国历史研究法》。 本演讲全部组织,可以分为“总论”“分论”两部。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其宗旨在使有研究历史兴味的人,对于各种专史知道应该研究并且知道如何研究。旧作所述,极为简单,不过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作法而已。此次讲演,较为详细,偏重研究专史如何下手。因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作好,通史更作不好。若是各人各作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此次讲演既然注重专史,所以又可叫做“各种专史研究法”。总论的部分,因为是补充《中国历史研究法》所不足,所以很零乱,没有甚么系统。分论的部分,因为注重各种专史的作法,所以较复杂,更丰富;其内容又可分为五项: (一)人的专史。即旧史的传记体、年谱体,专以一个人为主。例如《孔子传》《玄奘传》《曾国藩年谱》等。 (二)事的专史。即旧史的记事本末体,专以重大事情为主。例如晚明流寇、复社本末、洪杨之乱、辛亥革命等。 (三)文物的专史。即旧史的书志体,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如我去年在本校(清华)所讲“文化史”即属此项性质,此在专史中最为重要。 (四)地方的专史。即旧史之方志体。因中国幅员太广,各地发展之经过多所悬殊,旧史专以帝都所在为中心,实不能提挈全部文化之真相,所以应该分为若干区域,以观其各时代发达之迹。其边地如滇、黔、西域、关东等,尤当特别研究。 (五)断代的专史。即旧史的断代史体,专以一个时代为主, 但不必以一姓兴亡画分。例如《春秋史》《战国史》《晚唐藩镇及五代十国史》《宋辽金夏时代史》等。 虽然专史并不只此五种,然粗略分类,所有专史大都可以包括了。例如人的传记,一人如何做,多人如何做,年谱如何做;又如事的本末,战争如何做,变革如何做,兴亡如何做;其他文物的考据,断代的划分,应该如何。这类问题,以后每次讲一项,仔细研究,具体讨论,每项举一个例,将各种专史的做法,分门别类,讲演一番,于诸君日后自己研究上,或者较有益处。 总论之部,计分三章,其目如下: 第一章 史之目的 第二章 史家之四长 第三章 五种专史概论 此三章,不伦不类,没有什么系统与组织。其原因,一则因为有许多方法,旧作已经讲过,此外不必细述;再则因为此次讲演,专重专史的研究,那些空空洞洞的理论也没有细说的必要。这样一来,所以总论三章不得不极其简略了。 最先最近之史料则最可信,此固原则也。然若过信此原则,有时亦可以陷于大误。试举吾经历之两小事为例:(一)明末大探险家、大地理学者徐霞客卒后,其挚友某为之作墓志,宜若最可信矣。一日吾与吾友丁文江谈及霞客,吾谓其曾到西藏,友谓否;吾举墓铭文为证,友请检《霞客游记》共读,乃知霞客虽有游藏之志,因病不果,从丽江折归,越年余而逝。吾固悔吾前此读游记之粗心;然为彼铭墓之挚友,粗心乃更过我,则真可异也。(二)玄奘者,我国留学生宗匠而思想界一巨子也。吾因欲研究其一生学业进步之迹,乃发心为之作年谱。吾所凭借之资料甚富,合计殆不下二十余种,而其最重要者,一为道宣之《续高僧传》,二为慧立之《慈恩法师传》,二人皆奘之亲受业弟子,为其师作传,正吾所谓第一等史料也。乃吾研究愈进,而愈感困难,两传中矛盾之点甚多,或甲误,或乙误,或甲乙俱误。吾列举若干问题,欲一一悉求其真,有略已解决者,有卒未能解决者。试举吾所认为略已解决之一事,借此以示吾研究之径路:玄奘留学凡十七年,此既定之事实也;其归国在贞观十九年正月,此又既定之事实也。然则其初出游果在何年乎?自两传以及其他有关系之资料,皆云贞观三年八月,咸无异辞。吾则因怀疑而研究,研究之结果,考定为贞观元年。吾曷为忽对于三年说而起怀疑耶?三年至十九年,恰为十七个年头,本无甚可疑也。吾因读《慈恩传》,见奘在于阗所上表中有“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等语;上表年月,传虽失载,然循按上下文,确知其在贞观十八年春夏之交;吾忽觉此语有矛盾,此为吾怀疑之出发点。从贞观十八年上溯,所谓十七年者,若作十七个年头解,其出游时可云在贞观二年;若作满十七年解,则应为贞观元年。吾于是姑立元年、二年之两种假说以从事研究,吾乃将《慈恩传》中所记行程及各地淹留岁月详细调查,觉奘自初发长安以迄归达于阗,最少亦须满十六年有半之时日乃敷分配;吾于是渐弃其二年之假说而倾向于元年之假说。虽然,现存数十种资料皆云三年,仅恃此区区之反证而臆改之,非学者态度所宜出也。然吾不忍弃吾之假说,吾仍努力前进。吾已知奘之出游,为冒禁越境,然冒禁何以能无阻?吾查《续高僧传》本传,见有“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数语,吾因此知奘之出境,乃搀在饥民队中,而其年之饥,实因霜灾。吾乃亟查贞观三年是否有霜灾,取《新、旧唐书?太宗记》阅之,确无是事。于是三年说已消极的得一有力之反证。再查元年,则《新书》云“八月,河南陇右边州霜”,又云“十月丁酉,以岁饥减膳”,《旧书》云“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又云“是岁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是元年确有饥荒,而成灾又确由霜害,于是吾之元年说,忽积极的得一极有力之正证矣。惟《旧书》于二年复有“八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饥”一语,《新书》则无有,不知为《旧书》误复耶?抑两年连遭霜灾,而《新书》于二年有阙文耶?如是则二年之假说,仍有存立之余地。吾决意再觅证据以决此疑。 吾乃研究奘途中所遇之人,其名之可考见者凡三:一曰凉州都督李大亮,二曰高昌王麴文泰,三曰西突厥可汗叶护。吾查《大亮传》及《高昌传》,见二人皆自元年至四年在其位,不成问题。及查《西突厥传》,乃忽有意外之获:两书皆言叶护于贞观初被其叔所弑,其叔僭立,称俟毗可汗,然皆未著其被弑在何年。惟《新书》云:“贞观四年俟毗可汗来请昏,太宗诏曰,突厥方乱,何以昏为。”是叶护被弑最晚亦当在贞观三年前。再按《慈恩传》所记奘行程,若果以贞观三年八月发长安者,则当以四年五月初乃抵突厥,其时之可汗,已为俟毗而非叶护矣。于是三年说之不能成立,又得一强有力之反证。吾犹不满足,必欲得叶护被弑确年以为快。吾查《资治通鉴》,得之矣!贞观二年也!吾固知《通鉴》必有所本,然终以不得之于正史,未能踌躇满志。吾发愤取《新、旧唐书》诸蛮夷传凡与突厥有关系之国遍翻之,卒乃在《新书?薛延陀传》得一条云“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于是叶护弑年无问题矣。玄奘之行,既假霜灾,则无论为元年为二年为三年,皆以八月后首涂,盖无可疑;然则非惟三年说不能成立,即二年说亦不能成立。何则?二年八月后首涂,必三年五月乃抵突厥,即已不及见叶护也。吾至是乃大乐,自觉吾之怀疑有效,吾之研究不虚,吾所立“玄奘贞观元年首涂留学”之假说殆成铁案矣!其有小小不可解者,则何以诸书皆同出一辙,竟无歧异? 然此亦易解,诸书所采同一蓝本,蓝本误则悉随之而误矣。再问蓝本何故误?则或因逆溯十七个年头,偶未细思,致有此失;甚至或为传写之讹,亦未可知也。再问十八年玄奘自上之表文何以亦误?则或后人据他书校改,亦在情理中耳。吾为此问题,凡费三日之力,其所得结果如此。——吾知读者必生厌矣。此本一极琐末之问题,区区一事件三两年之出入,非惟在全部历史中无关宏旨,即在玄奘本传中亦无关宏旨。吾自治此,已不免玩物丧志之诮;乃复缕述千余言以滥占本书之篇幅,吾不能不向读者告罪。虽然,吾著本篇之宗旨,凡务举例以明义而已。吾今详述此一例,将告读者以读书曷为而不可以盲从。虽以第一等史料如慧立、道宣之传玄奘者,其误谬犹且如是也,其劳吾侪以鉴别犹且如是也。又将告读者以治学当如何大无畏,虽以数十种书万口同声所持之说,苟不惬于吾心,不妨持异同;但能得有完证,则绝无凭藉之新说,固自可以成立也。吾又以为善治学者,不应以问题之大小而起差别观,问题有大小,研究一问题之精神无大小,学以求真而已,大固当真,小亦当真。一问题不入吾手则已,一入吾手,必郑重忠实以赴之,夫大小岂有绝对标准,小者轻轻放过,浸假而大者亦轻轻放过,则研究精神替矣。吾又以为,学者而诚欲以学饷人,则宜勿徒饷以自己研究所得之结果,而当兼饷以自己何以能研究得此结果之涂径及其进行次第,夫然后所饷者乃为有源之水而挹之不竭也。吾诚不敢自信为善于研究,但本篇既以研究法命名,吾窃思宜择一机会,将吾自己研究所历之甘苦委曲传出,未尝不可以为学者之一助。吾故于此处选此一小问题可以用千余言说明无遗者,详述吾思路所从入,与夫考证所取资,以渎读者之清听。吾研究此问题所得结果虽甚微末,然不得不谓为甚良。其所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亦即近代科学家所应用之归纳研究法也。读者举一反三,则任研究若何大问题,其精神皆若是而已。吾此一段,乃与吾全书行文体例不相应,读者恕我!吾今当循吾故轨,不更为此喋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