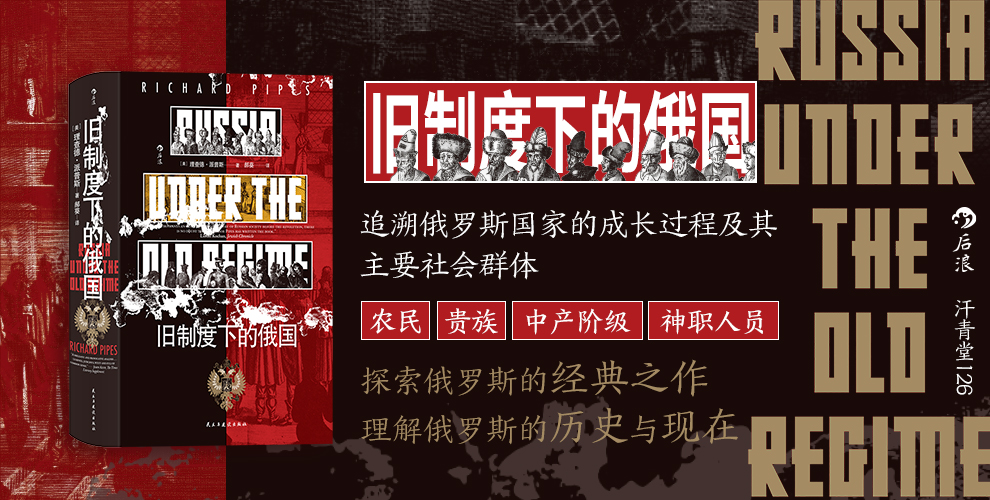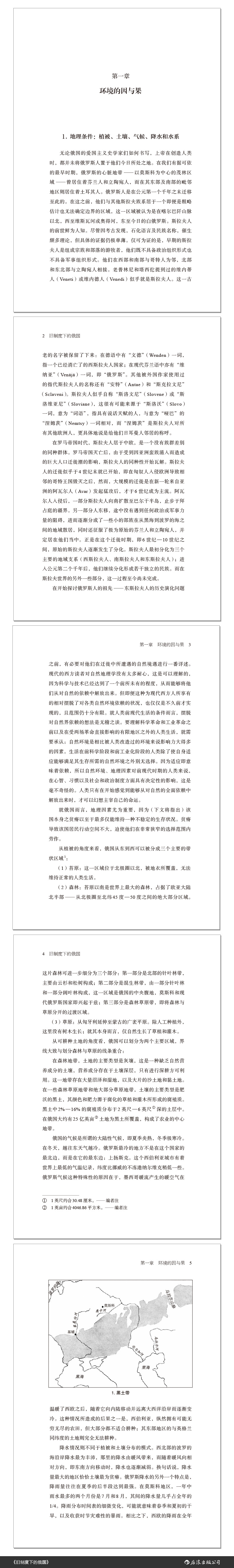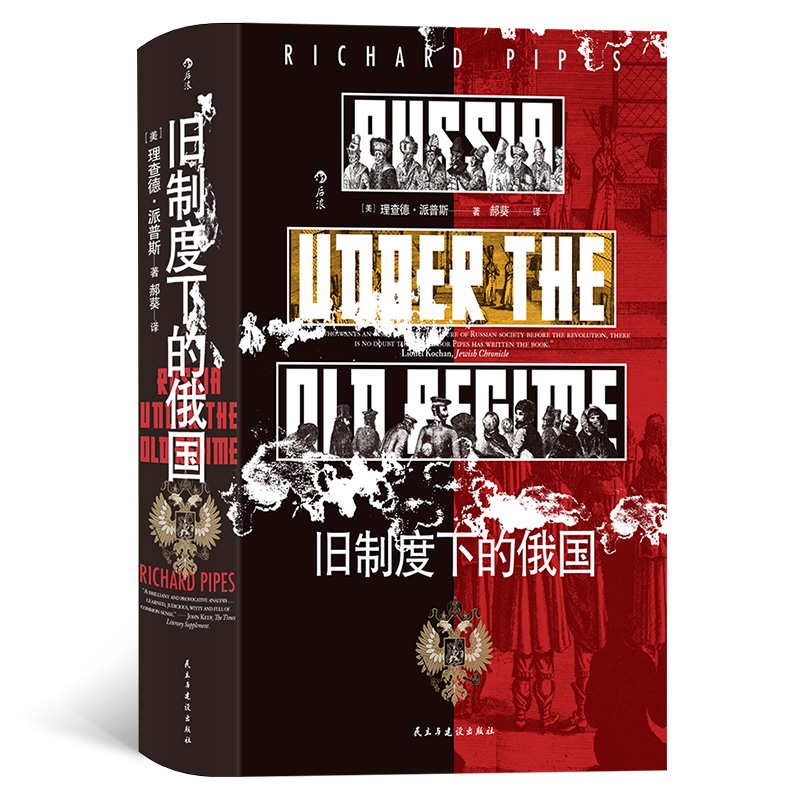
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
原售价: 99.80
折扣价: 63.90
折扣购买: 旧制度下的俄国
ISBN: 9787513941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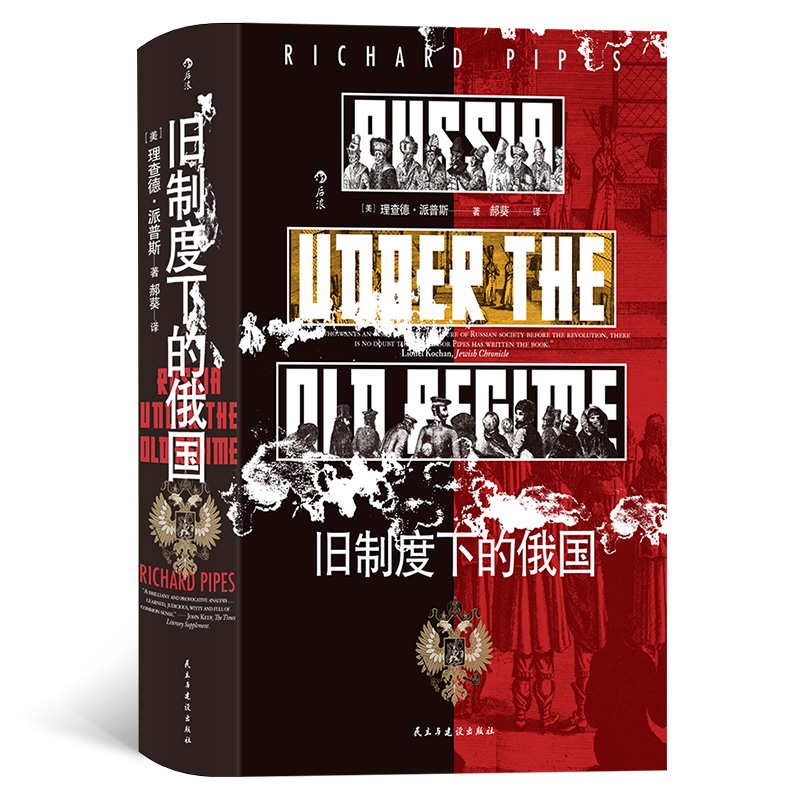
著者简介 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著名俄国史学者。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担任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研究所高级顾问。他因突出的研究成果获得诸多奖项和荣誉,包括古根海姆研究员、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历史协会乔治路易斯比尔奖等。 译者简介 郝葵,山西武乡人,俄罗斯历史文化研究者、译者,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学士,第比利斯国立大学俄语语文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世界史(俄国史方向)博士。
第一章 环境的因与果 1.地理条件:植被、土壤、气候、降水和水系 无论俄国的爱国主义史学家们如何书写,上帝在创造人类时,都并未将俄罗斯人置于他们今日所处之地。在我们有据可依的最早时期,俄罗斯的心脏地带—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茂林区域—曾居住着芬兰人和立陶宛人,而在其东部及南部的毗邻地区则居住着土耳其人。俄罗斯人是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之末迁移至此的。在这之前,他们与其他斯拉夫族系居于一个即便是粗略估计也无法确定边界的区域,这一区域被认为是在喀尔巴阡山脉以北,西至维斯瓦河或奥得河,东至今日的白俄罗斯。斯拉夫人的前世鲜为人知。尽管因考古发现,石化语言及民族名称,催生颇多理论,但具体的证据仍极单薄。仅可为证的是,早期的斯拉夫人是组成宗族和部落的游牧者,他们既不具备政治组织形式也不具备军事组织形式。他们在西部和南部与哥特人为邻,北部和东北部与立陶宛人相接。老普林尼和塔西佗提到过的维内蒂人(Veneti)或维内德人(Venedi)似乎就是斯拉夫人。这一古老的名字被保留了下来:在德语中有“文德”(Wenden)一词,指一个已经消亡了的西斯拉夫人国家;在现代芬兰语中亦有“维纳亚”(Ven?j?)一词,即“俄罗斯”。其他被外国作家使用过的指代斯拉夫人的名称还有“安特”(Antae)和“斯克拉文尼”(Sclaveni)。斯拉夫人似乎自称“斯洛文尼”(Slovene)或“斯洛维亚尼”(Sloviane),这很有可能来源于“斯洛沃”(Slovo)一词,意为“词语”,指具有说话天赋的人,与意为“哑巴”的“涅姆茨”(Nemtsy)一词相对,而“涅姆茨”是斯拉夫人对所有其他欧洲人,更具体地说是给他们日耳曼人邻居的称呼。 在罗马帝国时代,斯拉夫人居于中欧,是一个没有族群差别的同种群体。罗马帝国灭亡后,由于受到因亚洲蛮族涌入而造成的巨大人口迁徙潮的影响,斯拉夫人的同种性开始瓦解。斯拉夫人的迁徙似乎于4世纪末就已开始,即在匈奴人入侵欧洲导致相邻的哥特王国毁灭之后,然而,大规模的迁徙是在新一轮来自亚洲的阿瓦尔人(Avar)发起猛攻后,才于6世纪成为主流。阿瓦尔人入侵后,一部分斯拉夫人向南扩散至巴尔干半岛,止步于拜占庭的疆界。另一部分人东移,途中没有遇到任何政治或军事力量的阻碍,进而逐渐分成了一些小的部族在从黑海到波罗的海之间的地域散居,同时还征服了极为原始的芬兰人和立陶宛人,并定居在他们当中。正是在这个迁徙时期,即6世纪—10世纪之间,原始的斯拉夫人逐渐发生了分化。斯拉夫人最初分化为三个主要的地域支系(西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和东斯拉夫人);进入公元第二个千年后,他们继续分化形成若干独立的民族。而在斯拉夫世界的另外一些部分,这一过程至今尚未完成。 在开始探讨俄罗斯人的祖先—东斯拉夫人的历史演化问题之前,有必要对他们在迁徙中所遭遇的自然境遇进行一番详述。现代的西方读者对自然地理学没有太多耐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科学与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能够将他们从对自然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但即便这种为现代西方人所享有的相对摆脱了对各类自然环境依赖的状况,也仅仅是不久前才实现的,且范围仍十分有限。就人类前现代生活的条件而言,摆脱对自然界依赖的想法是无稽之谈。要理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前以及在受两场革命直接影响的有限地区之外的人类生活,就需要承认:自然环境是相比被人类改造过的环境来说影响力大得多的因素。生活在前科学阶段和前工业化阶段的人类除了使自身适应能够满足其生存所需的自然环境之外别无选择。因为适应即意味着依赖,所以自然环境、地理因素对前现代时期的人类来说,在心智、习惯以及社会和政治制度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毫不奇怪的。人类只有在开始感觉到能够从对自然的全面依赖中解放出来时,才可以幻想主宰自己的命运。 就俄国而言,地理因素尤为重要,因为(下文将指出)该国本身之贫瘠以至于最多仅能维持一种不稳定的生存状况。贫瘠导致该国居民行动空间不大,迫使他们在非常狭窄的选择范围内劳作。 从植被的角度来看,俄国从东到西可以被分成三个主要的带状区域1: (1)苔原:这一区域位于北极圈以北,被地衣所覆盖,无法维持正常的人类生活。 (2)森林:苔原以南是世界上最大的森林,占据了欧亚大陆北半部—从北极圈至北纬45度—50度之间的绝大部分区域。这片森林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北部的针叶林带,主要由云杉和松树构成;第二部分是混生林带,由一部分针叶林和一部分阔叶林构成,这一区域是俄国的中央腹地,莫斯科和现代俄罗斯国家即兴起于兹;第三部分是森林草原带,即将森林与草原分开的过渡区域。 (3)草原:从匈牙利延伸至蒙古的广袤平原。除人工种植外,这里没有树木生长;就其本身而言,仅自然生长了草植和灌木。 从可耕种土地的角度看,俄国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区域,界线大致与划分森林与草原的线条重合: 在森林地带,土地的主要类型是灰壤,这是一种缺乏自然营养成分的土壤,营养成分存在于土壤深层,只有进行深耕方可利用。这一地带存在大量沼泽和湿地,以及大片的沙土地和黏土地。在一些森林草原地带和绝大部分草原地带,土壤的主要类型是肥沃的黑土,其颜色和肥力源于腐化的草植和灌木所形成的腐殖质。黑土中2%—16%的腐殖质分布于2英尺—6英尺[ 1英尺约合30.48厘米。——编者注]深的土层中。在俄国大约有25亿英亩[ 1英亩约合4046.86平方米。——编者注]土地为黑土所覆盖,构成了农业的中心地带。 俄国的气候是所谓的大陆性气候,即夏季炎热,冬季极寒冷。在冬天,越往东天气越冷。俄罗斯最冷的地方不是在这个国家的最北边,而是在它的最东边:上扬斯克。这个西伯利亚城市有着世界上最低的气温纪录,纬度比挪威的不冻港纳尔维克稍低一些。俄罗斯气候这种特殊性的原因在于,墨西哥暖流产生的暖空气在温暖了西欧之后,随着它向内陆移动并远离大西洋沿岸而逐渐变冷。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后果之一是,西伯利亚,纵然拥有可能无穷无尽的农田,但大部分都不适合耕种;其东部地区的与英格兰同纬度的土地则完全无法耕种。 降水情况则不同于植被和土壤分布的模式。西北部的波罗的海沿岸降水最为丰沛,那里的降水由暖风带来,而随着暖风向相对方向,即东南方向移动时,降水也逐渐减弱。换句话说,降水量最大的地区恰恰土壤最为贫瘠。俄罗斯降水的另外一个特点是,降雨量往往在夏季的后半段达到最强。在莫斯科地区,一年中雨水最多的两个月份是7月和8月,其间的降水量几乎占全年的1/4。降雨分布时间表的细微变化,可能就意味着春季和夏初的干旱,以及收获时节灾难性的暴雨。相比之下,西欧的降雨在全年内的分布要均衡得多。 最后来谈一谈水系。俄国的河流呈南北走向,主干河流没有东西走向的。不过那些大河的支流则是东西走向的。由于俄罗斯较为平坦(其欧洲部分没有海拔超过1400英尺的地方),其河流不是源自高山,而是源自坡度较缓的湿地及湿地形成的湖泊。因此俄国拥有独特的通航水道网络,这一网络由主干河流及其众多支流组成,通过便利的连水陆路[ 连水陆路(волок):古时两水路之间可以拉过船只、货物的陆地。——译者注]相互连接。即便借助原始的运输方式,也有可能实现从波罗的海横穿俄罗斯行至里海,并可通过水路到达此间的大部分陆地。在西伯利亚,水系形成的绝佳交通网络,使得17世纪时俄国的毛皮商贩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穿越数千英里[ 1英里约合1.61千米。——编者注]抵达太平洋,并通过水路运输开辟西伯利亚与本土之间的定期贸易。如果没有这些水路,在铁路出现之前,俄国人的生活几乎很难超过仅能维持生计的水平。由于距离太过遥远,加之大面积的极寒条件下,维护道路的代价太过高昂,俄罗斯只有在冬天当冰雪覆盖的地面可供雪橇滑行时,陆地交通才是可行的。这也解释了俄国人对于水路运输的极大依赖。直到19世纪下半叶,大宗商品运输都是靠舟船实现的。 2.极北的地理位置对经济的影响 和其他斯拉夫民族一样,古代的俄罗斯人主要是半游牧民族;而当他们在一个新的地方定居下来后,则会慢慢向农业生活过渡。然而对东斯拉夫人来说不幸的是,唯独他们所拓殖的地区极不适合耕种。作为土著的芬兰人和土耳其人把农耕当作副业,主业则是在森林渔猎和在草原畜牧。俄罗斯人则与之不同,他们在不利的自然条件下严重依赖农业,这也许是俄国历史一系列问题的最基本原因。 我们已经提到的一些困难有:北方土壤的贫瘠,分布不均的降雨,即收益最少的地方雨下得最大,且在农耕时节雨水往往来得太晚。有记录以来,俄国平均每三次收成中就有一次歉收。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降雨在地形和季节分布上的特殊性。 然而,最严重和最难解决的问题在于该国所处的极北的地理位置。俄罗斯与加拿大同属于世界上地理位置最北的国家。诚然,现代俄国控制了大片的亚热带地区(克里米亚,高加索和突厥斯坦),但是这些地区并入俄国的时间较晚,大多是在19世纪中叶,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并入的。混生林地区是俄罗斯国家的摇篮,就如同勃兰登堡对德国的意义,法兰西岛对法国的意义一样。直至16世纪中叶俄罗斯人几乎都被限制于这一地区,因为令人垂涎的黑土草原还处于敌对的突厥部族的控制之下。尽管俄罗斯人从16世纪下半叶就开始向草原渗透,但是直至18世纪末在他们彻底击溃了土耳其人之后才成为其主人。在他们的国家形成时期,俄罗斯人不得不居住在北纬50度—60度之间的区域。这大约相当于加拿大所处的纬度。然而在对两国进行比较时,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一些差别。首先,加拿大的大部分人口一直居住在该国最南段,沿五大湖与圣劳伦斯河,即北纬45度的地区,在俄国对应克里米亚和中亚草原的纬度。加拿大90%的人口生活在距美加边境200英里的范围内,在北纬52度以北的地区人口极其稀少,几乎没有任何农业活动。其次,纵观加拿大历史,该国一直与其富裕的南方邻邦保持着友好关系,并以此维持着紧密的经济往来。(加拿大至今仍然是受美国投资最大的国家。)最后,加拿大从未有过供养众多人口的负担;对于那些本国经济无力为他们提供谋生机会的加拿大人来说,已经习惯于季节性或长期性地移居美国。就俄国而言,上述优势一条都没有:邻邦既不富裕也不友好,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源来维持18世纪中叶时数量就超过了今日之加拿大的众多人口。 农耕季节的短暂 俄国所处地理位置带来的主要后果是它的农耕季节极其短暂。在诺夫哥罗德和圣彼得堡附近的针叶林地带,一年中仅有4个月的农耕季节(5月中旬至9月中旬)。莫斯科附近的中央地区,农耕季节延长至5个半月(4月中旬至9月末)。草原地带的农耕季节为6个月。在俄国,一年中除了农耕季节之外的其他时间完全不适合农业劳动,因为土壤硬如岩石,大地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 相比之下,西欧的农作物生长季节则能持续8—9个月。换言之,西欧农民可以支配的田间劳作时间要比俄国农民多出50%—100%。此外,在欧洲的一些地方,冬季气候温和,仍然可以从事农耕之外的劳动。这种简单的气候因素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将在下面的篇章中阐明。 短暂的农作物生长季节及其必然结果,与漫长而艰难的寒冬,还给俄国农民造成了另外的困难。农民不得不将自己的家畜在室内圈养的时间比西欧农民要多出两个月。因而俄国农民饲养的耕牛错过了早春的牧养时机,而当它最终被放牧在草场的时候,则处于彻底消瘦的状态。俄国的牲畜一直质量低劣,尽管政府和开明的地主试图改善,但仍然无济于事;从西方引进的品种,总是迅速地退化到和本地的糟糕品种没什么差别的状态。饲养牲畜方面的困难阻碍了森林地区肉业与乳业的发展,同时对役畜的品质产生了不良影响,并导致了畜粪肥料的长期短缺,尤其是在最需要这种肥料的北方地区。 农业的低产 俄国土壤的贫瘠、降雨的不均和农耕季节的短暂,这些因素所带来的后果是长期的农业低产。 通过种子自身繁殖次数的反映来衡量农业产量是最有意义的。例如,播种时投放1颗谷粒,收获时获得5颗谷粒,就可以说产出率是1∶5。欧洲中世纪时期产出率通常是1∶3,最好的是1∶4,这是使农业具有生产意义和创造维持生命条件的最低比率。必须指出的是,1∶3这一产出率意味着年收成量为投入量的两倍而非三倍,因为必须要把每年收成的1/3预留作种子。这也意味着每三亩可耕种的土地中必须有一亩用于种子培育。在13世纪下半叶,西欧的粮食产量开始大幅上升。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城市的发展,城市中的商业和手工业人口放弃了粮食种植,取而代之的是从农民那里购买。城市中出现了谷类与其他农产品市场,这促使西欧的地主与农民通过使用更加密集的劳动力与加重施肥的方法来实现增收。在中世纪晚期,西欧的产出率已经达到1∶5。后来,在16世纪和17世纪,产出率又进一步提高至1∶6和1∶7。到19世纪中叶,以英格兰为首的一些农业发达国家通常可以获得1∶10的产出率。如此戏剧性的提升具有比该数字本身更大的经济意义。在那些播种一粒而收获十粒的土地上,农民只需要为育种留出1/10的土地和1/10的收获,就像在1∶3的产出率下留出1/3。在产出率为1∶10的条件下,所获得的净回报是产出率为1∶3条件下的4.5倍,这使得理论上能够在既定区域中维持更多的人口生存。这种多年盈余所产生的累积效应很容易理解。可以说,文明只发端于那些投入1粒种子,至少可以获得5粒收成的地方;正是这个最低盈余决定了(假设没有食物进口)是否能有相当比例的人口,可以从必需的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从事其他行业。“在一个粮食产出率相当低的国家是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商业和交通的。”2此外,还可以补充一句:也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政治生活。 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俄国在中世纪时期的平均农业产出率也是1∶3。但不同于西方的是,俄国的农业产出率在后来的几个世纪没有经历任何改善。至19世纪,俄国的农业产出率大体上仍然与其15世纪的水平相当,差的年份会降至1∶2,好的年份会升至1∶4甚至1∶5,但几个世纪以来的平均数是1∶3(北方地区略低于这个数字,南方地区略高于这个数字)。这一产出率基本上处于足够维持生活的水平。把俄罗斯农民描绘成某种自古以来就在压迫下苟延残喘、为勉强维持悲惨生活而刨土觅食的生物,根本站不住脚。一位俄国农业史学家近来用下面的文字对那种盛行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我们面临着一个悖论。一位学者对封建社会早期的农民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那时农民的状况就已经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正在全面走向死亡。但是后来,他们的境况又变得更糟了。15世纪更糟,16世纪、17世纪、18世纪、19世纪一直都是更糟,而且越来越糟。就这样一直糟下去,直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没错……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有波动的,是有可能下降的,但是不可能无限地下降。否则,他们是如何活下来的呢?3 答案当然是:对于俄国农民生活状况和生活水平的传统认识一定是错误的。近来有研究对15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农民和16世纪的白俄罗斯与立陶宛农民(他们都居住在北部的低品质灰壤地区)的收入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充分表明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养活自己。4俄国农业面临的困难不是无法养活其耕种者,而是从来都无法实现显著的盈余。俄国在生产力方面与西欧之间的差距逐世纪增大。至19世纪末,效益好的德国农民通常能够从1英亩土地上收获超过1吨的谷类,而同期的俄国农民仅能勉强收到600磅[ 1磅约合0.45千克。—编者注。]。19世纪晚期的俄国,1英亩小麦的收成仅为英国的1/7,且不足法国、普鲁士或奥地利的一半。5俄国农业生产率,无论是用谷物产出率还是土地产出率计算,在当时都是欧洲最低的。然而,俄国土地低下的生产力不能完全归咎于气候。斯堪的纳维亚尽管也处于北方地区,但在18世纪时的农业产出率也已达到了1∶6;俄罗斯帝国的波罗的海沿岸省份,当时的土地处在德意志贵族的掌控下,在19世纪前50年的农业产出率在1∶4.3至1∶5.1之间,即一个有可能开始累积盈余的比率。6 著名俄国史学者理查德·派普斯的代表作之一,是他对俄罗斯国家制度与社会的集大成之作,表达了他对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的深刻而独特的见解。 这是一本分析俄罗斯国家从最初的形成到变为腐朽的沙皇俄国这一历程的经典之作,深入研究了沙皇俄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揭示了俄国的世袭制、个人统治和封建主义等特征对于俄罗斯历史和文化发展所产生的的深远影响,适合任何对俄罗斯历史、政治、文化感兴趣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