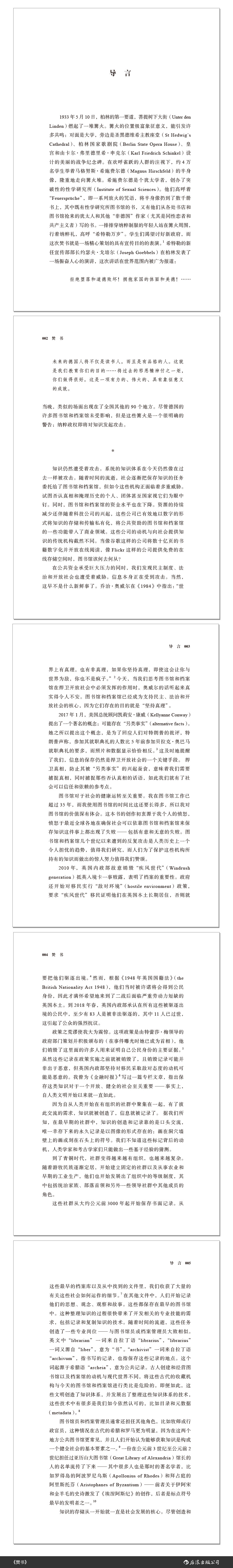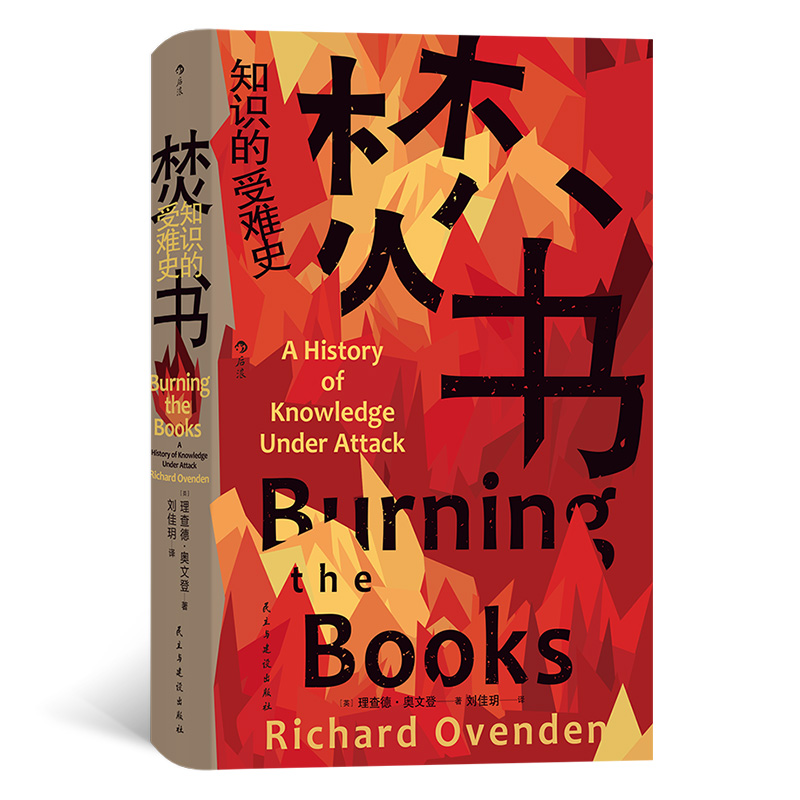
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4.20
折扣购买: 焚书:知识的受难史
ISBN: 97875139416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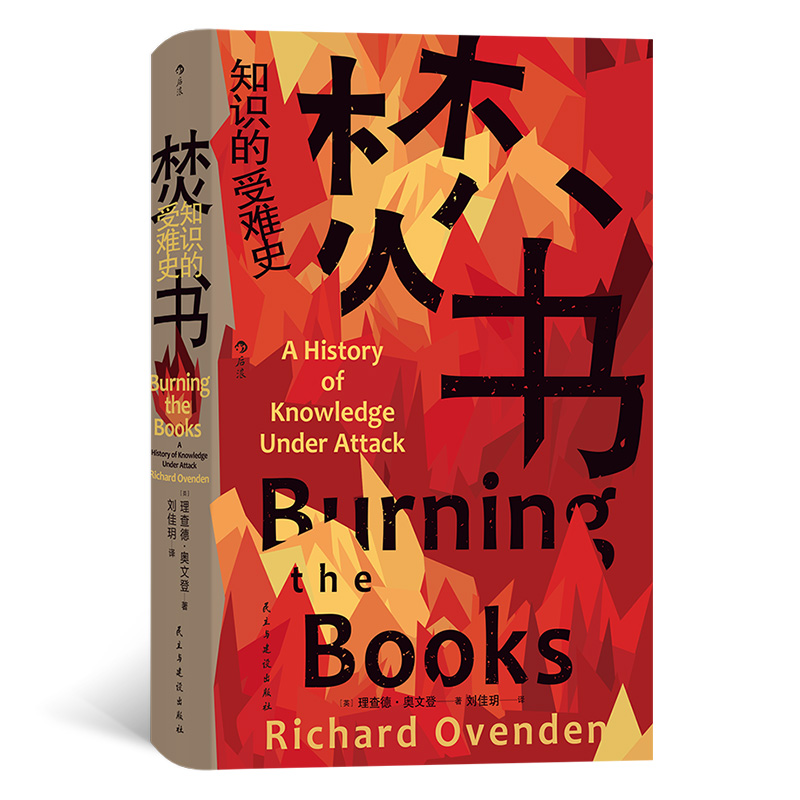
著者简介 理查德·奥文登(Richard Ovenden),毕业于杜伦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并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担任研究员。他自2014年起任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馆长。在此之前,他曾在杜伦大学图书馆、上议院图书馆、苏格兰国家图书馆和爱丁堡大学任职。他是古文物研究学会和皇家艺术学会的会员,美国哲学学会的成员,还是《摄影师约翰?汤姆森(1837—1921)》的作者。他于2019年英国女王寿辰荣获大英帝国勋章。 译者简介 刘佳玥,伦敦大学学院硕士,近代早期研究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17世纪女性作者的手稿和出版物。
得益于将近两个世纪的考古工作,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古老的民族有着高度发展的文化,促成了图书馆、档案和文书的诞生。随着最早的文明的形成,从游牧到定居,人们也渐渐意识到建立交流和存储知识的永久记录的必要性。当亚述巴尼拔王的图书馆运作时,其使用的泥板很笨重,因此它需要被存放在莱亚德发现的那种房间里,以便于人们缮写或者检索他们需要的信息。随着研究推进,学者们从泥板中发现了编目和整理的证据。 1846 年,莱亚德开始将资料运回英国,他的考古发现一在伦敦登场就立刻引起了轰动。在新闻报道和公众压力的推动下,大英博物馆董事会的看法得到了改变,同意为进一步的考古探险提供资金,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政客们将考古挖掘的成功视为与法国对手竞争的胜利,因此他们十分鼓励继续考古活动。莱亚德成了民族英雄,得到了“尼尼微之狮”的绰号,并利用自己的新名气为其作家和政客的职业铺路。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也许是他最重要的发现。 雕塑、陶器、珠宝和塑像(目前在伦敦、柏林、纽约和巴黎的大型博物馆中展出)在美学上令人惊叹,但对这些藏品所含知识的解密则真正改变了我们对古代世界的理解。 通过研究这些出土的泥板,如今的我们了解到,亚述巴尼拔的皇家图书馆也许是在一座建筑内集结当时能收集到的全部知识的第一次尝试。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馆藏主要分为三类:文学和学术文本,神谕问询和占卜记录,以及信件、报告、人口普查、合同和其他形式的行政文件。这里的大量资料(与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许多其他古代图书馆一样)涉及对未来的预测。亚述巴尼拔王希望他的图书馆中的知识能帮他决定何时是开战、结婚、生孩子、种庄稼或从事生活中任何必要事情的最佳时间。图书馆对未来是必要的,因为它们从过去收集到的知识,要被交到决策者手中——在尼尼微,最重要的决策者是亚述巴尼拔。13 这些书稿文本涵盖了从宗教、医学、魔法到历史、神话等广泛主题,并且被整理得井井有条,按主题顺序排列并带有标签。我们今天可以将其视为目录记录,甚至是元数据。这些被保留为永久参考资源,而档案材料则被暂时保留,以解决有关土地和财产的法律纠纷。14 莱亚德和拉萨姆在尼尼微的一项最重要的发现是包含了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吉尔伽美什史诗》——的一系列泥板。人们在尼尼微发现了几组不同的泥板,显示了多代人对这一关键文本的所有权,它们都被保存在一起,从一代国王传给下一代国王,甚至还有一个信息页声称它是亚述巴尼拔王亲手书写的。 从美索不达米亚档案馆和图书馆内容的考古发现中,以及对出土泥板上的文字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识别出当时人们整理知识的独特传统,甚至还能确认当时负责这些藏品的专业人员的身份。在今天,档案管理员和图书馆员的职业角色划分得非常清晰;古代则不同,在古代社群中,这些界限不太明确。诸如亚述巴尼拔这样的图书馆展现了当时人们对管理信息的渴望,也使我们了解到知识对于统治者而言是多么宝贵,以及他们愿意以任何方式获取信息的决心。 ?入围2021年沃尔夫森历史奖短名单 《新政治家》年度图书 《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图书 ?牛津大学图书馆馆长倾情讲述,几千年来焚书与救书的辛酸血泪史! “哪里有人放火烧书,最后就会有人放火烧人。” 对知识的肆意破坏常常是系统性的,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发起的攻击。古代中国有“焚书坑儒”,英格兰有宗教改革运动对修道院藏书的打击, 德国则有纳粹开展的焚烧犹太典籍的行动。另一方面,仍然有无数仁人志士为濒于灭绝的知识和档案赴汤蹈火,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除了知识存储所面临的政治灾难,本书还提到了图书馆由于疏于管理造成的悲剧,作者及其亲属的意愿导致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数字时代信息保存与监管的缺失,以及巨头科技公司垄断的威胁……正如本书所言: “图书馆和档案馆几个世纪以来遭到的反复攻击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值得我们研究,而人们为了保护这些机构所持有的知识而做出的惊人努力值得我们赞颂。” 本书作者理查德·奥文登自2014 年以来担任英国第二大图书馆——也是牛津大学主图书馆——博德利图书馆的馆长,他在《焚书:知识的受难史》中对知识保存的危机逐一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和重现,不仅具有权威性,更传达了作为一名知识保存者的洞见和担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本“书之书”所具有的价值不仅在于带领我们重回书籍受难的历史情境,更在于唤起我们对知识存储和保护的清醒意识,特别是意识到在“互联网没有记忆”的时代个人与社会面临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