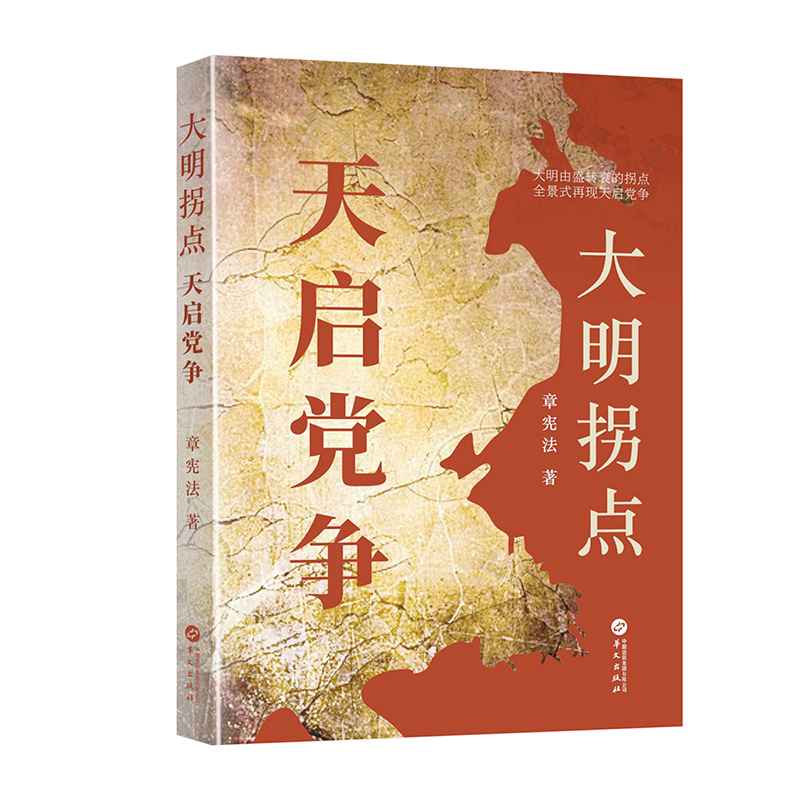
出版社: 华文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3.10
折扣购买: 大明拐点 : 天启党争
ISBN: 9787507559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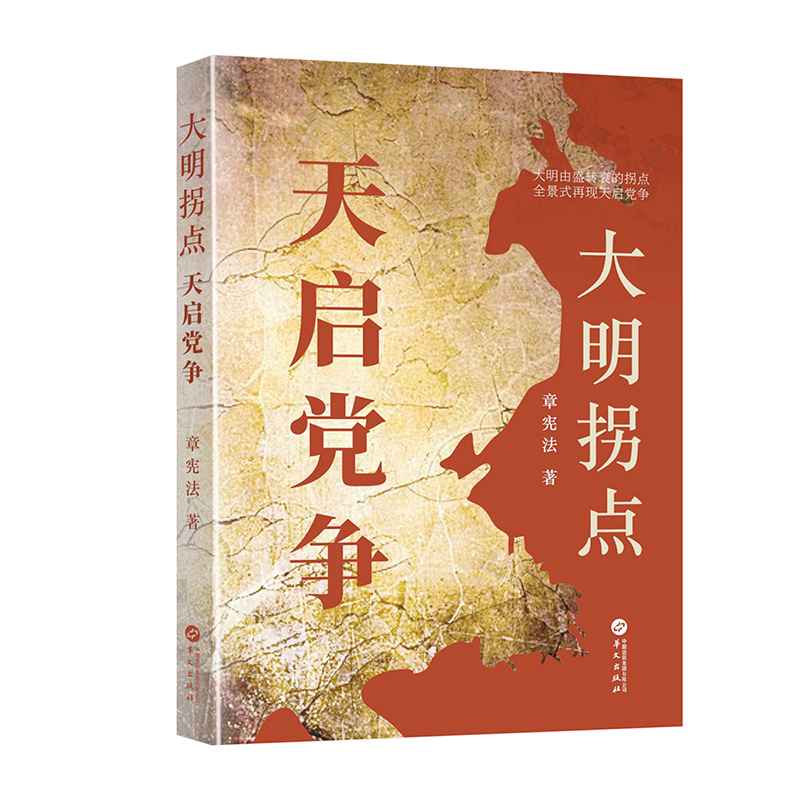
章宪法,安徽枞阳人,明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苍生鬼神》明季闲谭《明朝大败局》《明朝暗事》《明朝大博弈》《海上大明》《文状元》国器之邦》等。
第一章 外朝内廷 一大早,左光斗早早地来到了城门前。来得太早了,城门还没有开。 左光斗(1575-1625),字遗直,一字共之、拱之,号浮丘、苍屿。南直隶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枞阳)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 左光斗当时任浙江道监察御史,也是杨涟最亲密的朋友。那天杨涟进宫,左光斗预感到会有大事发生,准备晚上向杨涟打听。结果,杨涟没有回家,留在六科房值班了。 六科班房在午门以内,左光斗想进去也没办法,晚上老想着发生了什么事,越想越睡不着,干脆起床提着灯笼出门了。 九月的北京,凌晨的天气凉飕飕的,左光斗忍不住打了个喷嚏,然后一边擦鼻涕,一边狠狠瞪了一眼城门上的铜钉。 左光斗的预感是对的,朝廷确实发生了大事,比他预想的还要严重。 一、抢夺 杨涟起得比左光斗更早。凌晨时分,杨涟就接到太监传达的皇帝口谕,让他立刻进宫觐见。接到同样口谕的,还有在内阁入值的大臣们。大家嘴上没说什么,一边穿衣服一边猜:啥事这样紧急,不会是皇帝…… 不用再猜了,宫里又有人传出话来:泰昌皇帝驾崩了。 赶往乾清宫的大臣们,尽管心里七上八下,还是拼命加快步伐。几个上了年纪的大臣手脚迟钝,正在边走边系衣服,以最快的速度向宫门赶去。 杨涟赶到乾清门前,发现侍卫比往日多了许多,一个个手持长梃站在门口。还有比杨涟到得早的:礼部尚书孙如游、吏部尚书周嘉谟、左都御史张问达等。三个人在一边等人一边聊点什么,杨涟隐约听见周嘉谟在问:“皇长子今年十几啦?”“十六。”孙如游肯定地答道。周嘉谟咂了一下嘴:“这怎么办呢?” 皇长子十六岁登基,周嘉谟面露犹豫的神色。孙如游跟着叹了一口气:皇长子的事,确实是个难题啊! 这有什么难的?皇上昨天托孤时讲得够明白的了。杨涟准备接过孙如游的话茬,张问达已经先开口了。张问达的意思:就目前这情况,皇长子只能交给李选侍照顾。十六岁的皇帝直接亲政,皇室要有个人管教引导。人选无非两个:要么养母李选侍,要么祖母级的郑贵妃。 杨涟一下子激动起来:“不可!” 杨涟的声音从来都不会小,张问达抹了一下脸,明显是杨涟的唾沫星子飞上来了。 张问达不便发作,脸一下子沉了下来。孙如游打了个圆场,说先不议这些吧,等方首辅过来,让他拿个万全的主张吧。 虽然大家都住在内阁,同时得到了通知,毕竟一岁年纪一岁人,有几个阁老年纪大、反应慢,还没看到人影,到得晚一点十分很正常。时间也不是太长,方从哲、刘一燝、韩爌都赶过来了。十几个大臣,围向了方首辅。方从哲道:“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家有三件事,先从紧的来,大家简单地议几句吧。” “最要紧,当然是新皇帝登基的事!”杨涟在这帮大臣中官最小,声音最大,还是最先开口。 方从哲转向孙如游,说:“皇长子登基的事,细节上没有什么问题吧?” 作为礼部尚书,礼制上的事孙如游没有含糊之处,声音不大地对方从哲道:“皇长子是白身,登基的事要尽快办完,啥事都没有。怕就怕时间拖长了,会节外生枝。” 孙如游一说,众大臣顿时明白过来,都主张首先解决皇长子继位的事。在朱由校继承皇位的问题上,大臣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周嘉谟将方从哲推到领头的位子,众大臣一齐迈向乾清宫。侍卫们并未收起长梃,而是将大臣们拦住了。走在后面的杨涟,一个箭步上前,大吼一声:“奉旨进宫,不得阻拦!” 杨涟号大洪,声音也是又大又洪亮。侍卫们迟疑了一下,杨涟将方从哲推了一把,大臣们一窝蜂上前,一下子拥进了乾清门。 侍卫们回过神来,拖着长梃边追边喊:“回来,不准进去!”杨涟回过头来断后,扯起大嗓门吼道:“我们是顾命大臣,你们是什么东西?都退回去!” 这些侍卫,都是李选侍派来的宦官。他们见过大官,但没见过这么凶的大官。灯下的光线也不是很好,看不明白官员胸前的补子,他们甚至以为这个最凶的杨涟,就是最大的官——内阁首辅。 奴才当习惯了,没拦住,那就算了。 顾命大臣们进入乾清宫,在泰昌皇帝灵柩前跪地痛哭,杨涟的哭声依旧是最大的。依例行完礼,他们都起身擦眼泪。杨涟的眼泪,同样是最多的。 方首辅起身后,也用袖子在眼睛上擦了擦。上了年纪的人,流不出年轻人的泪,他用眼扫了一下四周,没有发现皇长子的影子,暗想:那接下来要做的事,岂不落空了? 刘一燝与方从哲同处内阁,对方从哲太了解了。方首辅什么事都能想到,他也想到了,关键是方首辅擅长将自己想做的事,让别人提出来,他再“帮”别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将事情拖一拖,一般能拖出自己想要的结果,这叫进退有据。眼下这情形,不能跟方首辅比耐力了。 刘一燝问太监:“皇长子在哪儿?”宫里的太监应该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反正没有一个人回答。杨涟冲着最近的一个宦官问:“在哪儿?快说!”宦官闪向一旁,啥也没说。就算他真知道在哪儿,也不会说,李选侍跟他们打过招呼了。这个宦官很精明,看了一眼刘一燝,又看了一眼王安。 王安,真正的大太监,宦官们如果在王安与李选侍之间非要得罪一个,那宁可得罪李选侍。 王安走到刘一燝旁边只说了两个字:“暖阁。” 声音不大,但好几个顾命大臣还是听见了。杨涟一听,就要去暖阁,但身上一边是王安的手,一边是韩爌的手。两只手几乎同时重重地按住了他。 这是宫里,乱闯是要出问题的,韩爌就怕杨涟捅出娄子。 不捅娄子,又想达到目的,韩爌这回是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其他大臣也不知道,便把脸转向英国公张惟贤。 顾命大臣中,张惟贤资格最老,爵位最高,但他也是没有什么好办法,谁敢在内宫乱闯? 王安说:“我去看看。” 王安径直奔向暖阁。李选侍见王安进来,赶紧问大臣那边的情况,尽管早有宦官不断给她反馈情况。魏忠贤更是焦急,用近乎乞求的嗓音道:“王叔,这场面我们也没见过,您赶紧拿个主意吧!” 魏忠贤也是王安门下的人,那时候还叫李进忠。 王安表情很轻松,对李选侍说:“没什么特别的。他们要安排先皇的丧事,需要跟皇长子当面商定。”王安最清楚李选侍的心思,哄骗好使就先骗她几句。 李选侍“呵”了一声,表情顿时也轻松了不少,叫出朱由校,让他一道去一下,商量好了马上回来,并叮嘱王安要尽快将皇长子送回自己的身边。 朱由校“嗯”了一声,王安则满口应承。李选侍似乎还有点不放心,让魏忠贤跟着王安和皇长子一道出去。 说真话镇定自若,说假话气定神闲,这是官场的基本功。王安历仕三朝,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有遇到过,几句话蒙住了李选侍,领着朱由校就往外走。 但是,李选侍并不蠢,至少是女流之辈中的精明人。朱由校跨向门槛的一瞬间,李选侍弹射似的奔了过来。只是太迟了,冠军与第二名之间,差的就是这么零点零几秒。 王安甩掉李选侍伸过来的手,抱起朱由校冲出暖阁。门外,是接应的顾命大臣们。 在泰昌皇帝的灵柩前,大臣们山呼万岁。这个“万岁”,指的是朱由校。这一曲,叫作“柩前即位”。 谁离最高权力中心最近,谁就是官场中人的喉中鲠骨。在排斥李选侍的问题上,大臣们的观点高度一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离开这里。否则,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 王安在前边开路,宫里敢拦王安的宦官当时还没有;刘一燝、张惟贤一左一右扶住朱由校的手,护卫朱由校往前走;方从哲等人也紧围在朱由校的周围,杨涟负责断后,他那副大嗓门,对付七嘴八舌的几个宦官不在话下。 宫内瞬间闹出的问题,超出李选侍的预料。身边这几个宦官又不管用,李选侍只有亲自出马,但朱由校已经被大臣们拥出了乾清门。 这道门槛,一个嫔妃是万万跨不得的。李选侍扶在门上,发出一段尖厉而失望的叫声:“哥儿却还——” 哥儿,李选侍对养子朱由校的昵称。 乾清门外有一顶轿子,两老臣将朱由校扶上轿,但没有办法送一程——事先没有准备,轿夫没有过来。王安赶紧传唤轿夫,杨涟大吼一声:“我来!”周嘉谟、刘一燝、张惟贤也来不及说话,与杨涟一道抬起轿子就走。 周嘉谟七十多岁了,老尚书平时坐轿都嫌颠,没想到抬轿子还又快又稳。人的潜力,全是拼出来的。 绕过内左门,经崇楼、文楼,众人直奔文华殿。朱由校离了身边,李选侍怕是急疯了。这边大殿里正行君臣之礼,那边李选侍就不断派人来催,一共催了三次,都是要朱由校回到乾清宫。 这怎么可能呢?但不回去,总不能让朱由校住大殿吧?孙如游说,合理又合礼的办法,是让朱由校暂回慈庆宫,这里本来就是太子宫,毕竟还未举行登基大典。 究竟是“柩前即位”后算皇帝,还是登基大典之后才算皇帝?有时标准模糊一些是好事,凡事要便利自己,免为条条框框所困。 礼部尚书的意见,群臣一致赞成。那什么时候举办登基大典呢?诸臣商议时就难以统一了。最激进的主张是当天午时登基位,理由是本朝孝宗皇帝驾崩,武宗就是立即登基的;有人说最快也得初三日,登基大典要隆重,没有几天时间,准备工作做不好。杨涟一向风风火火,这回竟然迟疑起来,说:“先皇死而未葬,大礼不容草率,还是往后推一推,皇上登基大典是不是定到初六?” 该方首辅发话定夺了。方从哲说,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到底定哪天,这要看“安稳”二字。 表个态都拐弯抹角,杨涟当场怼了过去:“登基早晚,有什么安或不安的?”但最终杨涟还是很高兴的,诸臣商议的结果,是新皇登基的时间暂定九月初六,朱由校登基前这几天,就住在慈庆宫。 这一天,顾命大臣们辛苦了一天,大家总算如愿以偿。 傍晚路过文华殿,杨涟一眼就看到了左光斗站在道旁。看得出来,左光斗是有意等候在这里的。杨涟兴冲冲地把事情告诉了左光斗,说大事已妥,你就不用担心了。 左光斗听后,颜色更变,指着杨涟的鼻子骂道:蠢啊!即时登基,这么好的事情被你给搅了,若是夜长梦多,将你食肉寝皮犹为不足! 杨涟一下子被骂傻了,觉得左光斗骂得对,但又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 新皇帝迟几天登基,问题有那么严重吗? 1 黄仁宇式观察角度。作者把明朝历史从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横切了一刀,从此切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神宗驾崩,光宗速亡,熹宗柔弱,曾经历无数惊涛骇浪的明王朝,驶入了最为陡险的历史拐点;天启一朝,东林党迅速崛起,阉党随之坐大,其他朋党及各类正邪官员夤缘攀附。这不仅使全书获得全新的历史观察视角,充分透辟展示了1620—1628年间党争的来龙去脉,也借以状述万历末年天灾边年频仍、关外努尔哈赤起兵、大明王朝内忧外患骤然迭起等丰厚的历史背景,以及天启党争的尾声,而且由此形成了干练冷峻、妙趣横生的语言感受。 2 充分展示天启一朝前后明代宫廷政治的仪式与实践之侧面。作者精通万历皇帝、左光斗、叶向高、赵南星、顾宪成、魏忠贤、阮大铖等典型人物以及其中“移宫疏”、“东林党”崛起、宦官干政等典型情节之间丰富复杂的细节,以人物小传和细节勾连情节,推演事件逻辑,由此能够让人明白历史题材的镜鉴价值,同时不失形成有较强可读性、文学性的作品。 3运用恰切而生动有趣的史料。作者将相关史论、制度等寓于《明史》《大明律》《明实录》《天启起居注》等公共历史,以及《陈时政急著疏》《东林点将录》《宦梦录》《草木子》《先拨志始》《辨野史》等相关文人著述、稀有文人札记,如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史实史论融合,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