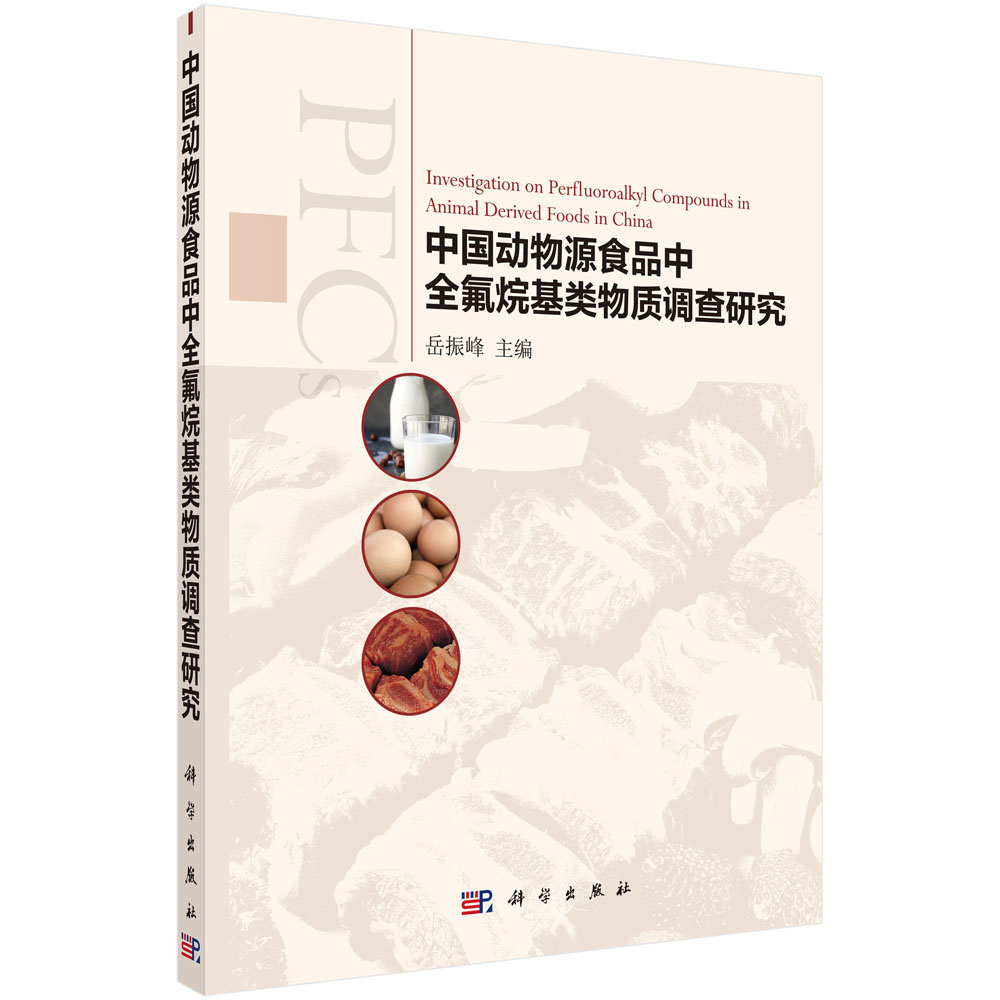
出版社: 科学
原售价: 368.00
折扣价: 290.72
折扣购买: 中国动物源食品中全氟烷基类物质调查研究
ISBN: 97870306988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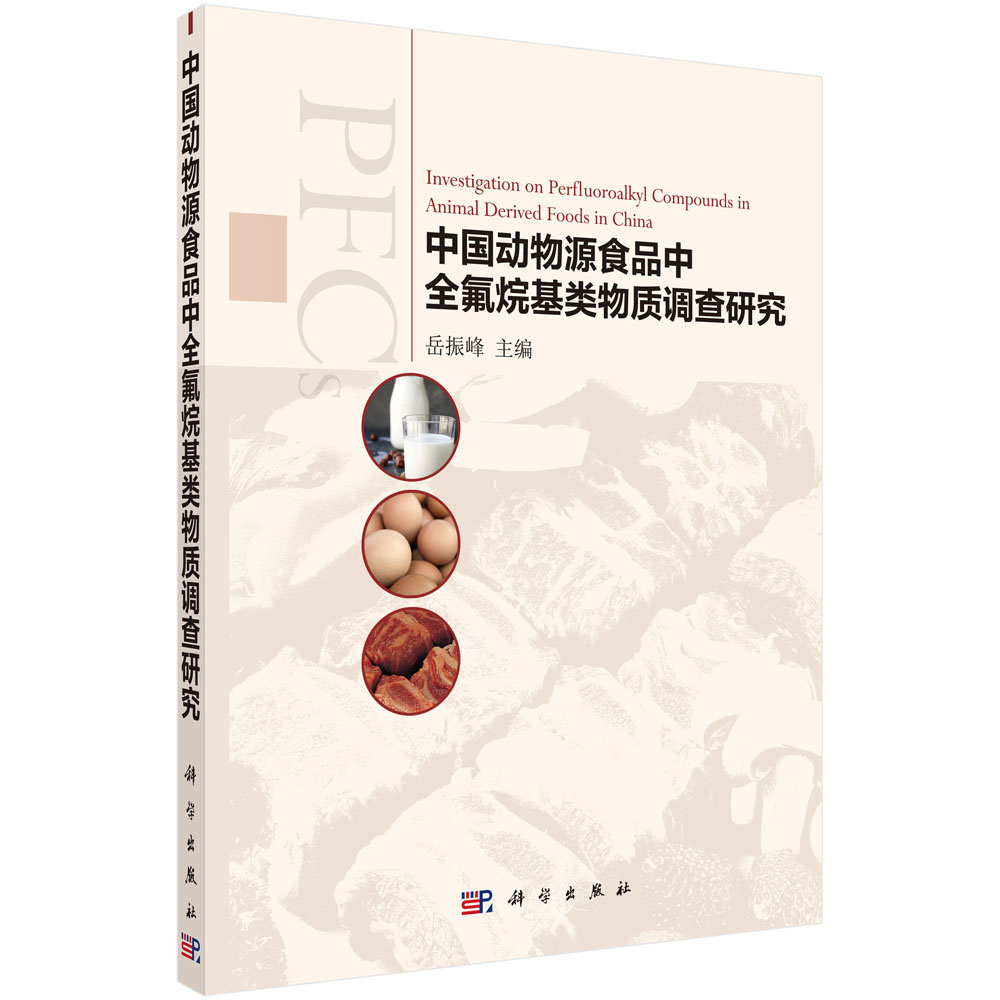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动物源食品中PFCs调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PFCs的化学性质与毒性
全氟烷基化合物(perfluorochemicals,PFCs)是烷基链上氢原子全部被氟取代,化学通式为 F(CF2)n-R,其中 R为亲水官能团的一类人工合成有机氟化物,主要是由离子型PFCs和非离子型PFCs等组成。随着工业技术的快速发展,多种PFCs被大量合成,其中,离子型PFCs是目前应用最广泛、影响最大、研究最多的一类化合物,常见的PFCs见表1-1。PFCs烷基链上的官能团为羧酸和磺酸基团,其化合物种类已达几百种,分别为全氟羧酸类(perfluorocarboxylic acids,PFCAs)和全氟磺酸类(perfluoroalkyl sulfonic acids,PFSAs)化合物。全氟辛酸(perfluorooctanoic acid,PFOA)和全氟辛烷磺酸盐(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PFOS)是PFCs的典型化合物,也是长链全氟羧酸或磺酸的最终降解产物。由于PFCs分子中存在极性极强的 C—F共价键(键能约115 kcal/mol),其中 F原子的3对孤对电子对中心碳原子有屏蔽效应,使其难以被亲核试剂进攻,因此这类化合物具有较强的化学稳定性、耐酸碱、抗氧化性和表面活性等性质。
表1-1 23种常见PFCs中文名称、简写、英文名称、分子量及结构式
目前,PFCs广泛应用在工业以及民用领域,如电镀、纺织品、皮革、食品包装材料、光盘表面材料、洗涤剂、农药、油画等。研究表明,PFCs是一类可对生态环境系统造成污染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可以通过大气、洋流、水体和食物链等途径蓄积在生物体内。实验表明,PFOS和PFOA在人体内的半衰期平均分别为8.7年、4.4年,PFOS的半衰期最长可达21.3年。体内PFCs残留与人体的环境暴露显著相关,近年来,PFOA和PFOS在多个国家人体血液、母乳,甚至胆汁和脑脊髓液中被频繁检出,与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对PFCs的暴露密切相关。研究数据指出,饮食、饮水和呼吸是PFCs进入人体的3种主要途径。现有研究表明,PFCs对人体的生物毒性主要通过与血清中的蛋白质结合来改变血浆或肝中游离和结合脂肪酸的分布或平衡。PFCs在生物体中有很高的蓄积水平,是二英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数百倍至数千倍,主要富集在动物体组织中(如血液、肝、肌肉和脾等),以血液和肝中分布浓度最高,在一定剂量下可对生物体产生肺泡壁变厚、线粒体受损、基因诱导、心血管中毒、甲状腺中毒、免疫中毒、致癌性等生物毒性。PFOS和PFOA为代表的PFCs因其表面活性高而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各个领域。据估算,PFOS全球累计排放量约达45250 t,PFOA为2700~6100 t。PFOS、PFOA等全氟烷基化合物具有耐光、热、化学和生物降解以及沿食物链放大的特性,能与生物体内蛋白质结合、蓄积并引发线粒体能量代谢障碍、脂肪代谢紊乱,以及生殖、发育、神经系统等的中毒现象。
二、我国PFCs产业现状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承接了发达国家的大量PFOS产业转移,环境和生态污染形势严峻,本底数据不清。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发达国家PFOS生产向我国的转移,我国近年来PFOS生产企业增加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能力,产能和产量增长迅速,实际年产量约达300 t。另外,还有部分PFOS企业刚刚投产,准备开机或试运行。因此,我国将面临妥善治理PFOS生产企业和妥善消化现有PFOS的巨大压力。作为第一批签署《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缔约方之一,我国已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等条例,旨在推动我国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减产减排的实施。但是,和欧洲国家相比,国内PFCs残留的研究工作起步晚,PFCs的数据和证据极其匮乏,不能客观体现PFCs在我国环境介质,动、植物食品,以及职业、非职业人群中的暴露情况。况且,我国的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出现了有毒化工等污染由工业向农业转移、由城区向农村转移、由地表向地下转移、由上游向下游转移、由水土污染向食品链转移的趋势,污染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污染混合的复杂局面,对生态系统、食品安全、人体健康等构成难以预料的威胁。中国履约,任重道远。
三、国外对PFCs的管理规定
鉴于PFCs有机污染物存在的广泛性、持久性、生物蓄积性及其对人体和生物体产生多种毒性,其对健康造成严重威胁。2012年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监测2006~2012年PFCs数据,发现膳食摄入能导致人体暴露PFCs的潜在风险。基于“清洁生产”和“环境友好”理念,美国3M 公司于2002年已停止生产PFOS及其相关产品,并于2015年前全面禁用PFOA。美国环境保护署(以下简称美国环保署,EPA)于2006年将PFOA称为“可能”或“疑似”致癌物质。目前,国际上许多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美国环保署、欧盟等]和国家积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管理及限制PFCs的生产与使用(主要是针对PFOS和PFOA的限量规定,表1-2)。政府组织也纷纷参与到其中,可见研究环境中PFCs的污染状况已成为备受关注的全球性热点问题。我国目前暂未出台对PFCs的政策和规定,但是我国对PFCs的管理规定高度关注,并正积极参与其中。
表1-2 不同国家(地区)或组织应对PFCs的措施
四、我国作为《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签约国的义务
作为PFCs的生产国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缔约方,我国不但有义务开展动物源食品中PFCs的残留水平调查工作,而且鉴于其对食品安全的重要影响,开展调查工作已迫在眉睫。畜禽肉类、鱼、虾、蛋、奶等动物源食品营养价值高,是人体获取优质蛋白的最佳来源和居民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成人日均摄入畜禽肉类50~75 g,鱼、虾50~100 g,蛋类25~50 g,奶类约300 g。但我国尚未开展动物源食品中PFCs的系统调查和监测,本底数据匮乏、系统性差,尚无法了解我国动物源食品中PFCs的残留状况和暴露本底值,更无从评价国民经动物源食品暴露PFCs的风险,这对全民族健康素质构成极大潜在威胁。因此,开展我国居民膳食结构的主要动物源食品(牛肉、牛肝、羊肉、羊肝、猪肉、猪肝、鸡肉、牛奶、鸡蛋、鱼、虾、贝类)中PFCs残留水平调查已非常迫切。根据项目研究成果将建立溯源性强、权威、系统的动物源食品中PFCs残留水平数据库,科学评价国民经动物源食品暴露PFCs的风险,保护人民健康,为PFCs控制、减排和摸清本底提供可溯源、权威、系统的科学数据,这不但是作为《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对于国家宏观决策、保障食品安全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二节 PFCs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PFCs的污染途径及环境污染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PFCs已在全球大范围使用。国际上生产PFCs的国家主要有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等。3M、杜邦和阿珂玛是著名的PFCs生产公司。Paul 等2009年对全球PFOS产量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79~2002年的总产量为96000 t。我国PFCs的相关数据不详,但现有的资料表明,截至2006年我国PFOS的年生产量约为200 t,且逐年增长。PFCs对地球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生产、运输、使用及产品废弃物处置过程中直接排放进入环境;另一方面是作为材料中的前体物,通过大气、洋流、水体和食物链等方式间接引入环境介质中。直接排放是造成环境中PFCs污染的主要因素。21世纪后期PFCs的环境污染问题已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研究人员已积极展开PFCs污染水平的调查工作。目前,PFCs在环境中污染范围广泛已是不争的事实,该类化合物在许多国家的环境介质中普遍检出,见表1-3。
表1-3 部分国家环境样品中PFCs污染水平
二、人体中PFCs污染水平国内外研究现状
人体PFCs的暴露途径为饮食、饮水和呼吸。有关PFCs人体样本的研究,对象多集中在人血、母乳等样本,分析其污染状况、分布规律,探究PFCs的人体暴露来源、途径及其影响因素等。在世界范围内的人体血液样本中也均检出PFCs,其主成分为 PFOS、PFOA和 PFHxS,数据主要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地区),结果呈明显的地区分布差异。Kannan等2001年分析了美国、巴西、比利时、意大利、波兰、日本等国家的473份血样,结果显示PFOS的检出率最高,其中美国肯塔基州的人血中PFOS含量最高(73 ng/mL),其次是波兰(54 ng/mL),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比利时、巴西等平均污染水平在10~20 ng/mL。Yeung等2006年分析研究了我国江苏津唐、浙江舟山、辽宁沈阳、贵州贵阳、湖北武汉、北京、福建福州、福建厦门、河南郑州等地的人血样本,其中沈阳 PFOS、PFHxS、PFOA的含量最高,与其他国家相比,尽管PFOA的含量偏低,但是 PFOS的含量最高,平均浓度为52.7 ng/mL,超过了美国、波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金一和等2006年研究了沈阳、重庆两地区人血中PFCs的残留状况,发现沈阳人血清中 PFOS、PFOA的含量高于重庆,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
2004年,Kuklenyik等第一次报道了母乳中存在PFCs残留,之后关于母乳的研究陆续有报道。Tao等2008年用 Waters的 WAX的小柱富集母乳中的PFCs,分析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母乳样本,结果显示母乳中PFCs的主要污染物是 PFOS,其含量为131 pg/mL,约为人血清的1/10。另外,Tao等在2008年分析了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和印度等7个亚洲国家母乳中的PFCs残留,共检出6种PFCs,PFOS为主要的污染物,7个国家中日本的PFCs残留最高,PFOS为232 pg/mL,PFHxS为92 pg/mL,根据 EPA的标准,可由此推算出1~6月婴儿的 PFOS日均摄入(average daily intake,ADI)为5.7~28.7 ng/kg。
三、动物体内PFCs污染水平国内外研究现状
作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PFCs易被处于食物链高端的食品动物富集,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地区)已积极开展动物源食品中PFCs的残留水平调查工作。“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直接影响公民最基本的权利—生命权、健康权,进入动物体内的PFCs主要与血清蛋白结合,蓄积并残留于肝、肾、肌肉等组织和蛋、奶中。诸多证据表明,鱼对 PFOS和 PFOA的生物放大作用可达500~12000倍,经食物链途径,在生物种群间转移,最终高浓度地蓄积在食物链高端生物体内。在高等动物体内已发现了高浓度的PFCs残留,其残留水平为有机氯农药、二英等 POPs的数百至数千倍。食品动物位于食物链的高端,其主要富集作为环境中最终代谢产物的全氟磺酸类(perfluoroalkyl sulfonic acids,PFSAs)和全氟羧酸类(perfluorocarboxylic acids,PFCAs)。当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已将 PFOA及 PFOS列入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表,以期对这些化合物在人体内的残留水平、变化趋势进行跟踪和评价,少数国家也着手对本土肉类食品中的PFCs进行分析检测。
关于动物样本中PFCs的残留报道,包括水生和陆生生物样品。雨水、河水、湖水、海水甚至北极地区海域等均已受PFCs的污染,使得水生生物样本中无一例外地检出PFCs的残留。伴随食物链的生物富集效应,北极熊、北极狐等陆生哺乳动物体内的 PF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