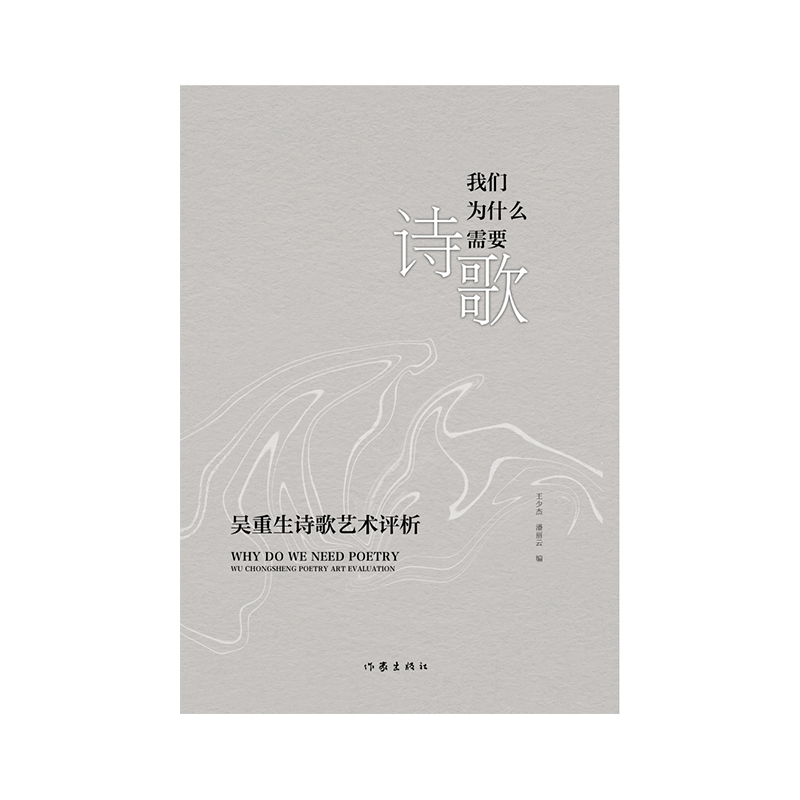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4.20
折扣购买: 我们为什么需要诗歌:吴重生诗歌艺术评析
ISBN: 9787521225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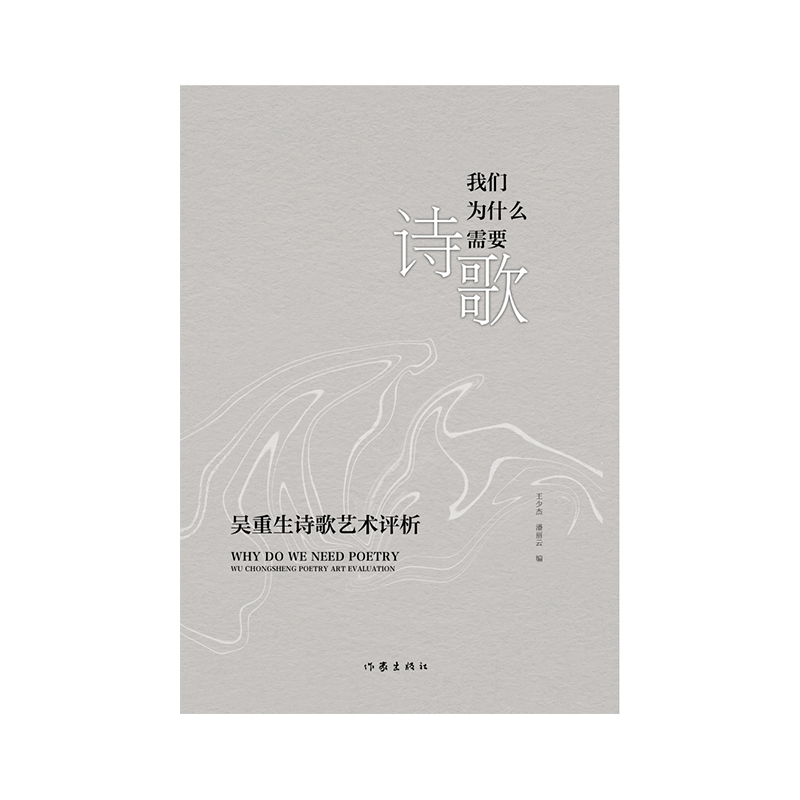
管王少杰,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权保委主任。供职于浙江省新闻出版系统。 潘丽云,浙江省特级教师,浙江省金华市外国语实验学校校长,浙江省名师网络工作室学科带头人。
用心中的光温暖彼此 谢?冕 一 各位下午好! 今天外面是艳阳满天,我们是久别重逢。我们隔离的时间太久了,从冬到春,从春到夏。对我自己来说,我的自我隔离是在己亥年的除夕开始的,那一天,我主动放弃了与家人团聚。不觉就到了庚子元宵,那一天,北京有一轮非常明亮的月亮。 吴重生有诗写到《今夜,我们不需要团圆》,但是吴重生的月亮是很独特的,也是前所未有的——“今夜,月亮是一支白蜡烛的横断面/风都躲在已经发芽的树梢里/今夜,我们不需要团圆/我们用心中的光温暖彼此”。也是这一天,一位诗人朋友微信向我祝贺元宵,我回复她:“元宵有月无节,大家也多保重。” 接着,就到了今天。岂止是久别重逢,今天是劫后重逢,我们都经历了一场浩劫。庚子年的春天,北京很奇怪,一场雪下完又一场雪,而且雪下得很大。也是诗人写的《昨晚,全世界都在下雪》,他用深情的诗句,向医生李文亮致敬:“从南到北,只有漫天飞撒的白/只有燃烧不尽的眼泪/就连夜的残骸,都是白的。”诗人用这些意象——“一支白蜡烛的横断面”以及“从南到北……漫天飞撒的白”,为我们概括了一个特殊的、难忘的年月。 有的人不在了,更多的人活着,诗歌和散文活着,文学和艺术活着。吴重生两本厚书,就证明我们都活着。捕云也好,捕星也好,诗人和文学家、艺术家是用天上的云彩来装扮我们的生活,是用天上的星光来温暖我们的心灵,用诗歌和文学来温暖我们、安慰我们。 谢谢大家。 根据作者2020年6月7日在“我心中的星辰云海:吴重生新书分享会”上的发言记录整理,已经作者本人审定。 二 2006年七八月间,吴重生随浙江省作家采风团赴新疆采风,当时我刚好在乌鲁木齐,我们一见如故。我为他题写了“穿越冰达坂”几个字,勉励他要努力穿越诗歌的“冰达坂”。 七年后,重生调北京工作,我与他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我与他曾多次一起参加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举办的诗歌活动。有时候活动结束得晚,重生就主动开车送我回昌平寓所。一路上我们聊人生,聊诗歌,话题广泛。2017年,他的女儿考上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我们之间有了一层新的缘分。 2020年6月7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在雍和书庭举办吴重生诗歌作品分享会,我应邀参加,并发表了感言。那天天气晴朗,我们以吴重生诗歌的名义相聚,朋友们久别重逢,分外高兴。其实岂止是久别重逢,简直是恍如隔世!我们都经历了一场新冠病毒带来的冲击。诗人吴重生用深情的诗句,向医护工作者致敬,为我们概括了一个特殊的、难忘的年月。 捕云也好,捕星也好,诗人和文学家、艺术家是用天上的云彩来装扮我们的生活,是用天上的星光来温暖我们的心灵,用诗歌和文学来温暖我们、安慰我们。 吴重生的诗写得好,散文也写得不错。这得益于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文学素养。我曾应邀去过吴重生的家乡浙江浦江,那是一个山清水秀、文风鼎盛的地方。这本《太阳被人围观》的诗集里有很多描写他家乡的内容。他的大境界得益于乡风的熏陶和家族的传承,他的乐观豁达和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得益于他“星空下赶路人”的人生定位。他的作品之所以充满温度与生命质感,是因为他在行走中指山为证,与云同行。他本身就是一条河流,在流动中与千万条河流相遇、交融;他的诗如桂兰,似菊梅,不择地而自芳。 吴重生的诗歌整体格调是激越温暖、昂扬向上的,光明是他的诗歌底色。在诗歌文体方面,吴重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读他的诗作,既可以读到气势的恢宏,又可以读到意境的深邃,还可以读到旁征博引的乐趣和善于发现的哲思。他的诗是内敛而深刻的,每一首诗里都藏着一个不一样的吴重生。 诗的太阳之所以被人围观,是因为它的光是柔和而可爱、美丽且温暖的。借用吴重生的一句诗敬告读者诸君——“我们用心中的光温暖彼此”。 原载《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2年9月30日)。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名誉院长,《诗探索》杂志主编。 致信太阳的诗人 ——我读《你是一束年轻的光》 吴思敬 吴重生的诗集《你是一束年轻的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来,得到了读者的关注和好评。特别是在作者的家乡浙江,可以说是掀起了一阵写诗、读诗、评诗的热潮。我通读了整本诗集,为他澎湃的诗情所感染。 吴重生是一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有不少优秀的新闻作品问世。不过,写诗需要有另一种笔墨。如果说新闻是走路,那么诗就是跳舞。走路有明确的目的,有明确的指向性,新闻的针对性就非常强,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缺一不可。诗在求真这一点上和新闻是一致的,诗说到底就是掏自诗人心窝的一句真话。不过新闻强调的是反映客观世界的真实,而诗歌则更强调表现主观世界的真实。何况,诗光强调“真”还不够,诗还应当是美的化身。从审美的角度说,诗是跳舞,跳舞不是要跳到哪里去,其自身就构成审美对象。而对诗歌之美的理解,也不应仅仅停留在美丽的字句上,而是要看其有没有独特的发现。 我想从诗作《我以树茬的名义致信太阳》说起。我认为这首诗是吴重生的代表作,因为这首诗里融入了他的生命,他的独特发现。诗人把半截树茬赋予了一种象征含义,把自己的生命注入其中。他把半截树已失掉的部分看成是自己的前半生,而他还要走下去,所以诗中说:“我积攒了这么久的岁月,被你生生折去,这半茬树桩,叫我如何系住流光”,这里寄寓了何等深刻的人生感慨!著名诗人牛汉1972年在咸宁“五七”干校写过一首诗《半棵树》,据诗人说是看到冯雪峰消瘦的形象受触发而写的。令人震撼的是它的结尾:“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这不只是宿命的宣告,更是带血的预言。当然,吴重生没有重复牛汉,调动自己的独特的人生感受,展开联想:“假如你让我变身桅杆,从这京城河畔,直抵宽阔的海洋,让我的后半生与风云相伴,如影随形,惊涛骇浪,才不枉你生生折去的岁月”。这里表现的是他对于已逝岁月的怀念和他对未来岁月的希冀。诗的末尾说:“今天就让我以树茬的名义致信太阳,给我一些火,我要将梦想点燃。”虽然前半生有蹉跎、有损失,但诗人并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而是渴望太阳的点燃。点燃什么呢?点燃梦想,点燃生命,让平凡的生活经过诗人心灵的过滤发出诗的光泽,让自己通过勤奋的劳动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这是一首很感人的诗,其强烈的生命意识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像《我以树茬的名义致信太阳》这样的好诗,吴重生的诗集中还有不少。比如有一首《切割时光的树叶》,此诗写的是树叶。而树叶曾是无数诗人吟咏过的题材。贺知章的“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可以说把树叶写绝了,你还怎么往下写?而吴重生偏能独出心裁,他不是从描写树叶的形态入手,而是从想象的层面展开:“这世界/真正能够切割时光的是树叶/每时每刻/切割时间和空间/ 把梦想切割成锯齿/把黑夜切割成鱼鳞/剩下的时光/将被来年的树叶切割”。多么巧妙,他把树叶想象成一种切割时间的刀具,一下子触发读者想到生命正是在时间的切割中被损耗的,从而促人警醒,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再如他写的《那一排椅子》,没有简单地去描摹这排椅子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给什么人坐的,而是展开想象的翅膀:“当我们老去/椅子们也随我们老去/只有风和云朵不会老/它们天天从背山面湖的地方经过/它们代表我/问候这些正在老去的椅子”。这首诗写的是椅子,同时也寄托了很深的人生感悟。日本学者松浦友久说过:“诗歌抒情最主要根源来自回顾人生历程时升华起的时间意识。”吴重生的作品就体现了这种时间意识。 最后,我还想就吴重生提出的“一日一诗”的主张说几句话。作为具有记者身份的诗人,吴重生提出“一日一诗”,用勤奋写作的方式追踪现实,表达对现实的关注,这是无可非议的。古人也有过类似“一日一诗”的提法,那指的是初学阶段。清代诗论家李沂写过一部《秋星阁诗话》,其中提到“初学须日课一首,或间日课一首,勤作则心专径熟,渐开门路”。这表明要学诗,必要的笨功夫还得下,拙力用足,巧力出焉。真正的诗歌,都是得力于诗人经验与情感的长期积累,得力于诗人在潜意识中的酝酿,而诗情的勃发往往就是潜意识中酝酿的成果涌上显意识领域的那一刻,此时出现的一些奇思妙想,如同电光石火般照亮诗人的思路,一首富有独创性的诗作开始成形。这种诗的发现,不仅是突发的,而且是短暂的,根本不是有规律的,每天能准时到来的。因此,经过了初学阶段,就应适当地放慢节奏,更多地在涵养心灵,观察生活,体验人生上下功夫。 吴重生是一位以树茬名义致信太阳的诗人。他每天写的诗几乎都是从尘世寄往太阳的书信,他的每一个文字都是太阳的孪生兄弟,发着光,透着温暖。祝愿他的光和温暖能够一直传递下去。 原载《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日第24版)。作者系著名诗歌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从思想和文化层面,对吴重生诗歌艺术进行了多视角、多维度的深入评析,并对诗人不同寻常的人生历程所形成的独特诗风进行了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