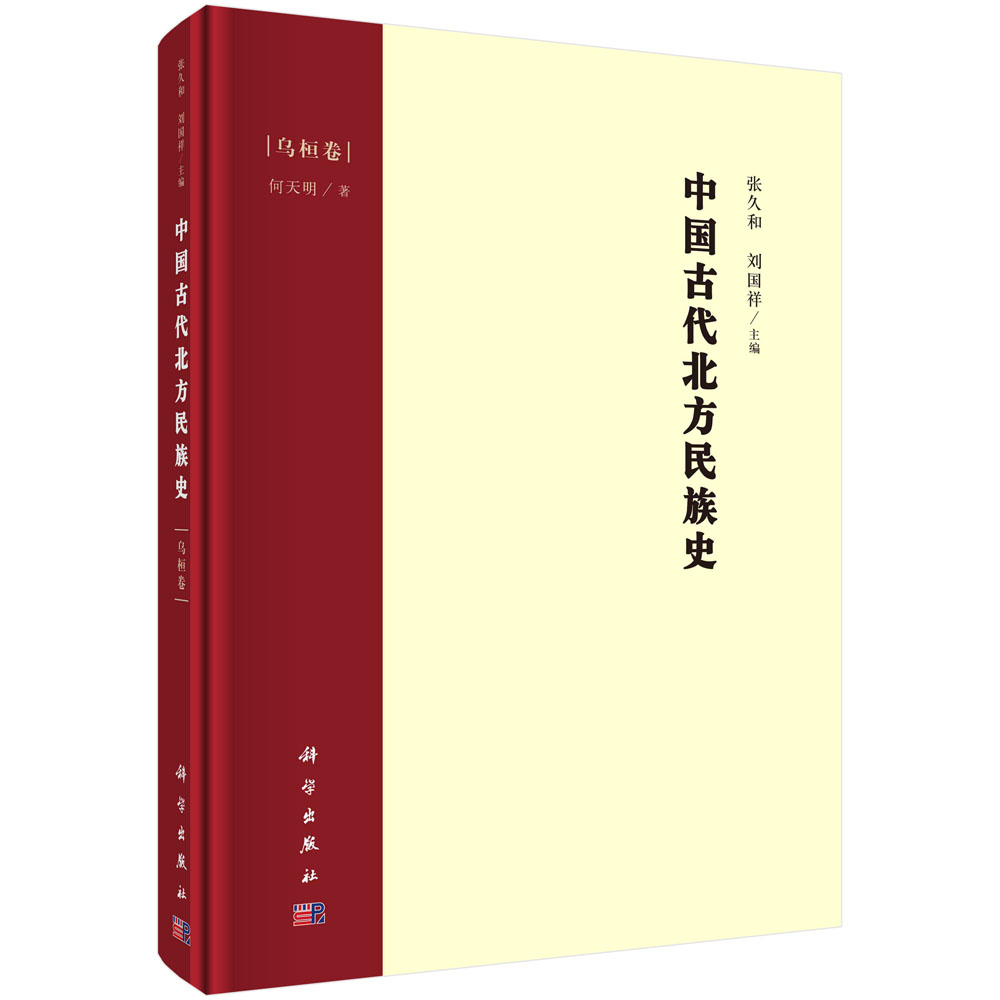
出版社: 科学
原售价: 128.00
折扣价: 101.20
折扣购买: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乌桓卷
ISBN: 9787030690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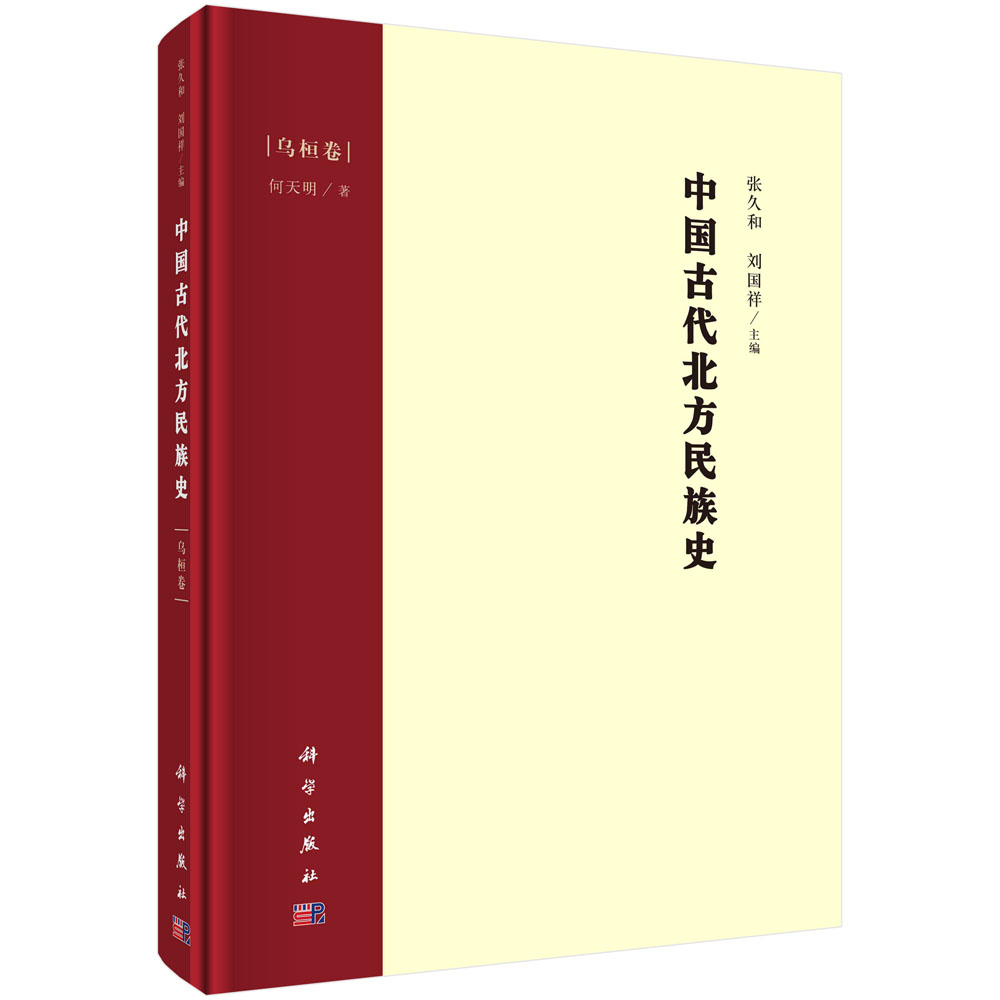
第一章 乌桓史料和研究概况
乌桓人在中国古代有千年左右的活动历史,西汉末年至东汉、魏晋时期比较活跃,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乌桓历史情况也主要反映其在这几个历史时段的情况。魏晋以后至辽代,乌桓史迹在文献记载中逐渐减少,且难究其真。清代,一些著述中涉及乌桓及乌桓山,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值得注意。考古发现与研究为研究乌桓历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新线索,把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深入分析是推进乌桓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第一节 文 献 史 料
乌桓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出现较早,但系统记载乌桓历史的文献却只有《三国志》以及《三国志》注引《魏书》和《后汉书》等几部,其他古籍也或多或少可见与乌桓有关的内容,但多为转抄或对相关史实的考辨。由于乌桓历史与东胡被击垮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涉及东胡历史情况的《逸周书》《山海经》《史记》等在研究中也被高度重视。东汉时期的刘珍等撰写的《东观汉记》、北齐人魏收的《魏书》、唐代房玄龄等撰写的《晋书》、宋代司马光主持编著的《资治通鉴》、清代梁玉绳撰写的《史记志疑》、清代张穆撰写的《蒙古游牧记》等史籍,也都对乌桓历史或多或少有所涉及、订正或评议。对于不同时代的各类史籍的记述,在研究乌桓历史时均应辨析和参考。
在先秦史籍《逸周书》中,简略地保留有东胡的内容。书中记载的“东胡黄羆”“山戎菽”等,对于辨析东胡的源流和活动区域,从动物和植物角度判断其生活地区的自然状况和经济生活都是值得重视的线索。黄怀信等撰、李学勤审定的《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广引各部史籍之说,对深入理解史料颇有启发。
另一部涉及东胡点滴史迹的文献《山海经》,也在探讨东胡源流时受到学界的关注。《山海经》大体成书于战国中期至汉代早期,作者尚不清楚。对于此书,学界褒贬不一。这部书中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中的神话、地理、历史、民族、动物、植物等丰富内容,共有《山经》五卷、《海经》十三卷。虽然所载内容有些怪诞,但对研究远古时代的历史以及地理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东胡的历史情况在《山海经》中有所反映,特别是将东胡的地理位置定位在“大泽东”,还举出了“夷人”“貊国”等与东胡邻近或大体在一个区域内活动的有关古族的地理位置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司马迁《史记》的记载相呼应,至今仍然是学界考察东胡活动区域时参考的重要线索。
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这部史籍不仅记载了中原地区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西汉武帝时期的历史,而且系统记载了当时活动在北方草原地区的东胡、匈奴、月氏等族的历史。因匈奴与东胡和月氏有多种形式的交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东胡又比匈奴强大,所以《史记》中针对东胡历史的内容也相对较多。史料中直接或间接记载的关于东胡与匈奴势力的强弱对比,双方所在的主要活动区域和习俗、社会和行政统治形态、政治和经济关系,东胡如何被匈奴击垮,东胡与燕国的地理位置关系以及战和交往等,对研究乌桓的源流都是十分珍贵的史料。而《史记 货殖列传》中提到“乌桓”这个名称,说明当时乌桓已为人们所知,也为探讨东胡与乌桓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线索。司马迁撰写《史记》是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至征和二年(前91),这部史籍中有“乌桓”名称出现,说明司马迁撰写时有相应的依据。
班固亦为汉代史家,其撰写的《汉书》,在体例上基本承袭了《史记》,虽然有取消《史记》的“世家”而将其并入“列传”等改动,但总体仍然是纪传体史籍。《汉书》尊奉刘氏为正统,注重系统地记载西汉时期中原政权历史的方方面面,并在帝王、官僚家族的记述方面着墨较多。对于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地区匈奴等族的历史,《汉书》没有回避,并且记述了一些《史记》没有载入的内容。乌桓族的一些历史情况,在《汉书》的《纪》《传》《志》各部分都有记载,而且比《史记》略显详细,直接提及乌桓情况的内容比《史记》有所增加。诸如西汉昭帝年间度辽将军范明友在辽东地区对乌桓的打击和迁徙;王莽时期与乌桓的关系,匈奴与乌桓的关系等。如果把《史记》和《汉书》对乌桓的记述结合起来,可以初步得知东胡被击垮以后乌桓历史的走向,与东汉时期乌桓的历史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所连接。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比较系统和全面地记载东胡与乌桓历史的史籍当属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生活在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一个政权(刘)宋时期。范晔少年好学,博览经史,个性颇强,凡事多有己见。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九年(432)冬,彭城太妃去世,范晔与兄弟广渊在其下葬的头天夜里酣饮,并以听挽歌为乐,激怒了彭城王刘义康,范晔被降职为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 ,时年34岁。可见,这部史籍是范晔在任宣城太守时着手撰写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点校说明”指出了范晔撰《后汉书》是“以《东观汉记》为主要依据,参考各家的著作,自定体例,订讹考异,删繁补略,写成《后汉书》”。可以肯定,“删众家《后汉书》”的过程,就是鉴别、取舍的过程,也说明当时可供参考的文献较多,如王沈的《魏书》、陈寿的《三国志》以及其他一些史籍。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内也谈到,“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 。以此来看,即便作者有凭主观判断选取内容之嫌,但博览众史,选“可意者”入书却是基本态度。至今,范晔当年参考的史书已经所存无几,《后汉书》保留下来的史料无疑是珍贵的。在这部史籍中,记载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至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间近200年的史事。实际上,其对建武元年以前历史的回顾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纪传体史书中的《乌桓鲜卑列传》,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乌桓的历史源流、习俗以及发展迁徙过程、与中原政权和北方草原地区各族的关系,这肯定是有益于系统全面地研究乌桓历史的。当然,在范晔撰写《后汉书》时,王沈的《魏书》和陈寿的《三国志》已经先其成书,《乌桓鲜卑列传》中的内容略同于《魏书》和《三国志》,说明范晔在撰写时做了参考和增删,也有保留。但是,不仅《乌桓鲜卑列传》的内容并不完全同于《三国志》和《魏书》,而且,《纪》《传》等内容中出现的与乌桓有关的史迹,也存在许多相异之处。所以在研讨乌桓历史时,《后汉书》仍然是值得细致辨析的重要史料。
研究乌桓历史的另一部史籍《三国志》,不仅记述了中国古代三国鼎立时期魏吴蜀大约60年的历史,还以较大篇幅记述了北方草原地区各族的历史,对乌桓被曹操迁徙到中原地区以前的历史记载较为系统。《三国志》记事相对完整,价值颇高。因其成书年代早于《后汉书》,又有裴松之的大量补注,史料价值尤显珍贵。
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涉及主要作者有陈寿以及为《三国志》作注者裴松之。陈寿(233—297)为西晋时期人,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省南充)人,《晋书》有《陈寿传》。陈寿担任西晋阳平令后,撰《蜀相诸葛亮集》。此后,又“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陈寿在《三国志》中专门设置了《乌丸鲜卑东夷传》。此中,对汉末魏初以来的乌桓历史做了简要记载,直至建安十一年(206)曹操亲征袁尚和蹋顿并将乌桓余众“徙居中国”,虽文字简练,但可窥其概貌。关于汉末魏初以前乌桓的历史情况,陈寿做出了“撰汉记者已录而载之矣”的解释。当然,在《三国志》的其他部分,也或多或少有与乌桓有关的记述,这些都是研究乌桓历史的宝贵资料。
虽然陈寿未能记载汉末魏初以前与乌桓有关的历史,但在陈寿死后约一百三十年,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增补了大量的内容,其中就有王沈的《魏书》、三国时期魏国人王粲的《英雄记》以及魏人鱼豢撰写的《魏略》。《宋书》卷64《裴松之传》记载,“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在裴松之的《上三国志注表》中,留下了他对陈寿《三国志》的评价,也谈到了为之作注时把握的几个原则,即“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按照这几项作注原则,对照王沈《魏书》关于“乌丸”的内容以及散布在《三国志》其他内容中的裴注,裴松之为《乌丸鲜卑东夷传》所补之注在内容上做了大量的增补,弥补了陈寿书中的不足。当然,对这些增补史料中那些类似“疑不能判”的内容,还需在研究中细致辨析,甚至要期待考古发掘的证明。
除上述史籍外,乌桓史迹还见诸唐代房玄龄等撰写的《晋书》、北齐魏收撰写的《魏书》,以及《旧唐书》《新唐书》《辽史》等各部史籍。这些史籍中记载的乌桓(或乌丸)情况,多与乌桓同各族交往、交融有关,内容呈零散分布状态,很难从中观察到乌桓在这些历史时期演变的总体面貌。而且,有的史料所载之事,已经是乌桓消失多年甚至百年以上的情况,如《旧唐书 北狄列传》所谓的“古乌丸之遗人”,《辽史》中提到的“乌州 本乌丸之地”等。这些与乌桓有关的史料,均应做仔细的辨析,在引用时当慎重对待。
第二节 研 究 概 况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乌桓是源自东胡,并在秦汉至魏晋时期有一定影响的游牧古族。
长期以来,学界对乌桓历史颇为关注,凡需进行考察和论证的问题,几乎都有专题性论文探讨,一些专著也用了较大篇幅系统阐述乌桓历史。在相关成果中,东胡与乌桓之间的族源关系、乌桓人的迁徙、乌桓人的习俗、乌桓与匈奴的关系、乌桓与鲜卑的关系等,学界的看法大体趋于一致。但是,由于史籍对乌桓史实的记载比较简略,可用来辨析和考订的内容很少,加之乌桓活跃在历史舞台的时间也较短,没有建立本族政权,其历史发展的纵向线索基本在被动迁徙的过程中展现出来,所以,对乌桓历史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整体把握始终是研究中的难题。如果与匈奴、鲜卑等大致处于同时代的北方游牧古族的历史研究相比较,乌桓史的研究仍处于较为薄弱的状态。尤其是在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上,研究者在对史料的取舍与认识、研究方法、对考古发现的评判等方面仍然各执己见,探讨之途仍然漫长而艰难。
至今,一些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为撰写一部全面、系统的乌桓史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只有汲取以往研究的精华,更为深入地分析史料,力争在有分歧的问题上有所推进,才能向着真实的乌桓历史面貌靠近。学界以往对乌桓的研究,正是在坎坷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为今天寻求新的突破点导向和铺路。
早在清朝初期,致力于地理沿革研究的顾祖禹在撰写《读史方舆纪要》时结合“赤山”“乌桓山”的关系和位置,讨论了与乌桓有关的问题。一般认为,这部书完成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前,在时限上虽然仍然属于中国古代时期,但作者对问题的辨析和讨论已非一般性叙述和罗列史料,所以,亦可视为讨论与乌桓有关问题的早期著作。此外,在清朝时期的史书中涉及乌桓山问题的还有《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大清一统志》以及部分志书。至清朝后期,由致力于西北地区历史地理的学者张穆撰写、何秋涛补注的《蒙古游牧记》于咸丰九年(1859)由祁寯藻筹资付印,书中也对乌桓、乌桓山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此书运用蒙古语转音方法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至今仍影响着相当多的学者。而在1915年浙江图书馆的刻本《浙江图书馆丛书》中,清末学者丁谦的《后汉书乌桓鲜卑传地理考证》一卷也是对后人研究乌桓和鲜卑历史影响颇大的论著。除了以上论著外,光绪十三年(1887)曹廷杰撰写的《东三省舆地图说》等,也都涉及与乌桓山、乌桓有关的问题,在研究中也得到学者的关注。
近现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在对乌桓的研究方面不断取得进展,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仍然争议较大,但视野不断拓宽。
1934年,在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撰写的《东胡民族考》一书中,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