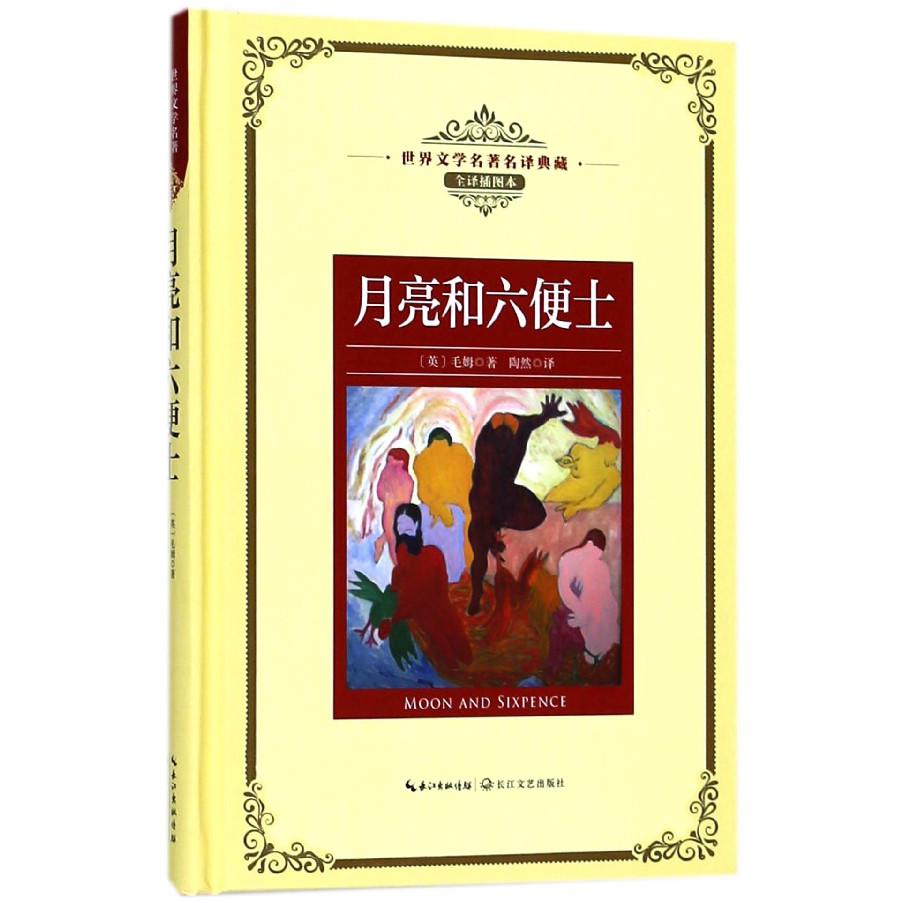
出版社: 长江文艺
原售价: 28.00
折扣价: 15.20
折扣购买: 月亮和六便士(全译插图本)(精)/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ISBN: 97875354914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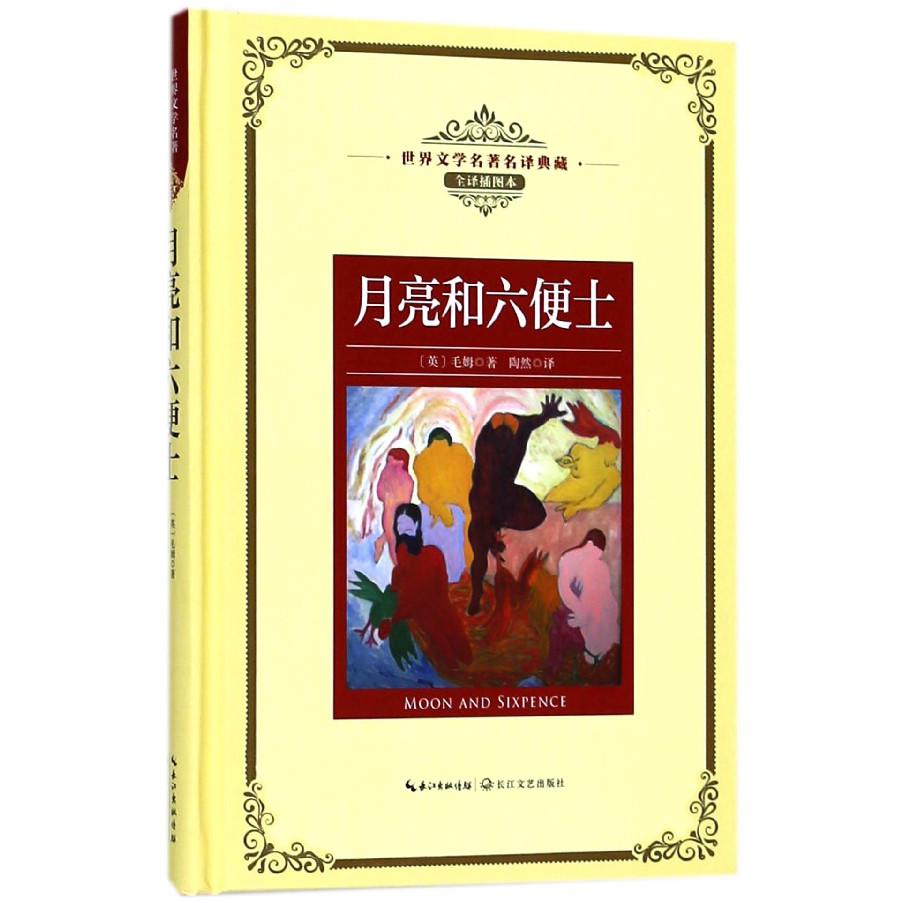
毛姆,英国小说家、戏剧家。生于律师家庭。父母早死,由伯父接回英国抚养。原来学医,后转而致力写作。他的作品常以冷静、客观乃至挑剔的态度审视人生,基调超然,带讽刺和怜悯意味,在**外拥有大量读者。**的有戏剧《圈子》,长篇小说《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等。
我离开大溪地的时候到了。岛上素有好客之道,许多熟人纷纷送来礼物,几只椰树叶编的篮子、野菠萝树叶编的席子、蒲扇什么的,提娅哈送我三颗小珍珠还有三罐她亲自用胖乎乎的双手做的番石榴果酱。从威灵顿去旧金山的邮船在这儿只停二十四小时,此刻已吹响汽笛,催促乘客上船。提娅哈把我紧紧搂在她巨大的胸前,我感觉像陷进波涛汹涌的大海。她眼里闪着泪,把红嘴唇压到我嘴上。邮船慢慢驶出泻湖,从礁石裂隙间轻巧地穿梭而过,驶进开阔的大洋。一阵忧郁涌上心头。拂面的微风依然夹着岛上的迷人清香。大溪地已远,我心知此生再也不会和她相见。翻过这段人生篇章,我觉得离无法逃脱的死亡又近了一点点。 回到伦敦,刚过一个月,我把手头的急事处理好了,心想斯朱兰太太也许想知道她丈夫*后几年的境况,就给她写了封信。我早在战前很久就没见过她了,从电话本中才把她的地址找出来。她如今住在卡姆敦丘, 我照她**的时间来到那栋整洁的小房。她这时肯定已六十开外,但保养得很好,没人会觉得她年过五十。她脸庞瘦,没什么皱纹,是那种优雅老去的类型,让你误以为她年轻时肯定漂亮得多。她的头发没怎么变白,发型得体,一袭黑袍也很时髦。我记得听人说过,她姐姐麦克安德鲁太太在丈夫去世后没几年也死了,给斯朱兰太太留了份遗产。从她这栋住房和开门女佣的端庄模样看,这笔钱足以让斯朱兰的遗孀过得挺舒服。 女佣把我领进会客室,原来斯朱兰太太还有个访客。得知他的身份后,我心里暗猜她约我这个点儿来并非别无用意。那位客人叫范布泰先生,是美国人,斯朱兰太太一边向我介绍他的身份,一边带着迷人的微笑朝他致歉。 “你知道,我们英国人无知得很。请务必原谅,我得解释一番。”然后她脸对我说:“范布泰先生就是那位**的美国评论家。你要是还没读他的书,就太落伍了,一定要赶紧补课。他在写关于亲爱的查理的东西,过来问我能不能帮上点儿忙。” 范布泰先生是个瘦削的男子,长着皮包骨头泛油光的大秃脑袋,鼓囊囊的大脑门下是一张深深刻满皱纹的蜡黄面孔,显得很小。他话不多,格外彬彬有礼,有一点新英格兰腔,举止有一股苍白冷漠的僵硬感。我不禁暗想他到底干吗要挖查尔斯·斯朱兰的料。斯朱兰太太提到丈夫名字时故意显得很柔情,我暗自觉得好笑。他俩聊的时候,我把房间打量了一番。斯朱兰太太显然紧追时尚,莫里斯风格的壁纸不见了,简朴的大花窗帘撤掉了,爱诗利花园会客室墙上的爱伦道装饰画1848年成立的爱伦道协会(Arundel Society)以推广艺术为宗旨,发行多种名画复制品。也不见了,如今房间里充满绚烂奇妙的色彩,我心里暗自嘀咕,她到底知不知道流行时尚强加给她的五彩斑斓的色调其实是南太平洋某座小岛上某个可怜画家的梦境。她亲自给了我答案。 “你这些靠垫真漂亮。”范布泰先生说。 “喜欢吗?”她微笑着说,“巴克斯巴克斯(Bakst)是俄罗斯画家、舞台设计家。设计的,你知道。” 墙上有几幅斯朱兰名作花花绿绿的复制品,这多亏一家柏林印刷商。 “你在看我的画啊,”她顺着我的眼光瞧去,“当然了,原件我弄不到,但有这些也是安慰。出版商亲自送给我的,对我是莫大的慰藉。” “每天欣赏这些画肯定很愉快。”范布泰先生说。 “的确,它们极具装饰性。” “我*由衷的信念就是,”范布泰先生说,“艺术大作都是很好的装饰品。” 他们的目光落在一个给婴儿喂奶的**女人身上,女人旁边有个小女孩儿跪着向不谙世事的婴儿递去一朵花。一个满脸皱纹骨瘦如柴的老太婆注视着她们。这是斯朱兰心目中的神圣之家。我猜画中人都曾经住在他在达哈沃北边的家里,那女人和婴孩就是爱塔和他们的长子。我默默思忖,不知斯朱兰太太对事实有没有一丝觉察。 大家继续聊着,布泰先生的谈话技巧令人惊叹,哪怕是稍带一丝尴尬的话题,他都统统避开,斯朱兰太太也是一句假话都没讲,却巧妙地暗示自己与丈夫的关系向来美满。*后范布泰先生起身告辞。他握着女主人的手,讲了一大通优雅动听但未免矫揉造作的谢词,离开了。 “希望他没惹你烦,”她在他背后一关门就说,“当然有时候很烦人,但我觉得嘛,有人问查理的情况,我必须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告诉人家才是。身为一个伟大天才的妻子,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她用那双可爱的眼睛看着我,依然像二十多年前那样亲切真挚。不知她是否在捉弄我。 “你那打字生意肯定不做了吧。”我说。 “对啊,”她漫不经心地说,“我做的时候*多是为了喜好,而不是其他。孩子们也劝我卖掉那桩生意,他们怕我太累了。” 看来斯朱兰太太已经忘了自己曾干过自食其力这种不光彩的事。她具有上等女子的本能意识,认为花旁人的钱过*子才算体面。 “他们都在这儿,”她说,“估计会愿意听你谈谈他们父亲的事。还记得罗伯特吧,嗯?我很高兴告诉你,他已经被提名,很快要*领陆*十字勋章了。” 她走到门口叫孩子们。一个身穿卡其布**的高大男子走进来,脖子上系着牧师领,英俊中带着一些粗犷,但眼神还像他孩童时期那么坦率。他妹妹跟在身后,年纪肯定跟我初次见到她母亲时相仿,母女俩长得很像,她也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她少女时期肯定比实际上*漂亮。 “还以为你一点都不记得他们了呢,”斯朱兰太太自豪地微笑说,“我女儿现在是罗诺德森太太,她丈夫是*兵少校。” “他是正儿八经从士兵升上去的,”罗诺德森太太乐呵呵地说,“所以现在才是个少校。” 记得我许久前就预感她会嫁个**,这是注定的,她生就一副*太太的优雅范儿,和蔼亲切,但几乎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想法:我与众不同。罗伯特也精神焕发。 “真是有幸啊,你这次来我正好也在伦敦,”他说,“我只有三天假。” “他恨不得立即赶回去。”他母亲说。 “呵,我承认我在前线过得好极了。交了很多好朋友,那可是顶呱呱的生活。当然战争什么的都很恐怖,但也把人*好的品质给逼了出来,这一点无可否认。” 接着我把斯朱兰在大溪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他们。我认为没必要提爱塔和她儿子,其余事情我尽量照准叙述。讲完他的惨死我就没再往下说。大家沉默了一两分钟,然后罗伯特·斯朱兰划了根火柴,点了支烟。 “上帝的磨盘转得慢,却磨得极细。”他有点装模作样地说。 斯朱兰太太和罗诺德森太太闻言就面色虔诚地低下了头,我心里很清楚,她们以为这是句**引文。事实上,我不敢肯定罗伯特牧师本人不存在这个误解。罗伯特牧师说的“The mills of God grind slowly, but they grind exceeding **all”一语是英谚,并非出自**。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爱塔给斯朱兰生的儿子。听人说他是个快活爽朗的小子。我脑海浮现他的模样:在那艘帆船上,他浑身只穿一条粗蓝布裤子,夜色中船儿在轻风推送下轻快地滑行,水手们聚在高处甲板上,船长和押货员懒洋洋躺在甲板椅上抽烟斗,我仿佛瞧见他跟另一个小子跳舞,在手风琴呜里呜啦的伴奏下**欢跳,头顶是苍穹星斗,周围是空旷浩渺的太平洋。 一句**引文差点脱口而出,但我忍住了,因为我知道牧师认为俗人侵犯他们的专用话语园地有点渎神。我那在威斯特堡当了二十七年教区牧师的亨利舅舅碰到这种状况就会说,魔鬼总能引用经文干坏事。一先令能买十三只大牡蛎的*子他都记得。 传世经典,大师译本,名师导读,名家讲播 天才小说家毛姆不朽经典,马尔克斯,村上春树,张爱玲,莫言共同推崇的名作,千万文艺青年的梦想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