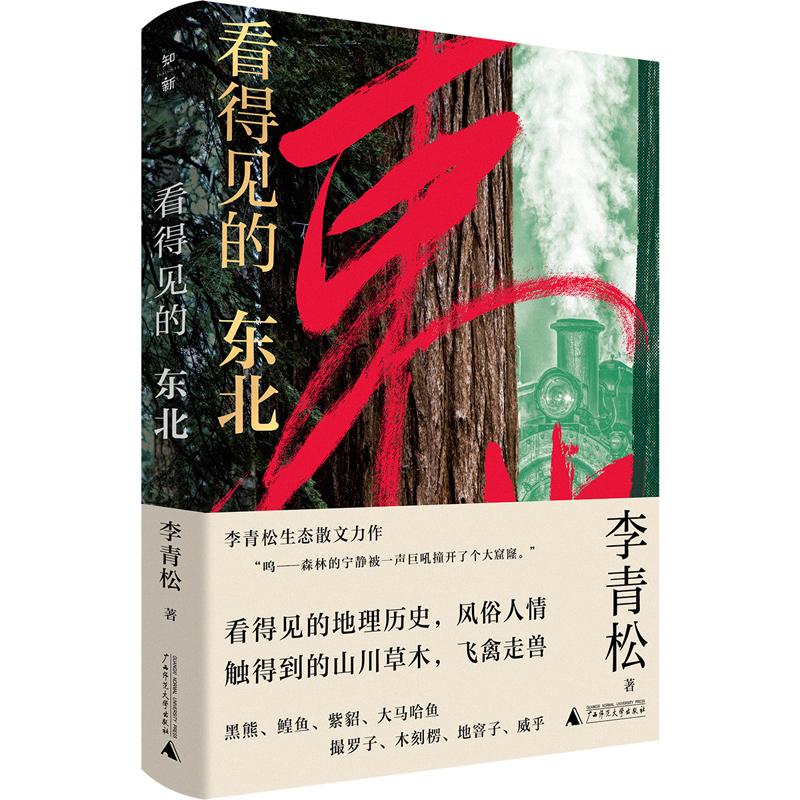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37.20
折扣购买: 看得见的东北
ISBN: 97875598735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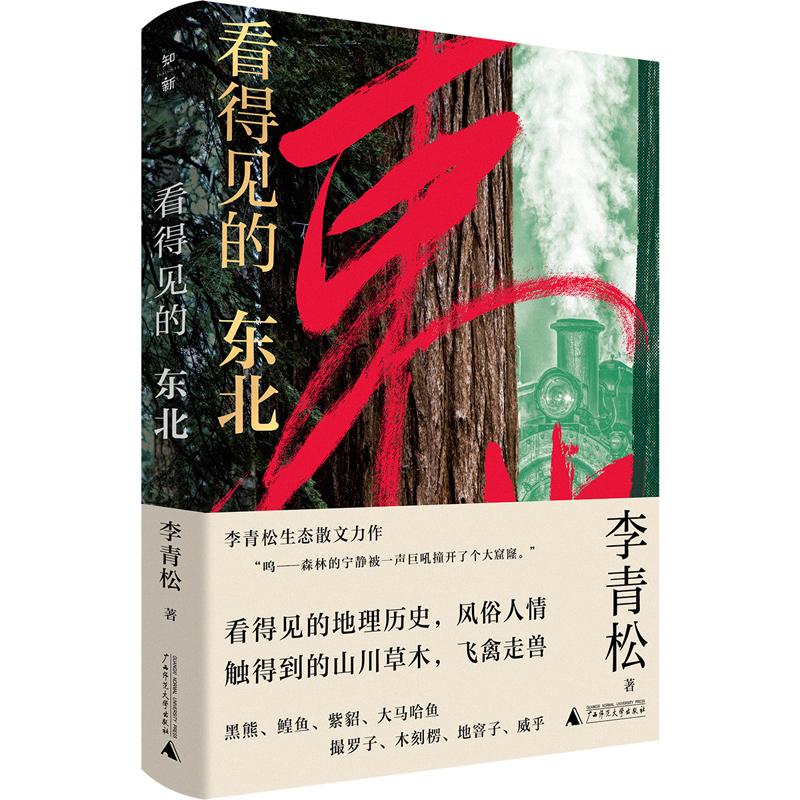
李青松,生态文学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第六届、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委。 长期从事生态文学研究与创作,发表生态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主要代表作品有《北京的山》《相信自然》《塞罕坝时间》《穿山甲》《万物笔记》《粒粒饱满》《一种精神》《茶油时代》《大地伦理》《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中国》等。 曾获新中国六十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北京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呀诺达生态文学奖等。
第 1 章 老号森铁 一 冬天,意味着寒冷和冰雪。 呜——森林的宁静被一声巨吼撞开了个大窟窿。疲惫的森林小火车吭哧吭哧喘着粗气,然后,吱的一声喷 出一口白雾,停在了林区某个小站。白雾飘舞,徐徐不散,或挂在行人的睫毛上,或挂在冻僵的树梢上,或挂在七扭八歪的木障子上,那场面很是有些喧嚣和野性。 曲波的《林海雪原》中有一句话:“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在“大木头时代”,林区人是多么牛气和豪迈啊!森林小火车运木头,一节车皮只能载三两根。那家伙,大呀,多了装不下呀!一根木头有多粗呢?光是树皮就 有砖头那么厚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早年间,林区吃的喝的用的都是小火车运木头从山外换回来的。的确,当年林区的辉煌和荣耀是与森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今天东北林区实行大禁伐,对森林来说无疑是个福音,但对森铁而言,却是个致命的打击。斧锯入库,森林休养生息了,森铁运什么?林 区人吃什么、喝什么? 传统意义上的林区已经很难找到了,与世隔绝、封闭的林区只是影视剧和小说里的事情了,到处是堆积如 山的大木头的林区已经不见踪影。林区特有的那种遥遥路途也已不复存在。如今,林区已大致成了静态的地方,它在地理上已经定域,今非昔比。 告别伐木时代之后,林区的困惑和尴尬,只有林区人自己知道。有的林区干脆把利用率低的森铁铁轨拆了,铁轨当废铁能卖几个钱算几个钱吧,总比在那里闲置着风吹雨淋地熬日月,生锈烂掉变成废品强。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森铁的问题并非一拆了之。 在黑龙江林区桦南林业局,我走访了森铁司机任景山。他开的是一辆老式外燃蒸汽机车,车号是“森 055”,需两个司炉不停地往炉内填煤,蒸汽产生动力,机车才能行驶。开小火车是个很脏的活儿, 任景山满脸都是油渍和煤灰,只有张口说话时的牙齿是白的。任景山干这个行当十余年了,对小火车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说,这家伙看起来很笨,但力气大,装上一座山也能拉走。他说,开小火车不需要太多的技术,最重要的是瞭望,对路况的把握要准,哪里该加速,哪里该减速,哪里要拉笛,一打眼便知道才行。 任景山微微叹一口气,说,早先森铁两边的树还很密,那时一年四季都在这条线路上跑,现在只有冬季里的两个月出出车,运运煤,干着不过瘾。我问他,没想干点别的吗?他说,干别的活儿,一下又很难适应。咱这森铁工人,若是离了森铁还真难活呢。说到这里时,他的眼睛有些潮。 我赶紧把话题岔开,说,咱们照张相吧。于是就喊当地的朋友傅刚为我们照相。咔嚓咔嚓,照了十几张,背景就是“森 055”号蒸汽机车。 这些照片,记录的也许是中国最后的森铁了。 二 清朝初年,清廷视满洲为其发祥地,实行封禁制度,即禁止采伐森林、禁止农牧、禁止渔猎、禁止采矿,通称“四禁”。因而,东北林区基本没有开发。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清廷设木植公司,山林的寂静才被打破。黑龙江东部,山脉纵横,林木茂密,其中最富之处,则为大青山,青翠弥望。光绪时订税章,由征收局代收,作为国家正款,其办法是由“木把头”领票入山采伐,木厂运销按照卖价而征其税。出于税源的考虑,清廷开始划分林区,组织木植公司进行采伐。 大雪封山之后,木植公司通过木把头雇用伐木工人,用大斧砍伐,用牛、马拉爬犁和河水流送的方式运输木材。 光绪年间, 清政府派员外郎魏震赴长白山考察林业。魏震在日记中写道:“木税为奉省入款第一大宗。”魏震 是个心细的官员,他在考察时把伐木工人怎么伐木,怎么运输,政府在哪里征税都搞清楚了。他写道:木把头每于冬初贷款携粮入山砍木,山雪封冻后道路溜滑如镜,木材由牛马自山巅拉运而下,堆存山沟。四月间,雪消水涨,奔流自山沟而下。乃穿成木排,编成字号运之入江,直达安东县大东沟,俗称南海。南北木商在此定购,奉局在此征税。魏震在日记中对临江还特意多写了几笔:据云,临江自二道沟以上至二十二道沟, 均在长白山之阳。山沟深处,丛林茂密,虽砍伐数十年不能尽,每年木把头约三万人。可见,当时的采伐规模之大,人数之众。 然而,无论怎样,这都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至一九〇三年,中东铁路的修筑完毕,掀开了沙俄掠夺中国森林资源的历史——此可视为中国森林史上惨痛的 一页。 一八九八年八月,中东铁路正式开始动工,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部三线,由多处同时相向施工。北部干线(满洲里至绥芬河)和南部支线(宽城子至旅顺),全长约两千五百公里,干支线相连,呈“T”字形,分布在中国东北的广大地区。中东铁路修到哪里,哪里的森林就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著名林学家陈嵘痛心地写道:“沿铁路两侧五十里内之森林,均已斫伐净尽。” 一个强盗尚未歇手,另一个强盗又抡起斧头。 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这场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两个列强间的战争,争夺的“肥肉”竟然是长白山鸭绿江流域的森林资源。沙俄战败后,日本无视中国主权,控制了这一地区的森林采伐权,强行没收了中国木商存放于大东沟的原木,蛮横掠夺了鸭绿江上的一切漂流木。 在强盗的眼里,中国东北的森林,可谓“遥望其状,苍苍郁郁,若黑云横天,际数十里,不见涯溪,近入林中,数千里古木老树,若巨蛇横溪,白日犹暗,虎狼跳梁,麋鹿腾踔,菁丛深邃,幽溪潺湲,疑在太古之世”。 一九〇八年,日本在安东(丹东)成立鸭绿江采木公司,进行更大规模的森林采伐。所采木材,除了在鸭绿 江水上流送, 还在临江十三道沟铺设森林铁轨,用森林小火车运输。 呜呜——呜呜呜—— 从此,东北林区就有了森林小火车喷云吐雾的身影。 一九三一年,日寇侵占东北后, 开始以“拔大毛”的方式盗伐红松、鱼鳞松、落叶松、水曲柳、黄菠萝、蒙古栎等珍贵木材。无数良材被森林小火车运出山外,再从安东用轮船运往日本本土或沉于日本海域,等用时捞出。 日寇侵华期间,总共从中国东北掠夺了多少木材,现在无任何资料可供查阅了,但有一个事实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日本投降后,东北林区的森林小火车光是运输日寇遗留下来的“困山材”(伐倒来不及运走的木材),就整整运了两年。 森林,疲惫不堪;森林,伤痕累累。 第 2 章 哈拉哈河 松鼠是森林里的精灵。 它那漂亮的尾巴飘飘然,轻巧灵活,光亮闪闪,妩媚动人。一会儿在身后,如同拖着一朵云,在林间蹿来蹿去,活力无限; 一会儿在身上,尾巴紧紧贴着后背,直立而坐,用前足当手,把食物送到嘴里;一会儿纵立伸直,停在树梢上,警觉地观察四周的动静;一会儿又优雅地卷起,翘过头顶,脑袋在尾巴的遮蔽之下,闭目养神。 它脚爪尖细,行动迅疾,身影转瞬即逝。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从一根倒木到另一根倒木,从一个树洞到另一个树洞。它生性胆小,机警敏捷,时刻小心翼翼。它是爬树的能手,脚爪歘歘歘,像带着电一样,上上下下,时而跳跃,时而采摘,时而抓挠。总之,它一刻也停不下来,挖着,啃着,咬着,嚼着,总是在折腾。它是快乐幸福的。秋天,它将橡果、松果、榛子收集起来,藏在洞穴里, 藏在倒木底下,藏在崖壁罅隙间,藏着藏着,自己也忘记藏在哪里了。无奈,冬天饥肠辘辘时,只得用前爪挖开积雪寻找食物。将积雪下挖出的坚果,一颗一颗带到树桩上,然后咬开,一点一点抠出里面的果仁。很快,树桩下,满是它扔掉的果壳苞片。几只喜鹊飞来,欢天喜地。喳喳喳!喳喳喳!喜鹊看见了果壳苞片里有东西在蠕动。 林学家说:“松鼠是播种能手。森林里,假如没有松鼠,树木的再生情况就会少之又少。” 大多数松鼠本性惧水,但哈拉哈河两岸的松鼠泅水本领超强。从此岸到彼岸, 抑或从彼岸到此岸,松鼠就抱着一块桦树皮跳进河里,用尾巴当桨,左右!左右!左右!顷刻间就划到对岸。有风的日子,它就御风而渡。尾巴直立在水面上,分明就是风帆呀,挺着挺着挺着,一摆一摆一摆,甚是有趣。 哪里河段宽,哪里河段窄,哪里河段水流急,哪里河段水流缓,松鼠清清楚楚。在哈拉哈河的狭窄河段,松鼠过河就更不成问题了。它只需在此岸的高大落叶松上抓住一根长长的松枝,荡来荡去,荡来荡去,然后将自己用力一抛,嗖的一声,一个弧线就抛到了对岸的 树上。 松鼠不仅多疑,且领地意识极强,对于擅自闯入自己领地的同类冒失鬼,必驱之。如果对方飞扬跋扈不愿离开,打斗一番就在所难免。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打斗,枯叶乱飞,断枝横跌,叫声悚然。 入夜,山的翅膀合拢成寂静。森林,在黑暗中生长。 后半夜, 月亮的牙齿咬碎了石头,哗哗哗!碎石落下来,惊醒了时间。 时间可以向前,时间也可以倒转。难以想象,哈拉哈河当初的一切都是液态, 还有燃烧物,以及一片火海。火山岩和砾石表面呈现出大大小小的石臼和蜂窝。 在石臼里,在蜂窝里,分明闪烁着躁动、发酵、渗透、磨蚀、膨胀、喷发等充满力量的词,这些词也许超越了矿物的范畴,无所不为,甚至不可为也为之。 可以想象火山喷发时的场面是何等壮观啊!俯身捡回几块扁扁的布满蜂窝的砾石, 拿回家做搓澡石吧, 一定很耐用。火山石仿佛还在散发着硫黄的气味, 这里空气像葡萄酒一样醉人。 站在高处望去,一切都骤然变了。 在粗大的蒙古栎和挺立的落叶松中间,闪着亮光的白桦,沿着山坡缓缓的斜面,一直延伸到河边。 在一处水流平缓的河段,只见几个渔人正在用拉网打鱼。网到的鱼多半是鳙鱼、嘎鱼、黑鱼,也有狗鱼、双嘴鱼、尖嘴鱼、鲇鱼、江鳕、白鱼。岸上开阔地带,立着一排一排的用木杆子做成的晒鱼的架子,上面摆放着大大小小的鱼坯子。 当然,如果运气好的话,网到了鲤鱼,是舍不得做鱼坯子的。 搬来几块火山岩,就架起了一口铁锅。找来一些枯树枝,用茅草点燃,木柴就噼噼啪啪地燃起来,一缕青烟,就袅袅升腾了。慢慢地,青烟飘进了林子里, 林梢上就像罩住了一张网。不经意间,那张网便被树枝划破了,变成了一团棉絮,既不像雾,也不像云。 瞧,铁锅里的内容可不是虚头巴脑的,仅仅流于形式,而是务实的大块儿的鱼肉,野性、豪横、蛮霸、磅礴。咕嘟咕嘟咕嘟!暗红的酱汤酣畅地翻滚,热气腾腾 一如阿尔山人的性格。这就是哈拉哈河岸边最著名的一道美食——酱炖鲤鱼。 哈呀! 空气里弥漫着鱼肉的香味,闻到的人馋涎横流。 然而,哈拉哈河的标志性鱼类并非鲤鱼,而是哲罗鱼。哲罗鱼生在哈拉哈河上游的江汊子里,长在 一代人的梦想之地,一域经济的腾飞之地 看得见的东北,是绿,是红,是生命,是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