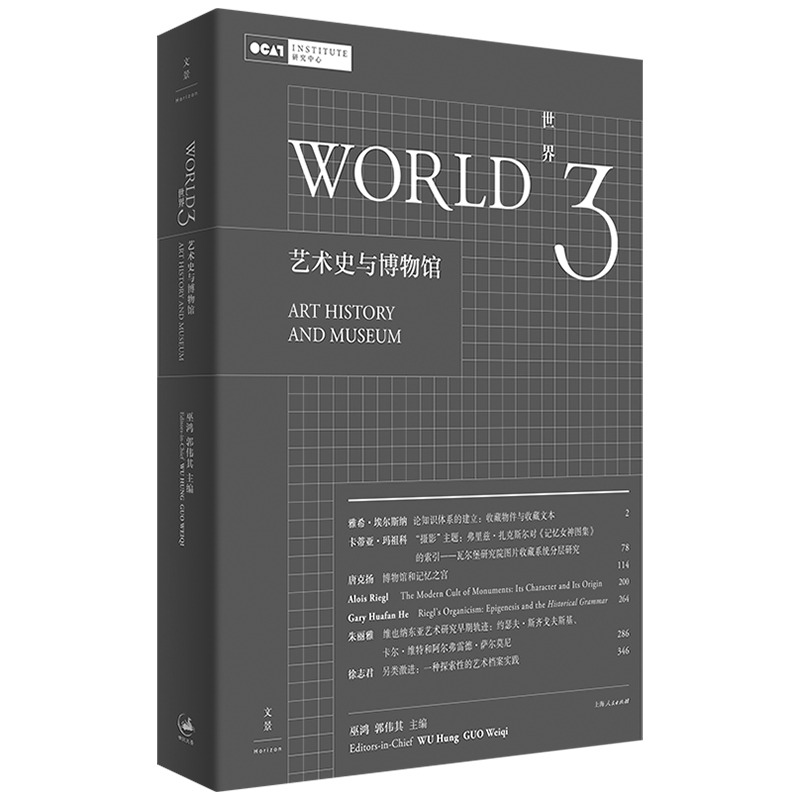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7.20
折扣购买: 世界3 : 艺术史与博物馆
ISBN: 97872081688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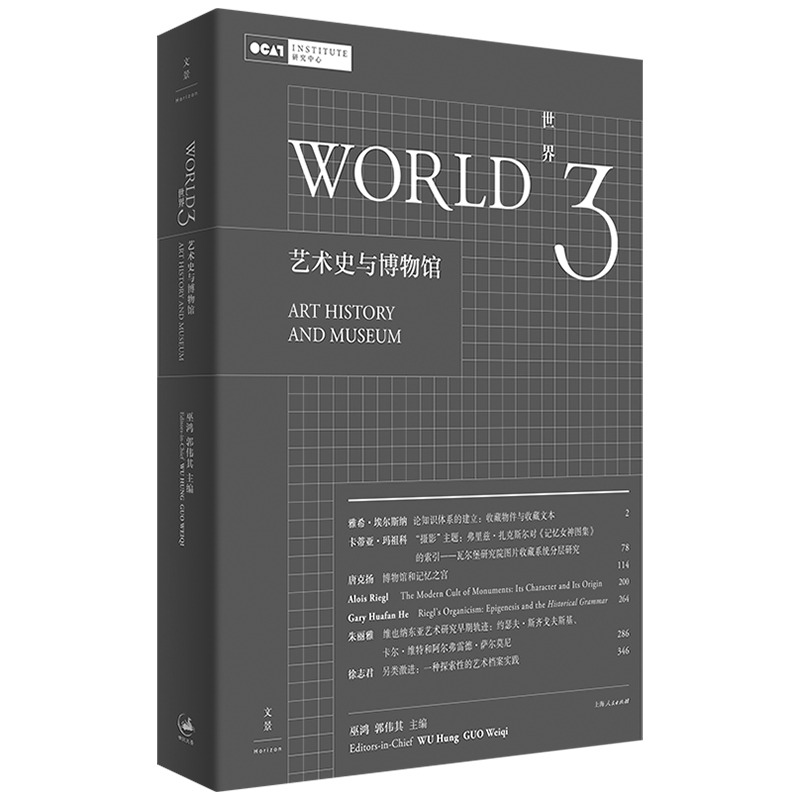
巫鸿,具有国际影响的美术史家、策展人。1963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1972—1978年任职于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1978年重返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与人类学双重博士学位。著有《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获1989年全美亚洲学年会最佳著作奖(李文森奖))、《中国古代美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获评1996年杰出学术出版物,被列为20世纪90年代最有意义的艺术学著作之一),参与编写《剑桥中国先秦史》(1999)等。 郭伟其,艺术史博士,2005年开始任教于广州美术学院,现为艺术与人文学院副教授,美术史系系主任,2016年起担任OCAT研究中心学术总监。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艺术史与学术史。代表性学术专著有《停云模楷:关于文征明与16世纪吴门风格规范的一种假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2年),代表译著有《时间的形状:造物史研究简论》(2019年)。
博物馆和记忆之宫(节选) 唐克扬 博物馆天然凸显建筑的时间属性—它“致力于研究、保育、传承和向社会宣谕世界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国际博物馆协会宪章》),它是过往和现下的桥梁。 “遗产”对应着博物馆不言而喻的核心观念,就是获取并让它的收藏贮存如初——“遗产”见证着过去人类活动的踪迹;可是,无论如何精心保存,“证物”毕竟是片段的,它注定和发展中的“世界”相暌隔,访问博物馆既是亲近也是远离真正的历史。不管是当代文化中的切片,还是从流沙腐土中被拾起的沧桑古物,它们在博物馆中便如身处冰箱冷藏室一样,无菌,清洁,虽然栩栩如生,却一律没有生命。作为一类“时间胶囊”,博物馆的显著空间特征,就是贮存物和外在环境的分离,内部时间和外在进程的分离—也许正是这种分离,让大多数博物馆建筑的外壳巍然不可冒犯。 与过往既相关又悖离,就这样,博物馆真正触及了文明的秘密,设计博物馆,便也是在进行时的文化中建立起一座“记忆之宫”。 不同文明的“记忆之宫” “记忆之宫”和不同文明的关系并非本文生造。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r)教授写过一本《利玛窦的记忆之宫》(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有关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年)在中国的行传。利玛窦利用了一种从希腊时代开始就风行西方的“记忆术”,来向万历年间的明代士大夫形象地宣谕西方文明的构成,试图以此让他们皈依陌生的宗教。大致说来,他所描述的室内是一座全然虚拟的“记忆之宫”,利用特定的空间关系把观念和形象组织在一起。 1596年,利玛窦首次向中国人解释,这样的“记忆之宫”是如何设计的,他感兴趣的不是揭示一般人的心理结构,而是试图利用房屋建筑的知识,建构起整个文明图景的“大厦”。他向与之交游的中国社会精英暗示,在泰西,“数百幢形状、规模各异的建筑物”构成了至为宏伟的“记忆之宫”群落,它超越了单个人的生命容量,这种恢宏的建构便也是一个文明的空间变身——当利玛窦在肇庆、南京、通州构思着他不可见的大厦,他是在回忆着文艺复兴的罗马吗?他在早年于那里学习了两年法律。 个体的经验是偶然的,体悟和心得是有关纷繁细节的,但是“记忆之宫”的一砖一瓦最终建成了一种总体性的结构,对应着人类经验的世界地图。它的机制,大约像传说中这种记忆术的发明者,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Simonides of Ceos)叙述的故事:诗人在宴饮的中间离席,突如其来的飓风吹塌了他身后的大厅,其他的欢宴者都被砸死,血肉模糊,肢体残缺,以至于难以辨认,但西摩尼得斯还记得他们各自的座位,依靠座位的空间关系重建灾难的现场,于是死者真实的关系由此建立。 这样的“记忆之宫”正像博物馆。在利玛窦笔下,构成“记忆之宫”的“宫殿、休息室和烟茶室”,都是常见的建筑类型,里面的陈设不乏日常物件,但是,它们所投射的却是一些不可见的心理结构,是逝去的,或者是间接的东西,后者就像隔着欧亚大陆,不为中国人所知的西方文明。与此同时,可见的物理现实所造成的具体的空间经验,决定了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记忆之宫”,即使同一国度的“记忆之宫”,也与当时社会发育的一般状况有关。尽管利玛窦觉得他的建构已经足够直观、形象了,但是他的士大夫朋友的反应莫衷一是——显然,生活在小红桥畔垂柳枝下的明代人,不可能用利玛窦同时代人帕拉迪奥(Andrea Palladio,1508—1580年)的方式去构造城市,想象与这种城市相应的社会制度。 于是,博物馆便同时浓缩了空间与时间。 仓库与镜厅 大多数博物馆的原型都是仓库。农业文明的仓库,来源于它的生产方式对不能把握的自然力的恐慌,当法兰西帝国从它的海外省源源不断搬回战利品的时候,或是阿拉贡的阿方索家族在他们的住宅中堆满希腊和罗马时期的古物、名人肖像时,这种贮存不复与具体的社会生产有关,但一样是多余之“物”—博物馆藏品和取得它的语境没有特别紧密的关系,相反,它明证着人工可以逆反自然。这样的贮存,就像谷仓中的谷子,不一定都被消耗和使用,有时候也超出了实际供给的需要。实际上,博物馆的收藏更类似于当代国家的战备储存,浪费掉的比例远大于实际流通的规模。 除非饥年来到,第一粒谷子和最后一粒间并没有质量和先后的差别——理想的仓库,因此是圆形的、静止的,并无空间秩序的分割,空气流通有限,其中也没有光。大多数的博物馆也正是如此沉睡着,它们滞涨的藏品库,可能永远也不会有清理清楚的那一天了,在老故宫博物院,或是堆满瓷器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展览仓库之类的地方,如果实在要准确地找出一件文物,人们需要依赖于枯燥的簿册(inventory),以及抽象的引得(index)去检抄货架,而不是空间本身的特征。 但是真实的博物馆实在又不止于此,它需要起码的逻辑,好在灰尘扑面的仓库里为由内而外的联想提供指南。如果有一件东西确实超出了人们的意识,那么它的存在实质上就失去了意义,记忆也是一样。根据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的比喻,纪念性质的空间之所以得以存在,是因为它赋予了社会中每个成员有关其成员身份的形象,即他或她的社会形象……假如以上种种反身性的形象聚集在一起,就会构成一个比单个的镜像更为忠实可靠的“集体镜像”——这,恐怕是“仓库”最终演化成博物馆的重要原因,它对应着古典传统中记忆是“灵魂容器”的观念;所以,博物馆对应着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也不是它的复制品,而是一个与之平行的世界。两者之间亟需沟通,哪怕是以招魂术的形式。 于是,“镜厅”代替了仓库。后者向前者演变进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是静默的空间中诞生了神秘的形象,最初,这种形象并不一定和当代生活有关,它可能是内向的,自我繁衍的。当路易十四将凡尔赛宫的中央大厅改造成其最辉煌的权力容器的时候,他能想到的最合适的象征图像,既不是符合“太阳王”隐喻的阿波罗,也不是力大无穷的赫拉克勒斯,而是自己——太阳发出熊熊光焰,但是会使人睁不开眼睛,古典图像的隐喻就像一层多余的墙纸,挡住了人们向比喻的本体投来的视线。现在,他的形象直接出现在墙壁上,与之呼应的是十七面巨大的拱镜,它们既反射出俯瞰花园的十七扇窗户,也让表现他个人功绩的视觉形象再现,以让人眼花缭乱的方式彼此映照,数量倍增。 好奇的人们会问:这些没有明确始终的镜像和反射,寓意着什么样的文明进程呢?在凯歌行进的历史到来之前,记忆并未真正苏醒,它只是天然有着增殖的本能—我们知道,同一时期的清代诸帝,也开始营造他们的“万园之园”,另一种样式的“记忆之宫”。在其中,不厌其烦的索隐和指涉成为帝国君臣的乐趣,那里的人们不需要“新”的文明发现,只需要自我延续的历史,它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掩盖了单性繁殖的秘密—正是在这儿出现了现代博物馆的滥觞,和人们寻常的印象相反,博物馆不只是忠实地守护着它的藏品,呆板地复制着现实世界的对称物,它一直在想法夸大它的容量,让记忆无边无际。正是有了“镜厅”,博物馆的实际规模才不再仅仅取决于它表面的尺度,正是莫测高深的外表,带来了对里面内容无端的猜测——“万园之园”也是“世界中的世界”,它打乱了人们对于等级和大小的通常理解,让博物馆不仅是一个时间的地窖,也成了意义突然爆发的超级星系。 著名艺术史家巫鸿主编,OCAT研究中心核心出版物。收录艺术史理论及相关领域的前沿性研究课题和译文,报道、评介国际资讯、图书、展览和研究机构。 “世界3”是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哲学名著《客观知识》中提出来的概念,它是指由人在历史中创造出来又作用于人的再创造的知识世界。本书书名援引“世界3”这个概念表明了它的学术态度和志趣,即希望开放性地研究艺术史的起源、现状、发展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