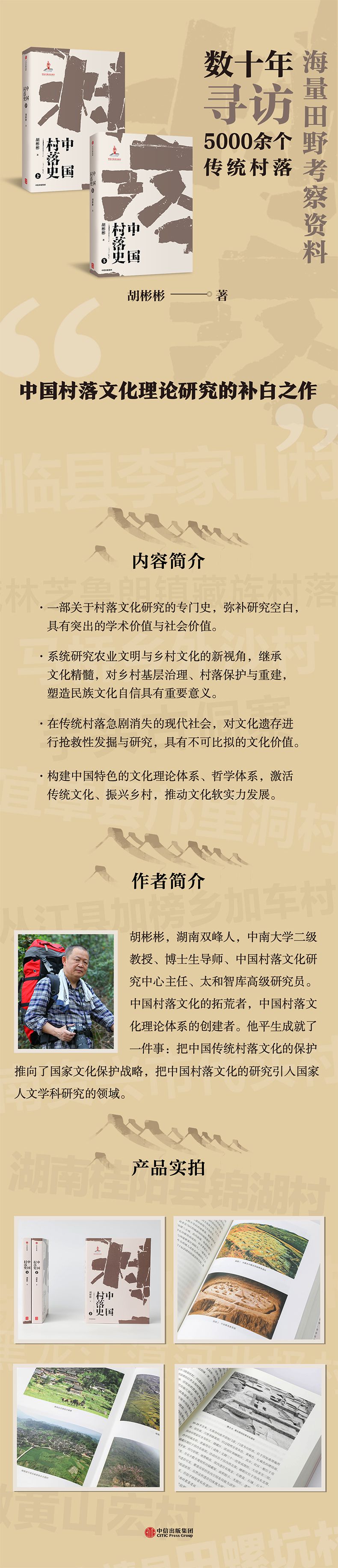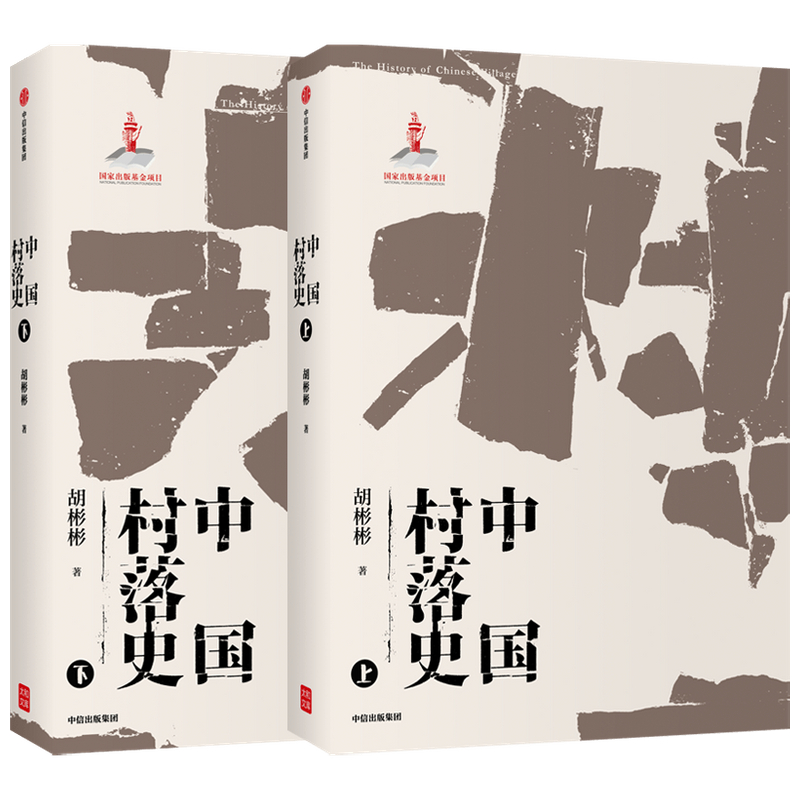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196.00
折扣价: 125.50
折扣购买: 中国村落史
ISBN: 97875217334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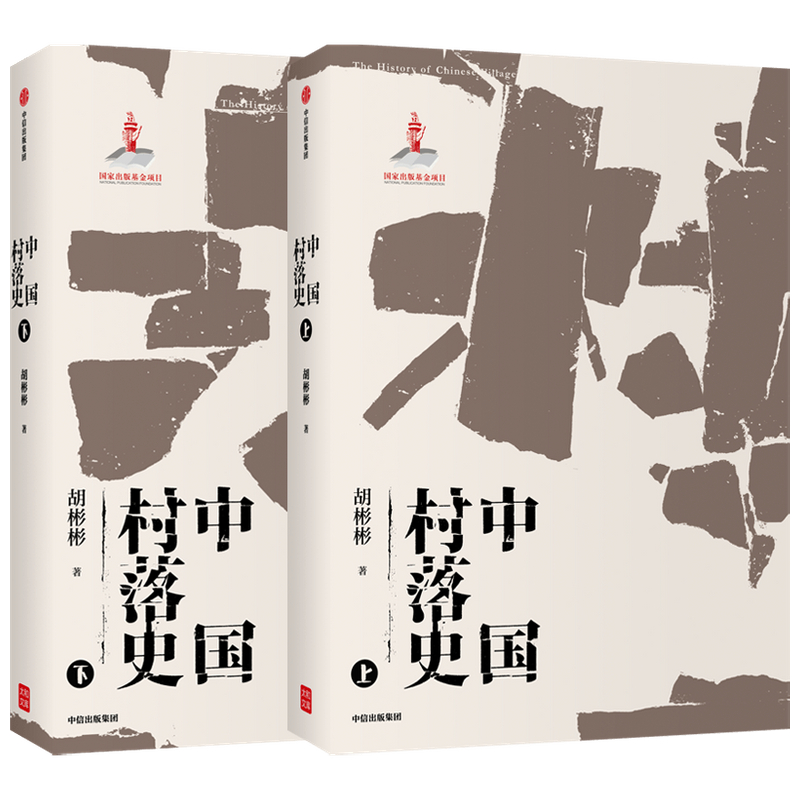
胡彬彬,湖南双峰人,中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村落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创建者,国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暨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平生成就了一件事:把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推向了国家文化保护战略,把中国村落文化的研究引入国家人文学科研究的领域。
自序 一 远古时期的中华大地,植物种类繁多,生长茂盛,伴随而生的许多动物遍布崇山峻岭和广袤草原,鱼类更是遍及江河湖泊。早期的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也是直接向大自然索取资源,以维持基本的生存。远古的中华先民,生活于山林中的,以打猎获取食物;生活于江河湖海沿岸的,以捕鱼获取食物。“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远古先民朴素的生存哲学。这些容易获得的肉类食物,让早期的先民形成了以渔猎为主的生存生活方式。不过,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先民的生活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距今12 000 年左右,北方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这一时期也正好是古气候学上的“新仙女木事件”1 发生期,冰期逐渐结束,气候开始变暖。不少草地变成森林,先民原先赖以果腹的动物随之减少。于是,他们开始采集植物为生,在漫长的实践中逐渐认识了可食用植物的种类,并初步掌握了其生长习性。他们意识到,通过种植劳动获得食物比纯粹依靠采集的方式获得食物更加可靠稳定。于是,他们开始注意收集种子,并不断摸索和改进种植技术。原始的种植业就开始萌芽了。同时,他们开始将一些捕获的尚未死亡的剩余猎物养殖起来。随着经验的积累,人们发现养殖动物比捕获猎物更省时省力,于是最初的养殖业出现了。种植业与养殖业,差不多是同时发生和存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北方地区各区域典型遗址,如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沙窝李遗址、属于磁山文化的磁山遗址、属于大地湾文化的大地湾遗址、属于兴隆洼文化的兴隆洼遗址、属于后李文化的月庄遗址等,均存在以粟、黍为代表的种植业遗存和以猪为代表的养殖业遗存。种植作物与饲养动物的出现,表明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具备雏形。而农业生产的形成,则使得人类定居生活成为可能。中华先民初步具备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不需要随处迁徙,可以比 较长时期地活动于某些相对固定和有限的地理空间之内。于是,早期的村落就在此基础上演变形成了。 在北方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远古村落民居,为半地穴式的方形建筑,屋内有保存火种与取暖用的圆形火塘,四周墙壁用木柱做骨架,外边敷一层草拌泥。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民居建筑,为半地下圆形,底部铺一层经火烧过的灰白色硬泥,墙壁光滑,屋顶为尖锥形。在南方地区,早期的村落建筑以干栏式为主,适合森林茂密、雨水较多、空气潮湿的山地,以后又有临水干栏式,发展到江河水溪遍布的平地。它以竹木为建筑营造材料,分上下两层,下层放养动物和堆放工具杂物,上层住人。东至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等许多遗址,西至云南的剑川海门口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川的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等,都有干栏式建筑分布。 定居生活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就目前考古发掘的出土资料看,在世界范围内,我国先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时间最早,距今1 万年左右就已开始。1978 年在甘肃发现的大地湾遗址,出土了已经碳化的粮食作物黍和油菜籽的残骸,距今已经8 200 年了。南方地区,在洞庭湖区的澧县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了距今6 500 年的水稻田,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保存最好、世界最早的人工水稻田。同样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中则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痕迹——稻壳与谷粒。而在湖南南部的道县玉蟾岩,更是出土了距今约1 万年的人工栽培稻种子。这是全世界目前所知出土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人工栽培稻种子。这些考古大发现确立了长江中游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稻作农业化的起源与发展中的重要历史地位,意义重大。 从自然条件来看,传统村落在中华大地产生,完全得益于温和的气候、适中的雨量以及肥沃的土壤。优越的自然条件为传统农业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所以在先民的农业思想里,就将农业与整个自然界视为一体。其中,时气属“天”,土壤属“地”,物性、树艺、畜牧三者属“物”,耕道、粪壤、水利、农器等则属“人”,天、地、人、物有机统一。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汉族农事历书《夏小正》,记载了战国之前的农业生产的内容,这些农业活动都在一年中特定的月份进行,与天象、气候、季节、物候紧密相连。这篇重要的农业文献,也将天地自然与农事活动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后来,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了传统的堪舆营造思想,村落的规划选址也更加注重与整个自然界的关系。 基于如前的出土物证,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之国。 商周时期的冶炼技术,带来了战国时期炼铁技术的成熟发展,这对于村落的发育有着重要的意义。铸铁铸造技术应用于农具制造,使得农耕文明的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铸铁农具的推广,使得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也使得人口规模扩大。中华大地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村落形态。其中,“聚”是文献记载的最早的村落形态,它有“汇集”“聚拢”的意思。这一时期的一些区域村落名称,大致还有“丘”“庐”等。 秦代开始,大一统的国家初步形成。不过,秦王朝持续的时间较短,它对于农耕文明的影响主要在汉代开始才见到成效。汉代的农牧分界线比较偏北,农耕技术也扩展到了塞外。汉武帝移民百万,使河套以南到陕北地区农业的繁荣程度可比关中。东汉到三国时期,气候逐渐寒冷,北方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与先秦时期相去甚远,加上连年征战,大量的农田遭到废弃。原来活跃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与农业民族争夺资源。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业经济出现大衰退。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带有防御体系的村落,即“坞壁”。著名的坞壁有许褚壁、白超垒(坞)、合水坞、檀山坞、白马坞、百(柏)谷坞,等等。这种防御性的村落,后世还在陆续产生。直到今天,湖南江永县的勾蓝瑶寨还遗存有城墙、碉楼、守夜屋等防御性建筑,它们为维护勾蓝瑶寨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以战略防御需求和客家文化为基础的福建三明、永安、龙岩等地和湖南郴州临武、宜章一带,更是有堡、寨、碉、楼等村落建筑,集防御与居住功能于一体,见证了人类战争军事、迁徙与农耕的历史。 唐代黄河下游许多林地已被开辟为农田,并通过兴修水利提高粮食产量, 隋唐江淮流域出现了强劲的开发势头。南方地区气温偏高,降雨量充沛,有利于水稻等高产农作物的种植,使得耕地在面积不变的前提之下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大量从中原地区南迁的移民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虽然政治文化中心仍然在北方地区,但是北方的粮食通常不能自给,需要从南方运过来。沟通南北地区的主要动脉,是此时修建完成的京杭大运河。南方丰富的粮食,从此可以源源不断地运至北方,为大唐盛世的开创打下了基础。中国传统农业以精耕细作、土地利用率高和单位产量高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到此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唐代的村落已经普遍开始以“村”来命名。杜佑的《通典》表明,唐代官方有明文规定,所有城墙外面的聚落都统统称为“村”。不过,它也许主要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地区。南方地区的村落,有一些是以“浦”“沟”“洲”“渚”等来命名的。从它们的水字旁就可以看出其明显带有南方水乡的特色。 北宋时,北方仍保持着政治文化的中心地位,但经济重心已逐渐转移到南方,南方的人口首次超过北方。为了应对人口增长和耕地不足的矛盾,王安石开始推行淤田。这是中国村落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此时,社会基本稳定,读书风气较浓。一些著名的文人主动关注村落生活,写下了大量有关农村安逸生活的诗歌,如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一》:“昼出耘田夜绩麻, 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它是在东晋陶渊明开创的田园题材诗歌的基础上的继续深化,即使在今天读来,仍旧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此时传统村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吕氏乡约》产生了。它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对后世明清的村落治理模式影响甚大。可以说,后来传统村落中的村规民约或者族约等,都是《吕氏乡约》的延伸版。 经历了元代的短暂战乱,明、清两代的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长江中下游的南方,一直都是当时的经济中心。其充足的农业生产,为北方提供了大量粮食、布帛和税赋。正是南方农业经济的开发与崛起,才使中国经济仍能保持大体平衡。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也大量增加。而且,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来自南美洲的玉米、甘薯等粮食作物开始传入,极大地解决了传统粮食作物产量不足的问题,使得在耕地面积总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粮食作物产量能够满足人口不断增加的需求。人口的繁衍,促进了村落的发展。不少今天被视为传统村落的村庄,大体上都是这一时期兴建和留存下来的。而我们视为传统村落文化主要内容的部分,包括建筑、民俗、乡约、教育、信仰等,也大多形成或定型于这一时期。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形成与延续,始终离不开传统农业的发展。中国是世界农业的起源中心之一,其传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发明创造,对中华文明的影响至为深远。可以说,中国传统农业是中华文明强大生命力的来源,是中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 村落的发展,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直接催生了传统城市的出现。种植业、养殖业带来手工业的产生,使得村落的产品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出现了“物物交换”这种最初的交易模式。随着交易的内容进一步扩大,以货易货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于是就产生了最早的货币——贝。金属货币的出现,让交易变得更为方便和规范。原始的偶然的交易场所,逐步演变成有固定时间和地点的集市。殷商时代,即出现了定时定点的集市贸易。《易经·系辞下》中说:“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村落集市的职能不局限于货物交易,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村落原住居民之间信息交流的场所。《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一句描述村落形成的话,经常被学者引用:“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它较为形象地反映出了当时一个小国的都城实际上是X 中国村落史 由早期的村落直接演变而成的。农事因人“聚”而成业,因人“聚”而成邑, 因邑落的发展而形成城市。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不需要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可以从农业中抽离出来,从事手工业、商业、教育甚至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 于是渐渐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传统村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与源。 二 尽管中国村落的发展历史如此漫长,但是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国内学术界足够的重视。20 世纪以来的一些乡村史研究成果,大多由日本学者取得, 这是令人汗颜的。原因在于,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史学家习惯于将目光聚焦在政治制度、朝代兴衰、学术思想、精英人物等方面,而极度轻视甚至排斥包括乡村社会在内的民间社会的历史、平民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研究被高度精英化。正如萧公权所说:“帝制中国的乡村居民绝大多数目不识丁。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所作所为通常不会引起那些能读能写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因而大部分未被记录下来。官员和学者经常提到的‘民间疾苦’,可能只是重述一般性的说法,而不是展示乡村生活的真实情况。”2 近代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少数史家开始批判传统史学的研究取向,倡导“新史学”,即历史研究要探索全民的活动,而绝非仅是帝王将相的活动,认为今日所需之史, 不再是“皇帝教科书”,而应是“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3。至此以后,特别是近代人文学科兴起以来,包括传统中国的乡村在内的民间活动及其历史才开始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当然,相比日本学者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热衷,近代以来的国内学术界仍显冷清。直至近几年国家将传统村落纳入国家历史文化保护战略之后,这一现状才稍微得以改变。当前学术界从文化、社会、经济和建筑景观等方面展开了对“村落”或“乡土”的研究,但对村落历史这一基本问题仍然极少涉足。因此,亟待对其展开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 村落史的研究有两种:一是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和泛指,指的是村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变迁,即村落作为一个聚落空间和社会单元在时间顺序上的纵向演化,包括村落的起源、发展、转型及其相关的影响因素和内容,强调对村落的宏观考察;二是作为一个具体概念和个体单位,指的是村落被组织起来的历史过程,包括村落的兴建、扩张、定型或废弃及其相关的影响因素和内容,强调对单个村落或村庄的微观考察,即所谓村史,具有村志性质。前者与人类进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以历史学学者关注最多;后者与一个族群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是一个相对具体的概念,以社会学、人类学学者讨论最为热烈,被称为民族志书写。如费孝通的开弦弓村、林耀华的义序和黄村、黄树民的林村、杨懋春的台头村、许烺光的喜州、杨庆堃的鹭江村、周大鸣的凤凰村等,都属于此类。拙著所述的村落史承系前者。笔者试图以历40年之久、数量5 000个以上的中国传统村落田野考察作为量化基础,对“中国村落”的缘起、形成与发展演变,以史学视角加以巡视。因而,本书并非某个具体村落的历史,但也并不忽视后者。后者往往作为前者的支撑个案,用于诠释、解读或者确证村落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面貌,反映村落的某些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作为有史以来便实际存在的生产生活空间和社会单元,村落是一个历时性和共时性兼具的概念,它不仅反映着有史以来农林渔牧业族群的生存生活状态,如食、衣、住、行、用等方面,而且承载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包括在前者基础上构建和形成的工具、器皿、衣物、建筑与制作它们的经验、技术,以及经济模式、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精神信仰、道德观念等在内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村落及其文化研究至少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7个方面的内容:(1)建筑营造与堪舆规划;(2)生产生活与经济模式;(3)文化教育与道德教化;(4)宗法礼制与村落治理;(5)民族民俗与宗教信仰;(6)民间艺术与手工技能;(7)生存空间与资源环境。4一方面,正因为村落包罗万象,所以与村落有关的内容亦十分广泛;另一方面,有关中国村落史研究的直接成果很少,事实上,非常有限而且取向不一的学术积累,也只是被分解于基层制度、乡村经济、宗族家庭、婚姻生育、民俗宗教和社会生活等不同层面的区分研究中,但哪怕是间接性的成果、个案研究的成果,对其加以充分的认识和梳理,仍然是有益而十分必要的。它的指向可能与村落史研究的学术理论有关,而且可能涉及历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科技史、宗教史、民俗史、建筑史、聚落史和环境史甚至历史地理等各个领域。这些散落在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一方面说明中国村落史研究尚有可供借鉴的某些间接性的前期成果,另一方面显示出村落尚未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广泛进入学术的视野,目前有关研究从视角到内容都仅处于碎片化阶段。与村落有关的学术理路显示,中国村落史尚未广泛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的视野,仍属于一块处女地。因而,无论从什么视角来展开对中国村落史问题的探索与研究, 从研究视角到研究内容上其开创性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没有成建制的体系性研究,但中国村落史研究已经历过三个阶段,大致如下。 1. 本书对中国村落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中国村落文化理论研究的补白之作。 2. 中国乡村中的活态文化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对村落史的研究能够提起学术界和广大社会群体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制度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视,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3. 在全球城镇化的浪潮中,乡村日益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但中国依然存在广大的农村人口,农民和农村、农业问题依然是关系基层治理和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对中国村落历史和乡村文化发展的深入研究和梳理,能够促使人们重新关注和重视乡村的价值和未来发展,为新时代的农村建设提供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