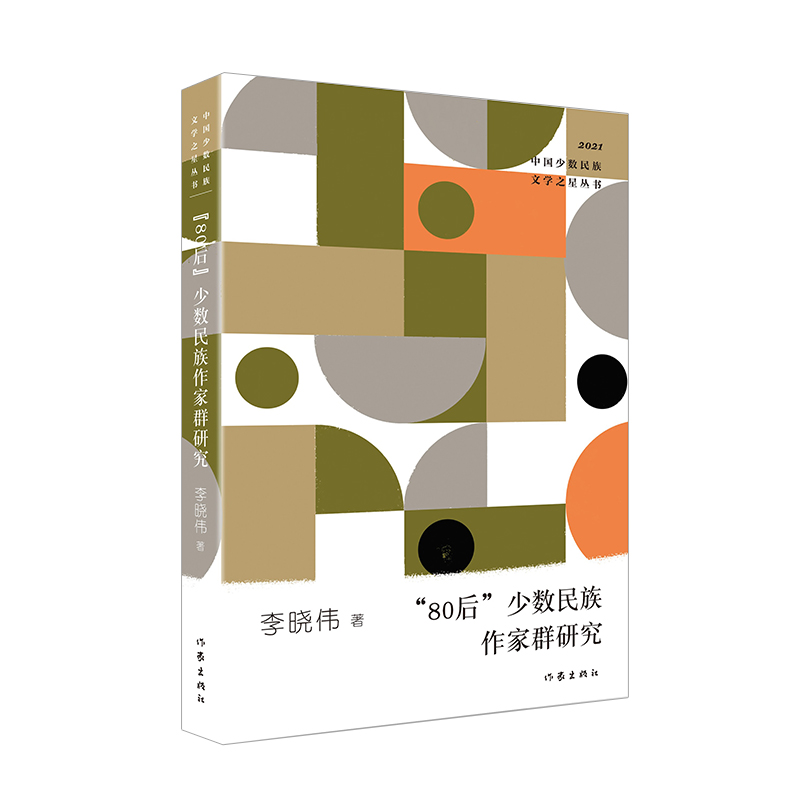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46.00
折扣价: 31.70
折扣购买: “80后”少数民族作家群研究
ISBN: 9787521215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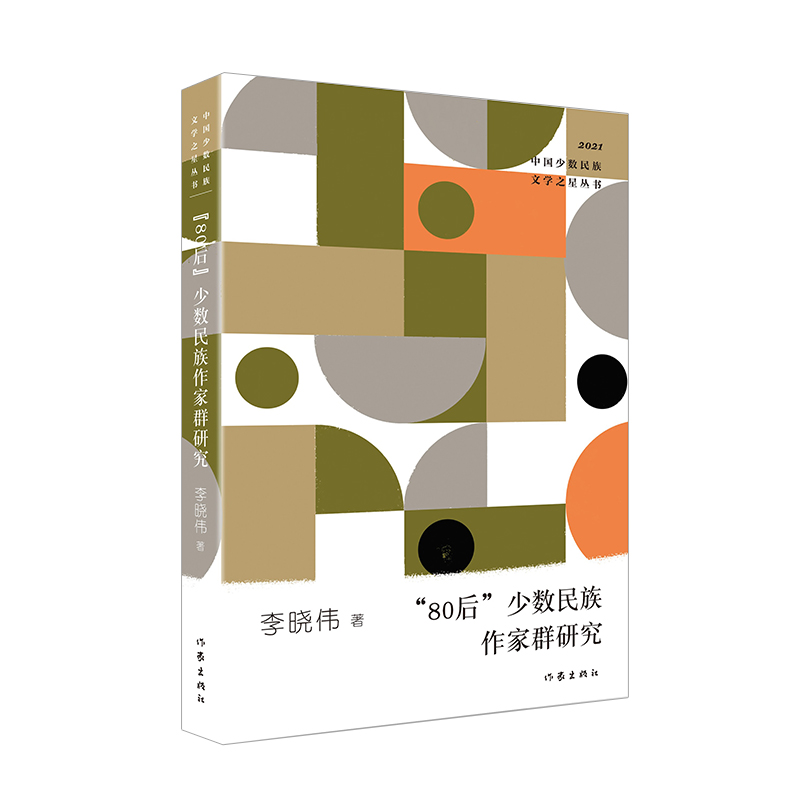
李晓伟,白族,1986年生于云南大理。曾先后求学于西北金城、东南金陵,获兰州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学位,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居鲁中,任教于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六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台湾大学访问学者,湖南大学中国全民阅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在《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鲁迅研究月刊》《文艺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图书评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等报刊发表文章二十余篇。自认是不入流的准文学研究者,但热爱与文学有关的一切,钟情鲁迅、卡夫卡,向往“五四”、“八十年代”。心怀善良,立己立人。关注边地、边缘。
绪 论 一、年代的侧影与群体的崛起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作家的队伍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在这其中,“80后”作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学生力军。因此,作为连接“80后”文学(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的一个重要纽扣,“80后”少数民族作家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在这里笔者愿意用这样一个关键词——“年代”来引出对当下多民族文学中的一些新态势的关注,这一年代当然首先意指文学中的年代书写,但在具体的讨论中,笔者更愿意挖掘的则是作家身上的年代标签,或者说是代际身份。尽管在整个文学场域之中,这群作家们看上去似乎还是文学新军,但在创作中却又呈现出极强的生长力。以自己对“年代”的敏感来书写不一样的年代,就如“80后”回族作家马金莲所言,“以年代为标题,把年份镶嵌进去,便是属于自己的年份书”①。 这样的“群体”我们大概可以从“大群体”—“小群体”的对应角度来理解,一方面,整体的“80后”作家在以代际依据命名下呈现出了大的群体特征,与之相对,在这一大群体之下,我们又可以以少数民族身份来找到一个小的群体,即“80后”少数民族作家群体;另一方面,这样的“大”—“小”又可以理解为大群体意义上的某一个或数个民族“80后”作家,以及小群体意义上的以地域性为特质的“80后”少数民族作家群体。 这些“80后”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普遍具有一种“双重视界”,即在“母语”与汉语、本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地方文化与都市文化之间游移,因此,对他们文学创作的研究,对于透视整个文学场域以及展望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都具有典型意义。在这样的代际命名之下,我们获得了一个别样的切入当下文学现场的视角。回溯文学史的线索,我们会发现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之路大致上是覆盖于整体的“80后”作家潮流之下的,而作为“‘80后’少数民族作家”这样一个在身份标识上更加细节化的作家群体称谓被文坛集中关注则要晚一些。2010年,作为唯一的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学杂志,《民族文学》以专号的形式在4、5、6三期分别推出了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青年作家的作品专集,在这其中,蒙古族作家专号实为“80后”作家专号,而在藏族和维吾尔族作家专号中也有着为数不少的“80后”作家的身影。在随后的两三年时间里,这些“80后”年轻作家便逐渐成为了一些研讨会和文学评奖活动中的主角,如2010年度的首届朵日纳文学奖上,陈萨日娜(蒙古族)的中篇小说《情缘》获得新锐奖,在此次文学奖活动上还同时举办了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青年作家研讨会。随后《民族文学》杂志社又在2013年的第5期推出了“‘80后’‘90后’作家专号”,至此,“80后”少数民族作家群可谓是真正地成形了。事实上,在2012年前后,一部分“80后”少数民族作家如鲍尔金娜(蒙古族)、杨蓥莹(满族)、马金莲(回族)、晶达(达斡尔族)、木琮尔(蒙古族)、陈德根(布依族)、陈克海(土家族)、何永飞(白族)、鲁娟(彝族)、冯娜(白族)、沙力浪(布农族)等也都先后出版了自己的作品,正式地走上了文坛。再到2016年度,又有十余位年轻作家推出了新作,这样集中的亮相可谓是当年度文学界“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个侧面”①。尤其是在2016年第十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上,陶丽群(壮族)、雍措(藏族)、马金莲、何永飞、鲁娟这五位“80后”年轻作家脱颖而出,在小说、散文和诗歌几方面分获大奖,而且马金莲还凭借《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奖,这足以说明这一年轻作家群创作的强大实力和生长性。 同时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与这些年轻作家们所取得的成绩相比,研究界对于他们的关注度却显得不那么“匹配”。年轻作家在迅速地崛起,但是对于他们的研究并没有能够“升温”。或者换句话说,研究者对这一群“80后”少数民族作家们的关注,更多的时候还是在一个整体的“80后”语境中去考察的。这样一来,一方面“80后”少数民族作家这一个极富创作活力的作家群体所具有的群体性特征就在整体的“80后”文学研究话语中被稀释了;另一方面,因为在整体“80后”文学中特异的少数民族身份的存在,常常使得这部分“80后”少数民族作家被单一地对应到某个民族文学当中,少数民族文学整体上的丰富性和多元化也随之被窄化。有学者就曾表达过这样的忧虑:“当某一位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出产生较大反响的作品时,我们很少或者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收获,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整体高度来界定其意义,而仅仅将之视为某个民族文学的收获,因此,其所具有的改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弱势和边缘地位的意义和影响便被大大削弱和降低。”① 再如另一位学者刘大先指出的那样:“……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批评与主流文学史的书写是脱节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捉襟见肘不光表现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著作的影响范围局限于民族地区和专门研究机构,更主要在于其研究水准的普遍低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边缘性地位并没有得到解决相反有日趋严重的倾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批评者话语系统的陈旧有关。”② 事实上不论讨论的出发点为何,这些学者们实际上都是试图在“多民族文学”的视野中来完成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重新观照,这也是本书的着眼点之一。 同时,这些焦虑实际上也代表着对这群作家展开研究的必要性所在,即在新时代语境下,对多民族文学的整体观照正在召唤着新的批评话语以及进入“多民族文学”这一文学场域的方式。在“前文学史”的语境中,作为文学史写作重要积淀的文学批评因为能够与时下的文学创作保持同步而兼具着记录、筛选、研究等职能。因此,研究的展开也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一群“80后”少数民族作家所强调的是“在场”的研究、批评,即保持研究与创作之间的互动。因为“文学批评的‘介入’,一方面,要求批评者在客观评价的前提之下对于文学的发展保驾护航;另一方面,批评者也与作家、作品一样都是独立的主体,所以‘介入’更应该强调一种‘对话’,而不是话语霸权。批评者与作家、作品甚至与读者之间都是平等的,在一种互动的交流、对话中共生、发展,并且推动作家继续创作,这是文学得以健康发展的依仗,也是批评的应有 之义”①。 二、文学生态场域的扫描 作为考察对象的“80后”少数民族作家,因自身特异的文学色彩和强劲的文学生长力在新世纪多民族文学版图中占据了重要的一角,与此同时,以这个作家群体为主的文学生态场域也在逐渐形成。 相较于同一时代的部分“80后”作家的登场,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们似乎更青睐于通过传统的文学期刊来开启自己的文学之路,特别是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国刊”的《民族文学》更是这些作家们重要的文学阵地,很多作家的重要作品都是在《民族文学》之上发表,并且在其上发表的作品数量也为数不少②,就如有论者指出的:“当代文学期刊形成的等级机制在少数民族作家身份认同的获得过程中表现了出来……文学期刊等级的高低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身份认同的范围和程度的大小。”③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专门刊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刊物,《民族文学》对于年轻作家的成长意义重大。 除此之外,一些着眼于民族文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省份或者是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所主办的文学杂志如《回族文学》(新疆)、《满族文学》(吉林)、《草原》(内蒙古)、《西藏文学》(西藏)、《朔方》(宁夏)、《边疆文学》(云南)、《山花》(贵州)、《飞天》(甘肃)等,也都是年轻作家们重要的发表阵地。不论是被视为“国刊”的《民族文学》,又或是各地区的文学期刊,这些刊物在不同的地理区域、期刊等级等维度间构建成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期刊方阵,它们对于少数民族作家、题材等方面的集中关注无疑是从外部来推动和强化了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们对自身民族元素的认识和书写,作家的群体性获得了塑形,这也是“80后”少数民族作家这一作家群体能够从整体的“80后”作家乃至是新世纪文学中突围出来的一个重要依仗。① 另外还需要注意到的是,这一批“80后”可谓是非常独特的一代,他们的成长是合流于中国融入全球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的。在这其中,改革开放、独生子女、互联网、城市化等时代关键词都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共同的时代印记。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逐渐渗透,让这一代作家们的书写方式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一些作家实际上是以网络作家的身份出道的,例如哈尼族作家秋古墨一开始就在网络上连载自己的作品,有《千年蛊虫》《葬仙》等逾三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到2020年又推出了新作《妖都行》,连载的方式是比较新颖的,一个是在“知乎”平台上连载的文字版,一个则是在“喜马拉雅FM”平台上进行的有声版的连载。但秋古墨的创作并不局限于网络,传统的文学形式也在他的手中持续,既有带着网络小说风格的《锦上花》(此作品也曾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的资助),也有以冷峻目光审视世态人生的《人间闹剧》,除此之外,他也还有编剧作品,这样丰富的书写形式当然是可以为这一批作家的多元化写作面貌做一个注脚的。 不少“80后”少数民族作家除了以传统的刊物投稿来发表作品之外,还集中在网络空间中进行自己作品的传播,例如利用博客、BBS等社交媒体空间,像向迅(土家族)、李达伟(白族)、何永飞、马金莲、张伟锋(佤族)等都从自己写作之初就开始将自己的作品整理之后发布到博客空间上,一方面,不论在纸媒上发表与否,作品都获得了更多的阅读,实现了从作者到读者的传递;另一方面,这个发表的空间又是开放的,作者与读者、作者与作者都能够在博客空间中与其他人进行交流、对话,所以文学空间实际上是被拓展了,从纸本再到网络虚拟,这显然是传统文学空间无法比拟的。① 在进入新媒体时代以后,文学的书写形式也有了更多的实践,这些作家们在保留着最初的博客空间的同时也开始了新的新媒体平台的实践,如壮族作家韦孟驰的微信公众号“文学营”,专注于广西年轻作家的推广;还有佤族作家张伟锋一直在管理着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土木文化传媒”(后更名为“诗与像”)。相较于博客空间,微信公众号的更新和传播要更加迅速、便捷,受众也更加地广泛,同时与传统传媒的差异也反向推动着作家们书写方式的多元化。以张伟锋为例,在他的公众号从“土木文化传媒”更名为“诗与像”后,写作形式的实验性质就被凸显出来了,即如公众号名字所代表的那样,“诗”与“像”也就是文字的 诗歌与图像的摄影两种形式的结合,无疑是对文学书写形式的有益尝试。 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各个级别层面的文学期刊互相交错,构建起了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的方阵,为这些年轻作家的文学成长提供了有效的空间。而在这些主流的期刊之外,其实还有着很多民间刊物在为文学默默发声,其中不少都是主要由“80后”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主持。例如仡佬族作家弦河曾经主持诗歌民刊《佛顶山》,于2012年创刊,连续出版5期后短暂停刊,后于2017年复刊,推出了“少数民族诗歌专号”“‘80后’‘90后’少数民族诗人诗选”两期专号,也受到了多方的关注。另外还有彝族诗人阿索拉毅虽然蛰居于大凉山,但却始终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回应着文坛。阿索拉毅于2011年10月独立创办了《此岸》诗刊以及“彝族现代诗歌资料馆”,主要通过收集、整理诸多的彝族诗人诗集(实物),包括诗集复印件、诗刊、电子诗集、诗论、彝族古代诗等相关彝族诗歌资料。截止到2019年,《此岸》诗刊一共出版23期,除一部分为合集外,其他均为各民族诗人作品专集。在主编诗刊之余,阿索拉毅还策划制作推出了“彝诗馆文丛系列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本是个人或是民间的编著,最终都得以正式出版,如《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1980—2012)》《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以及“当代彝族女性文学作品”系列选集等,不仅是对当下文学的记录,也是对过往文学资料的整理、收集。 可以说,这些来自于民间的文学声音与主流的文学期刊方阵为“多民族文学”营构了一个多元的文学场域,而“80后”少数民族作家无疑是这个文学场域中一道独特的年代风景。他们的写作既有着年轻一代的新颖和活力,也有着对传统的承续与发展,“从这些‘80后’少数民族作家身上,凸显着‘向内’与‘向外’两个维度上的思考……这些‘80后’年轻作家们思考内心的同时又关切外在,既有着民族性的独到,又同时在努力实现着更为广阔的跨越。”① 这样的“内”“外”兼修显然是他们群体性的重要特质。 将这些青年作家们以“作家群”的视野加以考察、研究,一方面是对当代文学版图的完善,另一方面则是力图在批评研究与作家创作这一个关系架构中找到一个互动的关节点,这是本书研究的目的之一;其二,“8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极具生长性,尤其是在新媒介时代背景下,对这样一种在各种平台之上呈现出成长式趋势的文学创作进行追踪式的研究,也是文学研究视野的一次转换;其三,“80后”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普遍具有一种“双重视界”,即在“母语”与汉语、本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地方文化与都市文化之间游移,因此,对他们文学创作的研究,对于透视整个文学场域以及展望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都具有典型意义。同时,对于这一年轻创作群体的整体关注与把握,能够对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前瞻性的指导作用。因此,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也将尝试从“80后”少数民族作家们文学内在的成长、与传统的对话和接续以及对于现实的多维书写等角度来展开对这群极富有文学生长性的年轻作家们的考察,以一种“在场”的研究姿态来回应这一股文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