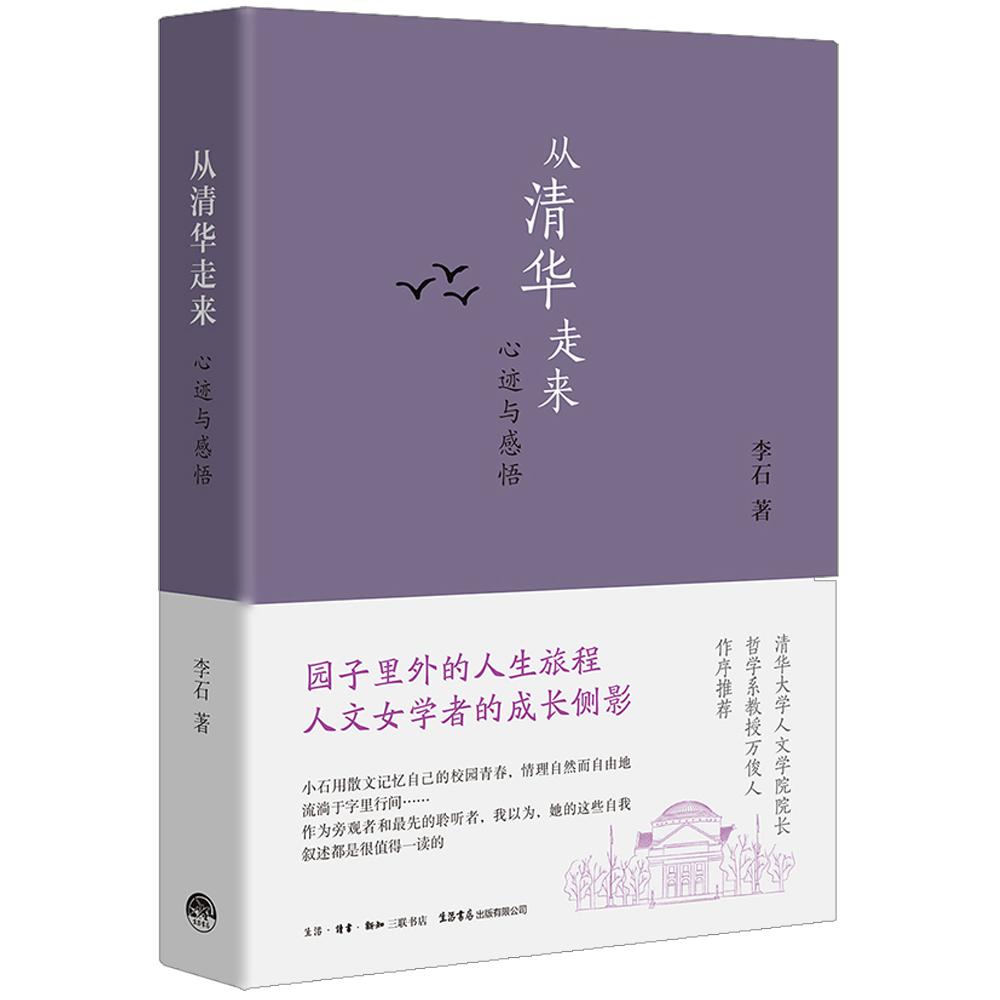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32.00
折扣购买: 从清华走来:心迹与感悟
ISBN: 9787807683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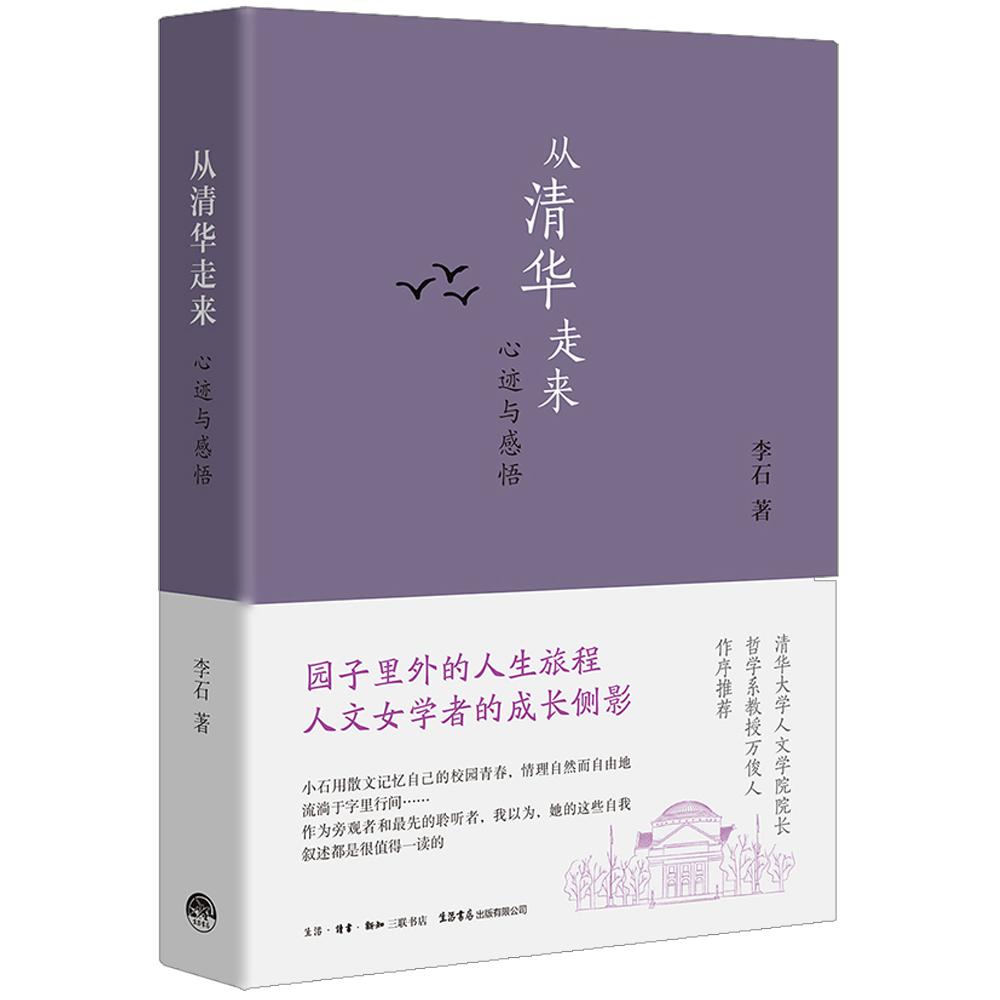
李 石 1979 年生于贵阳,清华大学理学学士、哲学硕士,意大利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LUISS)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先后访学于英国剑桥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学术专著四部、译著一部,发表论文六十余篇,主持个人微信公众号“她哲学”。 求学清华期间曾担任学生电影社团“露天社”社长,组织编辑人文月刊《露天报》;创办清华大学首个学生新诗社“火石新诗社”,定期出版社刊《火石诗歌》。诗作《露天,极美的一个词》收入《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诗集》(新诗卷)。
选摘一 幸运的背后(节选) 翻开我的履历,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我是个幸运的人。尤其是在学业上,自从中考之后,我就似乎没有经历过决定命运的考试。保送上大学、保送读硕士,申请博士留学、申请博士后工作……一路走来顺风顺水,基本没耽搁。然而,就像观赏绚丽惊险的花样滑冰的观众们看不到运动员在练习时会摔倒多少次,会付出怎样痛彻心扉的伤痛一样,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在这些幸运的背后都是什么。是明智的选择、残酷的竞争、亲人的鼓励,是坚持,是无奈,甚至是悲天悯人,这一切只有我自己最清楚。 一、一臂之力 二十多年后,我的高中同学们仍然会谈起我高三保送清华这件事,就像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似的。然而,当我回忆起二十多年前那个夏天发生的一切时,我却只能找到一个原因,那就是“幸运”。当然,幸运之所以眷顾于我,还缺不了父亲最终助我的“一臂之力”。 那是1997年的6月,我父母刚结束了一年的非洲之行,回到贵阳。他们回来的第二天,学校里就发布了一个关于“清华保送生”的通知。通知里说:清华大学要在贵州省招收两名“保送生”。(后来我才知道,清华每年会在全国招收大概90名具有领导才能、各方面综合素质较好,同时成绩也很优秀的学生。这些保送生被称为“干训保送生”。他们进入清华后会直接担任各班的班长或团支书,并参与组织学生活动。当时,清华每年大概招收90个班,每个班30人。)保送通知里明确指出,这两名学生会直接进入化学系化学专业。(按道理说,“干训保送生”并没有明确的专业限制。但是,到贵州招生的老师是化学系的,他大概非常想为化学系招到优秀的学生,所以限制了专业。)关于保送名额的分配,由于贵阳一中是贵州省最好的高中,每年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最多,因此,一个保送名额分给贵阳一中,另一个保送名额则留给贵阳市以外的学校竞争。 接到这个通知后,我第二天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一方面,我对于专业还没有什么特定的偏好。分文理科的时候,父母曾建议我读文科,但我一心想着要参加省里的数理化奥赛,所以执意要上理科。临近高考,我还一直怀着要当科学家的梦想,对于身边正在兴起的“经济浪潮”毫无知觉,也还没有考虑今后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另一方面,我的成绩在全校排在第一阵营靠后、第二阵营靠前的位置,这样的成绩发挥得好能考上清华北大,发挥不好就考不上清华北大。 与此同时,出乎我意料的是,学校里那些处在第一阵营的“学霸们”都没有报名,大概是由于专业的限制,这些好学生都情愿凭自己的努力考热门专业。另一方面,有传闻说学校里准备要推荐某位王姓大官的儿子参加竞争,但这位王姓大官的儿子与我正好是初中同学,他的成绩当时在班里处在中间位置,而我在初中一直是全校第一第二的成绩。后来,不知怎么他就自动放弃了。最后,学校推荐了七八个成绩在全年级前20名左右的同学参加面试。我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名。 面试那天,我穿着妈妈自己设计的红色灯芯绒蝙蝠衫,梳着短短的头发,拎着一大袋子证书就去了。这些证书里有“会考9A”证书、数理化省级获奖证书、手风琴全国比赛获奖证书、篮球比赛获奖证书等等。面试老师细致地询问了学习、课外活动以及做班级干部(我当时是班里的学习委员)的各种情况,最后还进行了英语口试。 我自己感觉面试效果很好,给老师留下了不错的印象。面试过程还被录制下来,在第二个周一的校园新闻里播放,让我一下子成了学校里的名人。面试之后,清华大学的招生老师选取了两个候选人进行笔试,而我又一次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 笔试是在学校的一个会议室里进行的,屋里就我们两个竞争者和招生老师。考题包括数理化和英语,考试时间两小时。题量不大,但非常难。现在回想起来,这应该是我考过的最难的一次考试,再没有经历过比它更难的。考完之后,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沮丧到了极点,好几个星期都打不起精神来。我觉得我一定上不了清华了;而保送不成,我也不敢报考了,清华梦碎。我似乎在真正的战斗之前就被打倒了。 招生老师临走前给我们两个竞争者留下了一些表格,让我们在一个月之内填好寄到清华大学招生办。我当时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根本没有心思去填这些表格,只是每天机械地去上学,尽量不让自己再受到“保送清华”这件事的影响。父母也尽量不和我讨论这个事,怕影响我复习的心情。 很快,一个月的期限就要到了,就在最后一天,父亲突然问我填表的事。我嘟囔着说,没填,没希望了。父亲并没理我,只是把表格都翻出来,开始帮我填。填着填着他突然发现,有些地方还要去学校和教委盖章,又急忙跑出去到各处盖章。傍晚时父亲才回来,脸上挂着欣慰的笑容,对我说,表格终于全都盖好章寄出去了。我当时并没有特别高兴,也没有觉得这件事意义有多么重大,只是机械地点点头。 父亲平时从不过问我的学习,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也从来没有去开过家长会,甚至有时候还会记错我在上几年级。他平时总是晚出晚归,我去上学的时候,他还在睡觉;我都上床睡觉了,他还没回家。所以,我们虽然住在同一个家里,有时候却会好几天见不着面。然而,这样一个让我有一些“生疏”的父亲,却在我人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助了我关键的“一臂之力”。 两个月之后,我作为“干训保送生”,提前一个月去清华大学报道了。来到北京,来到梦想中的清华园,我兴奋无比,就像挣脱了牢笼的小鸟,尽情地飞翔。我把家乡、父母、高中同学……都抛在脑后了,居然一个月都没想起来给家里打电话,急得我妈都快到北京来找我了。 后来,我在化学系见到那位到贵阳招生的老师,他笑着跟我说:“我们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招生办都快停止收材料了,你的材料才寄到。”我不好意思地回答:“我笔试感觉太差了,还以为自己考不上了呢,所以……”老师接着说:“是啊,你很幸运,你的笔试成绩只比另一个同学高一分。”一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似乎突然感受到了父亲对我的爱和给我的力量。那个很少关心我的父亲,那个很少夸奖我、甚至时不时地嘲笑和讥讽我的父亲,那个爱和妈妈吵架的父亲,那个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的父亲……曾在我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扭转了我的命运。 选摘二 问渠那得清如许 记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系的第一天 清晨,我的影子和树木们的站在一起 太阳暖暖的,慢慢升高 我穿行在枝干笔直的树木中间 阳光漫过来,将我们轻轻浮起 空中似乎有鸟在叫,一只绿色的鸟 我的影子和树木们的站在一起 太阳暖暖的,慢慢升高 这首诗写于2001年9月15日,是我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系的第一天。 那天,我起得特别早,在食堂吃过饭后,就顺着南北主干道朝着当时哲学系所在的文北楼走。清晨,主干道上没什么人,但阳光已经漫过来,像潮水一样,浸润着主干道两旁笔直高耸的白杨。树叶在微风中哗哗作响,和着布谷鸟的叫声,亲切而空灵。 晨光之中,我看见自己的影子穿行在白杨树高大的影子之间,恍惚中,我似乎看见了清华历史上人文大家们的身影:王国维、金岳霖、冯友兰、陈寅恪、赵元任、潘光旦、梁思成、林徽因……他们就像高大的白杨树一样守卫在主干道两边,用期盼的眼光注视着我。而我的影子穿行在树木的影子之间,正与大师们比肩同行。 想到这里,我心里不由得激动起来。我突然意识到:对于我的人生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从这一天开始,我终于可以在哲学人文的道路上,以清华的先辈们为榜样,去走我自己选择的路,去追寻我的梦想。 我也记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人文学科所吸引,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明确标志的话,大概是从上马哲公选课开始的。这门课的任课老师是哲学系的田薇教授。因为是必选课,选课的学生很多,但时常有人翘课,所以每次课堂上并没有多少学生。田老师的情绪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还是很用心地讲课。为了引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田老师先给大家讲德国哲学,讲康德和黑格尔。我现在已经记不起田老师都说过什么具体内容,只记得当时我好像被闪电击中了一般,突然觉得这门学问极有意思,有许多让人激动的谜团和思想构建,总是从最深刻之处反观自身,这是任何其他学科都无法比拟的。 渐渐地,我开始盼望上马哲课,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很“奇葩”的现象。下课后,我还会追着田老师问个不停。田老师推荐了一些书让我去读。于是,我又开始泡图书馆。尼采、萨特、斯宾诺莎、帕斯卡尔,不管看得懂看不懂,都如饥似渴地读。似乎这些让人似懂非懂的文字能解决我人生的困惑,抚慰我内心的忧伤,让我明白生命的价值,坚定生活的方向。 就这样,到了大三下学期,大家开始打算本科毕业之后的前途。那时,我心中慢慢明确了自己的主张:我要从化学系转入哲学系!这个决定犹如晴空霹雳,不仅让我身边的人感到震惊,最开始,就连我自己也有点接受不了。但是,自从这个念头产生之后,它就在我心里不断地长大,而我对于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的兴趣也在与日俱增。 还好,我父母比较好说服。毕竟,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让他们有这样的“惊喜”。高中文理分科的时候,他们曾极力劝我学文,而那时我因为想参加省里的数理化竞赛,坚决不同意。所以,现在我想转文科,一方面暗合了他们的本意,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觉得孩子大了管不了。所以,也就没有太大的意见了。 对于转专业的事情,我也曾咨询过一些人文类选修课的老师。有老师认为,人文可以作为爱好,没必要兴师动众、前功尽弃;也有老师认为,我可以转入清华的科学史或者科学哲学专业,这样,可以衔接上我本科四年的学习,不会使得以前学的东西完全浪费掉。然而,这些建议我都听不进去,当时的想法是“非哲学不学”,一门心思要转入哲学系,学习我心目中真正的学问。 当时,我在化学系的三十名学生中排名第八,拥有推研资格,可以选择在化学系读硕士或者直博。有了推研资格,我就整理好自己的简历和作品集,准备到哲学系参加面试。在本科四年的学习当中,我虽然一直在化学系学习,却参加了不少人文类的活动和竞赛,写过诗歌、散文、小说等等,所以当时的作品集沉甸甸的,简历也有好几页长。拿着简历,我信心满满地去面试了。 面试程序是自我介绍加提问环节。我记得当时有老师问我看过什么哲学经典著作,我回答说看过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老师又问这本书中的“酒神”代表什么,我犹豫了一会儿,说“ 代表‘丰收’”,老师听后脸上露出了微笑,似乎是满意了。一周之后,面试结果出来了,我排名第二,当年清华哲学系有三个校内保送名额,就这样,我顺利地进入了清华大学哲学系。 回首当年,清华跨系推研的过程虽然简单,却是我转型成功的起点。而我似乎在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一事件在我生命之中的重大意义,知道那必将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多年之后,我已在人民大学教书,有一次回清华,偶遇清华主管学生人文活动的程钢老师。他听说我从清华哲学系毕业后,又出国读了政治哲学的博士,回国后在人民大学教书,感慨地说:“你终于修成正果了,可喜可贺!”那时,我突然意识到,当初我执意转专业时,程钢老师大概也为我的前途捏了一把汗。人文选修课的老师们见过太多热爱人文的理工科学生,但又有多少学生如此执着,能最终将爱好做成专业呢?像我这样毅然决然地与过去决断而重启新生,直至将哲学当作自己毕生追求的学生,估计实属罕见。 我转入清华哲学系时,哲学系刚复系不久,师资和办公条件都比较紧张,而我也是伦理学专业的第一届硕士生。由于条件有限,我们时常在哲学系的会议室上课。会议室里挂着清华四大国学导师的画像。这样,在上课的间隙,我们就时常仰望老先生们。我有时候会走神,想象着自己的画像有一天也有幸挂在某一辈学生的教室里,想到这里就忍不住偷偷地开心。 哲学系的大部分同学都非常用心。我的两位师兄几乎天天在系里的资料室看书,我在文北楼里上上下下、上课办事都能看见他们。有一天,突然只看见一位师兄,我心里颇为惆怅,当晚写了一首诗赠师兄。结果,第二天就又看见两位师兄整齐地坐在资料室里看书,才发觉是自己多虑了。 哲学系的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甚至觉得仅靠课堂学习不够,于是自己举办读书会。听说,这种学生自己办读书会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我曾参加了一个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读书会,读的是英文版。我现在已经完全记不住都读了什么内容,只记得一个师兄非常热心,热情地邀约我参加读书会,还耐心地给大家分析和讲解。读书会结束后,师兄还把我送回宿舍,我们又在宿舍楼下争论康德的“物自体”概念,直至熄灯。那些动人的场景似乎还在眼前。 哲学系的课程既丰富又难懂,古希腊哲学的课要参照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文献。中国哲学的课要学古文,康德哲学的课要参照德文,相对简单的还是伦理学的课程,只要英文比较好就够用了。当然,要学得精的话,必须有分析哲学的功底,那也是要磨破脑壳的。 倏忽之间,清华哲学系三年的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2004年7月,我申请到意大利LUISS大学(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赴罗马攻读政治哲学博士,继续我的哲学旅程。三年,时光虽短,却奠定了我学术生涯的基础和最初的风格。质朴、真诚、执着、钻研精神……这些清华哲学人最美好的品质都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成为我最真实的“内核”。而我,不论过多久也不会忘记,在进入清华哲学系的第一天,我心中洋溢的幸福和希望;不论走多远也不会忘记,在清华主干道上,伟大的先辈们对我的嘱托。 ※提起“清华”,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历史上的四大导师,还有明信片上的二校门风光……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作为全国顶尖学府,清华自是“大楼”与“大师”齐备,当然更少不了一批批敏而好学、活跃多才的学子…… ※《从清华走来》便是一部清华人讲述自己求学历程和成长经历的小传,记录了政治哲学教授李石从一名不起眼的、甚至在校园里遭受冷落的清华女生出落成一位成熟学者、走向世界的蜕变过程。 ※或许她和你一样,曾在大学繁忙的学业之余,热衷于办社团、编报纸、演话剧,还经历过一场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校园恋情……但她又有些“不一样”。——身为佼佼者的贵州高中毕业生李石以“干训保送生”的身份进入清华,却在校园生活中屡受挫折;身为化学系本科生的她,却因着某种机缘而与人文学科结缘,最终走上哲学之路;从清华园到罗马LUISS,她手握一张漂亮的学术履历书,却在归国求职时不被看好、屡遭拒绝…… ※但在自强不息的性格下,众多“逆向反转”非但不是绊脚石,而是成长旅途中的助力器,也决定了这部小传的“出圈”潜能——不仅只献给清华及校友。它足以走出圈子,献给更多年轻学子,以及追求进步、热爱生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