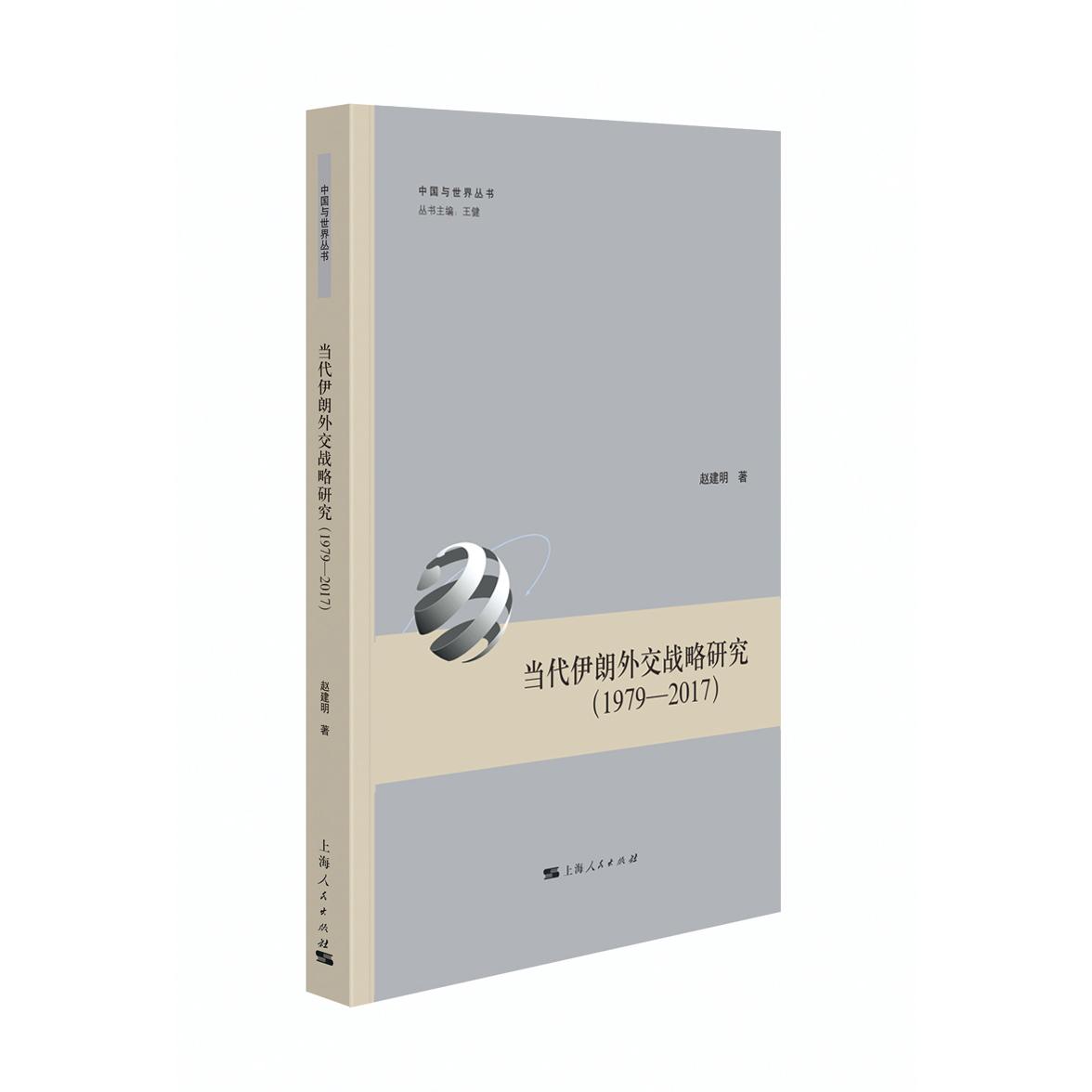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人民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67.70
折扣购买: 当代伊朗外交战略研究(1979—2017)
ISBN: 9787208185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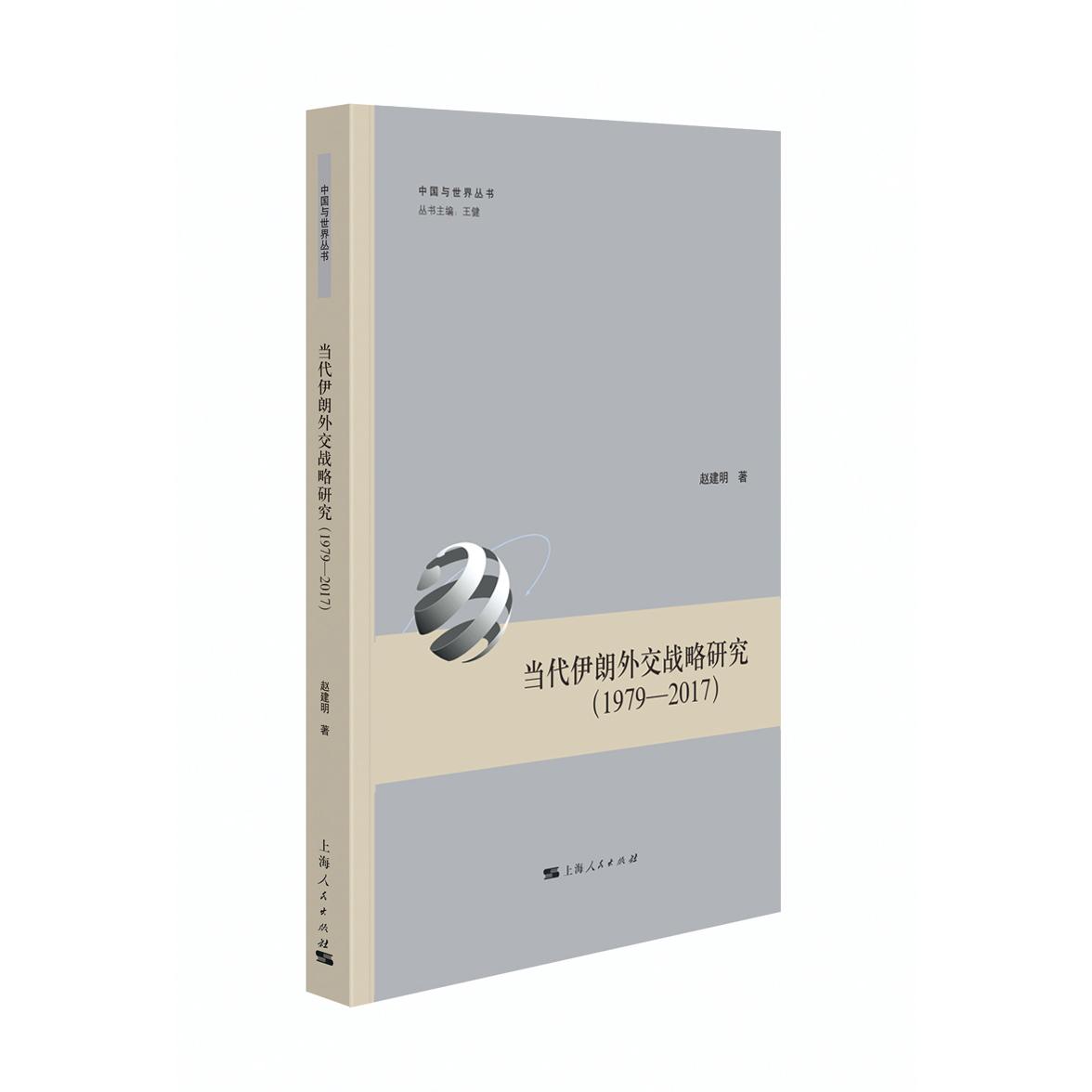
赵建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法学博士。长期从事伊朗问题研究、中东政治与宗教关系研究,入选上海浦江人才计划,在《美国研究》《外交评论》《现代国际关系》等刊物发表30余篇论文,获得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若干其他课题,出版专著《伊朗国家安全战略的动力分析》。曾在美国纽约大学、美国石汀生中心、伊朗国际关系学院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访学。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本书将革命后伊朗的外交战略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构想:第一,伊朗是中东地缘政治大国。从疆域面积、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宗教教派等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上看,伊朗的实力不可小觑。从地缘上看,伊朗的地理枢纽地位突出。伊朗东西连接阿拉伯半岛和印度次大陆,南北连接海湾和外高加索—中亚—里海。在资源上,伊朗横跨海湾和里海两大能源富集区,伊朗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产资源,是世界上重要的能源生产国和出口国。 第二,伊朗是理解中东教缘政治的“抓手”。伊斯兰世界的主流教派是逊尼派。沙特因为拥有圣城麦加和麦地那而成为逊尼派和伊斯兰世界的领袖。伊朗对中东教缘政治的意义在于,革命后,伊朗从世俗国家变为宗教国家,但伊朗的革命是什叶派的革命,伊朗由此成为什叶派的中心国家,并改变着什叶派同逊尼派两大教派之间的力量对比。革命后伊朗建立的是自认为唯一合法的由法基赫(Velayate Faqih, Governance of the Jurist,意为伊斯兰教法学的专家)主宰下的伊斯兰民主制度(本书以下简称为法基赫制度),否认沙特等逊尼派君主国家的政权合法性。伊朗还主张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城实行国际共管,否认沙特拥有对圣城的护持资格。这也让伊朗和沙特乃至中东的政治斗争具有强烈的教缘政治色彩。 第三,伊朗是热点国家,其内政外交的变化牵动着中东地区和国际政治的神经。从政治上看,革命后的伊朗不是西方所谓“正常国家”(Normal State)。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世俗君主政权,伊朗建立起法基赫制度,最高宗教领袖成为伊朗的最高统治者。制度转变让伊朗在内政外交上具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形态色彩。从外交上看,伊朗的外交牵动着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抛开巴列维的亲美亲以政策和霍梅尼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不谈,最近发生的伊朗核问题、苏莱曼尼遇袭等事件就足以触目惊心,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革命后的伊朗在内政外交上的变化。 第四,伊朗是中国大周边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沿线国家。中伊两国跨越了意识形态、政权更替等障碍并保持良好的关系。近些年随着中国外交外向型特性的凸显,伊朗已经成为中国大周边外交的重要国家。伊朗和沙特、土耳其、以色列等国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合作的重要国家。经贸投资、能源联系成为中伊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纽带。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伊朗实行“极限施压”政策,给中伊正常的经贸关系带来巨大的阻力,这考验着中伊关系的韧性和牢靠程度。 本书主要论述了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外交战略演变,以及由此映射出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外交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特性,这给伊朗外交设定了一个困局。但是两伊战争开启了伊朗外交的“破局”之路。从拉夫桑贾尼的务实外交,到哈塔米的“文明间对话”,再到鲁哈尼的建设性战略互动,伊朗开启了崭新的外交探索和转型的历程。作者将“设局”与“破局”作为探讨伊朗外交战略的主线,重点关注伊朗的意识形态在不同阶段发生的变化,并以伊朗核问题为抓手,探讨伊朗核外交及其对伊朗内政外交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