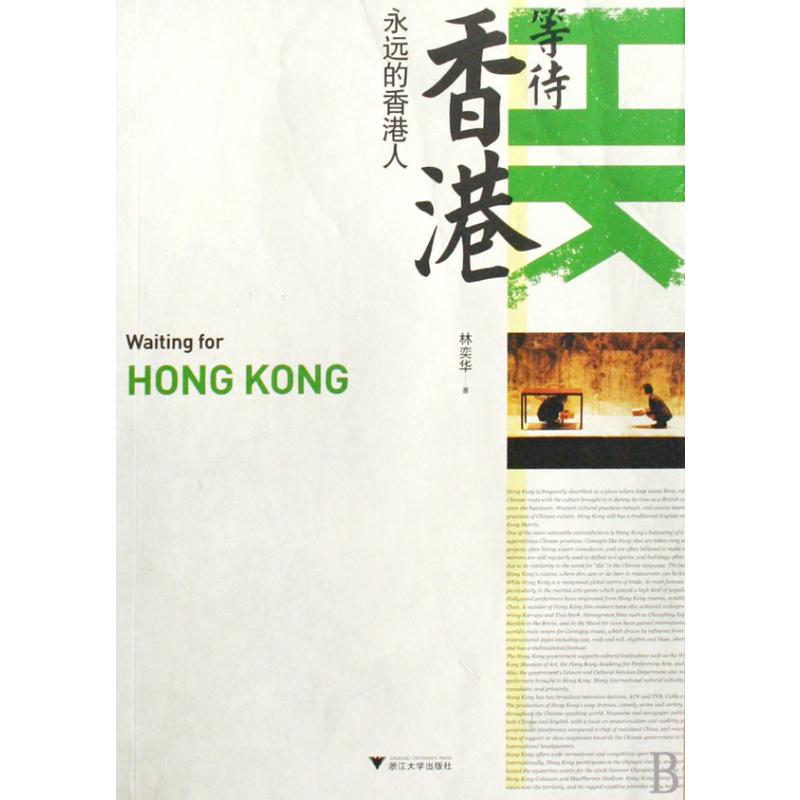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原售价: 26.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等待香港(永远的香港人)
ISBN: 9787308067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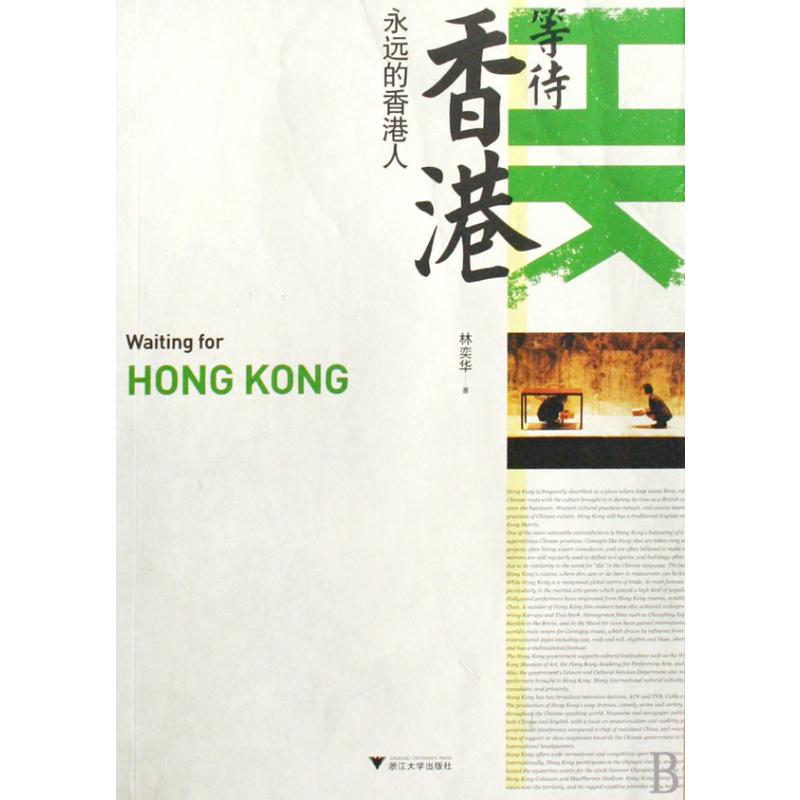
林奕华,香港文化界著名人物,横跨剧场、舞蹈、电影、教育等多个领域的香港多栖创作人、批评家。 中学时在香港丽的电视与无线电视任编剧。 毕业后与友人组成前卫剧团“进念·二十面体”。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五年旅居伦敦期间,自组“非常林奕华”舞蹈剧场,先后在伦敦、布鲁塞尔、巴黎、香港进行舞台创作。 一九九四年凭《红玫瑰白玫瑰》(关锦鹏导演)获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一九九五年回港后致力推动舞台创作,编导了四十多部作品,并与不同媒体、不同城市的艺术家及团体合作。 一九九五年获香港艺术家年奖,二○○五年获颁授“民政事务局局长嘉许奖”。 近期舞台代表作有《包法利夫人们——名媛的美丽与哀愁》、《水浒传》、《西游记》、《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男人与女人之战争与和平》、《红娘的异想世界之在西厢》、《贾宝玉》等。 其表演足迹踏遍伦敦、布鲁塞尔、巴黎、新加坡、澳门、台北、北京、上海、南京、杭州、西安、重庆等各大城市。 林奕华对文字情有独钟,在文化界颇有建树,自一九九七年至今担任香港大学通识教育、香港浸会大学人文素质教育、香港演艺学院人文学科讲师。亦经常替香港、北京、广州的报章杂志撰写文章,曾出版《等待香港》系列著作。其批评文章散见《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上海壹周》、《明日风尚》、《号外》等各地报刊杂志。
为什么我不是周星驰的fan? 因为我不是灰姑娘,我不需要玻璃鞋。因为我不指望被神仙打救,所 以我不迷信童话。因为我已看得太多太多的荷里活电影,我对公式化的梦 想成真已非常厌倦。因为如果我不想做这些幻想的奴隶,我便必须从童话 世界走出来,鼓起勇气面对被童话说书人形容为十分可怖、丑陋的现实世 界。因为现实世界纵然千疮百孔,但不见得会比那刻意被愈描愈虚幻的童 话世界更恐怖。因为童话其实不仅用来哄孩子入睡,它还可以把成年人如 你和我催眠。作为一个中国(香港)人,我已经够自卑和没有自信了,我最 需要的是学习脚踏实地和进步,而不是再多看几部周星驰的电影来麻醉或 暂时忘记我对自己的不满,甚至是自我憎恨。我如果不想做一个后现代阿Q ,我首先要停止幻想自己也有“特异功能”。 由《赌圣》到《少林足球》,大部分周星驰所扮演的角色看上去都是 平平无奇,其实是真人不露相——若不是天生神拳,就是拥有神腿。而这 些角色的际遇又总是万变不离其宗:先是怀才不遇,饱受欺压,继而忍无 可忍,最后天赋的神力会助他反败为胜,从此平步青云。这条方程式和《 仙履香缘》(Cinderella)如出一辙,所以我一直都说周星驰就是灰姑娘的 男装版。而当男性观众在看《赌圣》、《新精武门》和《少林足球》时所 产生的情绪反应和投射,其实与女性观众在看《仙履奇缘》时是一样的— —周星驰情意结之于男性,就是灰姑娘情意结之于女性。 灰姑娘和周星驰电影中的人物最为相似的一点,便是她和他(们)都要 “忍辱负重”。但周星驰所谓的“屈辱”,往往只是跟钱有关。没有钱, 一个人便没有力量,连站都站不起来。《少林足球》的那群落难少林子弟 ,虽然口口声声“理想破灭”,电影却从头到尾没有交代他们心目中的理 想究竟为何物,更不知道如何破灭。是发扬少林精神失败吗?但在世界各 地不是一直有人在推广少林?还是要把少林精神推向更高层次?如果后者 是他们的“理想”,我便无法理解打赢片中的球赛对于达致这个抽象的目 标有何作用。但我完全明白球赛的结果将是他们能否脱贫的关键,所以观 众才会紧张比赛的输赢——谁不关心一百万奖金花落谁家? 有钱才能“兑现”别人的尊重,没有钱便不是“人”,因而不论受过 多少挫折和自我否定,只要赚到钱,自我感觉随之亦会变得良好——是实 际利益让这一群少林子弟重拾信心,而这也正是《少林足球》派给观众的 定心丸。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幻想”的价值明显比“理想”更高——当现实 不过是由各式各样我们不想承受的暴力所堆砌而成。而偏偏这些“残酷的 现实”又是周氏电影中让人看得最“过瘾”处之一,当中除了包含虐人的 刺激,也有自虐的快感:“一个追求理想的人合该受到变态式的身心折磨 。”可以的话,我们当然会想尽法子少吃这些“因为追求理想”而得到的 苦头,多尝甜头。因为这样,“理想”在周星驰的电影中,往往不是被扭 曲,就是空口讲白话居多,实际有所作为却少之又少。最佳例子是《喜剧 之王》的男主角,他的所谓“坚持理想”,更接近是对客观世界失去观照 能力的喃喃自语,痴人说梦。假若像他般似是精神有问题多于理性地处理 自己的梦想也算是“坚持理想”,我认为周星驰对理想若不是有所误解, 便是明褒暗贬,拐个弯把它揶揄羞辱。 但是你别说,我怀疑“丑化理想”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庞大的市场 ,可是由于中国人对理性——不论是在文化方面,还是对自己的要求,仍 然有着太多莫名恐惧和抗拒?除了是对外在环境的期望,“理想”同时也 是“自我”的一幅自画像,所以热衷于“丑化理想”的人,有可能也是在 宣泄对丑陋的自己的怨恨。如果这个说法成立,我们不免要问:为什么中 国人会认为自己“丑陋”?是潜意识在作祟?还是有意识地自我轻视?其 中一个“自丑”的原因,会不会是我们一方面太过依赖外国人的价值标准 ,但又坚持不肯承认自己老是追求外国人的认同? 《少林足球》最后的一场戏,是“把少林武术发扬光大”的周星驰和 赵薇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大块周刊封面的广告板底下,是一大群中 国人分别用“少林功夫”来剪草、泊车、追巴士——看着用高科技拍成的 这个“生活化”得带点愚蠢的场面,我不禁发出以下的感慨:(一)“少林 功夫”并不是什么精神、哲学或艺术的领域,而是一种换取方便的手段。 说到底,实用才是中国人恒久追求的最高价值标准。(二)尖端科技早已帮 助人类实现许多不可能的梦,而在上述片段中,少林功夫却被用来反科技 。这叫我想到中国人既要与文明世界接轨同步,却又必须靠夸大自己的“ 特异功能”来突显民族的优越性和迎合国际市场。像这般自相矛盾和兜兜 转转的路,我们面前到底还有多少条,还要走多久? 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