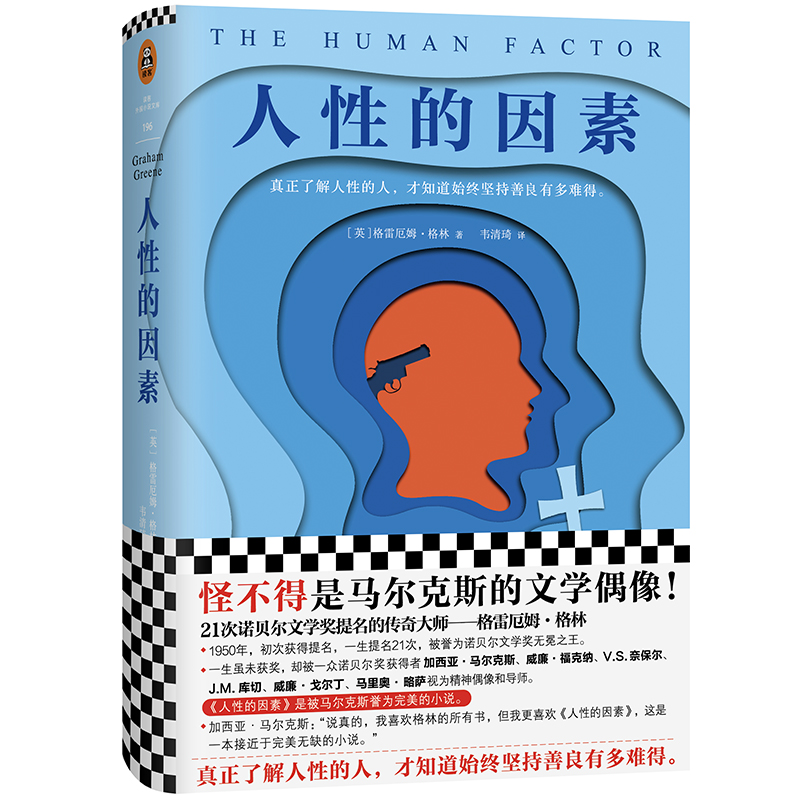
出版社: 江苏文艺
原售价: 65.00
折扣价: 37.70
折扣购买: 人性的因素(精)
ISBN: 97875399797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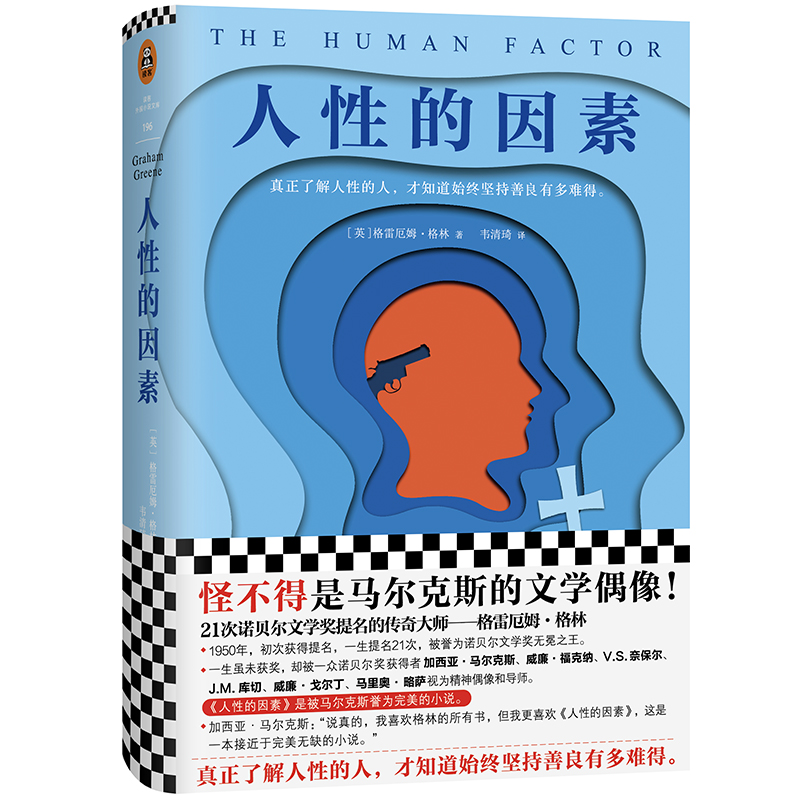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 21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传奇大师。67年写作生涯,创作25部小说以上,被评为20世纪大师级作家。1950年,初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1976年,获美国推理作家协会大师奖。1981年,获耶路撒冷文学奖。1986年,由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功绩勋章。 格林一生游历于墨西哥、西非、南非、越南、古巴、中东等战乱之地,甚至任职于英国军情六处,从事间谍工作,并以此为背景创作小说,关注人灵魂深处的挣扎与救赎、内心的道德和精神斗争,被誉为20世纪人类意识和焦虑的卓越记录者。 至今,每年格林生日期间,在格林出生地——英国赫特福德郡,都会举办为期四天的格雷厄姆·格林国际艺术节,全球的格林粉丝齐聚这里参加纪念格林的活动。
第一章 自从三十多年前,年轻的卡瑟尔到这里工作后,便一直在圣詹姆斯街后面的一家酒吧用午餐,那地方离办公室不算远。若问起缘由,他会归结为那里高品质的香肠。或许他也青睐那里的一种别有苦味的沃特尼啤酒,不过更要紧的是香肠的质量。他时时准备着解释自己的行为,哪怕是最没有疑问的,另外,他还总是很守时。 所以当钟报响一点时,他就准备出门了。与他合用一间办公室的助手阿瑟·戴维斯十二点准时去吃午饭,一小时后返回,但这经常只是理论上如此。戴维斯和他自己随时得有一人留着,以应对紧急电报的解码工作,这是很明确的,可他们也很清楚,在他们所属部门的这个分部里,从不会有什么真正紧急的情报。英国与由他俩负责的东非和南非各地的时差应对起来通常都绰绰有余——即便是在约翰内斯堡也只相差了一小时多一点——没有人会操心消息的迟滞。戴维斯常说,世界的命运永远不会由他们这块大陆来决定,无论中国或俄国在亚的斯亚贝巴和科纳克里之间开设了多少大使馆,也无论有多少古巴人登陆非洲。卡瑟尔给戴维斯写了张便笺:“如扎伊尔回复172号,送副本至财政部和外交部。”他看了看表。戴维斯迟了十分钟。 卡瑟尔开始整理公文包——他放了张字条,记的是要在杰敏街乳酪店为妻子买的东西,以及为早上和他闹了些不愉快的儿子准备的礼物(两包“麦提莎”巧克力);还放了一本书,《克拉丽莎》,他每次到第一卷的第七十九章就再也读不下去。他听见电梯关门及戴维斯在走廊里的脚步声,随即便离开了屋子。他的香肠午餐少了十一分钟。和戴维斯不同,他总是准点返回。这是上了年纪后具有的一种美德。 阿瑟·戴维斯的怪异行为在这间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十分惹眼。他正从白色长廊的另一端走过来,穿着如同刚在乡村的马背上度了周末,抑或刚从公共赛马场回来。他套一件单绿色斜纹软呢运动夹克,胸口衣袋里还露着一条带斑点的红手帕,颇似一位宾馆行李员的行头。不过他还是像一位被分错了角色的演员:当他尽力想和这套行头般配时,却常常笨拙地找不到戏路。如果说他打量伦敦的样子就仿佛他是从乡下来的,那么他到乡间造访卡瑟尔时又明白无误地是一副城里游客的模样。 “一如既往地准点。”戴维斯挂着惯有的讪笑说。 “我的表总走得稍快了些,”卡瑟尔像是在为并未说出口的微词致歉,“一种焦虑综合征吧,我想。” “又往外偷运绝密情报?”戴维斯问道,同时开玩笑地摆了个架势,要抢卡瑟尔的公文包。他的呼吸夹杂了甜腻的气味:他对波尔图葡萄酒很是贪恋。 “哦,我都留给你去兜售了。你那些见不得阳光的联系人会给你个更好的价钱。” “你真好心,我敢肯定。” “而且你单身,比已婚男士更需要钱。我的生活开支已减半了。” “啊,可那是些倒胃口的剩菜,”戴维斯说,“吃剩的牛腿肉重做成土豆泥肉饼,还有串了味儿的肉丸子。值吗?结了婚的男人连一杯上好的波尔图都喝不起。”他进了他们合用的办公室给辛西娅打电话。两年来戴维斯一直在追求辛西娅,可是这位少将的女儿却想攀上更高的枝头。尽管如此,戴维斯仍抱着希望;他解释说在部门内部谈恋爱风险总要小些——不会被视为有安全隐患,但卡瑟尔明白戴维斯实际上有多眷恋辛西娅。他既强烈渴望出双入对的夫妻生活,又不想失去单身男子有的那种防范性的幽默感。卡瑟尔到他的公寓去过一次,那是他和环境部的两个人合住的套房,在一家古玩店楼上,离克拉里奇酒店不远——地处中心,气派非常。 “你应该多来走动走动。”戴维斯当时坐在客厅里劝着卡瑟尔。房间拥挤不堪,沙发上摊满了各色杂志——《新政治家》《阁楼》,还有《自然》,其他房客开过晚会后留下的狼藉杯盘堆在角落里,等着日杂女工来收拾。 “你很清楚他们给我们的工资,”卡瑟尔说,“而且我有家室。” “严重的决策错误。” “可我不是,”卡瑟尔说,“我喜欢我妻子。” “当然还有那小杂种,”戴维斯继续道,“既养孩子又喝波尔图,我可掏不起这个钱。” “可巧我也很喜欢这小杂种。” 卡瑟尔正准备走下四级石阶到皮卡迪利大街时被门房叫住了。“汤姆林森准将想见您,先生。” “汤姆林森准将?” “是的。在A.3号房间。” 卡瑟尔只见过汤姆林森准将一回,很多年前了,久远得他都懒得去计算,也就是他得到任命的日子——他在《公务机密法约》上签字的那天,那时这位准将还是个很小的下级军官,如果还算军官的话。所有他能记得的就是那撇黑黑的小胡子,如同不明飞行物似的盘旋在一张吸墨水纸上,吸水纸完全空白,也许是出于安全的因素。唯一的瑕疵是他签过《法约》后留下的钢笔印迹,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张吸水纸随即就被粉碎并焚烧。近百年前的“德雷福斯事件”暴露出了废纸篓的危险。 “沿走廊左边走,先生。”门房在他就要走错方向时提醒他。 “进来,进来,卡瑟尔。”汤姆林森准将叫道。他的胡子现在跟吸水纸一样白了,而岁月还在他双排纽扣马甲下堆起了小小的将军肚——只有他的军衔仍像过去那样说不清道不明。无人知晓他以前归属哪个军团,如果确有此军团的话,因为在这幢楼里,所有的军队头衔都有些可疑。官阶可能也只是全副伪装的一部分。他说:“我想你不认识丹特里上校。” “不,我不认识……你好。” 尽管丹特里穿着整洁的深色西装,有着棱角分明的瘦削脸庞,但比起戴维斯他更加真实地具有一种户外活动的气质。若是说戴维斯第一眼看上去似乎可以在跑马场如鱼得水,那么丹特里则显然能在昂贵的狩猎围场或打松鸡的林沼间游刃有余。卡瑟尔喜欢给同事勾勒速画像:有时甚至真的画在纸上。 “我想我在科珀斯结识过你的表兄。”丹特里说。他的语气愉快,但显得有些烦躁,也许他还得到国王十字车站赶发往北部的火车。 汤姆林森准将解释道:“丹特里上校是我们的新长官。”卡瑟尔注意到丹特里随之皱了皱眉,“他从梅瑞狄斯那儿接管了安全工作。不过我想你可能从没见过梅瑞狄斯。” “我估计你说的是我的表兄罗杰,”卡瑟尔对丹特里说,“有不少年没见了。他在‘人文学科’中得过一等。我想他现在在财政部。” “刚才我在向丹特里上校介绍这儿的建制。”汤姆林森准将还在絮叨,紧扣自己的话题不放。 “我学的是法律。得了个差劲的二等,”丹特里说,“我想你读的是历史?” “是的。得了个非常差劲的三等。” “在牛津基督教堂学院?” “是的。” “我已经跟丹特里上校解释了,”汤姆林森说,“就6A部而言,只有你和戴维斯负责处理机密电报。” “如果那算是我们这个部的‘机密’的话。当然,沃森也要过问的。” “戴维斯——雷丁大学的,没错吧?”丹特里的问话里好像有一丝轻蔑的意味。 “看得出你做了不少功课。” “实际上我刚和戴维斯本人聊过。” “所以他的午饭多花了十分钟。” 丹特里笑起来如同伤口重又痛苦地绽裂开,那两片鲜红的嘴唇在嘴角张开时显得挺费劲。他说:“我和戴维斯谈到了你,所以现在我要和你谈谈戴维斯。公开核查。你得原谅我这把新扫帚。我得学着摸索这条绳子,”他补充的这些比方并没有把事情说清楚,“得例行公事——尽管我们对你俩肯定是信任的。顺便问一句,他有没有警示过你?” “没有。可是你为什么要相信我?我们也许串通好的。” 那伤口又豁裂开少许,接着又紧紧闭上。“我推想他在政治上略微偏左。是这样吗?” ◆怪不得是马尔克斯的文学偶像! ◆格雷厄姆·格林是21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传奇大师。 ◆1950年,初次获得提名,一生提名多达21次,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无冕之王。 ◆一生虽未获奖,却被一众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尔克斯、福克纳、V.S.奈保尔、J.M.库切、威廉·戈尔丁、马里奥·略萨视为精神偶像和导师。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虽然把诺贝尔奖授给了我,但也是间接授给了格林,倘若我不曾读过格林,我不可能写出任何东西。”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拉斯·福塞尔说:“未授予格林文学奖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人性的因素》是被马尔克斯誉为完美的杰作。 ◆马尔克斯:说真的,我喜欢格林的所有书,但我更喜欢《人性的因素》,这是一本接近于完美无缺的小说。 ◆《人性的因素》格林探讨人性的经典之作,写尽了人性的所有可能:残忍的、恐怖的、冷漠的、无力的、天真的、自由的、善良的、悲悯的、充满爱的……而影响我们人性作出选择的因素又是什么?是爱情、友情、亲情,还是工作、家庭、国家? ◆真正了解人性的人,才知道始终坚持善良有多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