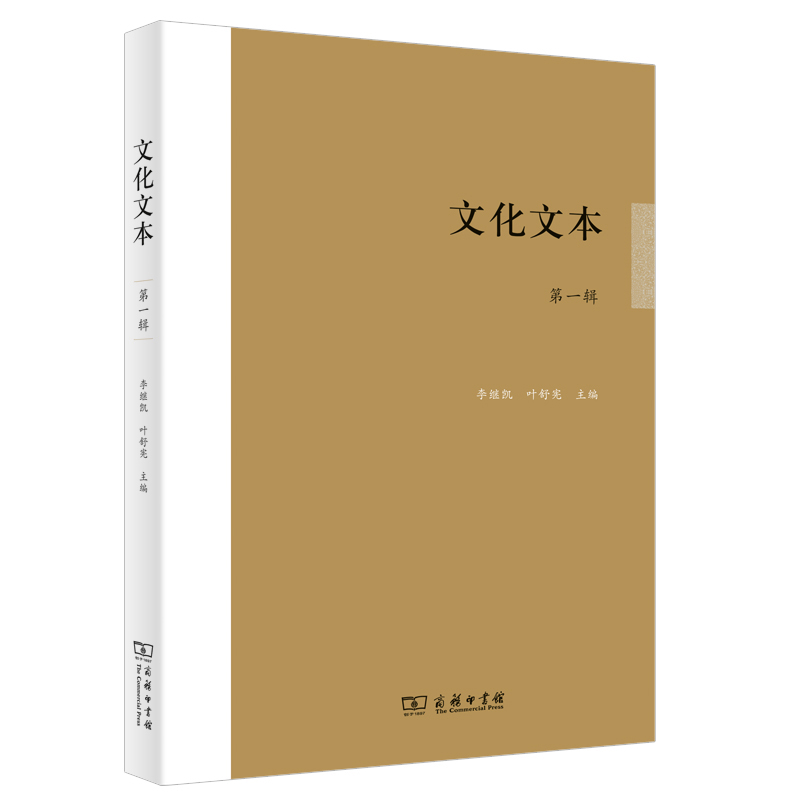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99.00
折扣价: 69.30
折扣购买: 文化文本(第1辑)
ISBN: 97871001982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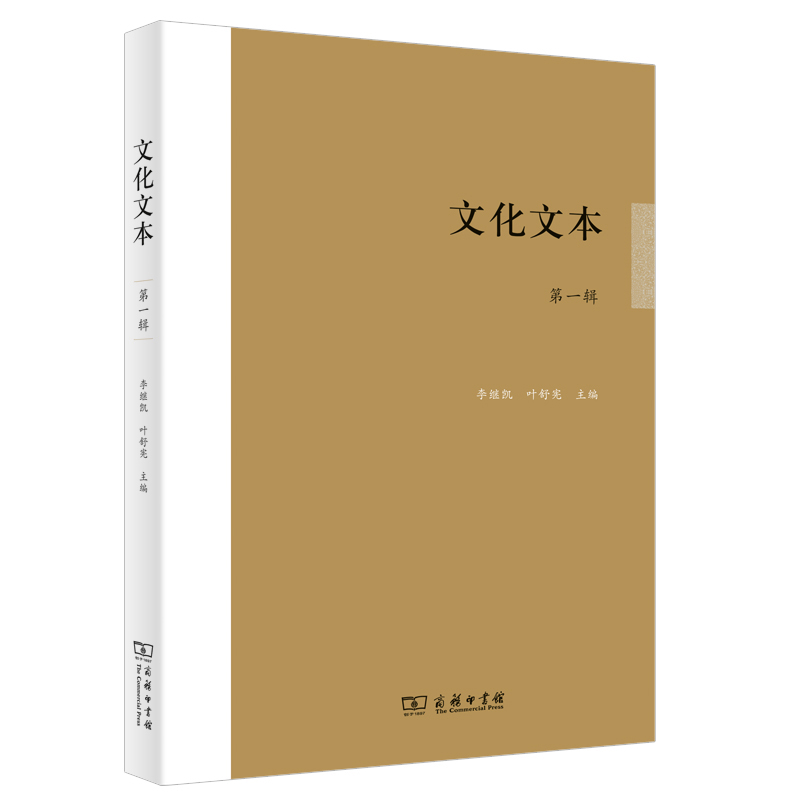
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学文化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规划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及参与主持、撰稿多项工作。主要著作有《新文学的心理分析》、《中国近代诗歌史论》(与史志谨合著)、《民族魂与中国人》、《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全人视境中的观照——鲁迅与茅盾比较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 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首批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青年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任《20世纪国外文艺学丛书》等多种丛书主编。在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研究等方面的研究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曾在《中国比较文学》、《文艺争鸣》、《上海文论》等刊物开辟个人专栏,已出版《文学与人类学》、《中国神话哲学》等专著、译著24部,在《北京大学学报》《中国文化》《哲学研究》《文艺研究》等发表论文300余篇。
从历史看,一个鼓励全民创新的时代是十分罕见的。可是,在我们从业的这个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领域,陈陈相因早已经成为常态,根本原因是旧的范式本身具有强大的束缚力。翻翻发行量较大的教科书的内容,你 就会明白:根本不能指望在常规教育中学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的一点点秘诀;只有强调学生去自学新知识,才有望达到“预流”的前沿性。 《文化文本》创刊伊始,就要鲜明地亮出理论创新和范式革命的旗帜,寄希望它能够成为这样一面旗帜。如今市面上各种学术出版物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几乎成泛滥之势,这会给后学的选择带来极大困惑。在学术追求方面,宁为鸡口,毋为牛后,权且作为办刊第一宗旨。文化文本,这个术语听起来好像既熟悉又陌生。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大潮到来之前,这是个完全陌生的概念。人文学界经历过结构主义思想的半个世纪的洗礼,大家对这个概念已经耳熟能详了。可是我们必须首先声明,本刊以“文化文本”为名,绝不是因袭和照搬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概念。这种情况和八年前我们采用“大传统”和“小传统”这一对现成术语的情况一样,颠覆性地再造、灌注新的内涵,以求引领学术变革,才是本刊采纳这个术语的初衷。 文学人类学派所强调的文化文本,除了名称上和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思路一致外,其所秉承的学术传统更多地侧重在文化人类学方面,而其研究旨趣则更接近符号人类学(亦称“象征人类学”)、历史人类学、认知考古学。在此,文化文本,若要发挥理论统领性的作用,需要让它和一切结构主义的文本概念划清界限。从文学人类学视角看,文化文本,不是指客体存在的、静止不动的文本,而是带有历史深度认知效应的一种生成性概念, 而是指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下不断生成和演变的文化符码系统本身。相对于后代的一切文本(不论是语言文字的,还是非语言非文字的),文化文本的源头期最为重要。没有源头的,即没有找到其原编码的文本,是没有理论解释力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共时性研究思路,被视为人文学科在20世纪发生的最重要的学术转向—语言学转向,并且和19 世纪的历史语言学思路相区别。但正是结构主义的共时性研究范式,阉割了文化文本生成脉络认识的可能性,所以必须有一个学术再转向,从关注共时性视角,到兼顾共时性与历时性,恢复发生学的视角。文化文本的生成方式是原编码,其演变的方式则是再编码,即在原编码基础上的某种置换变形或再创造。对原编码的追溯,在理论上几乎没有止境的。 我们在此暂界定在先于文字符号产生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和整个新石器时代,以免使研究领域漫无边际。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旧石器时代的符号材料十分稀少,因而可以暂且侧重研究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时段。对于有文字的社会传统而言,原编码是先于文字而存在的。文字的出现,就已经是再编码。在N级编码论中,甲骨文只能算二级编码。就华夏文明而言,探寻文化文本的原编码工作,不能在甲骨文字产生以后的年代里进行。因为我们经过四十年的探索,直到最近才终于觉悟到:一个古老文明的所有重要的文化原型,一定是在先于文字符号的更早年代里出现的,这就必然要诉诸考古学和史前史的全新知识领域,要相对地弄清楚:文字符号出现以前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没有这个补课的功夫,就永远无法知道文字世界是如何取代无文字世界的。试问,哪一种结构主义的或符号学的教科书是这样教给你谈起“文化文本”的概念呢?如果你发现以前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一派的学者并没有这样做,那么文学人类学派所标榜的“文化文本”的范式革新意义,就会逐渐不言自明了。为了更好地说明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当下理论建构意向,有必要回溯先于文学人类学的交叉学科思路而存在的文化人类学的范式转型。 一面理论创新和范式革命的旗帜 主题较为新颖,文学人类学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新的研究流派,是跨学科研究中一个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