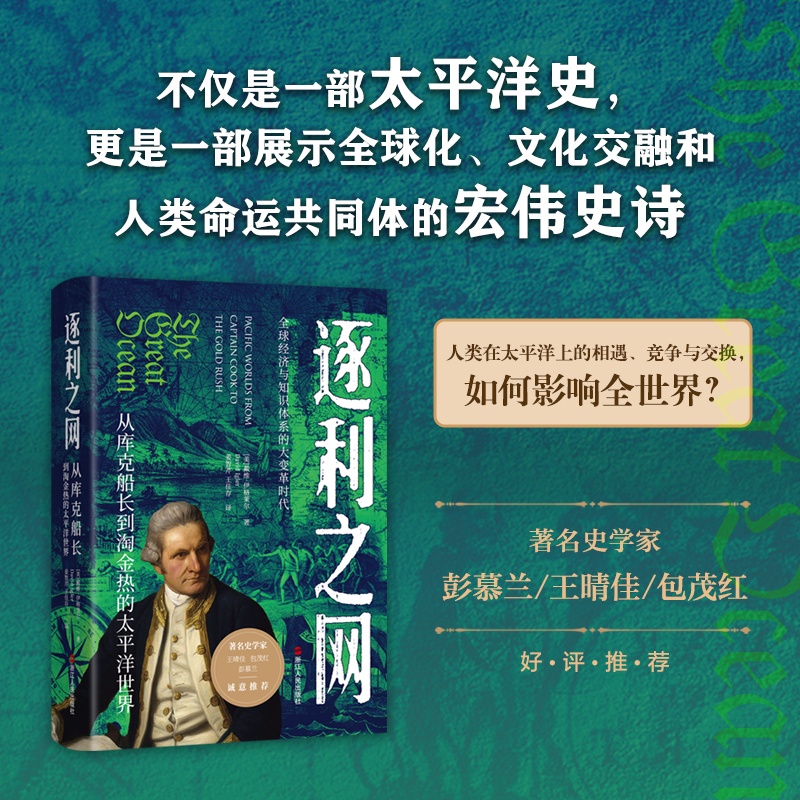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人民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2.80
折扣购买: 逐利之网(从库克船长到淘金热的太平洋世界)(精)
ISBN: 9787213112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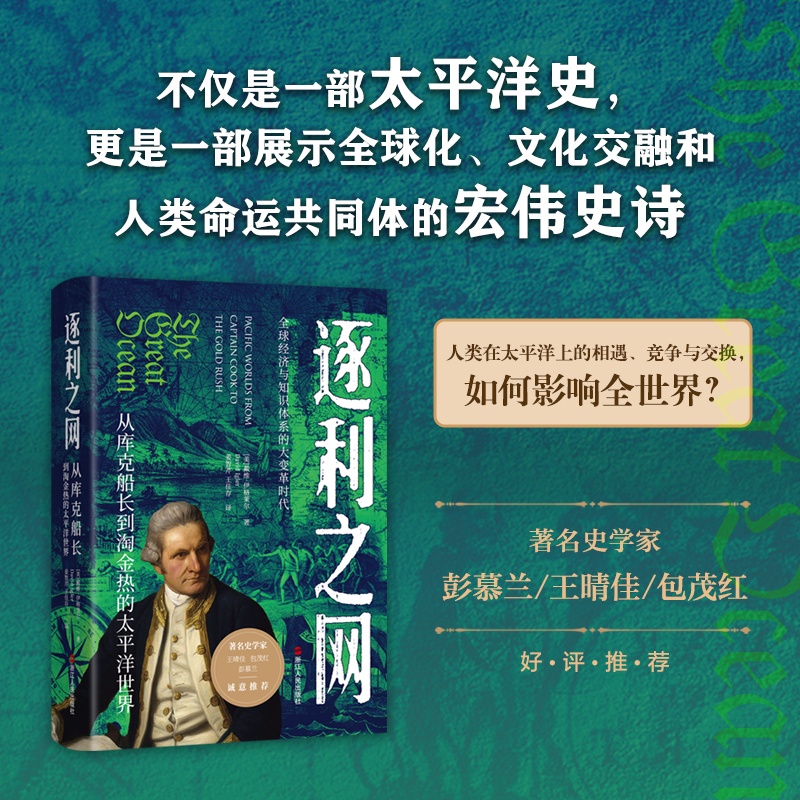
戴维·伊格莱尔(David Igler),美国历史学会太平洋海岸分会主席,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学系主任。主要从事美国西部、太平洋、加利福尼亚等领域的历史研究。著有《工业牛仔:米勒、勒克斯和“远西地区的转型”(1850-1920)》、《逐利之网:从库克船长到淘金热的太平洋世界》。? 姜智芹,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中国形象建构》《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莫言作品海外传播研究》等,译有《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文学艺术》《希腊三百年》等。 王佳存,语言学博士,先后任职于山东省科技厅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从事国际科技交流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调研与合作工作,译有《横财:全球变暖 生意兴隆》《被掠夺的星球》《未来地球》等著作。
本书分几个历史专题详细考察了这些变化,这些专题的内容可简述如下。18世纪70年代以前,东太平洋既有土著人口居住的相互隔离的家园,也有欧洲帝国组织的相互竞争的探险。不过,几十年以后,商业活动迅速扩大了海上贸易人员和土著居民交往的广度。由于探险和贸易船队给土著部落带来了新的疾病,从波利尼西亚(Polynesia)到阿拉斯加的当地居民都遭受了传染病的灾难。土著人和外来者的交易一般是在海滩上、村子里或商船上进行。在这样的交易中,经常发生被扣押人质的交换或当场俘虏交易人员的事件。越来越扩展的贸易网逐渐将东太平洋尤其是大洋的某些特产,和世界市场联结在一起。这一时期,对于海洋哺乳动物的“大捕猎”,造成了太平洋大部分海獭、海狗和鲸鱼的消亡。到了19世纪20年代,在太平洋上往来穿梭的人员已经具有国际性,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本地或外来的体力劳动者、商人以及海滩流浪人员。科学考察大都是在政府资助下进行的,博物学者在人种学、生态学和地质学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研究,目的是了解太平洋上人类和自然的多样性。由于种种因素,东太平洋越来越为人所知,进入了世界市场、帝国以及知识的大背景中。到19世纪40年代末,由于全球贸易扩张、连续几十年土著人口减少以及美国领土征服的影响,太平洋东部的水域被极大地改变了。 本书的海洋视角似乎违背了一些读者对传统历史和地理空间的理解。“地方”这个词通常用于历史分析,可以指国家、地区和地点,是有着固定边界的土地,所以才构成了领土的历史。历史学家很难想象,海洋空间能将人和政治连接起来,而不是将它们分开。看起来,海洋很难进入历史学家关于空间的“认知地图”,更难成为那个地图上的重要地方,因为我们一般都把大洋想象成与历史及人类相疏离的虚无区域。 比较起来,在最早的太平洋土著旅行者以及现代早期大量闯荡太平洋的欧洲人和美洲人的认知地图上,海洋占据着十分显著的地位。古波利尼西亚人出海远航时,会在夜间仰望星空,把夜空看作是大海变幻莫测的海平面的映像图。在这样的远航中,他们最东边到过拉帕努伊岛(Rapa Nui,复活节岛),最北边到过夏威夷群岛,通过祖先世系的传承,在大洋(Moana,莫阿娜)之上建立了历史和传统(故事)。对于一千年以后来自全球的商人和水手来说,太平洋给他们提供了远航探索、实现帝国雄心以及创造历史的平台。詹姆斯·库克、让弗朗索瓦·德·加劳普·拉佩鲁斯(Jean Francois de Galaup de La Perouse)、维他斯·白令(Vitus Bering)以及麦哲伦(Magellan Ferdinand)都是这方面的范例,他们都是远航太平洋的卓越探险家,但是再也没有从最后的远航中返回。他们的死亡是写在航海的内在危险以及帝国的贪婪自大上的墓志铭。对其他人尤其是本书提及的那些不太出名的人物来说,个人的抱负以及追逐私利的野心引领着他们走向太平洋。威廉·谢勒祈求通过与中国做生意攫取财富,玛丽·布鲁斯特渴望一船鲸油并安全回家,季莫费·塔拉卡诺夫(Timofei Tarakanov)祈盼从被奴役中获得自由,詹姆斯·德怀特·达纳对地球起源的科学解释孜孜以求。一位名叫卡杜(Kadu)的马绍尔人所想的是,去大洋更多的地方看看,结识更多远道而来的人。阿德尔贝特·冯·沙米索认真地编写自然和人种学日志,路易斯·柯立芝(Louis Coolidge)唯一的希望是从可怕的坏血病中活下来,拿到自己的海员工资。他们的故事以及与他们一样的很多其他人的故事,为了解东太平洋上的水上世界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万花筒般的视角。 所谓东太平洋,包括美洲海岸及其沿海诸岛和太平洋群岛中最接近美洲的岛屿。众所周知,对于如此浩渺、复杂的海洋空间,这个术语表达的是一个不稳定的概念。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是出于概念称呼上的方便:它描述了一片界限模糊的水域,是通过海道连接起来的各不相同的海岸地区的拼盘。直到18世纪末,东太平洋的概念都还不怎么清晰。在16世纪,西班牙属美洲港口和菲律宾之间的白银贸易开启了跨太平洋的商品交换,将“西班牙湖”(Spanish Lake)带到了世界市场。同时,在西太平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也早在1800年以前就与欧洲商人建立了强有力的经济关系。因此,全球商品流动在19世纪以前就已经在南太平洋和东南亚兴起了。但是,整个太平洋的经济融合和类似太平洋世界等概念的出现,还需要东太平洋和北太平洋区域的商业发展。直到库克船长的几次远航以及随后英国、西班牙、俄国、法国和美国商人纷纷在美洲海岸开展贸易活动,东太平洋的这些区域才与大洋的其他地方以及更远的地方连接起来。 诸如东太平洋那样的地理概念,是随着大海和陆地上的发展才渐渐清晰起来的。在美洲海岸,土著人和西班牙人越来越多地往西部拓展他们的贸易,融入海上商业体系之中,而不是往东发展,与大陆帝国或前土著贸易伙伴做生意。在1800年前后的几十年里,美洲沿海贸易(航行大西洋航线的商船所从事的贸易)大量兴起,从当时俄国的阿拉斯加一直往南,扩展到智利和秘鲁的海岸。渐渐地,夏威夷群岛不仅成为贸易的核心目的地,也是水手满足情欲需求、博物学家进行科学考察的目的地,到了19世纪20年代,还是清教徒传道布教的目的地。东太平洋上的这些联系也映射了西太平洋和南太平洋上的海洋体系。 东太平洋的水域为相互隔离的疆域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主要通道。但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很多因素综合起来改变了大洋中的这些联系。从智利到墨西哥,殖民地脱离西班牙帝国获得独立,宣布自己对于陆地和海洋空间的主权。俄属阿拉斯加(以及俄美公司)成功地大肆捕杀市场所需的海洋哺乳动物,从而导致资源枯竭,自掘了坟墓。同时,土著人口的减少削弱了一度繁荣的当地社区的活力。除其他很多因素外,美墨战争、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以及美国对太平洋沿岸领土的吞并,都改变了大洋中的各种交往,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极大地重构了沿海地理的面貌。对于奉行扩张政策的美国来说,东太平洋的很多区域迅速地变成了美国的西部,而太平洋的其他地区也不可避免地融入更广阔的世界市场之中。19世纪40年代末的几年非常关键,因为这些年开启了太平洋巩固和融合的新阶段。 “东”这个修饰词是为了将这块大洋空间区分开来,不过,东太平洋的概念不稳定。与此相似,太平洋世界也是一个不稳定的概念,而且还问题多多,但是,人们依旧很难不使用这个简略说法。一方面,“太平洋世界”这个术语不仅认为太平洋中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联系是真实的,而且认为那些联系对于太平洋国家和人们来说更加重要,不论对于土著人还是非土著人,都是如此。更进一步说,作为一个概念工具,太平洋世界这个术语提供了与“大西洋世界”相似的分析框架。作为一种描述,大西洋世界这个说法对哥伦布大航海以后非洲、欧洲和美洲相互交融的历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认识。有很多不同因素可以将这两个大洋世界区分开来。比如繁荣的时间(大西洋中的“哥伦布大交换”在17世纪中叶达到鼎盛),比如大洋的面积(太平洋远比大西洋大,很难设想它只是“一个”海洋世界),比如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跨大西洋迁徙的人口中,大多数是被奴役的非洲人),比如与土著人的交往(直到18世纪末,大多数太平洋土著还一直不为外人所知),比如全球商业的性质(在欧洲人进入太平洋的几十年里,市场资本主义冲击了太平洋的部分地区)。除了有以上不同外,大洋世界的概念看起来对于太平洋是适用的,特别是考虑到它与大西洋、印度洋越来越多的交往。 不过,依然有很多顾虑让人不得不谨慎使用诸如太平洋世界这样的概念。首要的问题是:哪个太平洋的历史?谁的太平洋的历史?太平洋历史包括很多与不同地域相关联的历史,这些地域有亚洲、亚北极地区、北美洲和南美洲、澳大利亚以及通常来说组成太平洋历史核心的25000个岛屿。尤其是,这些地理区域每一个都包括众多的海域以及文化,就像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的 “地中海世界”概念一样,其中也包括“众多的海洋”和不同的“文明”。从这个观点看,太平洋真的是太广大、太多元、太复杂了,不能把它只看作一个海洋“世界”,也不能对它众多的区域概而论之。历史学家马特·松田写道:太平洋是一个“多地域空间”,“其海洋史的写作必须更多地立足于岛民以及当地文化,并由此而向外观照”。马特·松田的观点将观察尺度和观察视角融合到一起。谁的太平洋?这个问题反映了欧洲人和美洲人等外来者对太平洋进行合理化认识的努力,他们把太平洋笼统地看作一个大洋,试图将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和自然问题简单化,但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而且最为严重的是,“太平洋世界”这个术语遮蔽了土著人的历史,凸显了帝国的活动。如果把太平洋世界当作一个统一的概念,那么其价值在于给历史本身确定了一个框架,那就是所采取的是海洋而非陆地的视角,聚焦的是有人生活的而非空旷的水域,把太平洋看作一个有人活动和交往的地方,采用的是在全球、海洋和当地等不同层面寻求重要交互影响的方法。 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将全球、海洋和当地这三个层面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联系起来。18世纪60年代以后,全球因素包括国际贸易、疾病传播、资源需求以及科学考察,开始汇聚于东太平洋。这一时期的帝国扩张和冲突在全世界上演,但是,正如历史学家安·斯托勒(Ann Stoler)所言:“对于土地、劳力以及‘生存区域’的部分主权和模糊主权”,可能最真切地描述了大多数海外帝国在东太平洋中的作用。因此,本书不怎么关注全球帝国的正式行动,而是更加关注帝国的局限性、非官方人员之间的磋商以及那些难于进行分类的地方的重要性。这种对帝国政治的淡化还反映了我自己对特定历史时刻和历史人物的解读。比如,人们认为约翰·肯德里克在太平洋的冒险可能象征和预示着美国对于海洋霸权的终极渴望以及获得其他全球性帝国的认可。但是,如果这样阐释肯德里克在太平洋艰险曲折的经历,那就是在倒推历史,同时也忽略了肯德里克闯荡的那个流动的、竞争的海洋世界。最有可能的是好奇心和个人贪欲引导着他的行为,而不是什么地理政治的野心。 全球力量与海洋上的事件和趋势是相互联系的,并影响了整个太平洋。比如,1763年结束的七年战争以及1815年结束的拿破仑战争都给太平洋带来了特别的冲击。七年战争结束以后,对整个太平洋进行最初探险的时期开启了;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在太平洋进行商业贸易和对其进行科学考察的时期开启了。在这两个时期,不论是东西跨越太平洋,还是南北穿越美洲太平洋海岸线,都发生了新的商品、病菌和人员的流动。海洋规模也是人类认知扩大的结果,人们通过这种认知把太平洋构建为一个地理主体。博物学家阿德尔贝特·冯·沙米索在他1815年至1818年期间的航海中就是这么做的,而在这方面,鲜有人比地质学家詹姆斯·德怀特·达纳更具有洞察力,他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就发现了太平洋诸岛、大陆边界以及整个大洋盆地在地质上的一致性。 最后,当地的村庄、部落和船只也在引发和响应全球与海洋趋势方面,显示了个人以及生态的推动力。发生在火奴鲁鲁海湾、哥伦比亚河流域或马格达莱纳湾等地的事件,不仅仅是外来者要求或强制的结果,当地的部落政治在这一切中更是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卡米哈米哈国王不遗余力地巩固其在夏威夷群岛上的权力。当地的生态也同样产生了影响,比如努查努尔特人酋长马奎纳(Maquinna)在18世纪90年代遇到了生存危机,再比如在马格达莱纳湾,由于独特的迁徙路线,太平洋灰鲸整个种群被快速屠杀。总而言之,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塑造海洋历史和世界历史方面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正如本书各章所显示的那样,某些地理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趋势不仅清晰地反映在全球层面和海洋层面上,还反映在当地层面上。在19世纪最初的10年里,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衰落给欧洲带来了重大变革,深刻影响了太平洋的贸易模式,导致诸如墨西哥等新的民族国家的出现。不过,有些太平洋事件虽然鲜为人知,但与其历史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已经预示着分裂新西班牙(New Spain)的革命运动。比如,1789年爆发的努特卡海湾危机显示出西班牙控制美洲西北海岸的力量严重不足,而西北海岸是西班牙一直希望控制的地区。西班牙一度是太平洋上的欧洲海洋强国,但是它没有听从其最了解太平洋政治动向的航海专家的建议。比如,西班牙航海家亚历山大·马拉斯皮纳(Alejandro Malaspina)在18世纪90年代初期完成了环球航海,26他善意地向西班牙皇室提出建议,实行自由贸易,进行帝国改革,但是他不但一无所获,反而在圣安东(San Antón)城堡冰冷的监牢里度过了六年牢狱时光。 西班牙在美洲影响力的衰落正好遇上美国作为大陆强国的开疆扩土。詹姆斯·库克船长1768年首次出发航海的时候,美国还不存在呢;到他1779年第三次航海回到英国的时候,美国的独立战争还胜负未分。不过,到了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的1848年,美利坚合众国已经赢得了对英国第二次战争的胜利,在俄亥俄河谷重新建立了定居点,从法国购买了路易斯安那领地,通过掠夺土著人的土地和发动美墨战争,建立起大陆帝国。但是,这个关于美国扩张的常见叙事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水手一直持续不断地在太平洋上航行,并于18世纪80年代末以后逐渐主导其中的一部分区域。如果把太平洋(及其通往亚洲的航道)列入美国大陆扩张的范围内,那么它也是几十年前美国民间海洋利益团体所致力于实现的目标,这些美国商人对于海上自由贸易抱有坚定的信念。 中国在太平洋与世界的大融合中也发挥了显著作用。中国广州的商人对于发生在大洋上的变化洞若观火。如果说在如火如荼的淘金热出现之后全世界都“涌向”了加利福尼亚,那么此前60年,穿越太平洋的商人则是一股脑儿地冲向开放的港口广州。这个商热潮是西班牙商人开启的,他们用白银向中国商人购买商品,而且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太平洋商人不断寻找中国商人和消费者需要的商品(如毛皮、鸦片、奇珍异宝、檀香木等)。在18世纪末,大英帝国希望通过东印度公司控制和垄断与中国的贸易,但是中国商人有自己的盘算,他们坚持自行与在广州的很多不同国家的商人打交道。至少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市场对于太平洋商业及其与世界贸易的联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海洋航行为本书中的各章提供了结构和叙事上的框架。本书参考利用了数百次有文字记录的航行,以此作为一个窗口,来观察太平洋上发生的商业、文化和生态方面的变化。那些航行,有些是亲身经历的人千辛万苦记录下来的,有些仅仅通过考古发现或土著人的记忆才为人所知。一些专门的航行和日志也为不同的历史主题提供了切入点。比如,第一章就首先利用了美国双桅横帆船“莱利亚·拜尔德号”(Lelia Byrd)船长威廉·谢勒出海远航和开展贸易的资料。 在1802—1806年期间,威廉·谢勒四次穿越太平洋,往返于中国与美国海岸。他关于航海的个人记述在回来两年后发表在《美国纪事》(American Register)上,反映了太平洋上早期商业的情形,以及彼此隔离的太平洋土著部落和全球贸易体系之间建立起新联系的动态发展。特别是在东太平洋,通过其商业网络以及将上加利福尼亚、夏威夷群岛、美洲西北海岸、阿拉斯加海岸、秘鲁这些与市场繁荣的广州联系起来的港口,一下子涌现出很多商业活动。如果分析这一时期的商业增长,就会发现有两个交织在一起的重要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新太平洋贸易的构成要素,包括港口、货物、社会习俗以及航行。第二个主题是诸如谢勒等商人与他们的土著贸易伙伴之间交往的个体特征,双方的贸易叙事反映了在这个大洋市场中,所谓的“自由”贸易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各种紧张关系。 在这一时期,海上贸易给太平洋的土著居民带来了一些隐蔽的“全球旅行者”,也就是新的病菌,造成了可怕的死亡,降低了土著妇女的生育能力,使得很多土著部落遭受了人口灾难。本书第二章主要是通过考察土著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性关系,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性病梅毒的传播,来分析这些可怕的变化。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 Clerke)是詹姆斯·库克船长的副手,14他在第三次太平洋航行中的不幸经历揭示了病菌传播所造成的悲剧。不论是库克船长还是克拉克大副,都没有在这次航行中幸存下来,令人哀恸不已,但是比他们的死亡更令人哀恸不已的,是欧洲和美国航海人员传染给所有土著的疾病及其带来的恶果。这一章讨论那些到访夏威夷、加利福尼亚(包括下加利福尼亚和上加利福尼亚)、塔希提岛、美洲西北海岸的哥伦比亚河流域的细菌携带者,记述海上航行以及人际交往在太平洋上所造成的惊人的生命代价。 除了疾病,外来者和土著人在交往中还交换了各式各样的东西,包括物品、语言以及知识体系。第三章考察一种特别的人员交流,即俘虏和临时人质。在整个太平洋盆地,人质和掳掠俘虏成为人员交往的共同特色,其中最盛行的地方是北美的西北海岸沿线。1810年以前就兴起的毛皮贸易将大量的土著居民与来自俄国、英国、西班牙和美国的商人汇聚在一起。季莫费·塔拉卡诺夫是俄美公司的年轻雇员,他深知这条海岸线上的危险和机会,也知道如果发生灾难应采取的生存方法。他遭遇的船难以及他被俘的故事,与俘虏他的印第安人所口耳相传的故事各有千秋,共同为人们了解世界上这片波涛汹涌的水域里自由和被俘生活的种种现象,提供了令人震撼的一瞥。 19世纪初期,物品、疾病和人员的交流都在东太平洋新的社会关系中发挥了作用,而所有这一切人类活动的主要推动者,是一种被当作商品的非人类物种:海洋哺乳动物。本书第四章详细讲述了“大捕猎”。这是一场由外国商人和当地渔民沿着美洲西海岸对太平洋最有价值的哺乳动物联合实施的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从北边的阿拉斯加一直延续到南边的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由于这种残酷的虐杀,在19世纪初期,海獭和海狗面临着物种几近灭绝的困境。几十年后,太平洋数不胜数的鲸鱼遭遇美国快速扩张的捕鲸船队。由于要获得鲸油,美国的捕鲸船队就开始了规模巨大的杀戮,主要受益者是美国的工厂。玛丽·布鲁斯特的丈夫是捕鲸船“老虎号”(Tiger)的船长。作为鲸鱼被捕杀的见证者,玛丽·布鲁斯特讲述了捕鲸造成的后果。在下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环礁湖里,她亲眼看见一支小的捕鲸船队攻击灰鲸设在偏僻处所的繁殖基地,接着,她又看见鲸鱼群进行反击。总起来说,70年的大捕杀展现了杀戮、流血和贪婪的历史。 本书最后两章探讨训练有素的博物学家和业余博物学者的工作。几乎每次政府资助的远洋航海都把博物学家带到太平洋,他们参与航海的目的,就是要了解这个鲜为人知的大洋及当地的文化和生态知识。15第五章聚焦拿破仑战争结束后20年间被雇佣跟随俄国、法国和英国远洋航行的博物学家,其中有些科学家,比如阿德尔贝特·冯·沙米索,试图通过与当地人的接触获得关于当地的知识,有一个名叫卡杜的马绍尔群岛人就陪着他航行了一段时间。其他博物学家则一概把所有太平洋土著居民看作即将灭亡的种族,比如英国医生梅雷迪斯·盖尔德纳(Meredith Gairdner)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只是,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科学野心,最后转向盗掘印第安人的墓地。 与多数博物学家受局限的世界观相反,地质学家詹姆斯·德怀特·达纳对太平洋及其陆地的基本结构采取了综合性、理论性的认知方法。他是跟随美国探险远征队(US Exploring Expeditions,1838—1842)的七名科学家之一,是第一位研究东太平洋并将整个太平洋海盆的潜在联系理论化的地质学家。就像比他早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一样,达纳的科学观点很大胆,但又基于实践,他对太平洋发生的令人震撼的地质过程,比如火山、地震和珊瑚礁等,都进行了创新而实际的科学思考。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他考察了整个太平洋以及与之相连的所有陆地,并把那些陆地作为相互连接的太平洋世界的一部分。不过,到了19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最杰出的地质学家们发现,大陆地质学可以用来服务国家事业,满足国家开拓大陆边疆的需要,从而为国家带来利益。因此,达纳这项新的科考工作为美国疆域的巩固之路提供了支撑。 约翰·肯德里克1792年致信“华盛顿夫人号”商船船主约瑟夫·巴雷尔(Joseph Barrell)的时候,脑子里根本没有想什么帝国梦的事。当肯德里克率领的这艘商船停泊在中国澳门港口的时候,巴雷尔则居住在半个地球之外的波士顿家中,对于肯德里克长达四年的杳无音讯以及在这期间的所作所为也只能在心中暗自揣度。肯德里克远航逾期不归,一个钱都没有赚到。不仅如此,他还在信中对巴雷尔说,他目前深陷困境,包括高企的债务、因坏血症和溺亡造成的船员减员、在美洲西北海岸装错弄丢的毛皮、现下正从事走私而不是在广州进行诚实贸易、“华盛顿夫人号”被海水侵蚀严重急需修理等,只有在这些问题解决以后,他才能“最终直接返航或辗转返航”。28约瑟夫·巴雷尔收到这封信以后,很有可能在失望、焦虑中摇头。这封信是来自肯德里克的最后消息,两年后,他就在火奴鲁鲁湾猛烈的炮火中死于非命了。不过,通过肯德里克的航行,巴雷尔可能在关于太平洋商业方面获得了一些教训,也可能认识到,他需要一个信得过的船长。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更多的外国人蜂拥进入太平洋,他们或是为贸易,或是为科考,或是为捕鲸,或是为美国开疆拓土,他们结识了具有多种文化背景的人,见识了众多的海域,其中有些人把疾病传染给土著居民,而诸如约翰·肯德里克那样的其他一些人,则殒命于在世界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沿着早期探险者的航行路线,这些后来的外国人继续追寻着商业的海洋。 不仅是一部太平洋史,更是一部展示全球化、文化交融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史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