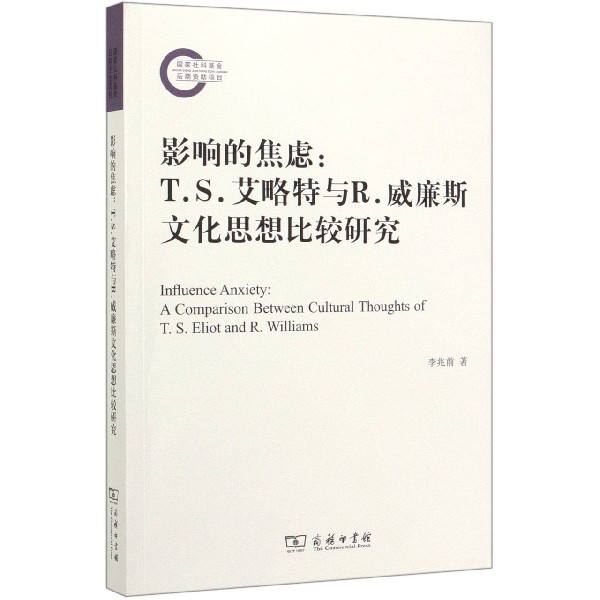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80.00
折扣价: 56.00
折扣购买: 影响的焦虑--T.S.艾略特与R.威廉斯文化思想比较研究
ISBN: 97871001745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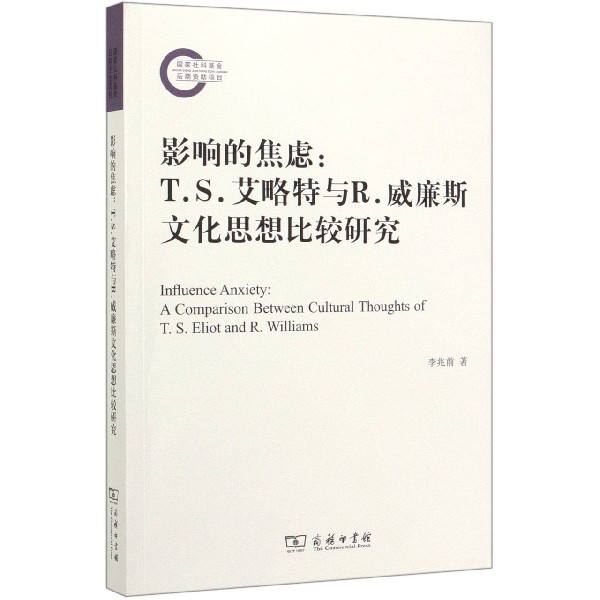
李兆前,女,1970年生,湖南人,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时至2018年,从医十余年,从教十余年。目前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和文化研究。曾出版专著一部:《范式转换: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发表论文数篇:《<边界乡村>中的记忆与身份认同》(《当代外国文学》,2018(2));《创造性误读理论视域下的<枯叟>》(《国外文学》,2017(2)),等等。完成科研项目数个:“T.S.艾略特与R.威廉斯文化思想比较研究”(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雷蒙德?威廉斯的乌托邦研究”(湖南省社科一般项目),等等。
对比雷蒙德?威廉斯和T.S.艾略特的文化研究可知,作为后辈的威廉斯自主地经历了布鲁姆总结的“选择、认同、抗争、‘化身’、重新解读和修正”的强者自我成长过程。具体说来,首先是威廉斯选择艾略特等值得超越的前辈作为自己文学和文化学习的对象,从而深受他们的影响,之后他对他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解读,开始思考他们的伟大之处,并尝试对这些伟大之处进行利用和修正,最后当完全把握它们时,他勇敢出手,点对点地彻底突破前辈们的障碍,在前辈的伟大基础上另起炉灶,成为新一代强者。 前辈的影响对于具有高度创新自觉的后辈来说是把双刃剑:是前进路上的障碍,更是成功创新的必要阶梯,因为“通过前辈认知,通过误读前辈创新,从而拓宽人类体验范围是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创造力或者说独创源于前辈(们)铺就的某一片土壤(前辈作品中的伟大之处),后辈(们)从中发芽,尔后独立成长为一个与前辈地位相当或者超越前辈的新有机体,并且为下一代强者准备可供选择的土壤。“任何诗都是与其他诗歌互文的……诗歌不是创作,而是再创作,并且就算强势诗是一个新的开端,亦只是再次开始。”任何一个强者此一时是前驱强势文本的误读主体,彼一时又成了后一个强者的误读客体,如此形成的强强斗争之关联流,不断前行,为文学和文化传统等提供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源。俄国形式主义者迪尼亚诺夫早就从文学形式演变的角度谈论过创新的斗争性,因为他认为,“文学上的一切延续首先是一场斗争,也就是摧毁已经存在的一切,并且从旧的因素开始进行新的建设”。然而,创造性误读过程中成长的新文艺有机体最终赢在在一定程度上与母体相互对抗,而不仅仅是斗争,因为它是卓越的原创性作者为摆脱前辈的影响有意或者下意识进行否定、修正和势不两立的结果。 上述影响与创新的关系说明,文艺作品首先是“人书写和思考”的产物,而不是“文本之外别无他物”。文艺作品是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文艺人通过个人独创意志否定、修正、反抗传统与前辈而实现超越后的逆向创新物。成为拥有流芳百世的文艺作品的伟大者之有效途径是通过强大的权力意志(即在文艺领域求生存的欲望和创造的本能)吸收并活用前辈而赢得强者所创造的强者文本之间的战争,或者说赢得作为后辈个体的自己与前辈个体或者与前辈群体之间的潜在的意志之战以及由此而生的显在的文本之战。总而言之,前驱经典文本幽灵般存在于新的强势文本之中是文艺新人得以脱颖而出的法宝,新的强势文本不断产生并经典化又是文艺传统蓬勃发展的法宝。影响下的创造性误读不失为实现文艺独创性的一条有效途径,这既是文艺批评者的福音,也是文艺创作者的福音。这对于改变中国在当前世界文艺理论领域没有话语权的现状是有启示作用的,因为中国并不缺乏经典的文学理论概念、术语和思想,缺乏的是勇于用现代性话语和世界性话语创造性误读中国经典而自成一派的强者。 摘自“结语 影响与独创性” 关于20世纪两位文化批评大师的文化思想的一本涉及面较广、有相当思想深度和较大启发意义的比较研究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