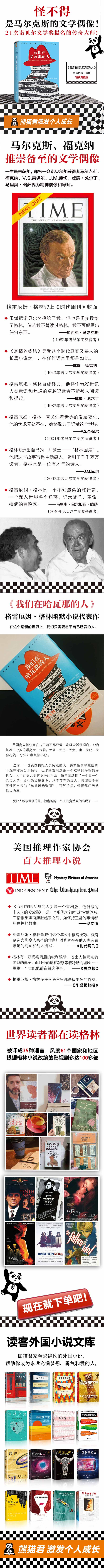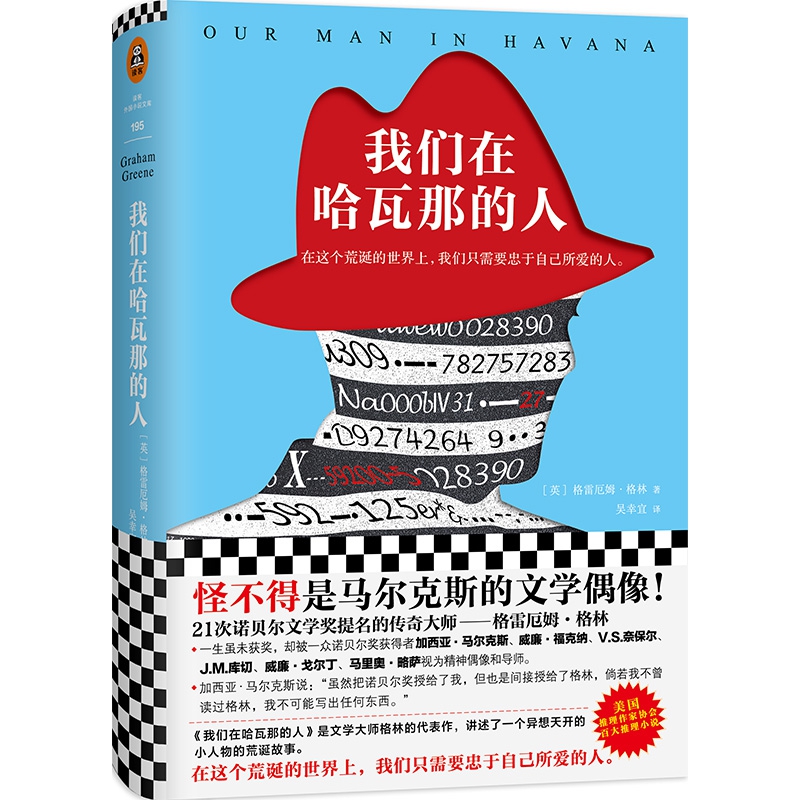
出版社: 江苏文艺
原售价: 59.90
折扣价: 34.80
折扣购买: 我们在哈瓦那的人(精)
ISBN: 9787539979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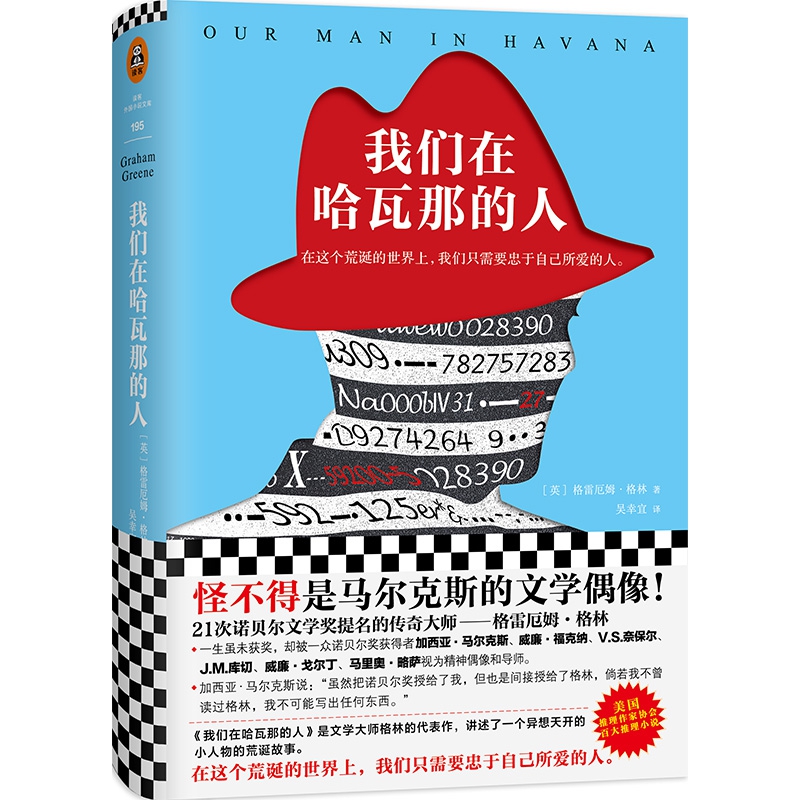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 21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传奇大师。67年写作生涯,创作多于25部小说,被誉为20世纪大师级作家。1950年,初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1976年,获美国推理作家协会大师奖。1981年,获耶路撒冷文学奖。1986年,由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功绩勋章。 格林一生游历于墨西哥、西非、南非、越南、古巴、中东等战乱之地,曾任职于英国军情六处,从事间谍工作,并以此为背景创作小说,关注人灵魂深处的挣扎与救赎、内心的道德和精神斗争,被誉为20世纪人类意识和焦虑的卓越记录者。 至今,每年格林生日期间,在格林出生地——英国赫特福德郡,都会举办为期四天的格雷厄姆·格林国际艺术节,世界各地的格林粉丝齐聚这里参加纪念格林的活动。
第一部 1 “那个走在街上的黑人,”海斯巴契医生站在惊奇酒吧里,对身旁的人说,“让我想到了你,伍尔摩先生。”海斯巴契医生向来如此,虽然两人交情已有十五年,他还是不忘加上“先生”二字——这份友情进行得戒慎缓稳、字斟句酌,一如他所下的病情诊断。或许要等到站在伍尔摩临终的病床边搜寻着他愈见衰弱的脉搏时,海斯巴契医生才会改口叫他一声 “吉姆”。那黑人瞎了一只眼,两腿一长一短;戴着旧式毡帽,透过褴褛的衬衫肋骨历历可见,有如一艘报废的老船。一月的暖阳照耀,他在红黄交错的廊柱外沿着人行道边缘行走,边走边数着自己的脚步。当他走过惊奇酒吧转往瓦杜德街时,正数到“一千三百六十九”。他走得很慢,好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吐出这么长的数字——“一千三百七十”。他是国家广场的熟面孔,经常出没在这一带,偶尔会放下那长串的数字,向游客兜售春宫画,之后又回到刚才的数字,继续往下数。当一天终了,他就像 一个搭乘大西洋渡轮的精力充沛的游客,清清楚楚知道自己这一天总共走了多少路。 “你是说乔伊?”伍尔摩问,“我一点也看不出他哪里像我—— 当然,跛脚除外。” 但他还是本能地朝着那面标示有“热带Cerveza1 ”的镜子觑了自己一眼,仿佛他走在老镇的街道上也是那么无力颓败。可是从镜子里回望着他的那张面容,除了因为蒙上码头吹来的沙尘而略带苍白外,其他还是一样:四十来岁,细纹密布,满面愁容。他比海斯巴契医生年轻得多,但陌生人看到这张脸铁定觉得它撑不了多久—— 暗沉已经进驻,那股忧容连镇静剂都抚平不了。黑人蹒跚着走出他们的视线,弯进帕萨奥街的拐角。这一天来来往往的尽是擦鞋匠。 “我指的不是跛脚。你真的看不出相似的地方?” “是啊,看不出。” “他的脑袋里只装了两件事,”海斯巴契医生解释道,“做他的工作和数数儿。还有,他也是英国人。” “我还是不觉得……” 伍尔摩喝了口鸡尾酒润润喉。从店里到惊奇酒吧花了他七分钟,等下再花七分钟走回去,中间六分钟的空当则留给友谊。他看看表,想起这表慢了一分钟。 “他也很可靠,是个可信赖的人。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这样。”海斯巴契医生说,语气带着不耐烦,“米莉还好吗?” “非常好。”伍尔摩说。这个回答从来没有变过,但他是说真的。 “她十七号就十七岁了,对吧?” “没错。”他匆匆回过头瞄了瞄,仿佛觉得有人在跟踪他,接着又去看表,“米莉生日那天,你会过来和我们喝杯酒吧?” “这事我从来没失约过,伍尔摩先生。还有谁一起呢?” “我想就我们三个了。你知道,古柏回家去了,可怜的马洛还在医院里,而大使馆的那些新人,米莉好像一个也不喜欢。所以这件事我们知道就好,就当个家庭聚会。” “我很荣幸成为这个家的一分子,伍尔摩先生。” “或许我们会在国家俱乐部订个位子——还是你觉得那里不太——嗯,不太适合?” “伍尔摩先生,这里不是英国,也不是德国。女孩子家在热带地方长得快。” 对街一扇百叶窗戛然开启,在飘忽的海风轻轻摇晃下,像个老爷钟滴答作响。伍尔摩说:“我得走了。” “菲氏吸尘器公司少了你照样可以营业,伍尔摩先生。”这一天尽是令人不快的真相。“就像那些病人,没有我照样活得下去。”海斯巴第一部 1 “那个走在街上的黑人,”海斯巴契医生站在惊奇酒吧里,对身旁的人说,“让我想到了你,伍尔摩先生。”海斯巴契医生向来如此,虽然两人交情已有十五年,他还是不忘加上“先生”二字——这份友情进行得戒慎缓稳、字斟句酌,一如他所下的病情诊断。或许要等到站在伍尔摩临终的病床边搜寻着他愈见衰弱的脉搏时,海斯巴契医生才会改口叫他一声 “吉姆”。那黑人瞎了一只眼,两腿一长一短;戴着旧式毡帽,透过褴褛的衬衫肋骨历历可见,有如一艘报废的老船。一月的暖阳照耀,他在红黄交错的廊柱外沿着人行道边缘行走,边走边数着自己的脚步。当他走过惊奇酒吧转往瓦杜德街时,正数到“一千三百六十九”。他走得很慢,好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吐出这么长的数字——“一千三百七十”。他是国家广场的熟面孔,经常出没在这一带,偶尔会放下那长串的数字,向游客兜售春宫画,之后又回到刚才的数字,继续往下数。当一天终了,他就像 一个搭乘大西洋渡轮的精力充沛的游客,清清楚楚知道自己这一天总共走了多少路。 “你是说乔伊?”伍尔摩问,“我一点也看不出他哪里像我—— 当然,跛脚除外。” 但他还是本能地朝着那面标示有“热带Cerveza1 ”的镜子觑了自己一眼,仿佛他走在老镇的街道上也是那么无力颓败。可是从镜子里回望着他的那张面容,除了因为蒙上码头吹来的沙尘而略带苍白外,其他还是一样:四十来岁,细纹密布,满面愁容。他比海斯巴契医生年轻得多,但陌生人看到这张脸铁定觉得它撑不了多久—— 暗沉已经进驻,那股忧容连镇静剂都抚平不了。黑人蹒跚着走出他们的视线,弯进帕萨奥街的拐角。这一天来来往往的尽是擦鞋匠。 “我指的不是跛脚。你真的看不出相似的地方?” “是啊,看不出。” “他的脑袋里只装了两件事,”海斯巴契医生解释道,“做他的工作和数数儿。还有,他也是英国人。” “我还是不觉得……” 伍尔摩喝了口鸡尾酒润润喉。从店里到惊奇酒吧花了他七分钟,等下再花七分钟走回去,中间六分钟的空当则留给友谊。他看看表,想起这表慢了一分钟。 “他也很可靠,是个可信赖的人。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这样。”海斯巴契医生说,语气带着不耐烦,“米莉还好吗?” “非常好。”伍尔摩说。这个回答从来没有变过,但他是说真的。 “她十七号就十七岁了,对吧?” “没错。”他匆匆回过头瞄了瞄,仿佛觉得有人在跟踪他,接着又去看表,“米莉生日那天,你会过来和我们喝杯酒吧?” “这事我从来没失约过,伍尔摩先生。还有谁一起呢?” “我想就我们三个了。你知道,古柏回家去了,可怜的马洛还在医院里,而大使馆的那些新人,米莉好像一个也不喜欢。所以这件事我们知道就好,就当个家庭聚会。” “我很荣幸成为这个家的一分子,伍尔摩先生。” “或许我们会在国家俱乐部订个位子——还是你觉得那里不太——嗯,不太适合?” “伍尔摩先生,这里不是英国,也不是德国。女孩子家在热带地方长得快。” 对街一扇百叶窗戛然开启,在飘忽的海风轻轻摇晃下,像个老爷钟滴答作响。伍尔摩说:“我得走了。” “菲氏吸尘器公司少了你照样可以营业,伍尔摩先生。”这一天尽是令人不快的真相。“就像那些病人,没有我照样活得下去。”海斯巴第一部 1 “那个走在街上的黑人,”海斯巴契医生站在惊奇酒吧里,对身旁的人说,“让我想到了你,伍尔摩先生。”海斯巴契医生向来如此,虽然两人交情已有十五年,他还是不忘加上“先生”二字——这份友情进行得戒慎缓稳、字斟句酌,一如他所下的病情诊断。或许要等到站在伍尔摩临终的病床边搜寻着他愈见衰弱的脉搏时,海斯巴契医生才会改口叫他一声 “吉姆”。那黑人瞎了一只眼,两腿一长一短;戴着旧式毡帽,透过褴褛的衬衫肋骨历历可见,有如一艘报废的老船。一月的暖阳照耀,他在红黄交错的廊柱外沿着人行道边缘行走,边走边数着自己的脚步。当他走过惊奇酒吧转往瓦杜德街时,正数到“一千三百六十九”。他走得很慢,好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吐出这么长的数字——“一千三百七十”。他是国家广场的熟面孔,经常出没在这一带,偶尔会放下那长串的数字,向游客兜售春宫画,之后又回到刚才的数字,继续往下数。当一天终了,他就像 一个搭乘大西洋渡轮的精力充沛的游客,清清楚楚知道自己这一天总共走了多少路。 “你是说乔伊?”伍尔摩问,“我一点也看不出他哪里像我—— 当然,跛脚除外。” 但他还是本能地朝着那面标示有“热带Cerveza1 ”的镜子觑了自己一眼,仿佛他走在老镇的街道上也是那么无力颓败。可是从镜子里回望着他的那张面容,除了因为蒙上码头吹来的沙尘而略带苍白外,其他还是一样:四十来岁,细纹密布,满面愁容。他比海斯巴契医生年轻得多,但陌生人看到这张脸铁定觉得它撑不了多久—— 暗沉已经进驻,那股忧容连镇静剂都抚平不了。黑人蹒跚着走出他们的视线,弯进帕萨奥街的拐角。这一天来来往往的尽是擦鞋匠。 “我指的不是跛脚。你真的看不出相似的地方?” “是啊,看不出。” “他的脑袋里只装了两件事,”海斯巴契医生解释道,“做他的工作和数数儿。还有,他也是英国人。” “我还是不觉得……” 伍尔摩喝了口鸡尾酒润润喉。从店里到惊奇酒吧花了他七分钟,等下再花七分钟走回去,中间六分钟的空当则留给友谊。他看看表,想起这表慢了一分钟。 “他也很可靠,是个可信赖的人。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这样。”海斯巴契医生说,语气带着不耐烦,“米莉还好吗?” “非常好。”伍尔摩说。这个回答从来没有变过,但他是说真的。 “她十七号就十七岁了,对吧?” “没错。”他匆匆回过头瞄了瞄,仿佛觉得有人在跟踪他,接着又去看表,“米莉生日那天,你会过来和我们喝杯酒吧?” “这事我从来没失约过,伍尔摩先生。还有谁一起呢?” “我想就我们三个了。你知道,古柏回家去了,可怜的马洛还在医院里,而大使馆的那些新人,米莉好像一个也不喜欢。所以这件事我们知道就好,就当个家庭聚会。” “我很荣幸成为这个家的一分子,伍尔摩先生。” “或许我们会在国家俱乐部订个位子——还是你觉得那里不太——嗯,不太适合?” “伍尔摩先生,这里不是英国,也不是德国。女孩子家在热带地方长得快。” 对街一扇百叶窗戛然开启,在飘忽的海风轻轻摇晃下,像个老爷钟滴答作响。伍尔摩说:“我得走了。” “菲氏吸尘器公司少了你照样可以营业,伍尔摩先生。”这一天尽是令人不快的真相。“就像那些病人,没有我照样活得下去。”海斯巴第一部 1 “那个走在街上的黑人,”海斯巴契医生站在惊奇酒吧里,对身旁的人说,“让我想到了你,伍尔摩先生。”海斯巴契医生向来如此,虽然两人交情已有十五年,他还是不忘加上“先生”二字——这份友情进行得戒慎缓稳、字斟句酌,一如他所下的病情诊断。或许要等到站在伍尔摩临终的病床边搜寻着他愈见衰弱的脉搏时,海斯巴契医生才会改口叫他一声 “吉姆”。那黑人瞎了一只眼,两腿一长一短;戴着旧式毡帽,透过褴褛的衬衫肋骨历历可见,有如一艘报废的老船。一月的暖阳照耀,他在红黄交错的廊柱外沿着人行道边缘行走,边走边数着自己的脚步。当他走过惊奇酒吧转往瓦杜德街时,正数到“一千三百六十九”。他走得很慢,好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吐出这么长的数字——“一千三百七十”。他是国家广场的熟面孔,经常出没在这一带,偶尔会放下那长串的数字,向游客兜售春宫画,之后又回到刚才的数字,继续往下数。当一天终了,他就像 一个搭乘大西洋渡轮的精力充沛的游客,清清楚楚知道自己这一天总共走了多少路。 “你是说乔伊?”伍尔摩问,“我一点也看不出他哪里像我—— 当然,跛脚除外。” 但他还是本能地朝着那面标示有“热带Cerveza1 ”的镜子觑了自己一眼,仿佛他走在老镇的街道上也是那么无力颓败。可是从镜子里回望着他的那张面容,除了因为蒙上码头吹来的沙尘而略带苍白外,其他还是一样:四十来岁,细纹密布,满面愁容。他比海斯巴契医生年轻得多,但陌生人看到这张脸铁定觉得它撑不了多久—— 暗沉已经进驻,那股忧容连镇静剂都抚平不了。黑人蹒跚着走出他们的视线,弯进帕萨奥街的拐角。这一天来来往往的尽是擦鞋匠。 “我指的不是跛脚。你真的看不出相似的地方?” “是啊,看不出。” “他的脑袋里只装了两件事,”海斯巴契医生解释道,“做他的工作和数数儿。还有,他也是英国人。” “我还是不觉得……” 伍尔摩喝了口鸡尾酒润润喉。从店里到惊奇酒吧花了他七分钟,等下再花七分钟走回去,中间六分钟的空当则留给友谊。他看看表,想起这表慢了一分钟。 “他也很可靠,是个可信赖的人。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这样。”海斯巴契医生说,语气带着不耐烦,“米莉还好吗?” “非常好。”伍尔摩说。这个回答从来没有变过,但他是说真的。 “她十七号就十七岁了,对吧?” “没错。”他匆匆回过头瞄了瞄,仿佛觉得有人在跟踪他,接着又去看表,“米莉生日那天,你会过来和我们喝杯酒吧?” “这事我从来没失约过,伍尔摩先生。还有谁一起呢?” “我想就我们三个了。你知道,古柏回家去了,可怜的马洛还在医院里,而大使馆的那些新人,米莉好像一个也不喜欢。所以这件事我们知道就好,就当个家庭聚会。” “我很荣幸成为这个家的一分子,伍尔摩先生。” “或许我们会在国家俱乐部订个位子——还是你觉得那里不太——嗯,不太适合?” “伍尔摩先生,这里不是英国,也不是德国。女孩子家在热带地方长得快。” 对街一扇百叶窗戛然开启,在飘忽的海风轻轻摇晃下,像个老爷钟滴答作响。伍尔摩说:“我得走了。” “菲氏吸尘器公司少了你照样可以营业,伍尔摩先生。”这一天尽是令人不快的真相。“就像那些病人,没有我照样活得下去。”海斯巴契好心加上一句。 “人一定会生病,但他们不一定会买吸尘器。” “但是你的收费比较高。” “可是我只赚取其中的百分之二十。这样的利润存不了什么钱。” “这不是存钱的年代,伍尔摩先生。” “我必须存钱,为了米莉。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 “反正这年头没有人对人生怀有高度期望,所以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些动乱对生意很不好。如果电力中断,光有吸尘器有什么用?” “我可以帮你弄个小额贷款,伍尔摩先生。”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担心的不是今年或明年,而是长远的未来。” “那根本不值得你担心。伍尔摩先生,我们生活在原子时代,只要那些人按个钮——砰一声,到时哪里还有我们?麻再来一杯威士忌。” “那是另一回事。你知道我那家公司干了什么吗?他们给我寄来一个原子炉吸尘器。” “真的?我不知道现代科技已经这么进步了。” “哦,不是,它跟原子扯不上半点关系,光是个名称罢了。去年的噱头是涡轮喷射引擎,今年是这个原子炉吸尘器。其实根本没两样,一样要插电。” “所以有什么好担心的?”海斯巴契医生又说了一遍,像在哼什么主题曲一般,一面啜了口威士忌。 “他们不了解,这类名称在美国或许行得通,这里却不行。这里的牧师动不动就高唱反对滥用科学的论调。上星期日我和米莉到教堂去——你知道她对做弥撒的想法,我知道她认为她能感化我——结果门德斯神父花了半个钟头描述氢弹的作用。他说,那些相信天堂存在于地球的人,创造了一个人间地狱,还说得活灵活现的——这用意太明显了。你想想,星期一早上我就要在橱窗里展示这个新型的原子炉吸尘器,我该作何感想?如果哪个野孩子砸了我的橱窗,我是不会惊讶的。‘天主行为’‘耶稣天主’,到处都是这种东西。海斯巴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卖一个给门德斯神父,在主教的殿堂里用。” “但他很满意那个涡轮。那是台好机器。当然这台也很好,能把书架上的灰尘吸得更干净。你知道的,我从来不卖不好的机器。” “我知道,伍尔摩先生。但你能替它改个名字吗?” “他们不让我这么做。他们以它为荣,认为这是打从‘打败灰尘,清洁溜溜’之后的最佳句子。你知道吗,他们在涡轮那款上放了一种叫作滤净片的零件,那是个挺精巧的设计,只是没人特别注意它。不过昨天有个女人到店里看到这个原子炉吸尘器,问我,那种尺寸的滤净片真的能吸收所有的辐射线吗?锶902 呢?” “我可以给你一份医学证明。”海斯巴契医生说。 “你从来不担心任何事吗?” “我有秘密武器,伍尔摩先生。我对生命充满兴趣。” “我也是,可是……” “你是对人有兴趣,不是生命。人会死去,或是离开我们——很抱歉,我并不是在说你太太。可是如果你对生命有兴趣,它绝不会令你失望。我对人生百态有兴趣。你不爱玩填字游戏,对吧,伍尔摩先生?我喜欢玩,而那种游戏就像人,每一局都有尽头,都有玩完的时候。我可以在一小时内解决任何字谜,但我对人生百态却从未有过定论,虽然我会梦想那一天的来临…… 哪天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实验室。” “我一定去,海斯巴契。” “你应该多做点梦,伍尔摩先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你大可把现实抛诸脑后。”契好心加上一句。 “人一定会生病,但他们不一定会买吸尘器。” “但是你的收费比较高。” “可是我只赚取其中的百分之二十。这样的利润存不了什么钱。” “这不是存钱的年代,伍尔摩先生。” “我必须存钱,为了米莉。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 “反正这年头没有人对人生怀有高度期望,所以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些动乱对生意很不好。如果电力中断,光有吸尘器有什么用?” “我可以帮你弄个小额贷款,伍尔摩先生。”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担心的不是今年或明年,而是长远的未来。” “那根本不值得你担心。伍尔摩先生,我们生活在原子时代,只要那些人按个钮——砰一声,到时哪里还有我们?麻烦再来一杯威士忌。” “那是另一回事。你知道我那家公司干了什么吗?他们给我寄来一个原子炉吸尘器。” “真的?我不知道现代科技已经这么进步了。” “哦,不是,它跟原子扯不上半点关系,光是个名称罢了。去年的噱头是涡轮喷射引擎,今年是这个原子炉吸尘器。其实根本没两样,一样要插电。” “所以有什么好担心的?”海斯巴契医生又说了一遍,像在哼什么主题曲一般,一面啜了口威士忌。 “他们不了解,这类名称在美国或许行得通,这里却不行。这里的牧师动不动就高唱反对滥用科学的论调。上星期日我和米莉到教堂去——你知道她对做弥撒的想法,我知道她认为她能感化我——结果门德斯神父花了半个钟头描述氢弹的作用。他说,那些相信天堂存在于地球的人,创造了一个人间地狱,还说得活灵活现的——这用意太明显了。你想想,星期一早上我就要在橱窗里展示这个新型的原子炉吸尘器,我该作何感想?如果哪个野孩子砸了我的橱窗,我是不会惊讶的。‘天主行为’‘耶稣天主’,到处都是这种东西。海斯巴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卖一个给门德斯神父,在主教的殿堂里用。” “但他很满意那个涡轮。那是台好机器。当然这台也很好,能把书架上的灰尘吸得更干净。你知道的,我从来不卖不好的机器。” “我知道,伍尔摩先生。但你能替它改个名字吗?” “他们不让我这么做。他们以它为荣,认为这是打从‘打败灰尘,清洁溜溜’之后的最佳句子。你知道吗,他们在涡轮那款上放了一种叫作滤净片的零件,那是个挺精巧的设计,只是没人特别注意它。不过昨天有个女人到店里看到这个原子炉吸尘器,问我,那种尺寸的滤净片真的能吸收所有的辐射线吗?锶902 呢?” “我可以给你一份医学证明。”海斯巴契医生说。 “你从来不担心任何事吗?” “我有秘密武器,伍尔摩先生。我对生命充满兴趣。” “我也是,可是……” “你是对人有兴趣,不是生命。人会死去,或是离开我们——很抱歉,我并不是在说你太太。可是如果你对生命有兴趣,它绝不会令你失望。我对人生百态有兴趣。你不爱玩填字游戏,对吧,伍尔摩先生?我喜欢玩,而那种游戏就像人,每一局都有尽头,都有玩完的时候。我可以在一小时内解决任何字谜,但我对人生百态却从未有过定论,虽然我会梦想那一天的来临…… 哪天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实验室。” “我一定去,海斯巴契。” “你应该多做点梦,伍尔摩先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你大可把现实抛诸脑后。”契好心加上一句。 “人一定会生病,但他们不一定会买吸尘器。” “但是你的收费比较高。” “可是我只赚取其中的百分之二十。这样的利润存不了什么钱。” “这不是存钱的年代,伍尔摩先生。” “我必须存钱,为了米莉。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 “反正这年头没有人对人生怀有高度期望,所以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些动乱对生意很不好。如果电力中断,光有吸尘器有什么用?” “我可以帮你弄个小额贷款,伍尔摩先生。”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担心的不是今年或明年,而是长远的未来。” “那根本不值得你担心。伍尔摩先生,我们生活在原子时代,只要那些人按个钮——砰一声,到时哪里还有我们?麻烦再来一杯威士忌。” “那是另一回事。你知道我那家公司干了什么吗?他们给我寄来一个原子炉吸尘器。” “真的?我不知道现代科技已经这么进步了。” “哦,不是,它跟原子扯不上半点关系,光是个名称罢了。去年的噱头是涡轮喷射引擎,今年是这个原子炉吸尘器。其实根本没两样,一样要插电。” “所以有什么好担心的?”海斯巴契医生又说了一遍,像在哼什么主题曲一般,一面啜了口威士忌。 “他们不了解,这类名称在美国或许行得通,这里却不行。这里的牧师动不动就高唱反对滥用科学的论调。上星期日我和米莉到教堂去——你知道她对做弥撒的想法,我知道她认为她能感化我——结果门德斯神父花了半个钟头描述氢弹的作用。他说,那些相信天堂存在于地球的人,创造了一个人间地狱,还说得活灵活现的——这用意太明显了。你想想,星期一早上我就要在橱窗里展示这个新型的原子炉吸尘器,我该作何感想?如果哪个野孩子砸了我的橱窗,我是不会惊讶的。‘天主行为’‘耶稣天主’,到处都是这种东西。海斯巴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卖一个给门德斯神父,在主教的殿堂里用。” “但他很满意那个涡轮。那是台好机器。当然这台也很好,能把书架上的灰尘吸得更干净。你知道的,我从来不卖不好的机器。” “我知道,伍尔摩先生。但你能替它改个名字吗?” “他们不让我这么做。他们以它为荣,认为这是打从‘打败灰尘,清洁溜溜’之后的最佳句子。你知道吗,他们在涡轮那款上放了一种叫作滤净片的零件,那是个挺精巧的设计,只是没人特别注意它。不过昨天有个女人到店里看到这个原子炉吸尘器,问我,那种尺寸的滤净片真的能吸收所有的辐射线吗?锶902 呢?” “我可以给你一份医学证明。”海斯巴契医生说。 “你从来不担心任何事吗?” “我有秘密武器,伍尔摩先生。我对生命充满兴趣。” “我也是,可是……” “你是对人有兴趣,不是生命。人会死去,或是离开我们——很抱歉,我并不是在说你太太。可是如果你对生命有兴趣,它绝不会令你失望。我对人生百态有兴趣。你不爱玩填字游戏,对吧,伍尔摩先生?我喜欢玩,而那种游戏就像人,每一局都有尽头,都有玩完的时候。我可以在一小时内解决任何字谜,但我对人生百态却从未有过定论,虽然我会梦想那一天的来临…… 哪天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实验室。” “我一定去,海斯巴契。” “你应该多做点梦,伍尔摩先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你大可把现实抛诸脑后。”契好心加上一句。 “人一定会生病,但他们不一定会买吸尘器。” “但是你的收费比较高。” “可是我只赚取其中的百分之二十。这样的利润存不了什么钱。” “这不是存钱的年代,伍尔摩先生。” “我必须存钱,为了米莉。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 “反正这年头没有人对人生怀有高度期望,所以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些动乱对生意很不好。如果电力中断,光有吸尘器有什么用?” “我可以帮你弄个小额贷款,伍尔摩先生。”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担心的不是今年或明年,而是长远的未来。” “那根本不值得你担心。伍尔摩先生,我们生活在原子时代,只要那些人按个钮——砰一声,到时哪里还有我们?麻烦再来一杯威士忌。” “那是另一回事。你知道我那家公司干了什么吗?他们给我寄来一个原子炉吸尘器。” “真的?我不知道现代科技已经这么进步了。” “哦,不是,它跟原子扯不上半点关系,光是个名称罢了。去年的噱头是涡轮喷射引擎,今年是这个原子炉吸尘器。其实根本没两样,一样要插电。” “所以有什么好担心的?”海斯巴契医生又说了一遍,像在哼什么主题曲一般,一面啜了口威士忌。 “他们不了解,这类名称在美国或许行得通,这里却不行。这里的牧师动不动就高唱反对滥用科学的论调。上星期日我和米莉到教堂去——你知道她对做弥撒的想法,我知道她认为她能感化我——结果门德斯神父花了半个钟头描述氢弹的作用。他说,那些相信天堂存在于地球的人,创造了一个人间地狱,还说得活灵活现的——这用意太明显了。你想想,星期一早上我就要在橱窗里展示这个新型的原子炉吸尘器,我该作何感想?如果哪个野孩子砸了我的橱窗,我是不会惊讶的。‘天主行为’‘耶稣天主’,到处都是这种东西。海斯巴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卖一个给门德斯神父,在主教的殿堂里用。” “但他很满意那个涡轮。那是台好机器。当然这台也很好,能把书架上的灰尘吸得更干净。你知道的,我从来不卖不好的机器。” “我知道,伍尔摩先生。但你能替它改个名字吗?” “他们不让我这么做。他们以它为荣,认为这是打从‘打败灰尘,清洁溜溜’之后的最佳句子。你知道吗,他们在涡轮那款上放了一种叫作滤净片的零件,那是个挺精巧的设计,只是没人特别注意它。不过昨天有个女人到店里看到这个原子炉吸尘器,问我,那种尺寸的滤净片真的能吸收所有的辐射线吗?锶902 呢?” “我可以给你一份医学证明。”海斯巴契医生说。 “你从来不担心任何事吗?” “我有秘密武器,伍尔摩先生。我对生命充满兴趣。” “我也是,可是……” “你是对人有兴趣,不是生命。人会死去,或是离开我们——很抱歉,我并不是在说你太太。可是如果你对生命有兴趣,它绝不会令你失望。我对人生百态有兴趣。你不爱玩填字游戏,对吧,伍尔摩先生?我喜欢玩,而那种游戏就像人,每一局都有尽头,都有玩完的时候。我可以在一小时内解决任何字谜,但我对人生百态却从未有过定论,虽然我会梦想那一天的来临…… 哪天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实验室。” “我一定去,海斯巴契。” “你应该多做点梦,伍尔摩先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你大可把现实抛诸脑后。” ◆怪不得是马尔克斯的文学偶像! ◆21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传奇大师——格雷厄姆·格林! ◆1950年,初次获得提名,一生提名多达21次,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无冕之王。 ◆一生虽未获奖,却被一众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尔克斯、福克纳、V.S.奈保尔、J.M.库切、威廉·戈尔丁、马里奥·略萨视为精神偶像和导师。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虽然把诺贝尔奖授给了我,但也是间接授给了格林,倘若我不曾读过格林,我不可能写出任何东西。”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拉斯·福塞尔说:“未授予格林文学奖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我们在哈瓦那的人》入选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百大推理小说。 ◆1959年,《我们在哈瓦那的人》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由世界著名导演卡罗尔·里德执导,是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这本书里,格林讲述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小人物的荒诞故事。 ◆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我们只需要忠于自己所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