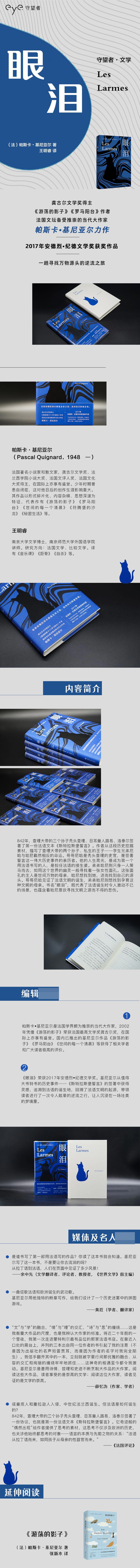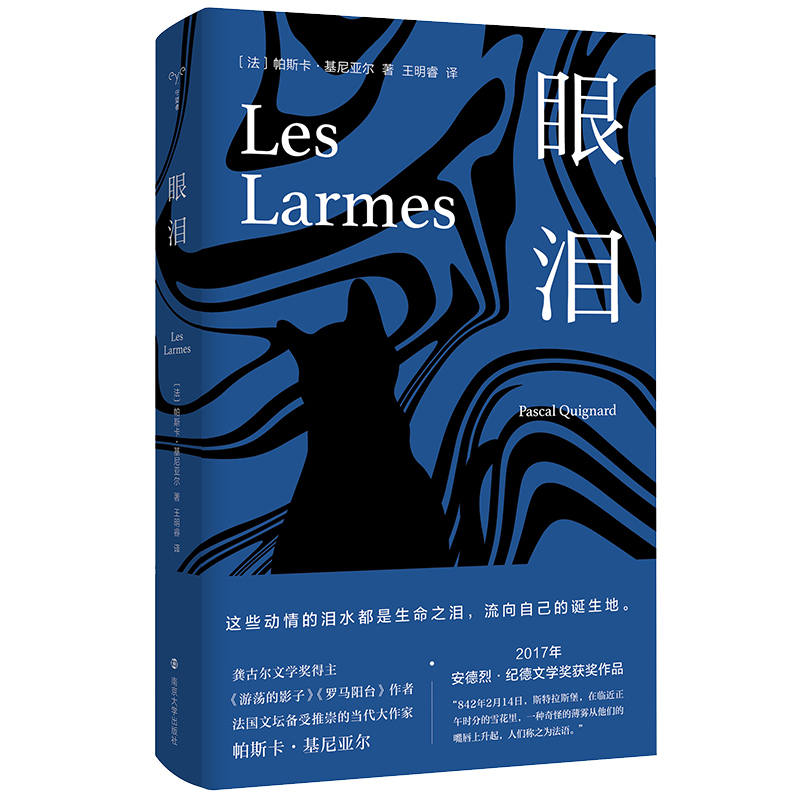
出版社: 南京大学
原售价: 65.00
折扣价: 39.70
折扣购买: 守望者·文学:眼泪
ISBN: 97873052446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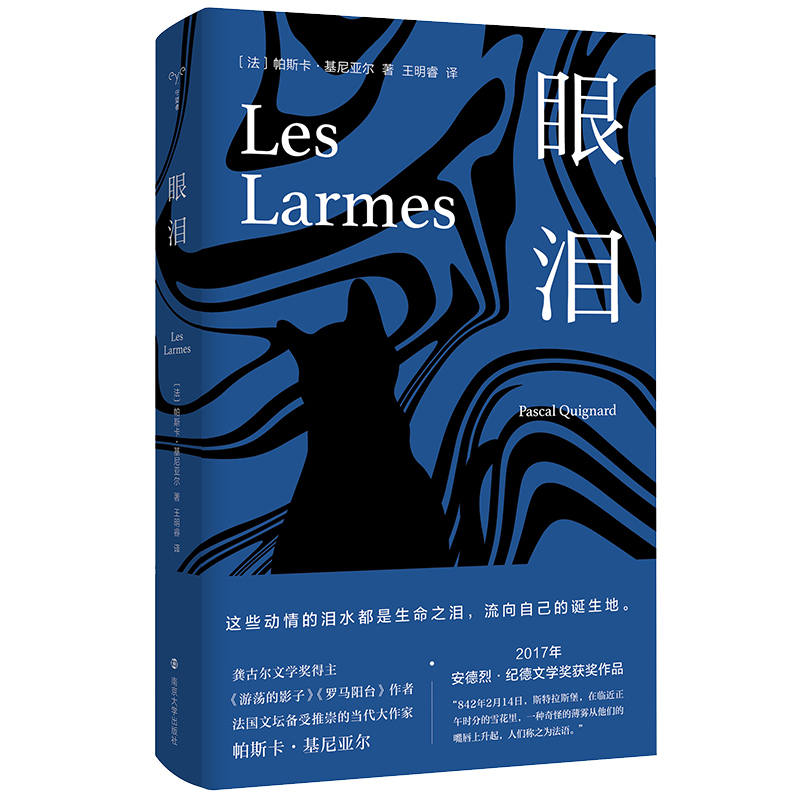
帕斯卡?基尼亚尔(Pascal Quignard,1948 —),法国著名小说家和散文家,龚古尔文学奖、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法国文评人奖、法国文化大奖得主,在国际上亦享有盛誉。少年时期曾患自闭症,这对他日后的创作生涯影响重大。其作品以形式碎片化、内容杂糅、思想深邃为特征,代表作有《游荡的影子》《罗马阳台》《世间的每一个清晨》《符腾堡的沙龙》《秘密生活》等。 译者简介 王明睿,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法国文学、比较文学。译有《音乐课》《距骨》《自杀》等。
Ⅰ(蓝莓男子书) 1. 马的故事 从前,马儿们是自由的。它们驰骋在大地上,没有人想要得到它们、圈住它们,把它们集成队列、给它们套上绳索、给它们设下陷阱、把它们套在战车上,给它们安上马具、装上马鞍、钉上铁蹄,骑上它们、牺牲它们、吃掉它们。有时候,人们和动物一同歌唱。一方的长久呻吟引起另一方的奇异嘶鸣。鸟儿们从天而降,来啄食残食。残食落在马儿的四条腿之间,它们正抖动着自己华美的鬃毛。残食落在人们的大腿之间,他们仰着头,席地而坐,围着篝火,吃得狼吞虎咽,吃得咋咋作响,大快朵颐,突然有节奏地拍起手来。当篝火熄灭,当歌声不再,人们站起身来。因为人们不似马儿一般站着睡觉。他们擦去阴囊和阳器被放在地上时留下的痕迹。他们重又跨上马,骑行在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骑行在大海潮湿的岸边,骑行在低矮的原始森林里,骑行在时常刮风的旷野,骑行在大草原上。一天,一个年轻人创作了这样一首歌:“我来自一个女人的身体,我重又面对着死亡。我的灵魂在夜里于何处消失?它去了哪一个世界?有一张我从未见过的面孔,它困扰着我。为何我又见到了它,这张自己并不认识的面孔?” 他踏马而去,只身一人。 突然,正当他在白昼里奔驰,天黑了。 他俯下身。他惊恐地抚摸着马儿脖子上的鬃毛,还有它温热又颤抖的皮肤。 可天空变得漆黑一片。 骑手拉着缰绳上的铜链。他下了马。他在地上铺开一条毯子,毯子由三张紧紧交织的驯鹿皮制成。他系起毯子的四个角,竭尽全力地保护自己、保护马儿的脸。他们重新上路了。 空气纹丝不动。 忽然,雨水压将过来。 他们缓慢前行,在嘈杂声和雷鸣般的雨水里,用眼睛寻找道路。 他们来到一座山丘。雨停了。黑暗里,有三个男人被绑在树枝上。 中间的,是一个全身赤裸的男人,额头上有一顶带刺的王冠,他在嘶吼。 奇怪的是,另一个男人在用灯芯草的顶端朝他嘴边递去一块鹿蹄。与此同时,在他身旁,一个士兵正将长枪刺进他的心脏。 2. 哈古斯遇上的故事 后来,过了几百年,有一天,夜幕降临,他独自行走,用笼头牵着身后的马儿来到索姆河岸。幽暗开始笼罩河水,他停下了。 男子发现在一堆板岩上有一只死去的松鸦。 离静静的河水约有十米远。 那里有一棵桤木。 那堆松松的、灰灰的岩石板沐浴着夕阳,上面躺着一只松鸦,展开宽大的翅膀,张着嘴。 马儿喷着鼻息。男子抚摸着遮盖了它脊柱的又长又厚的毛发。 哈古斯是这条河的摆渡人,他把船系在大桤木的树干上。他朝困惑的骑手和僵化的马儿走来,待在他们身旁。他把船篙靠着自己的肩,将自己的目光融进他们的目光。 因为这只死去的松鸦身上有些许古怪。 于是哈古斯鼓足勇气,走向那只长有蓝色翅膀的鸟。 可他几乎立刻就定住了,因为松鸦正在有节奏地扇动蓝黑相间的羽毛。他喘着气,向后转了转身子。他的动作是这样的:有时朝向河岸、小船、桤木的叶子与河水,有时朝向蓟草、被自己的所见吓得动弹不得的骑手,以及一动不动、惶惶不安的马儿。 实际上,松鸦在向最后一抹阳光的温热献出自己的彩色羽毛。 它在晒羽毛。 随后,不到一秒钟,它迅速旋转,立起爪子站起身,一下就飞了起来,栖息在河岸摆渡人的船篙顶端。 哈古斯顿时在自己的肩上感到,他该离开这个世界了。 他把头朝鸟儿转过去,它在看着他,发出可怕的叫声,又转向骑手,但是身旁已空无一人。骑手和马儿走了,他没有发现他们已经消失了。 忽然,鸟儿重新展开自己蓝黑相间的翅膀,离开了栖息处——哈古斯靠在肩上的船篙——飞走了。 鸟儿冲进了天空。 渐渐地,哈古斯的性情变得阴郁了。他开始对自己在河边的职责不上心了。他把船扔在灯芯草丛里。他任由倾盆大雨侵袭着小船。两个季度后,妻儿厌倦了他的忧伤,焦躁不安地与他交谈一番后,带上行李,走了。哈古斯不再需要家人陪伴,于是也离开了亲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不再和人类说话。他避开刺眼的光线。一切可见的事物都让他害怕。即便是动物的脸,他也会逃避,因为他觉得这些脸在谴责自己。他左躲右闪,不想碰上黄嘴老鹰的眼神,不想遇见燥热之夜在荒野上企图用歌声吸引自己的青蛙的眼睛。 3. 八音盒 从前有个略显罗圈腿的男子,他背着一只带有小格子的木盒。他行走在各个村落里。他把盒子放在一块石头上,或是一棵树的树桩上,或是一只箱子上,或是一条长凳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盖子。人们看到了十二个洞。每个洞里都有一只青蛙。晚上,他抬起头,呼喊着凡?西苏,像是一个有脚疾的男子在向天空发出祈祷。“说话吧,凡?西苏!”他叫喊道。又让旁边的一个孩子拿来一只水壶,往每只脑袋上浇水。它们唱歌了。 孩子们和各色人等从田野和林间小路聚集而来,围着他,一个个紧紧地挨着他,想看看盒子里究竟有什么。“如果你们保持安静,”他对他们说,“你们就会听到一种隐约的钟声。” 于是,就连孩子们也不说话了。人们听着缓慢升起的歌声,眼睛湿润了,因为每个人都认识另一个世界里的某个人。有人低声喊着“妈妈!”,心里已双膝跪下、瘫倒在地。他们低低地说着:“妈妈!妈妈!” 4. 尼哈出世 从前,尼哈出生的那天,安吉尔伯特伯爵——孩子的父亲,也是索姆湾献给圣人里基耶的那座修道院的院长——在孩子从贝尔特肚子里滑溜溜地出来后抱着他说:“你第一次抬起眼皮,你褶皱的皮肤如此脆弱,你在光亮中睁开两只湿漉漉的大眼睛,我以父、以子、以灵的名义祝福你。”此时一声新的啼哭响起。在贝尔特的肚子里有一个孪生兄弟:人们能看到黄色的额头在顶着腹部内壁,已经出现在贝尔特发紫的宽大阴唇之间,就在那片金色体毛下面,它们遮住了她一直紧绷到肚脐、快要撕裂的皮肤。安吉尔伯特院长伯爵想抓住他。可这个新生儿浑身湿漉漉的。黏糊糊的小身体四处乱扭,像一条鳗鱼在手里滑动。院长喊道:“你的感觉开始在自然中四下寻找抓手,你张开细小的手指,如此顽强而炽热地紧紧抓住我的大手,我这个在若干季节之前将你孕育的人,现在为你祝福。这张面孔与尼哈相像得连影子都远远不及:他几乎像是倒影一样反射着尼哈!在这张面孔里,尼哈再次降生,这是上帝传达给我们的信号。上帝想让尼哈的日子里有一个同伴,就像他自己有约翰睡在肩膀上!” 说完这些后,他进行了第二次洗礼,给婴儿起名为哈尼。 5. 尼哈的受孕 从前,在尼哈出生前的九个月,一天下午,他们躲开他人的视线,藏在黄白相间的忍冬和蓝色的大片藤萝后面,那位叫贝尔特或贝尔塔的皇帝之女,拉着安吉尔伯特伯爵的手,对他说: “来吧。” 她又说道: “来吧。我深爱着你。” 她拎起长裙。他进入她的身体。 她享受着。 他自己在那儿体验到莫大的快感,又深深地进去了一次。 她享受着。 这发生在尼哈和哈尼出生之前。萨尔是索姆湾的萨满,她在那时即兴创作了这样一首诗: “因为,若说鸟儿们爱唱,它们也爱听这歌。 它们爱听白垩峭壁下汹涌澎湃的北海,它们在海浪面前逐渐沉默不语,海浪涌起,又在沙滩上跌碎,滚压着沙滩,垂直的白色岩壁在这侵蚀下化作了沙子。 能吸引鸟儿的,只有港湾沿岸池塘死水里芦苇的窸窸窣窣。 它们向海边牧场和芦苇丛走去,走进深处。它们发出吱吱的叫声,为风在自己身上吹动的歌唱伴唱,以此为乐。” “就是说,”萨尔说道,“雨啊, 当它落到森林的树叶上, 便让鸟儿的嘴惶恐不安,以此报复。 雨水减慢了它们的变奏,降低了它们放声长鸣的音高。 有时,暴雨和阵雨打断了它们。 啁啾声被哗啦声和轰鸣声彻底取代。” 所有鸟儿都会回应——当它们终于不再作声,即便是这出人意料的安静也是在回应。 所有鸟儿都会因地制宜地转调,场景为它们的奇怪指令组织的动作和特殊共鸣提供伴奏。 当场地置于薄雾,几乎没有琶音会叮当作响。 任何有节奏的连续呼唤在屋顶下都不会响起两次。 在鸟儿的世界里,低音比高音传播得更远——就像我们世界里的痛苦。 慢节奏比快节奏更易辨认。 我,萨尔,我会说: “鸟儿的示意比你们感受到的忧愁更柔更软。 对我的耳朵来说,它们比人类吐字清晰的语言更容易读懂,只要这些人着了魔、在打转,却不知在承受苦难时该如何面对它,我就会帮助他们。” 6. 恋爱中的哈尼 一天,福音传教士马太在《马太福音》第13章第1句中写道:“In illo die, Iesu, exiens de domo, sedebat secus mare.”(一天,耶稣走出屋子,坐在海边。)一天,哈尼走出屋子,坐在海边。突然起了风,卷起了沙子。他十三岁。有条船停在那儿。他登上船。他升起桅杆上的船帆。他朝着西边径直而去,又转向北方,松开了船舵。他睡着了。于是他航行了许久。他跨过了大海。他在阿克洛登上岸。在阿克洛港湾,哈尼遇见了一位住在岩石下的圣人。 哈尼在沙子上画下一副面孔,向圣人问道: “您认识这张脸吗?” 但隐士回答他说: “我不认张脸。为什么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我都不认识你、不认识你的身体、不认识你的脸,我只是刚才在石头小屋门口看见你在停船,看见你借着一根绳子从小艇上下来,摇摇晃晃,把小船拖到海盐泥浆里和岸上破贝壳的碎片上。” “因为我在找那个长着这张脸的女人。这就是我旅行的目的。对我来说,我自己的脸并不重要。因为当我出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的脸早就在这个世界里存在了。” 813年,贝尔塔(贝尔特,哈尼的母亲)公主在她父亲位于埃克斯拉夏贝尔的新宫殿里说: “我觉得他的头脑变得空洞洞的。当毛发沿着他的大腿生长、占领他的脸颊,爱情就令他心神不宁。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在哪里产生了幻象,可我知道有一个不属于他的身体登上了他的大脑。至少,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个形象爬上了他的头脑,紧紧攥着它。当黎明到来,当他从床上起身,这形象也没有消退。从这时起,他再也不愿看见自己的兄弟。这个形象变成一种狂热,强烈到他再也听不见人们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他想找回这张脸。只要面对着我的儿子,看到他现在的模样,没有人不会为之震惊。他在爱着某个人。” 在双胞胎中较小的、名叫尼哈的孩子面前,贝尔特正是这样评价了儿子的出走。因为,在双胞胎中,最早孕育的是最后出来的。哈尼,作为尼哈的另一种写法,由安吉尔伯特孕育、命名,由贝尔特怀孕、哺育,他就这样离开了海滨弗朗西。 本书是龚古尔文学奖得主、《游荡的影子》《罗马阳台》作者、法国文坛备受推崇的当代大作帕斯卡?基尼亚尔力作,荣获2017年安德烈?纪德文学奖。在这部形式新颖独特的小说中,基尼亚尔不仅讲述了法语语言的发端,更是回溯了一个文明的起源。作者在其中穿插了各类叙事、传奇和逸事,让读者和他一道进行了一次令人眩晕的逆流之行,追溯到法语的诞生地,甚至追溯到没有语言的世界,让人沉浸在一场壮美的梦境里。 帕斯卡?基尼亚尔是法国学界颇为推崇的当代大作家,2002年凭借《游荡的影子》荣获法国z高文学奖龚古尔奖,在国际上亦享有盛誉。国内已推出的基尼亚尔作品《游荡的影子》《罗马阳台》《世间的每一个清晨》等获得了相关学者和广大读者极高的评价。 《眼泪》荣获2017年安德烈?纪德文学奖。基尼亚尔从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斯特拉斯堡誓言》的签署中获得灵感,追溯到法语的诞生地,回溯了法语文明的起源,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令人眩晕的逆流之行,让人沉浸在一场壮美的梦境里。 《世界文学》前主编余中先、翻译家黄荭、作家薛忆沩联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