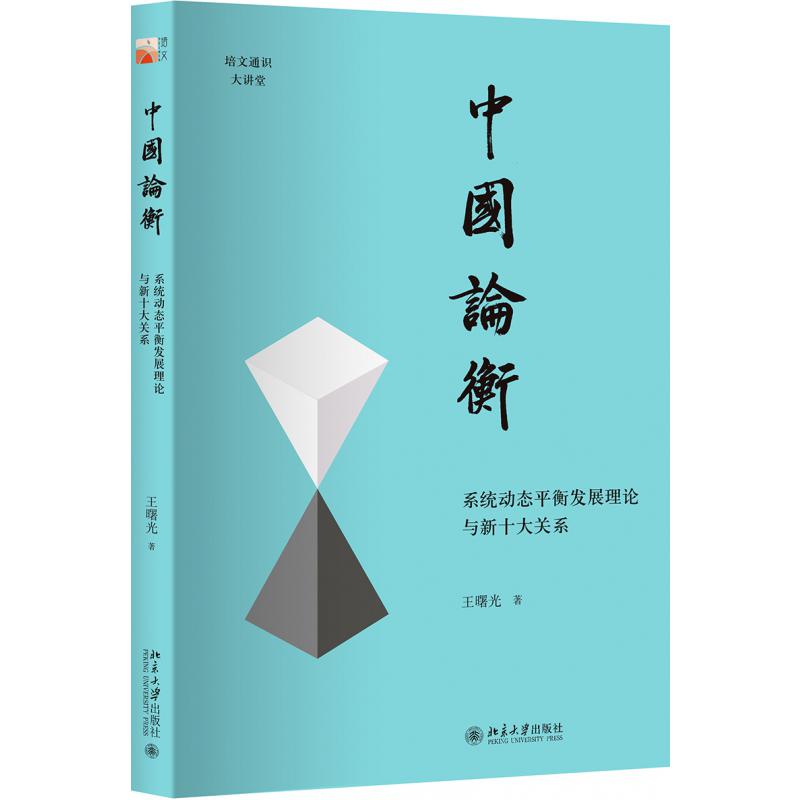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大学
原售价: 49.00
折扣价: 31.90
折扣购买: 中国论衡(系统动态平衡发展理论与新十大关系培文通识大讲堂)
ISBN: 9787301295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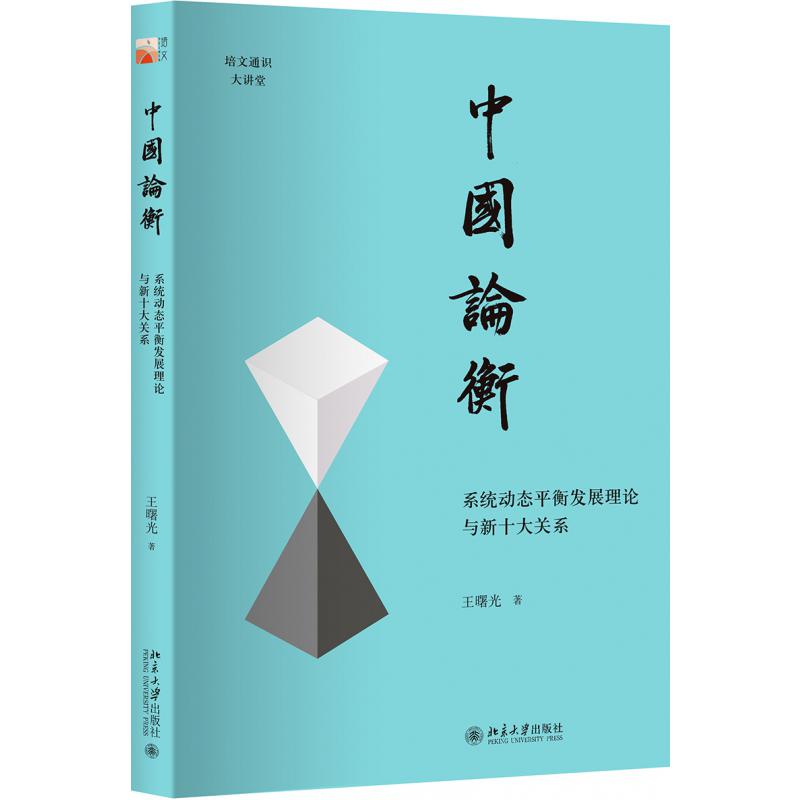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先后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王曙光教授是我国农村金融学科和金融伦理学科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已出版经济学著作《中国农村》《中国方略》《问道乡野》《农行之道》《告别贫困》《金融减贫》《金融伦理学》《农村金融学》等二十余部,发表经济学论文百余篇,并出版散文从集“燕园四记”和《明尼苏达书简》等。
"**章 论新十大关系 新中国在近70年的发展进程中,总体的表现是**优异的,无论是从**比较的横向的视角,还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的维度,新中国的经济发展都可称之为人类历**的奇迹,可以视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个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节点。在这个节点上,新中国以无比的勇气,在经济发展体制方面做出了很多创造性的制度安排,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而赢得整个民族命运的转机。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重新回到大国经济角逐的核心,而且逐步赢得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在不远的将来重新回到康乾时代中国的位置,即经济总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强,且人均收入居于世界的前列。这个愿景,现在看来是**真实的,而不是一个虚幻的目标。 在经济追赶和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当然中国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这条道路在整体上看是成功的,但即便如此,随着历史的变迁和中国经济地位以及经济形态的变化,这套发展模式也有着不断修正和不断创新的必要。而且*为严重的是,如果不对我们以前的发展模式做出**的深刻的反思,我们就不可能实现这种增长的可持续,甚至会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严重后果。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和历史**漫长的大国,任何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实施都应该经过仔细的权衡,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需要极其慎重的考虑和极其高超的平衡术。 而中国在近70年的经济发展中,尤其在近40年来,“非均衡”成为一种典型的特征。这个不均衡,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有其制度和文化背景,是历史地形成的,不是可以轻易地改变的。非均衡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体制特征,当然也是一个文化特征。从**的意义来讲,任何经济体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均衡的,经济总是在非均衡中寻找平衡,总是在非均衡的状态中实现发展。因此,我们所追求的,就必然不是一个静态的平衡的状态,而这种理想的静态的均衡也永远不会实现;我们所追求的,乃是一种动态的均衡,是在不均衡中逐步趋于均衡的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从经济发展的机制层面来说,某些不均衡的存在也是必要的,不均衡才能激发活力,激发创新,创造各种机会,使得经济社会超常规发展;就如同钟摆的摆动,如果左右力量**均衡了,钟摆就不摆动了,也就失去了活力。但是钟摆也不可处于一种过度的不均衡中,它的不均衡要保持一个度,否则就难以维系其安全性和正常的运作。经济的道理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客观看待非均衡,不要对经济发展中的非均衡一概以一种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视之,这是不客观的。但是也不要听任这种非均衡发展下去,不要使这种非均衡影响整个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也就是说,适度的非均衡是必要的和必然的,而过度的非均衡则是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应该加以矫正。这是我们**谈十大关系的根本方法论前提,这个思维方法贯穿始终。 **中国的发展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体制机制的问题已经系统性地表现出来。因此,我们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也要有系统性的变革,不能只是修修补补、敷衍了事,以致拖延了时间,丧失了变革的时机。 **讲十个方面:一、**和市场的关系;二、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三、速度和质量的关系;四、国企和民企的关系;五、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六、东部和西部的关系;七、富裕和贫困的关系;八、**战略和**战略的关系;九、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十、城市和农村的关系。 一、**与市场的关系 *近学术界出现了几次激烈的学术争论,我认为所有争议的核心实际上围绕着一个焦点,就是**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在经济史中,从近一百多年的历史维度来看,实际上崇尚市场作用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崇尚**作用的**干预主义这两种思潮,总是交替出现,互相消长,没有一种力量会**地在任何时间起**作用;总是一段时间**干预主义起**作用,占据主流地位,而另一段时间则经济自由主义起**作用,占据主流地位;而且这个特点在近百年以来特别突出,世界各个**都是如此。从**各个经济体的发展进程来看,各个**在**和市场关系中也出现了这种交替的现象,美国如此,欧洲如此,*本如此,俄罗斯也是如此。当代世界经济往往把市场和**的力量融合在一起。 所以,凡是那种**地认为**干预主义或者经济自由主义是不可怀疑的正确观点的说法,都是违背经济史真实规律的,都是教条主义的,不符合辩证的动态的观点。**和市场,无外乎是经济发展的两种不同的推动力量和要素,一种力量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过度了,就必然引发经济发展中各个层面的问题,从而逼迫经济体制必须发生变革,以纠正这种过度的不均衡的情况。比如说,在一个阶段,**发挥的作用太多了,抑制了市场的作用,从而导致体制不灵活,人民的福利下降,经济增长的效率*到损失,因此就必须加强市场的调节,削弱**的作用,矫正**过度介入的情况,克服**的一些弊端。同样地,如果一个阶段任由市场力量过度发挥作用,市场的自发作用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极其不均衡,出现了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导致垄断、贫富不均、公共品供给不足、社会混乱、**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突出,则应该进一步发挥**的作用,加大社会公共品支出,防止垄断和社会不公,对市场力量进行矫正和监督。一个良性发展的经济,总是在**和市场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和市场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作用,不缺位,也不越位。 当然,“把市场当作市场,把**当作**”,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所以经济体制的调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跟市场的关系问题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些学者提出,一个良好运作的经济体制是“有为**加有效市场”,但是这个概括歧义很大。什么叫“有为的**”?中国**对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极其深入的介入,难道还不够有为吗?应该是**有为了,但问题是这个“有为”怎么解释。有为“应该”是有所作为,不是乱为,*不是不为。“有为”这个词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并不是乱为的概念,并不是盲目瞎搞的概念,“有为”一般指的是正当且必要的作为,这叫“有为”。当然我觉得还不仅如此,因为在中国的语境里面,恐怕“有为”不仅是正确的作为,不仅是不乱为,而且意味着**有主动性,其潜台词是**要主动做事,主动介入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中。**要有所作为,而且主动地、积极地有所作为。但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有为”**的界限就不容易厘清,**的力量就容易发生偏差,就容易出现不当的介入。而且,在中国的历史中,官府(现在叫**)本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天然具有**市场的**性,它的自由裁量权常常不*限制,因此提“有为**”往往会引发决策层面和*作层面的很多扭曲,导致**权力过大,跨越了“有为**”本身应该具有的含义界限。 有为**是不是就不顾市场呢?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做法都是这样的:**很有为,地方**和中央**总是积极作为,但是对于市场的运作机制不够尊重(当然并非主观上如此),也不够熟悉,因此很多**干预往往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而收到消极的后果。这个问题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已经遇到了。***那时候已经意识到,在***计划经济的实施过程中,不能忽视市场的力量,应该客观看待***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在执行计划经济的过程当中,还必须尊重价值规律,尊重交换规律,你不尊重价值规律的话,计划经济所赖以实施的很多交换关系如何体现呢,全部的计划是难以达到一个供求均衡的状态的。所以在计划经济执行的过程中,那个年代的***已经意识到不可能**排斥市场的作用,不能不顾市场甚至**取消市场。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后来又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直到十四大即1992年才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十八大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好发挥**作用”,这个说法具有原则性,也很巧妙,尤其是 “*好”这两个字,值得好好思考,仔细研究。 《中国论衡:系统动态平衡发展理论与新十大关系》从“系统动态平衡理论”出发,深入探讨影响中国未来大趋向的“新十大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协调平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