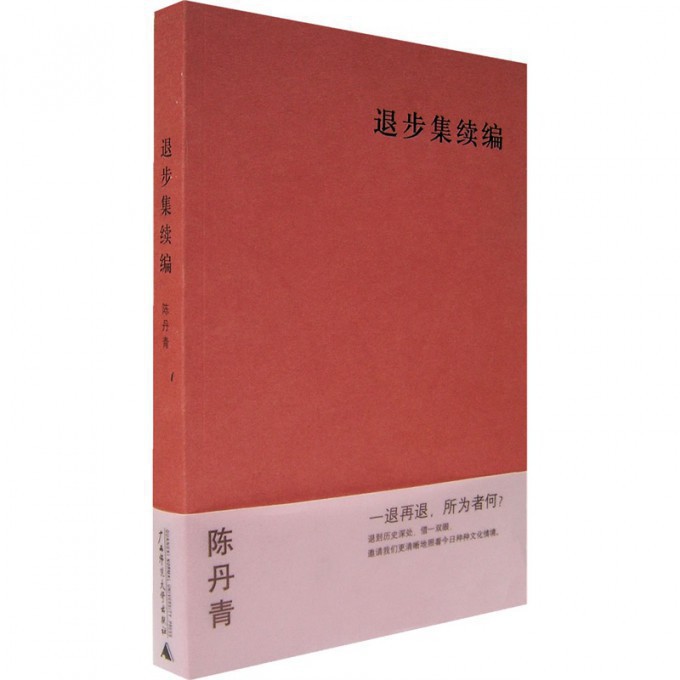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36.00
折扣价: 22.40
折扣购买: 退步集续编
ISBN: 9787563365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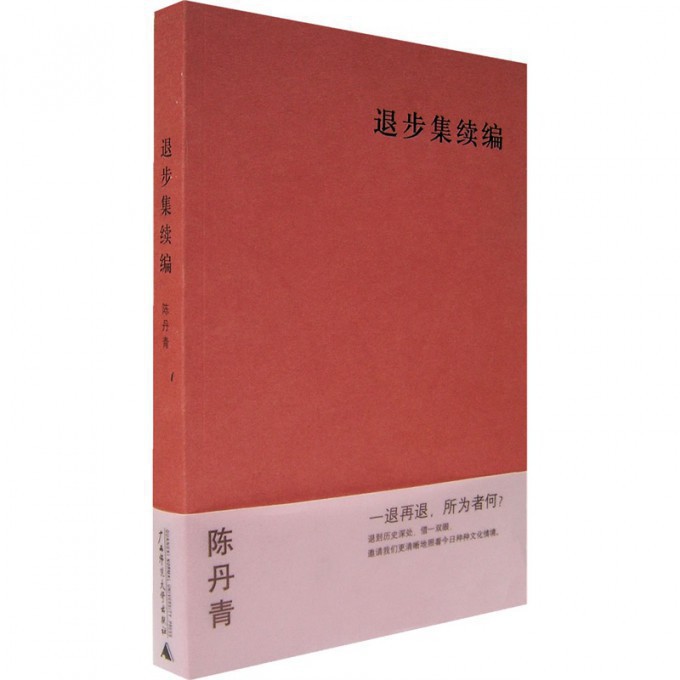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著名油画家、作家,是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批评者之一。 2000年回国,任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07年卸去教职。其间,因辞职事件及公开批评教育现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成为舆论一时焦点,更被媒体推崇为影响中国的五十位知识分子之一。除了教育,他对城市、影像、传媒等文化领域的诸多现象亦有独到见解和批评。著有《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外国音乐在外国》等。
鲁迅是谁? 写在鲁迅逝世七十周年 2006年10月14日在上海图书馆讲演 大家好: 这是我第三次谈论鲁迅先生了。每次都是又恭敬,又有点紧张。昨天特 地剃了头,换双新皮鞋。我不会当场讲演,讲到鲁迅的话题,尤其郑重,总 要事先写点稿子才能自以为讲得清楚一些。下面我按着稿子念,再作些发挥 ,请诸位原谅。 一 鲁迅先生的纪念会,七十年来不知开过多少次了。在中国,鲁迅至今是 个大话题。 粗略说来,从鲁迅逝世的1936年到1949年,鲁迅话题为民族革命问题所 缠绕;从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鲁迅话题则成为准官方意识形态,在大陆无 人敢于冒犯,在台湾被长期封杀。总之,“鲁迅话题”是百分之百的“政治 话题”。 八十年代中期,鲁迅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祭坛,挪进学术领域;九十年 代迄今,官方对鲁迅话题开始了沉默、回避、冷淡的戏剧性过程。二十多年 来,举凡重要的国家话题和政府语言,不再能够,也不再打算从鲁迅那里搜 寻任何说法,鲁迅话题的庞大利用价值似乎走到尽头,由“在朝”转向“在 野”,随即在学界与民间展开“鲁迅争议”,王朔,是这场争议的发难者。 到了新世纪,“鲁迅争议”衍生了“还原鲁迅”的愿望。就我所知,不 论是鲁迅的“捍卫派”还是“质疑者”,近十余年出版的鲁迅专著大幅度抛 弃官方意识形态尺度,试图描述真实的鲁迅。旧史料出现新的解读,一些新 的史料披露了。其中,最可注意的声音来自鲁迅后代:先有2002年周海婴回 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后有2006年海婴先生大公子周令飞同志在交通大 学的一场讲演,这位鲁迅的长孙直截了当问道:“鲁迅是谁?”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最为激烈而讽刺的发问。这一问,宣告七十 年来我们被告知的那位鲁迅先生,面目全非。 二 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几十年来,中国历史远远近近的大人物几乎都被弄 得面目全非。而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从五十年“政治 话题”到近二十年的“鲁迅争议”,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今天,鲁迅的读 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还原”。 鲁迅先生的寿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鲁迅著作 是一份遗产,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是另一份遗产。鲁迅的幽灵、鲁迅的读者 ,七十年来始终在两个鲁迅、两份遗产之间游荡。这是鲁迅公案的一面。另 一面,我们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歌德、黑格尔、托尔斯 泰、尼采、马克思……都是巨大的历史公案、文化公案,他们在身后被不断 解读、塑造、发掘、延伸。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但不属于政权;他 们对文化与政治产生深远影响,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他们的主张阶段性 过时了,因为后人接续了他们的文脉;他们历久常新,因为他们早经熔铸为 文化之链与历史坐标。 鲁迅身后的命运正相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但始终抵押在政权 手里;他对现实政治其实毫无影响,却沦为政治符号;他被悬置,但难以过 时,因为他身后既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等量齐观的人物;因此他历久长 在,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响,而是最高规格的孤立状态;他的全集一版再 版,但与当今文化难以建立活的关系——相比被封杀、被遗忘,鲁迅身后的 命运与处境更其诡谲,更其悲哀。 七十年来,鲁迅墓前曾有无数革命者或权势者的鲜花,近二十年,煞有 介事也罢,发乎内心也好,官方与民间不再主动拜祭。鲁迅清静了,不再被 利用,也不再被供奉。这种暧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热的“鲁迅政治” 一样,都是反常与变态,是历史的冻结。目前这份已告冷却的鲁迅遗产,仍 然是官方撤除之后的官方遗产。 九十多年前,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 :“救救鲁迅!” 三 鲁迅身后的所有话题,是鲁迅先生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是鲁迅 的问题,他的遗作俱在,要争议就争议,不愿读就不去读,无所谓还原不还 原;如果这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还原鲁迅?怎样还原?有没 有可能还原? 我想来想去,答案是:一,问题出在我们;二,鲁迅很难还原。三,要 还原鲁迅和无数历史人物,有待于“我们”发生根本的变化;四,不论是良 性的、恶性的、还是中性的,不论与鲁迅有关系还是没关系,这种变化的过 程会很长——可能需要另一个七十年——但眼下这变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鲁迅,不是还原,而是“我们”的变化。 以下试着扼要谈论鲁迅为什么难以还原,为什么这“难以还原”是我们 的问题。最近,香港凤凰台就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来访,给我一组关于鲁迅的 质疑。有的早就听过,有的闻所未闻。记忆所及,仅举如下数端: 一、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 承?三、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人们在“文革”中互相攻击斗争的恶习? 四、怎么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五、鲁迅的名句:“我向来不惮 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是否助长了中国人的恶? 在半小时访答中,我无能展开谈论,现在顺着问题想下去,我清清楚楚 看见,问题在我们,在那份鲁迅政治的遗产。 其一,鲁迅可以商榷吗?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 问题——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商榷”,理应“商榷”,但我不用“商榷 ”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当“商榷” 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杀批评,禁止怀疑的年代。 其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我的回答是:假如鲁迅 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 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 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 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其三,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 ?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别的国家、别的时代 ,文学家思想家怎样骂人——我不认为这是骂人,反而指为骂人者,真是一 种骂。但既是谁都用这个词,姑且从众吧——太远的例子不去说,仅看比鲁 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问福楼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 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托尔斯泰一辈子骂人,谁都骂, 骂皇帝和教主,骂莎士比亚和尼采,骂前辈赫尔岑,骂老朋友屠格涅夫,当 然,也骂他自己;尼采的咒骂则指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说,天下只有一位 基督徒,那就是耶稣,而“耶稣教”是两千年来欧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国 ,应该为温柔敦厚的良人们编一册世界文豪骂人史,虽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 家发生过“文革”,那样人整人。 这种人整人的恶习、模式、话语方式,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内部已经发难 ,成为五四百家争鸣的异化。八十年代出版了鲁迅论敌骂鲁迅的大部头史料 ,九十年代有一部书叫做《鲁迅:最被污蔑的人》,历历举证鲁迅被谩骂被 围攻的史实。这里仅举一例,即在新中国文艺牌坊中仅次于鲁迅的郭沫若同 志,即曾公然宣判鲁迅为“双重的封建余孽”。当郭同志出口定罪前,他自 称几乎不读鲁迅的书。 其四,怎样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是的,我们这代人都是“ 无产阶级专政”的子民。但不要弄错:从六七十年代的《红旗》杂志或《人 民日报》通栏标题读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和二三十年代在秘密书刊 以及文人写作中读到同一句话,是两种读法,两种后果,两回事。是的,鲁 迅曾是左翼阵营的大将——在他的时代,世界范围激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十 之七八选择左翼立场,譬如法国人文人阿拉贡、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意大利 导演帕索里尼、彼德鲁齐等等,不仅左倾,而且是准共产党员——当“双重 封建余孽”鲁迅先生晚期靠拢左翼,摹写“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不是出 于政治信仰,而是再三目击“无产阶级”青年肝脑涂地,被枪毙。但及早道 破左翼内部的虚伪、狡诈、霸道、浅薄,同样也是鲁迅。为什么呢? 因为其五,鲁迅“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这句话居然 “助长了中国人的恶”,且不说此话通不通,这是什么逻辑?莫非此后至今 遍中国滔滔不绝的恶人们在作恶之前,都曾请教过鲁迅的著作么——恶意, 分两种,一种是自知其恶,一种竟出于所谓“善意”,若是今天还有中国人 以这样的“善意”去责难鲁迅,这善意,在我看来就是十足的恶意。 不过以上的问,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笔现代中国是非观的糊涂账 ,是不值一谈的常识问题。可资翔实对照的是鲁迅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差异, 这差异,才是还原鲁迅真正的难处。 四 以下粗略排列一组时代背景、社会指标与文化形态,借以提醒我们为什 么难以还原鲁迅。 鲁迅青少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中山革命集团, 有无数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鲁迅壮年时期,北方是军阀政府,南方 是国民政府,江西是苏维埃政府;而军阀在各省据有势力,国民政府曾分为 宁汉政府,许多省份还设有苏维埃地下政府。到了鲁迅的中期与晚期,中国 粗粗统一,但仍有南京政府与延安政府,抗战时期还有南京伪政府与重庆国 民政府;而在鲁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与法租界。 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学界有前清遗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 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这些海龟派与今日的海龟派不可同日而 语,各有真正的学派、主张和势力。政治流派,则先后出现过君主立宪派、 共和派、保皇派、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 、民族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在座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巴金”的笔名 ,就是取两位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中文译名: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他比鲁 迅谈论“无产阶级专政”还激进,居然公开顶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名,活了一 百多岁——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挡节目还公布了史料:虽然昙花一现 ,形同儿戏,但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的政党出现过上百个。 鲁迅的同学、战友、论敌,有的是国民党要人,如蔡元培和陈仪;有的 是共产党要人,如陈独秀与瞿秋白;有的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如郭 沫若与田汉;有的既是学者教授又是党国重臣,如胡适之;当然,自也有许 多无党无派的文人。教科书总是凸显鲁迅年轻朋友中的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 ,察看鲁迅通信的朋友,却有国民党军人如他格外溺爱的李秉中;有鲁迅为 之谋职,解放后被镇压的国民政府县官如荆有驎;也有先左后右的青年,如 选择台湾的台静农。鲁迅与好几位左翼小青年从亲昵到绝交,但与国民党军 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闹翻的记载。鲁迅的外国友人,则有俄国没落诗 人爱罗先珂,有美国左翼小子史沫莱特与斯诺,而内山完造与增田涉等等日 本友人,非左非右,并没有政治色彩。 说到鲁迅与他同代人的交友范围,今天即便人脉最广,身份最特殊的角 色,也不可能与社会身份杂异、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人群维持朋友关系或彼 此为敌的关系。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朋友等同朋党,胡风集团、二流堂 圈子,均曾获罪,关押自杀多人,株连千百。政治集团的类似案例更是不可 胜数。八十年代迄今,则朋友关系大致是权利关系,或以升官,或以发财。 相对纯粹的私人友谊勉强恢复常态,然而众人的出身、职业、观点或有差异 ,但我们全是国家的人,教育背景和整体人格,都是一样的。 总之,鲁迅与他同代人的政治与文化版图,鲁迅与他敌友置身其间的言 行空间,以我们这几代人同出于一个模子的生存经验,绝对不可能想象,不 可能亲历,不可能分享鲁迅那代人具体而微的日常经验——当然,我们几代 人共享齐天洪福,免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免于乱世之苦,其代价,是我们对 相对纷杂的社会形态,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迹近生 理上的无知。 至于鲁迅的言论与思想,再早、再晚,都出不来。他的时代,是中国现 代史国家祸乱与历史机会最为密集的世代,也是春秋以来唯一一次短暂的“ 百家争鸣”时代。倘若他被认为高于其他人,因为有其他人;倘若其他人不 认同他,便说明那是群雄并起的年代。他身后被高悬、孤立,使我们只能仰 望他一个。近二十年,那个时代与他对立的学说大约出齐了,然而最初的阅 读形同烙印:我们读鲁迅在先,读其他人在后,听他骂人在先,得知骂他的 文章在后。这种先后差异,不可低估。 但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们几代人早已被塑造为另一群物种。 我们的思维模式、话语习惯、价值判断及无数生存细节,几乎无法与鲁迅及 他的同代人衔接对应。我们的困难不是不认识鲁迅,而是不认识我们自己。 要还原鲁迅,恐怕先得借助鲁迅的生存经验,做一番自我还原。 譬如,鲁迅在中国数度迁移,但不必到派出所申办户口或暂住证;他与 好几所大学有受聘解聘的关系,但从来没有一份人事档案尾随其后;他有身 居高官的老朋友,但从未受制于任何单位领导;他被特务监视,但弄堂隔壁 没有居民委员会;他的文章常被封杀禁止,但从未写过一纸思想汇报与书面 检讨;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伤,但并非出于卑怯的检举揭发;他被不同阵营 污蔑围攻,但从未被国民政府“打倒”并发动全国性批判;他活在战祸频仍 的时代,但从未领教过举国民众的武斗;他擅逃亡,但不是为了逃避隔离审 查、监督劳动或遣送下乡;他活画出旧文人孔乙己的凄惨末路,但对学者教 授沦为囚犯或贱人的经历毫无感知;他为我们留下永恒的阿Q,但绝不会料 到到阿Q同志后来可能当上役使乡民的村长,甚至县长;他私通乱党,名列 通缉,但从未被戴上一顶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 被平反的狂喜与委屈;许多人讥嘲他是位“绍兴师爷”,可他从未经手一件 我们时代哪怕最卑微的“冤假错案”;兄弟失和诚然是他最难释怀的内伤, 此外,要论无可申说的个人委屈和无妄之灾,他身后的大小文人都比他阅历 深厚;晚期,鲁迅主动阅读马克思学说,但从未被命令以唯物主义检讨、修 改以至公开否定自己的著作;不消说,他从未申请入党,从未听说全国文联 与作家协会,从未被阻止或恩准阅读“内部文件”,从未由于行政级别分到 或分不到一间住房,从未接受过哪位人事处科员的威胁或奉承;他的葬礼与 为他抬棺的巴金同志的葬礼完全不同,不是国家操办;他被覆盖“民族魂” 大旗的殊荣不是根据国务院或中宣部的指令;当国母宋庆龄与国师蔡元培以 私人身份出席他葬礼时,伙同沈君儒章乃器等第三势力,而葬礼的秘密策划 与公开策动,是当时的青年乱党如冯雪峰与大批左翼青年。这些人的政治身 份与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却堂而皇之站在鲁迅的灵柩旁轮番演说,慷慨激昂 ,公然咒骂政府的无能与不抵抗。 对不起,还有:鲁迅生前从未见过粮票和布票。 P267-276
责编陈凌云说:“读《退步集》时,能感觉到陈丹青的一腔热忱,文风犀利老辣轻快,是一个提问者的姿态。但到了《退步集续编》,他不仅提问而且试着回答,尤其是对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有些篇章显出用力过猛,这可能源自他逐步对国内现世的了解。另一个感觉是陈丹青缺少对话者。”
与《退步集》相比,本书话题有所调整:教育、城市的议论相对减少,人文与艺术的剖析,相对增加。回顾往事,作者向历史借一双眼,试图更为清晰地描述当今文化的种种情境,于是谈鲁迅、谈文艺复兴、谈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