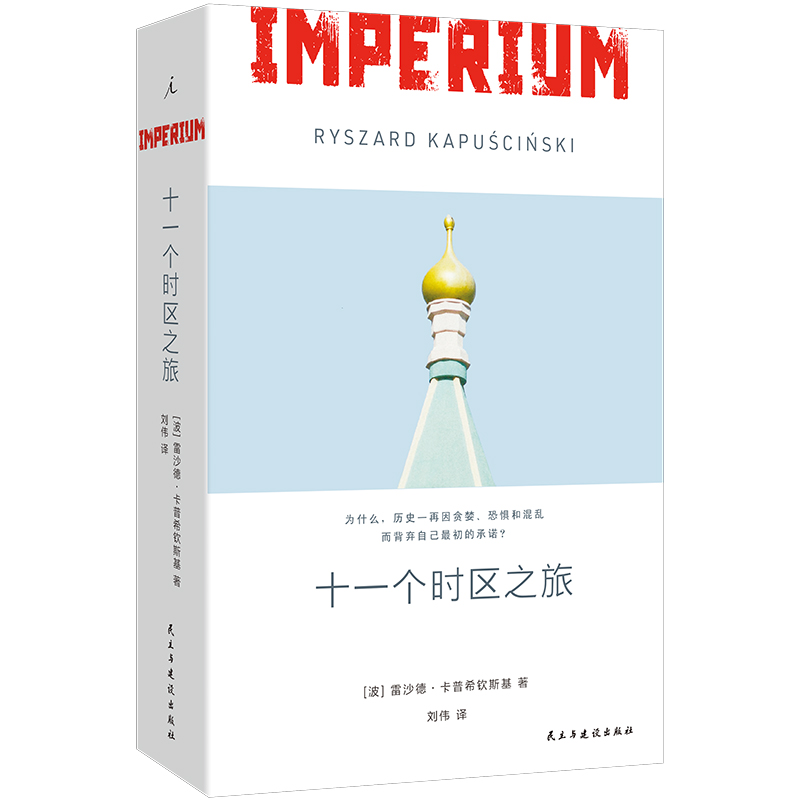
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
原售价: 72.00
折扣价: 43.20
折扣购买: 十一个时区之旅
ISBN: 97875139463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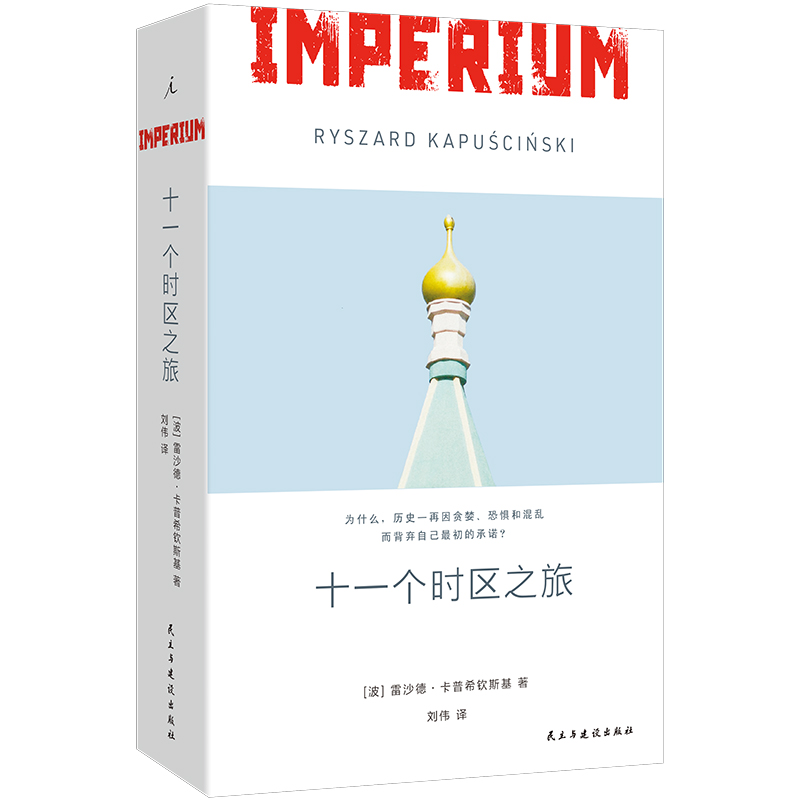
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Ryszard Kapu?ciński,1932—2007),波兰著名新闻记者、作家、摄影师、诗人,波兰新闻和文学界一位里程碑式的传奇人物,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深具影响力的作家和伟大的记者之一。在四十余年的驻外记者生涯中,足迹遍及一百余个国家,尤其深入亚非拉人迹罕至的地域,亲临火线,从大事件的现场发回一手报道。曾亲历二十七场革命和政变,四十余次被拘禁关押,四次被判死刑。创作了二十余部非虚构作品和诗集,被译成三十余种文字,获得五十多项国内国际大奖,六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加西亚·马尔克斯赞誉他是“真正的大师”;萨尔曼·鲁西迪称赞他的作品是“新闻报道和文学艺术的惊人融合”;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蕞杰出的见证者”;约翰·勒卡雷称他为“现代新闻报道的超凡魔术师”。 译者简介: 刘伟,自由译者。译有詹姆斯·索特《这一切》、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狐狸》、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黑暗中的谋杀》等。
后记:惊奇感 文_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听说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去世的消息时,我感到失去了一位朋友。不,不止于此:我失去了生命中一位不可或缺的人。当涉及复杂而艰深的事件之真相时,他是少数几个可以信赖的人之一,不是抽象地讲述,而是讲述具体细节——颜色,气味,感觉,触觉;某种境况。然而,我对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的了解根本不多。与人友善相交又保持距离感,这正是他身上一种罕见的品质。 我第一次见到卡普希钦斯基是在1984年。那时我和丈夫格雷姆·吉布森带着我们七岁的女儿住在西柏林,当时,西柏林还被那面著名的墙包围着。正是在那里,我开始创作《使女的故事》。就创作一本关于现代极权主义的小说而言,基调是现成的:每个星期天,东德的战斗机都会突破音障,用它们的超音速音爆提醒我们:它们随时有可能俯冲下来。苏联阵营一直延伸到德国东部,似乎坚如磐石。我们去过东德,那里有傲慢的边防军、指甲油似的冰淇淋和属于《史迈利的人马》那个时代的巧克力。我们还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想要说任何真话,都得走到公园中央,因为我们的捷克朋友们很害怕被窃听。 最后我们去了波兰,那里的情况完全不同。波兰一直被其邻国视为鲁莽的勇敢者,或勇敢的鲁莽者。波兰骑兵在马背上朝德国坦克冲锋的轶闻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无疑颇具象征意义。在1984年的华沙,这种鲁莽或违抗之举依然存在。出租车不会载你去任何地方,除非你有硬通货。作家们将大量“萨米兹达”(samizdat)——即非官方出版物——塞到你手中,它们就存放在所谓的共产主义作家协会的地盘上。我们在波兰期间,一名神父被杀了,可能是秘密警察干的。在天主教徒组织的游行上,我们看着那些眼神冷峻的修女、愤怒而坚定的神父及其追随者,心想,这个政权有麻烦了。 然后,我们见到了帮助推翻它的人。 1978年,卡普希钦斯基写下了《皇帝》(The Emperor: Downfall of an Autocrat)。从表面上看,这本书讲述的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及其腐败的专制政权的垮台,仅阅读这一层面,也会发现这是一本出色的作品。作为一名记者,卡普希钦斯基拥有波兰式的鲁莽,这让他经历了二十七次政变和革命——一波又一波难民朝一个方向涌去,逃离灾难,而卡普希钦斯基反其道而行,进入灾难的中心。他前往亚的斯亚贝巴,在黑夜里四处潜行,采访那些正东躲西藏的前朝弄臣,记录下关于皇帝的逸闻,其中既有无心插柳的喜剧,也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前者如,当皇帝坐到椅子上时,拿垫子的仆人必须在他脚下垫上高度刚刚合适的垫子,千万不能让他的小短腿悬空;后者如,乞丐们大口咽下宫宴的残羹冷饭,眼球从眼眶里喷射而出。 但对波兰人而言,《皇帝》还有另一层意义,在整个纳粹占领和苏联统治期间,波兰人已经习惯了说暗语。卡普希钦斯基本人在《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中这样描述那个时代:“没有什么是平实的、字面的、明确的——每个手势和词语背后都隐约透露出一些指涉性的符号,都有一双意味深长的眼睛在凝视。”如此一来,既然一个腐败的专制政权与另一个腐败的专制政权多有共同之处,那么《皇帝》便可被解读为对那个奄奄一息的波兰政权的批判。这本书很快被搬上舞台,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戏剧改编,对最终推翻了当权者的群众抗议贡献良多。《皇帝》在策略上的高明之处在于,当局几乎无法驳斥它,因为它不是在揭露君主制的弊端吗,而君主制不正是当局极力反对的政府形式吗? 1983年,《皇帝》被译成英语,我们正好读到了这本书,然后于1984年在华沙见到了卡普希钦斯基,与他握了手。他是同时代颇多非凡之士中的一员,这一代人还包括杰出的导演兼剧作家塔德乌什·康托尔,小说家塔德乌什·孔维茨基,这些人从小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成年后又一直生活在一党制的共产主义制度下,但仍然创作出令人惊叹的艺术作品。虽然卡普希钦斯基的创作背景多样,素材也各不相同,但他的基本主题却始终如一,那就是恐惧和压迫,以及人们如何应对或超越恐惧与压迫;困境以及困境如何使人变得扭曲或高尚;一元化政治带来的令人窒息的漫长折磨,以及人类对拥有自己灵魂的永恒渴望。考虑到卡普希钦斯基自己压抑的青年时代,这些主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我看来,卡普希钦斯基腼腆而迷人,还有些犹疑。我丈夫说这话没错,但这只是表面,内心深处他像钉子一样坚硬。我想他应该是两者兼具:在混乱的内战中,羞怯、魅力和犹疑让他不至于在路障前被枪毙,而钉子般的坚硬则让他一开始就走向了那些路障。 彼时,在苏联阵营内部与真正的作家见面,总有些超现实的色彩,也许,正是这种超现实主义造就了卡普希钦斯基的犹疑。在彬彬有礼的官方场合,有些话说了,有些话没说,但人们都应该心知肚明。在一次书展上,我问另一个作家,“为什么波兰有这么多插图精美的儿童绘本?”“你自己想想吧,”她回答说。 1986年1月,卡普希钦斯基在多伦多参加了《王中之王》(Shah of Shahs)英译本的出版仪式,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82年,讲述了伊朗国王被推翻时引人注目的景象还有他残酷的暴政,其中提到了“萨瓦克”(Savak),即他那些狰狞恐怖、擅长严刑拷打的秘密警察。现在重读这本书正当其时,因为它对那个世界中还在不断呈现的发展模式如此具有先见之明。卡普希钦斯基当时很紧张,因为他要出席港湾城国际作家系列活动,他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不足以进行公开朗读。我可以代替他说英文吗?可以替他朗读他的书吗?我说我很荣幸,但同时我也在想——等等!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紧张了?害怕读英语?在安全、没有任何威胁、哪怕他只蹦出一个词大家也会爱他的多伦多?那刚果的腥风血雨、洪都拉斯的炸弹横飞以及德黑兰危及性命的革命骚乱,又是怎么回事? 卡普希钦斯基在多伦多的紧张表现非常可爱,有点像苏格兰女王玛丽在上绞刑架之前担心自己的帽子是不是戴正了。不过话说回来,别人都紧张什么,是难以预料的。 卡普希钦斯基是一名驻外记者,并且多年来一直是波兰唯一一名驻外记者,所以他看起来无处不在,至少,当腐朽的政治结构处于崩溃、灾难或可怕的流血事件时是这样。哪里有混乱,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帝国》描述了1989—1991年他在苏联的旅行,当时苏联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其中有一段话很有代表性: 传来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说一座拥有百万居民的大型城市受到了严重的、危险的、致命的毒气污染。 “另一个切尔诺贝利!”朋友向我转述这个消息时说。 “我要去那里,”我说,“如果有座位,我明天就飞过去。” 卡普希钦斯基一生都渴望旅行,他渴望去的,恰恰是那些寻欢作乐的普通游客竭力避开的地方。因此,在他的最后一本书《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中,他乞灵于第一位从事此类旅行的作家、“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这再恰当不过了。卡普希钦斯基年轻时最想做的事是“跨越边界”——一开始是波兰的边界,但是后来,他渐渐想要跨越一切可能的边界。驱使他前行的,是他对人类各种形态的无尽好奇。像希罗多德一样,他倾听并且记录,但从不指责。他的一生都在探寻——探寻,而非完成什么使命。他想找到什么?当然是异国的细节;文化差异;在战后波兰极度缺乏的丰富拼图。但除此之外,他寻找的是人类共同的善意,即便在最极端的流血冲突、虐待狂式的复仇和堕落中也是如此。我们的希望在哪里?也许在于尊严——那种朴素的尊严,处处成为压迫者的眼中钉、却永远无法被彻底根除的尊严。那种说“不”的尊严。 考虑到他目睹过的一切,卡普希钦斯基比任何作家都更有理由悲观,但悲观并不是他惯常表达的情绪。他更常表达的是惊奇。惊奇世间竟然如此辉煌与卑劣并存。在《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的结尾处,有这样一句话。它描写的只是土耳其博物馆内的一个场景,但对于这位谦逊之士、我们这个时代的杰出见证者来说,却有一种墓志铭的味道。因此,我也把这句话放在这里: “我们身处黑暗,被光包围。” 1. “钉子一般坚硬”的世纪记者,跨越“帝国”五十年:行走苏联全境数万公里,实地探访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关于苏联蕞热情、蕞吸引人、蕞深刻的历史叙事”(叶礼庭,著名政治家,乔治·奥威尔奖得主,《火与烬》作者)—— 四十余年驻外记者生涯,足迹遍及一百余个国家。亲历二十七场革命和政变,四十余次被拘禁关押,四次被判死刑。创作非虚构作品二十余部,被译成三十余种文字,获得五十多项国内国际大奖。 “真正的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新闻报道和文学艺术的惊人融合”(萨尔曼·鲁西迪);“现代新闻报道的超凡魔术师”(约翰·勒卡雷);“我们这个时代蕞杰出的见证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2. 一份雷达全开的私人报告,苏联天空下的生存较量与命运书写:“他无处不在……哪里有混乱,哪里就有他的身影。”(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一个广袤的世界,“帝国”的领土总面积超过二千二百万平方公里,其陆地边界比赤道还长,绵延四万两千公里。 一位独一无二的向导,带你探索无比广袤、深不可测的苏联:“在这场旅行中,我努力抵达时间、力量和机会允许我抵达的一切地方。” 第一部分“初遇(1939—1967)”:从1939年苏军进入波兰小城平斯克,到作者穿越白雪覆盖、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的旅程,以及在外高加索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探险。 第二部分“鸟瞰图(1989—1991)”,记述了在“帝国”衰落和最终解体的若干年间,在其广袤领土上进行的几次时间较长的漫游。作者绕过官方机构和路线,独自开展了这些旅行,从苏波交界的布列斯特到太平洋上的马加丹,从北极圈内的沃尔库塔到阿富汗边境的铁尔米兹。旅程总计六万公里。 第三部分“未完待续(1992—1993)”,在旅行、谈话和阅读间隙产生的思考、观察和预言。“在我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主要的对象和主体分崩离析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新的国家崛起,其中包括俄罗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其中居住着几百年来被帝国激励并团结在一起的人民。”“俄罗斯以1905年的革命开启了二十世纪的历史,以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这个国家的历史就像一座活火山,不断翻腾,没有迹象表明它会平静下来,进入蛰伏期。” 3. 亲历与抢救式记录,解密复杂到难以想象的苏联帝国:了解俄苏的必读之书,“这本书是一个宝藏”“仿佛在鲸鱼腹中描绘鲸鱼”—— 斯大林时代的平斯克,赫鲁晓夫时代的西伯利亚,勃列日涅夫时代难以接近的南方加盟共和国,解体年代横贯全境的漫长行走…… 从遍布铁丝网的冻土带,到大海中央建造的石油不夜城;从北极圈的矿工罢工,到穿越战乱高加索的生死巴士之旅;从克林姆林宫的“魔山”,到科雷马废弃的古拉格……第一手的见证,抢救式的记录,当历史化身预言家: “我们的老师消失了。其他班级的孩子也越来越频繁地消失。很快,甚至不再有人问他们为什么没来,或者他们去了哪里。学校变得越来越空旷。” “无穷无尽的带刺铁丝网将天空和大地连接在一起。地球在这里没有尽头;世界在这里没有尽头。人不是为这种无限性而生的。” “她们当中哪一位是囚犯,哪一位是监工?年迈和贫穷给了她们暂时的平等;很快,冻土将使她们最终永远和解。” “锈迹斑斑的船只残骸,腐烂的瞭望塔,矿石开采后留下的深坑。一片令人沮丧的、了无生气的空虚。到处都是寂静,因为疲惫不堪的队伍已经走过,消失在永恒的寒雾中。” “这个地图对俄罗斯人来说是一种视觉上的补偿,一种特殊的感情升华,也是一种难以掩饰的骄傲。它还可以解释一切短缺、错误、贫穷和孱弱,并为之辩护。” “今天的帝国就像一个湖面,湖底的火山纷纷苏醒。平静光滑的湖面上突然涌现出气泡。随着时间的推移,气泡会越来越多。水四处沸腾。在深处,可以听到低沉的轰隆声。” 4. 经典之作全新译本,绝版多年重磅回归。特别收录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后记《惊奇感》—— “虽然卡普希钦斯基的创作背景多样,素材也各不相同,但他的基本主题却始终如一,那就是恐惧和压迫,以及人们如何应对或超越恐惧与压迫;困境以及困境如何使人变得扭曲或高尚;一元化政治带来的令人窒息的漫长折磨,以及人类对拥有自己灵魂的永恒渴望。……卡普希钦斯基腼腆而迷人,还有些犹疑。但这只是表面,内心深处他像钉子一样坚硬。我想他应该是两者兼具:在混乱的内战中,羞怯、魅力和犹疑让他不至于在路障前被枪毙,而钉子般的坚硬则让他一开始就走向了那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