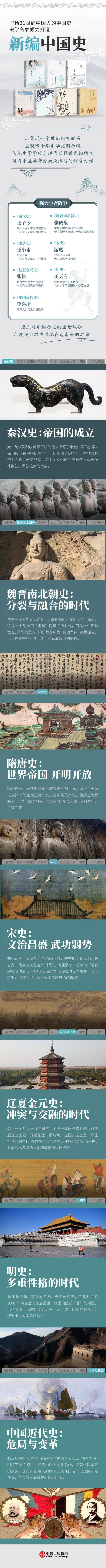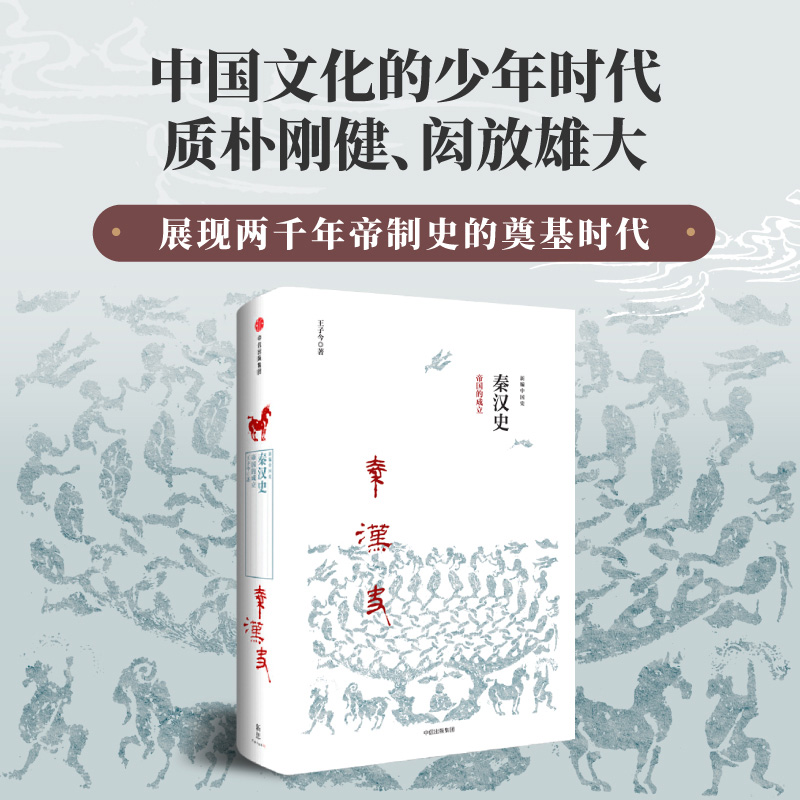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95.00
折扣价: 60.80
折扣购买: 秦汉史(帝国的成立)(精)/新编中国史
ISBN: 97875086700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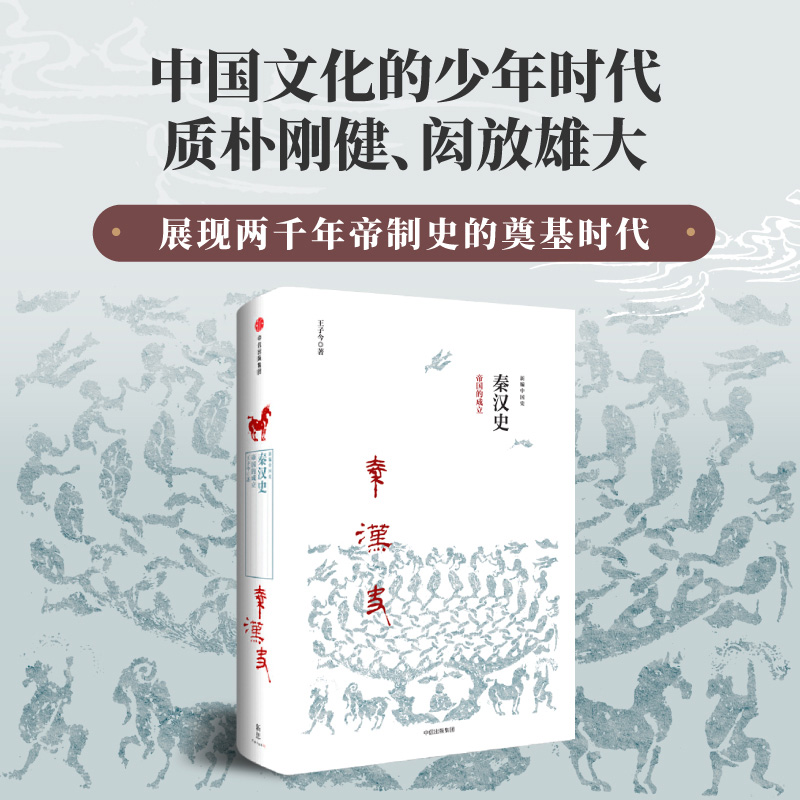
王子今,1950年12月生于哈尔滨。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中国古代史专业毕业。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陕西理工大学汉江学者。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岩画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已出版《秦汉交通史稿》《史记的文化发掘》《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秦汉社会史论考》《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秦汉称谓研究》《秦汉交通考古》《秦汉名物考》《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等学术专著4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700余篇。
第十二章 新政的试验 面对西汉末年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深重的政治危局,王莽正式取得帝位之后,即附会古礼,托古改制,期求以社会改革的形式,调整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改善国家效能,希望恢复政局的稳定。王莽新政的试验没有成功。 第一节 王田私属 西汉末年社会问题的症结,是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 汉哀帝时,师丹辅政,曾经建议以限田、限奴婢的形式缓和社会矛盾。汉哀帝发布诏书说,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聚集奴婢、田宅,没有限制,与民争利,百姓往往失业,重困不足。他指示朝臣制订予以限制的条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随即制订了限定的额度和限制的措施。规定贵族官僚及一般民众皆得名田,诸王、列侯得名田于国中,列侯在长安者及公主得名田于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的数额不得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的限定数量,诸侯王为二百人,列侯、公主为一百人,关内侯、吏民为三十人。以三年为期,“犯者没入官”,即违反这一规定的要受到严厉的惩处。然而这一设想遭到了当政的外戚、官僚的激烈反对,并没有能够真正实行。 王莽也认识到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是西汉末年社会问题的要害。 王莽在始建国元年(9)下令,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奴婢为“私属”,都严禁买卖。他又参照孟子曾经说到的“井田制”一夫一妇授田百亩的原则,宣布凡男口不满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应当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中无田和少田的人。没有田的民户,则按照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 王莽的这一措施,意图在于缓和土地兼并造成的矛盾,同时防止农民奴隶化。但是诏书颁布之后,分田授田的规定并不能够真正落实,仅仅只是冻结了土地和奴婢的买卖。地主、官僚和工商主当时违禁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以致获罪的不可胜数,于是纷起反对。王莽无力坚持,只得在始建国四年(12)宣布买卖土地和奴婢不再治罪,承认了这项改革尝试的失败。 地皇三年(22),王莽在新朝政权崩溃的前夕,最后废除了关于王田、私属的法令。 第二节 五均六筦 在王莽推行的一系列新政中,又有被称为“五均六筦”的城市经济政策。 “五均六筦”,即“五均赊贷”和“六筦”的制度。王莽曾经试图通过这一形式,改善对工商业和财政的管理。 “五均六筦”,即对六种经济活动实行管制,包括对盐、铁、酒实行专卖,政府铸钱,名山大泽产品收税,以及五均赊贷(即政府对城市工商业经营和市场物价进行管制,并办理官营贷款业务)等。 居延汉简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简文:“……枚,缣素,上贾一匹直小泉七百枚,其马牛各且倍,平及诸万物可皆倍。牺和折威侯匡等所为平贾,夫贵者征贱,物皆集聚于常安城中,亦自为极贱矣。县官市买于民,民……”3简文中所谓“牺和折威侯匡”,可能就是《汉书·食货志下》中说到的主持“五均六筦”的“羲和鲁匡”。事实证明王莽时代推行的“五均赊贷”制度不仅限于“盐铁钱布帛”,可能也曾试图涉及物资,包括“马牛”,“及诸万物”。 当时实行“五均”的六个城市,称为“五均市”。“五均市”就是: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洛阳(今河南洛阳东)、邯郸(今河北邯郸)、临菑(今山东淄博东)、宛(今河南南阳)、成都(今四川成都)。 《汉书·食货志下》记载,王莽当时颁布诏令说,《周礼》有“赊贷”制度,《乐语》有“五均”形式,传记等诸种典籍又多说到“斡”,其作用在于使众庶得到平均,使兼并得到抑止。于是在长安及五都设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其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分别设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 当时,新朝政府宣称希望通过类似的经济管理方式,限制商人对农民的残酷盘剥,制止高利贷者非法牟取暴利的行为,以完备国家的经济制度,调整社会的经济关系。但是,这些措施也多有不利于实行的成分,遭到了工商业者的联合反对,导致了明显的经济混乱。 王莽政权的最高决策集团,在确定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时,没有经过成熟的理论思考;在推行改革的法令和措施时,也没有进行必要的理论说明。他们只是简单地以传说中古代圣王的制度作为改革的理论基础。分田授田的规定,是依照孟子所谓“井田制”一夫一妻授田百亩的原则制定的。“五均六筦”制度的名号,也是儒者刘歆以古文经《周礼》和《乐语》为依据提出来的。 耐人寻味的是,“五均”政策本来是以汉武帝“平准法”为基点制定的,而“六筦”中,盐、铁专卖和政府铸钱也都是承袭汉武帝旧制,酒的专卖在汉武帝时代也曾经实行,但是新法的宣布,并不对汉武帝时代制度的利弊与成败进行总结和说明,却只是以古制相标榜。 “五均六筦”法实行了十数年,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收效。到王莽地皇二年(21),设计和主持“五均六筦”的刘歆、鲁匡在朝廷议政时受到公开指责。王莽“以百姓怨非故”,考虑到“众意”的压力,将鲁匡降职,已经对“五均六筦”政策表露出否定的倾向。然而这一政策还没来得及正式废除,王莽的新朝政权就覆亡了。 第三节 分州定域 王莽据说素好鬼神,迷信符命,惊惧变怪,政治行为往往“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事事都要在圣王事迹和儒学经典中寻求根据。虽然王莽改制缺乏完备的改革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其理论基点表现出盲目复古的倾向,只是简单地“追监前代”,“专念稽古之事”,但是新朝所试图进行的政治文化区与经济文化区的重新划分,却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文化地理观正逐步走向成熟。 王莽先据《尚书·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又据《禹贡》改为九州。他又曾经“以《周官》《王制》之文”更改地名和官名,将政治中心向东方转移的计划也列入了日程。 汉平帝元始五年(5),王莽曾经因为“皇后有子孙瑞”,开筑了由长安翻越秦岭通达汉中的子午道。子午道的开通,是地理与人文相互印合的特殊的史例,反映了当时神秘主义观念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 《汉书·王莽传上》记载,王莽期望在处理四夷之事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以为当时“既致太平,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外交在北方、东方和南方都多有创获,只是在西方并不理想,于是派人多持金币引诱塞外羌人献地内属。随即有羌人首领良愿等率其部族一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王莽说,当时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于是以所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期望奄有四海,透露出王莽地理观的政治文化基点。此后,又增置五十条新法令,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多以千万计,事实上开始了大规模充实西海的移民。 王莽又按照传说中先古圣王的行政区域规划,讨论确定州名及州界问题,以经义正十二州州名、分界。王莽始建国四年(12),又以“为万国主”的身份,宣布“分州定域,以美风俗”,再次讨论了十二州和九州的建置问题。这一次则确定按照《禹贡》中提出的制度,置定九州。 王莽的新朝建立之后,一时志欲方盛,“以为四夷不足吞灭”,于是又以强制性的行政方式确定了所谓“天下”“四表”。《汉书·王莽传中》记载,其东出至玄菟(郡治在今辽宁新宾西南)、乐浪(郡治在今朝鲜平壤南)、高句骊(在今辽宁东部)、夫余(在今吉林中部);南出则逾徼外,历益州;西出则至西域;北出者,至匈奴庭。 西方和南方,为了追求“九族和睦”的虚名,“尽改其王为侯”,将边地少数部族领袖由“王”贬称为“侯”。又授匈奴单于印,变易文字,不再称“玺”而改称“章”。匈奴单于称谓也被改为“降奴服于”。王莽轻视边地少数部族的做法导致了边境的动乱,一时匈奴单于大怒,东北与西南夷发生变乱,西域地区也随即因此叛离。 王莽时代大规模更改地名,后来成为历史上的笑柄。他在建立新朝之初,就改明光宫为定安馆,又更名长乐宫为常乐室,未央宫为寿成室,前殿为王路堂,长安为常安。郡县名称也纷纷更改。尤其引起行政烦乱和民间不便的,是地名的反复更改。《汉书·王莽传中》说,地名往往一年之内反复变更,有的郡名甚至先后五次变易,而最终又恢复原名。地名的频繁变化,使吏民不能明辨,于是每次颁布诏书涉及地方政策时,不得不在新地名之后说明原先地名。王莽推行的改革措施,往往随意性很强。心血来潮,朝令夕改,“号令变易”,“数变改不信”的情形相当多见。 西汉末年经济进步的显著标志之一,是关东地区从非政治重心的基点出发,经过累年的发展,已经逐步取得了其生产形势可以牵动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秦代及西汉前期实行“强干弱支”“强本弱末”的政策,以行政强制的方式剥夺关东地区,从而导致“东垂被虚耗之害”的做法,在当时已经被有识之士所否定,以为“非久长之策也”。 王莽专政时,最高执政集团已经看到了这一形势。当时所谓“分州定域”的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基本观念的调整,已经表现出对东方地区经济文化优势的倾重。 王子今,1950年12月生于哈尔滨,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中国古代史专业毕业,现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已出版《秦汉交通史稿》《史记的文化发掘》《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秦汉社会史论考》《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秦汉称谓研究》《秦汉交通考古》《秦汉名物丛考》《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等学术专著4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8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