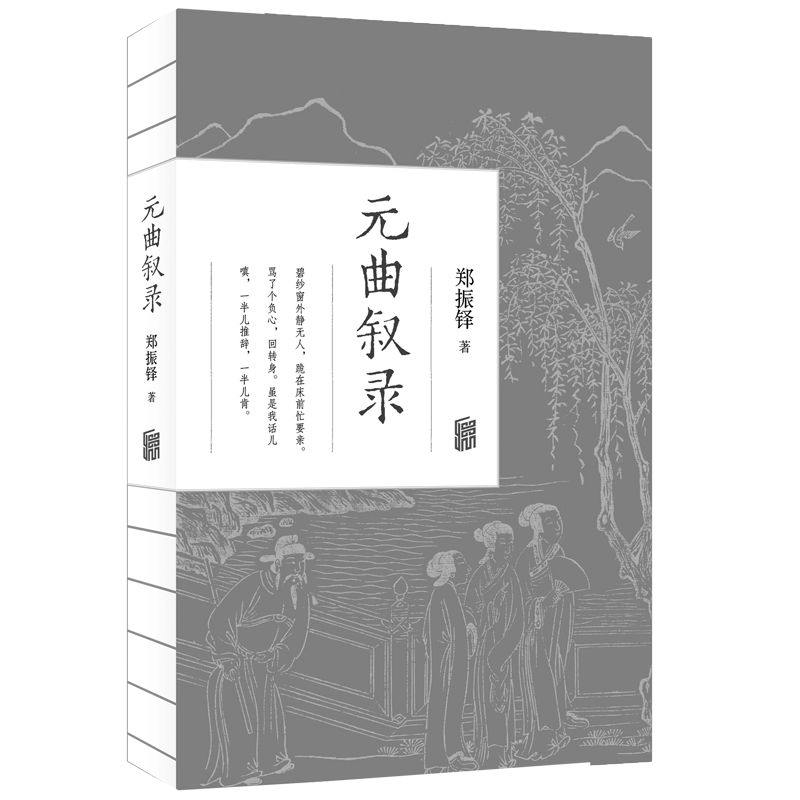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联合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元曲叙录
ISBN: 9787559630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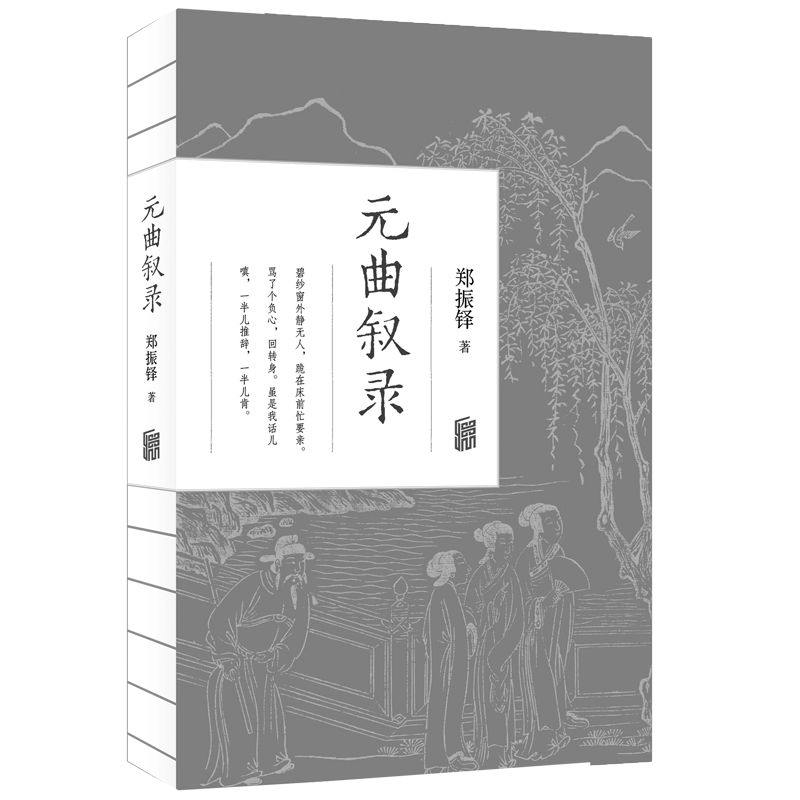
郑振铎(1**8年—1958年)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属于开拓性的工作。
《元曲叙录》是郑振铎先生1930年1月到1931年10月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一组文章。共介绍了三十一位作家的六十九本杂剧。近百年来,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文献整理,或史论著作,都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元曲叙录》这样的著述,或许已不鲜见。然而,当我们回首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学术研究的转型期,郑振铎先生的这一著作却包蕴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元曲叙录》写作于“整理国故”的大背景之下。整理国故运动是1919年开始,绵延至三十年代中期的文化思潮。1919年,针对当时出现的“复兴古学”的诸种论说与行动,毛子水在《新潮》杂志发表《国故和科学精神》一文,提出要以科学的精神研究国故。胡适在给毛子水的信《论国故学》中肯定整理国故的必要,认为: 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 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他说: 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1923年,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又谈到要扩大研究的范围: 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吴敬梓、曹霑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 把*野的文学、民间的作品列入研究的范围,将小说、戏曲作者与诗文作者并列。“文学研究会”响应“整理国故”的主张,把整理中国旧文学作为自己的重 要任务之一。1922年,郑振铎先生在《文学旬刊》发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 积极回应“整理国故”,称: 所以我们要明白中国文学的真价,要把中国人的传统的旧文学观改正过,非大大的先下一番整理的功夫,把金玉从沙石中分析出来不可。 文章提出“文学观”的问题,指出要重新确定中国文学的范围。1923年,郑振铎先生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後,在《小说月报》十四卷一期展开“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讨论,把“整理国故”视为反对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必要条件。在《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中,郑振铎先生说: 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 我所持的理由有二。**,我觉得新文学的运动,不仅要在创作与翻译方面努力,而对于一般社会的文艺观念,尤须**的把他们改革过。 第二,我以为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推翻一切中国固有的 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 郑振铎先生强调“整理国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搜找出来”,以新文学的眼光重估旧文学。把在文学**一贯被轻视的杂剧传奇小说等视为金石,给予从来没有过的重视,对文献的整理、研究,对俗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我们**件事,便要先廓清了许多非文学的著作,而使之离开文学史的范围之内,回到“经学史”“哲学史”或学术,思想史的他们自己的领土中去。同时*重要的却是要把文学史中所应述的纯文学的范围放大,……*重要的是,于诗歌、散文二大文体之外*要包罗着文学中*崇高的三大成就——戏剧、小说与“变文”(即后来之弹词、宝卷)。这几种文体,在中国文坛的遭际,*为不幸。他们被压伏在正统派的作品之下,久不为人所重视;甚至为人所忘记,所蔑视。直到了*近数十年来方才有人在谈着。我们现在是要给他们以历来所未有的重视与详细的讲述的了! 但这种新的资材,自小说戏剧以至宝卷,弹词,民歌等等,因为实在被遗忘得太久了的原故,对于他们的有系统的研究与讲述便成了异常困难的工作。 新材料实在太多了,有一部分是需要著者**次来整理,来讲述的。 而在对戏剧、小说、变文、宝卷等等文体价值的肯定中,郑振铎先生*特别提出了为杂剧传奇等编辑书目的问题。在发表于1923年的《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一文中,在谈到把金石从瓦砾中搜找出来时,郑先生写道: 譬如元、明的杂剧传奇,与宋的词集,许多编书目的人都以他们为小道,为不足录的;而实则他们的真价值,却远在四库书目上所著录的元、明人诗文集以上。 郑振铎先生在对元明戏曲、宋人词集的重视中,抓住历来书目编写上的忽视,批评许多编书目的人以剧本等为小道,以为不足录。 “叙录”是传统的古籍整理方式,在古籍保存和利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向来为学者所重视。随着晚清以来人们对戏剧、小说文体的推重,对戏曲叙录的写作也*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早在1908年,王国维在为《曲品新传奇品》作跋时,就曾感叹著录戏曲的书太少: 此书误字累累,文又拙劣,然无名氏《传奇汇考》,江都黄文旸《曲目》,多取材于此。盖著录戏曲之书,除元钟丑斋《录鬼簿》、明宁献王《太和正音谱》外,以此为*古矣。 1928年,大东书局出版《曲海总目提要》,胡适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说: 在这个时代,大家渐渐感觉剧本目录的需要。不但如王先生的《曲录》之仅仅列举剧名而已,必须有一种记载剧本作者与情节内容的详目,方才可以供收藏家的参考与文学史家的研究。 而郑振铎先生作为戏曲等文体叙录写作的早期倡导者,在“叙录”的写作方面投入了很多的精力。1923年后的数年间,他一再为戏曲、小说等写作提要,以此来完成对以往的轻视的纠正,实践自己整理国故的主张。1925年,他在《时事新报 鉴赏周刊》刊出《中国小说提要》,192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收录了他的《佛曲叙录》。戏曲方面,他不但致力于戏曲剧本的收集,而且花了很大的力量在“提要”的写作上。除了发表《元曲叙录》,1940年他在《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说: 又本书各剧“提要”,我也已随笔记录得颇详。 此外,1941年写作的《晚清戏曲录叙》中还谈到他劝如晦(阿英)先生作《叙录》事: 如晦先生收藏晚清文史资料*富,余前辑《晚清文选》,深资其助。尝劝其将历年搜访所得,刊为目录,公之于世。如晦先生深感余言,乃先将所藏晚清戏曲,编为一目印行,每书均加说明,嘉惠后学,有功于我等研究近代文史者不浅。 郑振铎先生的《元曲叙录》,通过“叙录”这一细致的、具有传统色彩的文献工作,为戏曲地位的提升,做出具体扎实的贡献,同时,也体现着郑振铎先生提倡的研究精神与整理国故的方法: 我们须有切实的研究,无谓的空疏的言论,可以不说。我们须以诚挚求真的态度,去发见没有人开发过的地。 *好是先有局部的研究,然後再进而为全体的研究,才能精密而详确。 郑振铎先生的《元曲叙录》是体现着他的戏曲观念的。在1922年发表的《文学的统一观》中,郑振铎先生曾讨论了文学的普世价值: 我却以为世界的文学就是世界人类的精神与情绪的反映;虽因地域的差 别,其派别,其色彩,略有浓淡与疏密之不同。然其不同之程度,固远不如其相同之程度。因为人类虽相隔至远,虽面色不同,而其精神与情绪究竟是几乎**无异的。无论人类的文化程度的高低如何,终是人类,终是同样的人类;虽文化至高之人类,其喜怒与食饮与居住的本能——原始的本能——终是不能有一点消减的。 在同年发表的《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一文中,郑先生曾强调要明确到底什么是文学,并把中国的文学分为九类,即:诗歌;杂剧传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笔记小说;史书传记;论文;文学批评;杂著。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指出: 中国文学所以不能充分发达,便是吃了传袭的文学观念的亏。大部分的人,都中了儒学的毒,以“文”为载道之具,薄词赋之类为“雕虫小技”而不为。其他一部分的人,则自甘于做艳词美句,以文学为一种忧时散闷、闲时消遣的东西。一直到了现在,这两种观念还未**消灭。便是古代许多很好的纯文学,也被儒家解释得死板的无一毫生气。 文学贵独创。前人之所以嘉惠后人者,惟无形中的风格的影响,与潜在心底的思想的同情而已。摹袭之作,决无佳构。 所论涉及对“文以载道”、以文学为消遣的反对,对“纯文学”的认可,以及对文学风格与传达共同情感的体认。在《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一文中,郑振铎先生提出“我们应采用已**的文学原理与关于文学批评的有力言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源流与发展”。郑振铎先生《元曲叙录》的**篇是关汉卿的小传,第二篇是“关汉卿作品全目”。关汉卿是《元曲叙录》中**有小传和作品全目的剧作家,显示出郑振铎先生在元代诸多杂剧作家中对关汉卿的重视,同时*在对关汉卿的论述中表达了自己的戏曲批评标准。 汉卿作品,于小令套曲十馀首外,其全力**注重于杂剧,所作有六十 五本之多,即除去疑似者外,至少亦当有六十本以上。今古才人,似他著作 力的如此健富者殊不多见(惟李玄玉作传奇三十三本,朱素臣作传奇三十本 差可比拟耳)。《太和正音谱》评汉卿之词,以为“如琼筵醉客”,又以为 “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然汉卿所作,通俗者为多,如《谢天香》、 《金线池》、《望江亭》、《玉镜台》之类,诚未必高出于马致远、郑德辉 诸作者,然如《救风尘》之结构完整,《窦娥冤》之充满悲剧气氛,《单刀 会》之慷慨激昂,《拜月亭》之风光旖旎,则皆为时人所不及,其笔力之无 施不可,比之马、郑、白、王(实甫),实有馀裕。 他赞赏关汉卿才力之健富,肯定其剧作的通俗,其笔力的无施不可,认为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王实甫均不及关汉卿,给予关汉卿“时人所不及”的剧坛地位。所言接*了王国维先生对关汉卿剧作从悲剧、结构、语言角度的评价: 其*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然如武汉臣之《老生儿》,关汉卿之《救风尘》,其布置结构,亦极意匠惨淡之致,宁较后世之传奇,有优无劣也。 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 承继了吴梅先生《中国戏曲概论》(1926年)卷上“元人杂剧”对关汉卿“雄肆”的肯定: 而关汉卿以雄肆易其赤帜,所作《救风尘》、《玉镜台》、《谢天香》 诸剧,类皆雄奇排奡,无搔头弄姿之态。 《元剧研究ABC》(1929)对关汉卿魄力的赞扬: 元曲以汉卿为大家,所作亦至多,有六十三种,自有曲家,无此魄力也。 但*在关汉卿诸剧作中,拈出《救风尘》、《窦娥冤》、《单刀会》、《拜月亭》四剧,分别从结构、悲剧气氛、风格的慷慨激昂与风光旖旎等方面赞扬了四部剧作的成就,称赞其“比之马、郑、白、王(实甫),实有馀裕”,显示出郑振铎先生对元人杂剧价值的重新审视,以及郑振铎先生在剧本、剧作家评价中,对悲剧、结构、语言表现、人物描摹、题材丰富性诸因素的重视。讨论所及均围绕着剧本的文学因素。这样的视角,与其对什么是文学的关切、对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的探讨,以及对“**的文学原理”的重视,可谓一脉相承。而这样的戏曲观念在他1932年刊行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得到贯彻和进一步的论说。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郑振铎先生在《元曲叙录》的评价之外,*加丰富、发挥了自己的论点。他说:“元人之善于写多方面的题材,与多方面的人物与情绪者,自当以汉卿为**。”赞扬关汉卿对女性人物的表现: 可见其如何喜欢且如何的善于描写女性的人物。在汉卿所创造的女主角中,什么样的人物都有。 总之,无一样的人物,他是不曾写到的,且写得无不隽妙。写女主角而好的,除了《西厢》、《还魂》等之外,就要算是汉卿的诸剧了。而汉卿能写诸般不同的人物,却又是他们所不能的。尽管题材是很通俗的,很陈*的,不能动人的;如像公案杂剧一类的东西,实在是*难写得好的,而汉卿却都会使他们生出活气来。如今读之,仍觉得是活泼泼的。当时在剧场上,当然是*为触目惊心的了。 感慨他对英雄的书写: 但汉卿不仅长于写妇人及其心理,也还长于写雄猛的英雄;不仅长于写风光绮腻的恋爱小喜剧,也还长于写电掣山崩,气势浩莽的英雄遭际。 赞叹他的描写艺术: 论到描写的艺术,他实可以当得起说是**等。我们很觉得奇怪,元剧作者,大都各有所长。……汉卿一人,兼众长而有之,而恰在于众人的首先,仿佛是戏剧**有意的要产生出那末伟大的一位剧作者,来领导着后来作者似的。 在具体的写作上,郑振铎先生的《元曲叙录》亦展示出新的面貌。《元曲叙录》对杂剧剧本的著录体例**明确,即:在每本杂剧的名下著录作者,说明版本,并按折逐一概括每折的情节、记录每折的登场人物、每折所唱曲子的名称,*後是剧作的题目正名。这和《传奇汇考》、《曲海总目提要》的记录作者、概括情节、说明本事或相关材料、有的稍作评论,表现出不同。《元曲叙录》逐折的载录方式、对曲牌和登场人物的记述,*清楚地传达出剧本的面貌,体现出杂剧剧本的特点,突出了剧本的舞台性。 《元曲叙录》包含了当时的新发现,且不论早前发现的《元刊杂剧三十种》 中的《单刀会》《西蜀梦》《拜月亭》《诈妮子调风月》等,像新发现的《绯衣 梦》(“近来涵芬楼购得明顾曲斋所刊的十六种曲,《绯衣梦》竟亦在其中。” )、《西游记》杂剧(“六本的《西游记杂剧》的出现,成为一件重要的大事。 “去年*本盐古温博士在宫内省藏书里发现了刻本吴昌龄《西游记》”),也 都被写进了《元曲叙录》,弥补已有戏曲叙录的不足,使研究者对新发现的杂剧 剧本有基本的了解。 此外,《元曲叙录》对关汉卿生平的勾勒亦有值得关注之处。“元代曲家,名位既微,传记*阙”。此前论者谈及关汉卿生平,除利用《录鬼簿》的记载,说明“号已斋叟,大都人,太医院尹”外,还会由杨维桢《元宫词》“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之句,论及关汉卿犹逮事金;会叙及《辍耕录》所载关汉卿与王和卿交往事;会谈到《太和正音谱》对关汉卿“琼筵醉客”、“初为杂剧之始”的评价。郑振铎先生则进一步追寻关汉卿的行迹,借助其套曲《杭州景》指出关汉卿曾经到过杭州。认为关汉卿的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二期:前期活动于大都,后期活动于杭州。这一番关于关汉卿生平的论述在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同样被沿用。 对“叙录”的提倡与写作是整理国故运动中郑振铎先生的重要贡献之一,他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推广了戏曲、小说“叙录”的写作,推动了戏曲、小说 研究的发展,後来阿英在《晚清戏曲小说目》的《叙记》中,谈到自己从1934 年到1941年“编写了不少书录,现存和还记得起的”有十数种,即可视为郑振 铎先生推动小说、戏曲“叙录”写作发展的一个明证。 《元曲叙录》作为郑先生叙录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只完成了对六十九种杂剧的介绍,虽然在作者考辨、版本著录方面还可*加完善,但该叙录的写作,为进一步展开文学历史的讨论打下了基础。为戏曲叙录的写作,为整理、研究古代戏曲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形式。而其中所体现的对文学价值、戏曲特点的重视与把握,亦是学术**重要的一页。值此郑振铎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敬仰之情。 李简 2018年10月 每一个剧目配有对应的元明版画及剧本,观赏性强 勾勒关汉卿的生平 叙录这一细致、古典文献整理方式的近代代表作 体现郑振铎先生的研究精神及整理国故的方法 杂剧剧目体例明确、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