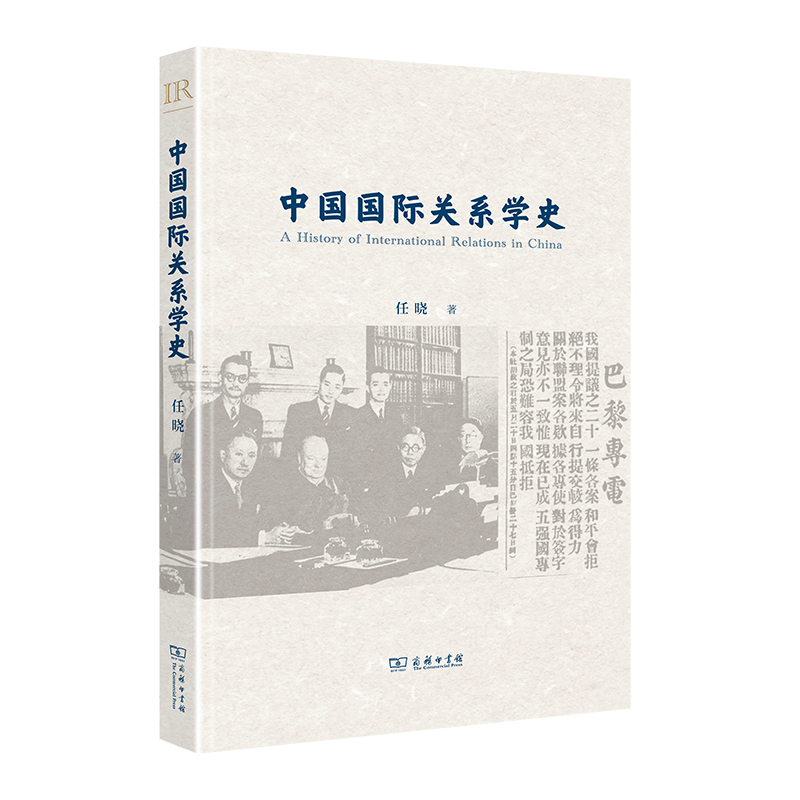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128.00
折扣价: 88.40
折扣购买: 中国国际关系学史
ISBN: 97871002093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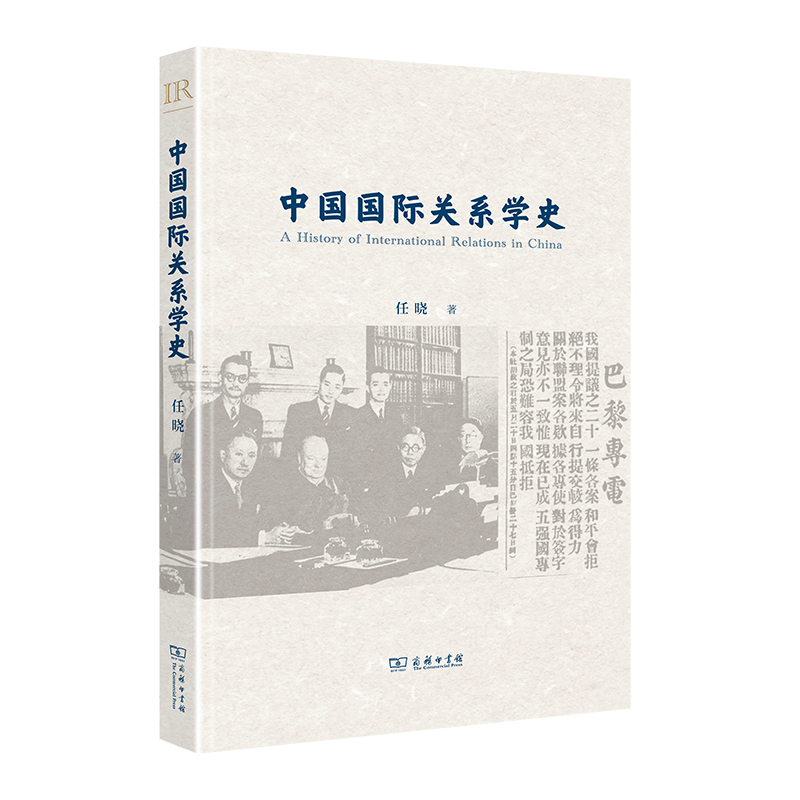
任晓,现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1990—1991年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留学。曾为欧盟博士后研究人员、日本名古屋大学客座研究员及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目前还担任外交学院兼职教授、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高级研究员等,并任六家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包括Globalizations,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East Asian Policy 和Journal of Global Policy and Governance。已发表中英文论著数种,并多次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奖及著作奖。
(1) 周鲠生则强调了这门学问的必要性,指出,一般人以为国际关系,远不如国内事情之直接于本身有切肤之痛。于是对于本国以外的事情,对于国际生活状态,视为无关紧要,不肯加意去考究。这样的疏忽态度,在闭关时代犹可说无害;到了现代,人类交际频繁,国际生活复杂,社会连带关系,由国内社会,推及于国际社会,那样的态度就不妥当了。平时不研究国际事情昧于世界大势,一遇国际关系上有事变发生,莫能穷其原因之所在,总不免把近因看作远因,误认事变的导火线为事变的真因。 (2) 胡愈之则撰写了“为什么研究国际问题”的文章。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大炮和火轮船,从百年前起,已冲破了几千年来紧闭着的大门。不必说,各大都市,已变成‘十里洋场’,就是内地偏僻的乡村,美孚公司的煤油,蓝开厦的棉布,德国的肥田粉,都已变成了农民的必需品。此外中国的农业生产,茶、丝、桐油、大豆、草帽辫、烟草等,一大部分也是专为了运输出口而生产的。世界小麦市场的不景气,立即影响到中国的小农,中国农民购买力的低落,也影响到世界贸易。因此,老旧的,孤立的,闭关主义的中国,在近百年中间,便脱胎换骨,变成了‘世界的中国’。”资本帝国主义把全世界造成整个的经济机构,而殖民地的中国只是这机构的一部分。经济上中国和世界已经是密切不可分离了,那么在经济生活的上层建筑的政治和文化方面,中国自然也脱不了世界的干系。许多国际事变,都和中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时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有一大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受国际的影响。……所以我们不懂得国际关系,就不懂得中国,不懂得中国,也不能懂得国际关系,因此不但为了中国的前途,我们应该明白世界潮流和国际关系的趋向。就是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国际问题也成为人人不可或缺的常识,没有了解着国际的关系,我们的生活,只是暗中摸索,准会到处碰壁,或者是开倒车的。 (3) 李平心认为,国际经济最根本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它是由许多单位的国民经济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错综地汇合而成的,所以它是种种矛盾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要素的统一体。但是它却不是各部分国民经济和各种经济形态的单纯结合,因为组成这个统一体的一切分子因素是在不息地交互影响,交互斗争。在研究国际经济时,人们的任务在于分解若干并存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体系之间的矛盾和联系,探求这种种的矛盾和联系怎样发生变化,并说明它们怎样引起和推动一般的国际关系的变化。 李平心分别讨论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自有其理。不难理解的是,在那时他还尚未自觉到合二者而提出“国际政治经济”之学,这门分支性的学科在中国得到倡导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4) 蒋廷黻则极为强调外交史料的重要性,指出:“外交史的特别在于它的国际性质。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研究外交史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其所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简称《辑要》)上、中两卷专论中日甲午之战以前的历史,材料专采自中国方面。原计划的下卷论下关条约(即马关条约)以后的历史,材料则中外兼收。蒋廷黻编这部书的动机不在说明外国如何欺压中国、不平等条约如何应该废除。他的动机全在要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更希望读者得此书后能对中国外交史做进一步的研究。《辑要》上、中两卷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31年和1934年出版。但是中卷出版后不久,蒋廷黻即投身政治,无暇继续这一庞大的计划了。 (5) 1930年前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步紧似一步,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北大台湾籍学生宋斐如以及彼此熟悉的吕振羽、谭丕模等人发起组织以日本问题和东方民族运动为中心的东方问题研究会,并编辑出版《新东方》杂志,刘思慕受邀参加了这个研究会,同时在宋斐如主编的《新东方》杂志担任编辑,他的注意力因而转向侧重于日本时事,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若干有关日本内政外交的文章。这是刘思慕从事日本问题研究写作的开端。全面抗战开始后,刘到了香港“国际新闻社”,担任类似国际方面专栏作家的工作,专门从事国际时事、特别是日本问题的分析。彼时,旧友宋斐如发起组织“战时日本研究会”,邀集一些留学过日本或对日本问题有研究兴趣的人士参加,并创办《战时日本》月刊。此二端推动刘对日本问题和国际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 (6) 无论参加巴黎和会,加入国际联盟,还是出席华盛顿会议,都会涉及中国旨在达成的目标若何,也必然涉及中国的国力状况,以及在国际上之地位所带来的制约、所造成的可能。巴黎和会上,几个大国上下其手,决定弱小民族的命运,中国欲从战败的德国那里收回早先被侵夺的权益,却遭受大挫,已给中国人一个教训。因而对于加入国际联盟之取舍,自不能不引起争辩。梁启超撰《论研究国际联盟之必要》文,表达了既要参与其中又不求“自庇”的务实态度。梁主张:“不必问国际联盟之近效何如;不必问我之能否厕其列以求自庇;但当求使我国堂堂立于天地间,不愧为组织此‘国家以上团体’之一健全分子;但当求以我国之力,促进此‘国家以上团体’之发荣滋长,而率以正轨。夫如是,则研究此初诞育之国际联盟,察其禀性,而觇其祈向,岂非全国民所当有事耶?” (7) 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建立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道亮色,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成立的第一个专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机构。张闻天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协助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主持外交部部务。“在周总理的大力支持下,闻天同志对于建立国际关系和外交问题的研究机构,促进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即便是邓力群,对此也不讳言。据邓力群回忆,他与张闻天接触时张谈得较多的意见是,我国要积极参加世界和平运动,但是应该有自己的看法;对国际法,应该研究,分别对待;我们外交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亚非拉,支持他们争取民族解放、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驻外使馆要组织工作人员系统研究所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情况;要加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情况的研究;等等。由此可见,张闻天对研究工作是极为重视的。 (8) 国际关系发展的动力问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把国家对“权力”和“利益”的不断追求,把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看作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动力。我们传统上则是以国际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阶级斗争的高潮和低潮的交替出现来解释国际社会的曲折前进的。把国际社会描绘成充满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的“自然状态”,把人性的消极方面说成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原动力,这即便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也是失之偏颇的。但是仅仅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说明国际关系的变化,也未免失之简单化。南北关系、东西关系是哪些阶级之间的对抗?恐怕难以自圆其说。作者们认为,至少还有如下四种视角:其一,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从国际关系来看,研究生产的国际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其二,研究国家以外的各种国际实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其三,不仅要研究国际政治活动的对抗形式,如战争、竞争、冲突等;也要注重国际政治活动中的非对抗形式,如合作、妥协、默契等。其四,各种国际性的民间活动对国际关系发展的一定推动作用也应当予以重视,如各国之间的非官方的民间团体往来、各种群众性的思潮、运动等。 (9) 十卷本《国际关系史》问世,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果。这部书由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组织了全国范围内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国际关系学者,经过多年努力始得完成。该书撰写的立意是,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状的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关系史学科的新体系。第二,着意于探索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历史发展进程,以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来评价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在不同时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略古详今。第三,以世界经济关系为基础,探明国际政治关系的发展过程与前因后果,并注意其相互作用与影响。运用历史“合力”的原理来剖析国际斗争的诸多因素与表现,避免把问题简单化。第四,重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随着历史进程在国际关系中所显示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反映客观的历史演变过程,尊重历史的真实性。第五,根据所掌握的大量资料,实事求是地阐明历史事实真相,不溢美,不隐恶,履行国际关系史学者应尽的职责。 (10) 思想的世界,正如物质的世界一样,需要积极的平衡。当只有一种思想占据支配地位时,这很可能不是一种健康的状态,而是一种需要引起人们警觉或警醒的状态了。同理,在世界国际关系学领域,如果只有西方理论独步天下,而没有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理论可作参照、比较、鉴别,也不是一种健康的现象。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的国家,中国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可能界提供独到、平衡的国际关系思想理论。 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属于一种“文化自觉”,过去若干年间,它已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生长发展,初试啼声,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费孝通的界定,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由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够和平共处,各骋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这是一段十分精辟和思想深邃的话,其中包括了如下几个要素或关键点:(1)对自身的文化底蕴要有“自知之明”,而非懵懵懂懂,更不是浑然不知。这也属于一种“知人者智,自知者明”。(2)要在与其他文化的接触交往互动中确立自身的适当位置,确立自主适应的意识并且具有学习能力。(3)要能与他者一起找寻,找到共同认可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秩序,同时又要各展所长,共同发展。 一书解读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来龙去脉 著名学者袁明教授、秦亚青教授作序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