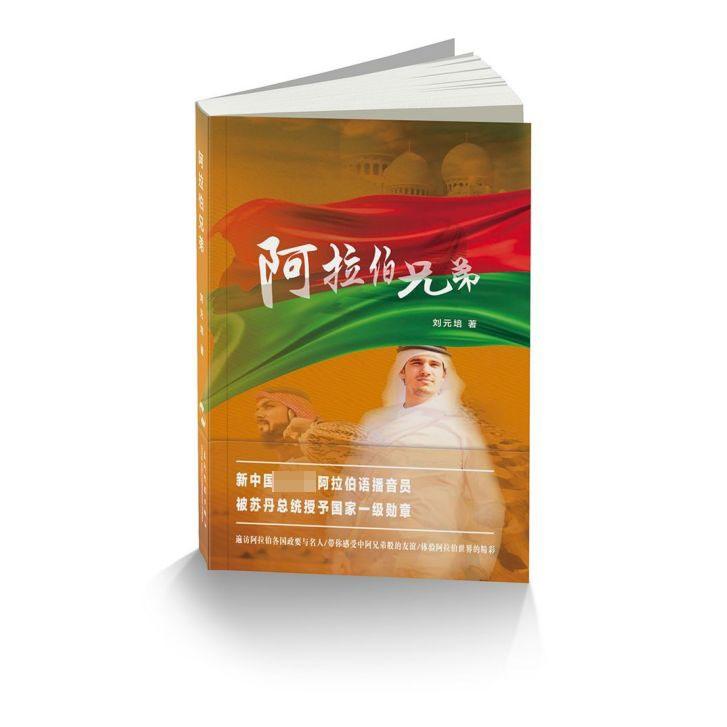
出版社: 五洲传播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1.40
折扣购买: 阿拉伯兄弟
ISBN: 9787508542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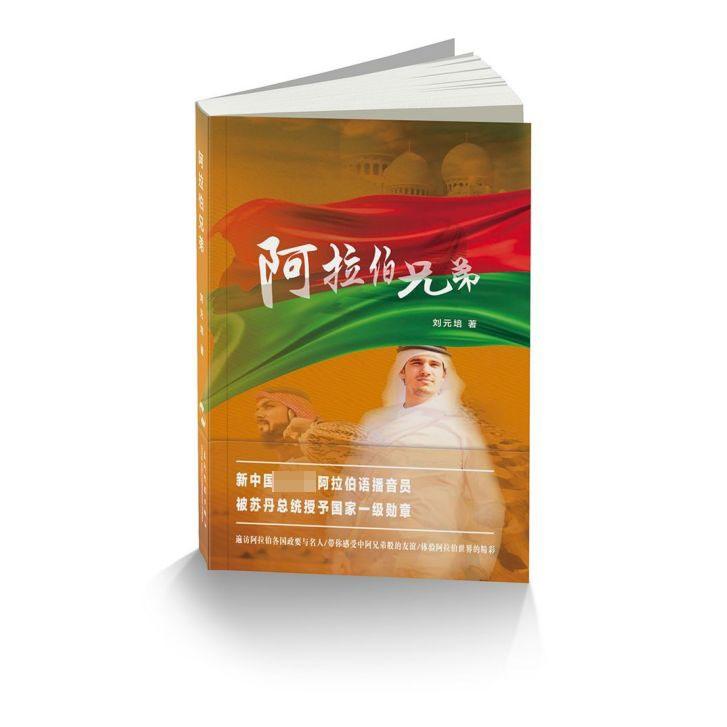
刘元培,1937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55—1960年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学习,1960年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拉伯语部工作并开始播音,成为新中国第一位阿拉伯语播音员。被突尼斯听众俱乐部评为最佳播音员。1982年接受苏丹总统尼迈里授予的国家一级勋章。 20世纪中后期,采访过阿拉法特等诸多阿拉伯国家的政要和各界人士、中国领导人和各领域的人物。任中国国际广播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海湾研究中心理事、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理事、沙特通讯社首任驻华记者、海湾合作委员会商工会中国代表处首席顾问、中国海湾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等。 深入利比亚战地、叙利亚乱局寻找硝烟里的真相,被称为“沙漠之花”; 意大利总统为她颁授骑士勋章“意大利之星
我采访的第一位国家元首是奥地利总统海因茨·菲舍尔。在位于霍夫堡宫殿的总统府内。霍夫堡宫殿曾经是哈布斯王朝奥匈帝国皇帝的宫苑,外观宏伟大气,内部装饰更是磅礴辉煌。那年我26岁。 总统海因茨·菲舍尔慈眉善目。他说:“你真年轻啊!” 这不经意的一句话,却让原本对采访成竹在胸的我变得紧张局促起来。还好随后的采访进展顺利。 结束后,总统在他宽敞得近乎“辽阔”的会客厅里带我“漫步”,一边欣赏墙上的油画,一边话家常。那些年里我是凤凰卫视驻伦敦站记者。菲舍尔总统年轻时也在伦敦学习生活过。他说他住在South Kensington,喜欢参观附近的博物馆。转眼四年过去了,我在海南博鳌再次采访了菲舍尔总统。 菲舍尔总统依然记得我们之前的那次采访。他笑着说:“你还是这么年轻!”而这一两次与阿拉法特面对面 阿拉法特是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曾14次访问中国。会见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曾与周总理和邓小平等进行长时间的交谈。我作为一名记者,曾数次见到阿拉法特,其中最难忘的是两次面对面采访他的经历。 周总理传授经验 我首次接触阿拉法特是1964年。那一年,他同他最亲密的战友阿布?杰哈德一起组成了第一个巴勒斯坦代表团访问我国。阿布?杰哈德是1959年阿拉法特在科威特任工程师时结识的,两人志同道合,一起筹建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中最大的游击组织——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 这一次,阿拉法特一行来华的主要目的是要向中国有关方面阐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希望能得到中国的理解与同情。当他们得知周恩来总理要接见他们时,惊喜交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与周总理会见时,他们直言不讳地告诉总理,西方国家一直把他们称作“破坏者”。想不到来华之后,竟然得到周总理的接见。总理听后开怀大笑,风趣地说:“对旧世界来说,我们都是破坏者。”周总理向阿拉法特详细讲述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并鼓励他们加强内部团结,依靠广大群众。 周总理的讲话使阿拉法特受到极大启发。对“法塔赫”组织产生了巨大影响。阿拉法特和他的战友们认为:中国革命经验对他们产生了积极的、正确的、深远的影响。阿拉法特在当时由他主办的《我们的巴勒斯坦报》撰文说:““通过对中国的访问和革命经验的学习研究,巴勒斯坦的革命方案应该包括:第一,建立稳固的领导集体;第二,赢得人民的信任,提高人民的觉悟;第三,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第四,对压迫者开展武装斗争。””文章还对中国的长征和毛主席给予了高度赞扬。 从此,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游击队员开始认真学习中国革命的书籍,特别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愚公移山》及其他有关做群众工作等方面的书籍。 就在阿拉法特访华的第二年,即1965年1月1日,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领导的“法塔赫”游击队打响了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经过几个战役,特别是1968年的卡拉玛战役,阿拉法特锻炼得更坚强、,更成熟了。此后不久,“法塔赫”宣布阿拉法特会为该组织的正式发言人。阿拉法特从此公开走上政治舞台。在这以后的巴解组织全国委员会的选举中,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等一批年轻人逐步取代了老一代政治家。 城堡内的正义呼声 1983年年底,我阅读了约旦加利勒出版社出版的一本阿拉伯文新书,书名为《被包围城堡内发出的书信》。该书收集了阿拉法特第一次围困在贝鲁特时写的92封书信。这是巴勒斯坦领导人,在坚持3个月的斗争中写成的,是第一部斗争、牺牲、坚持和胜利的历史记载,是从火山口向他的兄弟、同志、全体战斗员、革命者发出的心声。 阿拉法特第一封信是写给整个巴勒斯坦革命的,时间是1982年6月25日,这一天,以色列军队从海、陆、空加强了对贝鲁特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攻击。 4天后,阿拉法特发出了第二封信。从这天起,阿拉法特每天发一封信。有时,如1982年7月27日,甚至发两封。内容一般都是对巴勒斯坦革命形势的通报和对事态的评论。信的最后常常以一节或几节《古兰经》结尾。书信的语气根据情况和内容而异,有陈述的,有鼓励的,也有政治报告式的。情绪时而激昂,时而忧虑。从这些信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巴勒斯坦革命的前进步伐何等艰苦。 8月29日,阿拉法特发出最后两封信,一封是给各办公室、各地区和各部队的。信中写道:“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房屋被炸,30万难民和至少20万黎巴嫩人无家可归”;“贝鲁特战斗说明,我们阿拉伯民族能够抵抗一切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力量,一切相信自己事业正义的人比任何武器都要强大。” 另一封信是给黎巴嫩人民的,这是阿拉法特离开贝鲁特时写的,是他与黎巴嫩贝鲁特人的告别信。阿拉法特在信中说:“黎巴嫩贝鲁特的亲人们!共同作战的英雄们!男女老少们!过去我们并肩战斗在战壕内、工事里,我们一起流血牺牲,英勇奋战。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我要走了。让我们用光和火的语言写下这光辉的篇章,写下我们阿拉伯民族圣战的史诗。” 阿拉法特和他的武装力量离开了贝鲁特后,前往特里波利安营扎寨,不仅又被围困,处境比第一次围困更为困难。但是阿拉法特没有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没有完,他们仍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因为他们的口号是“革命,直到胜利”。 行动隐秘,采访不易 阿拉法特的行动十分隐秘,出访计划、动身时间和地点、出行的目的地和到达时间,事先从不向外界透露。阿拉法特自己也说:“谁也不知道今晚我在哪里睡觉。我坐进汽车后才告诉司机去哪里,飞机驾驶员也只有在飞机升空后才被告知降落的地点。” 我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拉伯语部与巴勒斯坦驻华使馆的关系很好。1988年9月,我得知阿拉法特可能访华,便联系当时的巴勒斯坦驻华大使优素福?拉杰卜先生,能否在阿拉法特方便的时候进行录音采访,大使答应尽量安排。 1988年10月3日,阿拉法特真的来到了北京,我立即与外交部礼宾司和西亚北非司联系,并与巴勒斯坦驻华大使拉杰卜通话,希望安排时间采访。这次阿拉法特访华仅两天,日程非常紧,既要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又要与阿拉伯驻华使团座谈,项目很多。但总算运气不错,3日晚,外交部通知我国际台第二天上午10点采访阿拉法特。 次日上午,我提前15分钟赶到钓鱼台国宾馆阿拉法特下榻的住地。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和翻译室的翻译把我领到采访的会客厅,等候贵宾到来。客厅很大,沙发足足有20张,摆成马蹄形。根据外交部礼宾司的安排,我和阿拉法特坐在中央的两张沙发上,沙发间有茶几,可放录音机。 不一会,即10点整,阿拉法特来到了会客厅。巴勒斯坦驻华大使优素福?拉杰卜介绍了我的身份。阿拉法特握着我的手说:“阿赫兰沃萨赫兰(阿拉伯语的意思为欢迎)!”站在我面前的这位中东风云人物中等身材,穿一身墨绿色军装,上衣扎在军裤内,腰系武装带,还别着一把左轮手枪,头缠黑白方格的阿拉伯头巾,左耳露出,右边的头巾一直下垂至腰间,脖子上围着与头巾相同图案的围巾,塞在军装衣领内,俨然是一位巴勒斯坦革命指挥官的形象。 大家各就各位后,我才发现客厅内人很多,在我的右侧是外交部的几位陪同,左侧是阿拉法特、巴勒斯坦拉杰卜大使、部分随行人员和巴勒斯坦通讯社及巴勒斯坦其他新闻单位的记者。以前我采访外宾时,室内仅我与采访嘉宾2两个人,有时加上外宾的陪同最多3—4个人。这一天,坐了满满一屋子人,我心情有点紧张,情绪有些激动。我试了试录音机,好让心情平静下来。 我知道阿拉法特的时间宝贵,不宜久留,便连珠炮似地向他提问。首先请他谈谈这次访华的目的。阿拉法特回答说:“毫无疑问,我们为有机会到中国访问而感到自豪,因为我们珍惜同中国、中国领导人、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谊和牢固关系。这种坚实的关系永远证明我们之间的关联在任何情况下是深刻的,坚强的。这次访问是在中东形势,特别是巴勒斯坦事业进行到重要而关键的时刻进行的,目的是就巴勒斯坦关键阶段的整个发展交换意见和共同商讨。出于这种考虑,我们进行了这次访问,这是一次对北京的快速的工作访问,期间,研究了我们面临的各种最紧要的问题。” 在这次采访前,阿拉法特曾5次访问过中国。当我问到前几次和这次访华成果时,阿拉法特说:“我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重要的会晤。这些会晤是在兄弟般的积极气氛中进行的。对所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我们人民发动的吉祥起义、我们在南黎巴嫩的人民群众面对以色列的攻击所进行的传奇般的抵抗、和在被占领的领土内我们的人民发动的惊心动魄的革命等问题达成了共识。我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领导对这一坚定的原则立场表示感谢。中国领导人已向我肯定下列长久不变的立场:中国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做出的选择,支持召开在联合国主持下、由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地区冲突各方平等参与的有效的国际会议。这是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首先是自决的权利和在巴勒斯坦的国土上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我可以自豪地说:“,所有的访问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将对巴勒斯坦和中国的关系,对本国、阿拉伯地区和国际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谈到巴勒斯坦问题时,他的语气显得坚定,他说:“毫无疑问,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第一次开始受到各方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美国的重视。当然,这是由于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立场,由于这个得天独厚的起义,这种起义被认为是当代独特的人民革命,它迫使美国政府多次派舒尔茨到中东。目前,以色列面临巴勒斯坦日益高涨的人民起义,美国当局这样做就是帮助以色列摆脱困境。但是,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将持续下去,直到结束以色列占领,和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阿拉法特特别谈到了中国和巴勒斯坦的关系,他说:“中国和巴勒斯坦的关系历史悠久,我们特别珍惜。在这方面,我要自豪地指出,1964年,我和我的兄弟阿布?杰吉哈德烈士组成第一个巴勒斯坦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现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中国政府、巴勒斯坦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这种关系仍然不断强大、持续发展。” 阿拉法特说:“在这方面,我必须满意地提及中国人民、党、政府和领导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起义的坚定和坚持原则的立场。巴勒斯坦起义是独特的人民革命,至今已在被占领土地坚持了10个月。我要再说一遍,我们的巴勒斯坦人民将以万分感激之情牢记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在所有国际论坛和场合支持我们正义事业的一贯的原则立场。我们在这里、在中国找到了真正的朋友。” 正式的录音采访结束后,我便和阿拉法特随便交谈起来,我向他介绍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阿拉伯语广播,并感谢1957年阿语广播开播时几位巴勒斯坦专家的帮助,其中有一位名叫阿卜杜?拉提夫?阿布?贾法尔,他回巴勒斯坦后担任巴解组织政治部(即外交部)总干事(即第二把手)。这时,站在一旁的的巴勒斯坦驻华大使拉杰卜立即向阿拉法特介绍了这几位专家的情况。阿拉法特听后十分高兴,不时点头微笑,他为巴勒斯坦派往中国的第一批专家而骄傲。 限定的采访时间很快到了,我们不得不停止交谈。分手时,阿拉法特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再次向友好的中国人民、友好的中国领导人和友好的中国共产党表示感谢。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这是在世界飞速发展的当下,很多人耳熟能详,并用来自省自警的一句名言,。但不一定都知道它是出自黎巴嫩的文坛骄子纪?哈?纪伯伦之口。 刘元培与阿语牵手同行已己六十三载。可贵的是,他不仅从未忘记为什么出发,而且至今仍对阿语、,对中阿交流事业情深意笃,热诚满满,本书就是个最新的证明。纪伯伦说:“如果能从工作里热爱生命,那就领悟了生命最深刻的秘密。”。刘元培做到了,他应该为自己的工作与人生感到骄傲,应该为自己的执着与追求鼓掌,并干上一杯! 张振华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台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