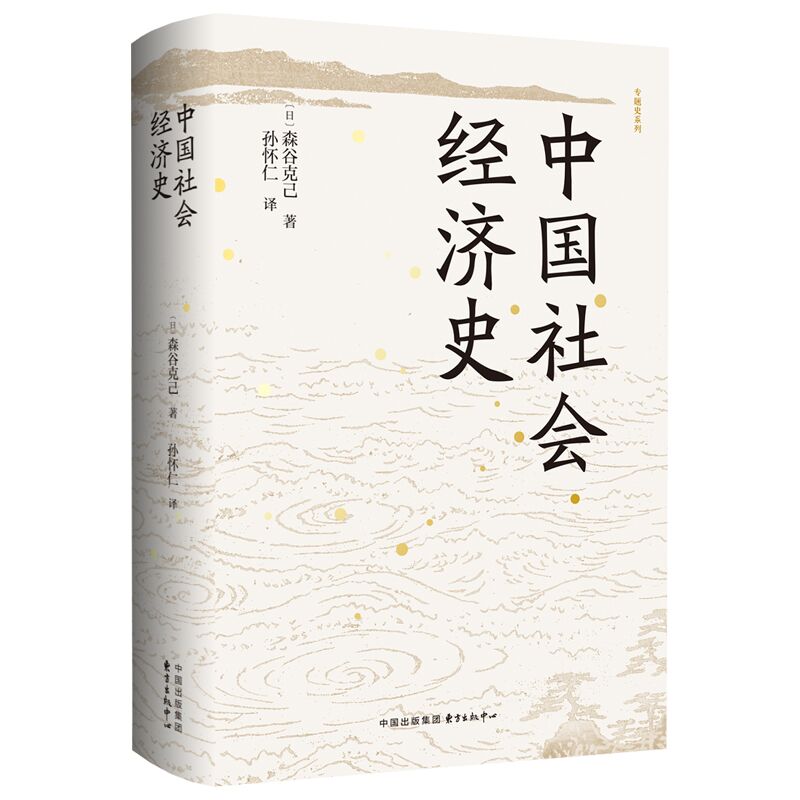
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原售价: 89.00
折扣价: 57.00
折扣购买: 中国社会经济史
ISBN: 9787547323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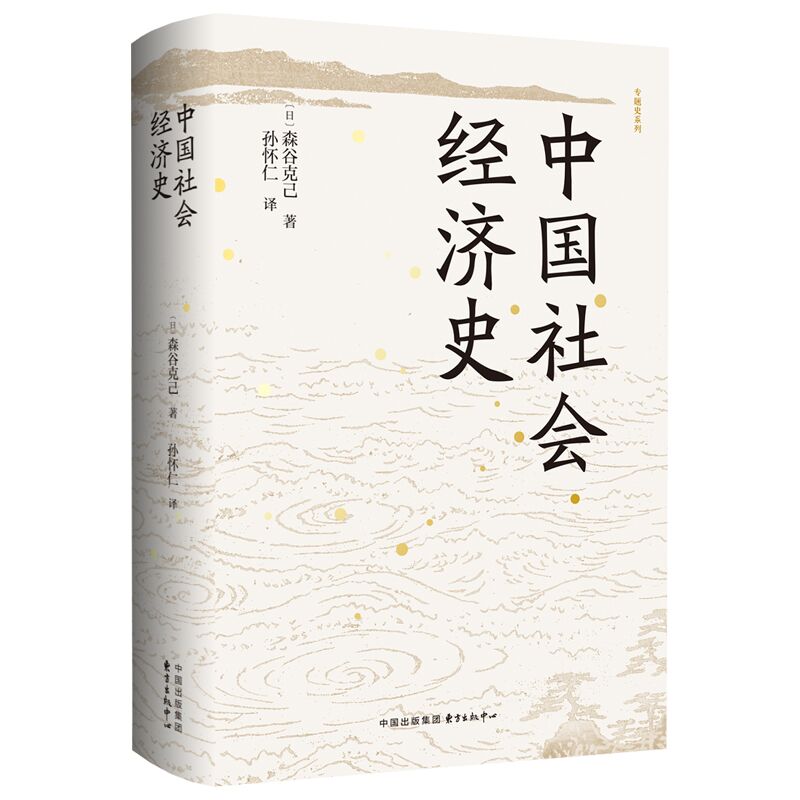
森谷克己(1904-1964),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擅长古代中国的社会及经济发展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东洋社会理论和中国古代史等领域积极从事著述与翻译活动,著有《东洋的生活圈》,译有《东洋社会的理论》。其主要汉学作品《中国社会经济史》1934年在日本出版,两年后(1936年)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孙怀仁(1909-1992),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系。历任暨南大学国际贸易系主任、上海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教授等。1958年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工业经济组组长。1978年起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兼任上海市政协第一至第六届委员、常委,第二至第五届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代表作有《关于纯粹流通费用中可变资本部分的补偿形式问题》《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等。
第二章 原始社会之崩坏时代 西历一八九八至九九年,洹水泛滥,在河南省北端——黄河北侧——彰德府(安阳县)西北,有一个名为小屯的村落中,土地流失,结果,露出了许多记载着奇体古字之龟甲兽骨片。在那里,农民更翻掘附近之田土,由黄土层中,发掘了数千同样之破片及若干之青铜器,象牙及土器等。其后,这土地传说实为古来之殷墟。即殷朝帝都之遗迹——《史记·项羽本纪》中曾记载着:“洹水之南之殷虚。”许多发掘起来之龟甲兽骨破片中记载的古文字,主要的即不外是殷王室中所行占卜之文辞。 中国在殷代末年——即纪元前第十一至十一二世纪左右——已发明了原始的文字,亦即今日字体之原型。换一句话说,那时文字正在形成之途中。自此而后,中国人遂依文字之发明,而进入于历史时代的阶段。同时,殷墟之发掘,使从来只靠《易经》《书经》《诗经》而对太古中国社会之研究,更得以前进一步了。 先根据传说的说法,最初在唐虞之时代,契为司文教的官“司徒”,被封于商。那里是今日陕西省西安府的商州,所以名为商者,据说是因为其地有商山之故。由契到第十四代的成汤,灭夏之桀王,然后统一天下,国号为商,都于亳。由汤王到第十四代的盘庚——其间有商、亳、嚣、相、耿之五个国都——迁都于殷。此后,王朝即称为殷商,或单称为殷。殷自汤王以至于第二十八代的纣王,为周之武王所灭。殷代前后(纪元前一七六六—一一二二年)据说包括六百余年。 殷之文化圈,在本质上讲,还是以山西南部至河南的一带为中心。但也许还要扩大一点,亦未可知。因为根据传说之说,殷王国为周所灭亡后,即归解体,在黄河南岸,河南地方,残留着殷之后裔而为宋之公领;在黄河北岸,即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之地方,原为殷之首都,后为卫之公领;在东北部之泰山山麓,则为鲁之公国。由这样看来殷之领域,当自山西高原之麓,东至泰山之麓,南及淮河上流之黄河边,或者还扩大至渭水流域,亦未可知。而在其周围,东有山东之“夷”;南东有徐“夷”与淮“夷”——这些人在某时代时,像是承认殷之宗主权的;南方长江流域为“蛮”之领域;在黄河之西方,居住着“戎”,在北方有“狄”。事实上,殷是被这些四方之诸蛮族所包围着的。 第一节 牧人种族土著定住而营农业 根据殷墟出土的《卜辞》与古器物,可以说殷人已进入于“未开”之上段。换言之,它们已知道金属之熔解与利用,已知农耕,且已发明着文字。但是在本质上——即由当时大部分及主要生产部门而观——还不能说它们已移入于农业社会。根据《史记》的《殷本纪》,殷人自契至汤,八迁其国,更自汤至盘庚,五迁其国——而盘庚迁殷以后,大体上可以认为是已土著定住。这样,我们对于迁殷以前之商代,容易假定为牧人生活。实际上就根据殷墟的出土品,也可以窥测出当时牧畜是很盛。虽然我们不能把殷人之社会,单规定为“牧人社会”,但像玛斯比罗(Maspero)氏那样的规定为“农业社会”,也不能不说是不充分的。要之,那可以看作为是由牧人生活至农业土著的开端。 (1) 牧畜 根据罗振玉氏读得出的《卜辞》之分类,在体上,关于生产占卜中之回数最多的:第一是卜田(狩猎);第二是卜风雨;第三是卜年(丰凶);第四是卜渔。但第二位卜风雨的占卜,正如郭沫若氏之亦所指摘者,可以说与牧畜也有关系的。但现在,就把这个姑置不论,此外可以使我们想像当时牧畜很盛的材料,也不贫乏。 根据小岛祐马教授之研究,《卜辞》中如羊,牛,犬,豕,豚,彘,马,鸡等家畜家禽的名称,实在可以看到很多。又牧畜之“牧”字,也可以发见。要之,不能不说殷代即在末年,距离以牧畜为支配的生产部门之时代,也还不远。 当时,家畜为重要的食粮资源,即某种家畜,以肉供食用,某种家畜,以肉与乳供食用。但家畜同时又供祭祀之牺牲用。这常常为数极多。不消说,家畜无疑的也还利用为役畜。但尚无使役于农业劳动之形迹。此外,家畜更使用为交换手段。最后,家畜死亡了,即以其角与骨等,利用为各种器具之材料,或王者占卜之材料。要之,家畜对于殷人是重要的财产,是重要的食粮资源。 (2) 农业 根据罗氏之《卜辞》分类,卜年(丰凶)之占卜,其数次于卜风雨之占卜,即后者为七十七,而前者为二十二。 殷代之劳动用具,不是铁器,最多不过是铜制。而这个还难承认是已到达至铜,锡意识的合金——青铜。不消说,在某种时候,因为铜与锡存在于一处的关系,偶然的造成过青铜,也未可知。但是发掘起来的铜器,经化学分析的结果,是纯铜。这样的铜器是很软而柔弱的,因此尚不足以驱逐石器。因而,当时石器还作为劳动用具,而负着重要之任务。石斧、石刀、石锹等都被应用着。不仅这样,木器无疑的也还作为劳动用具而负着重要之任务。因为就在一千年左右后之汉代,如后所述,也还有“木耕手耨”之故。在殷代,农用役畜当然还不知道。 殷代之农作物,以黍为主要作物,其次为禾,麦,米等。又,桑树似乎也已被种植着了。因为在《卜辞》中,“桑”字也可以发见之故。因而,桑树既已种植,当然养蚕也不能不说已经营着了。 要之,殷代之农业,以木器与石器为主要农具,主要的不能不说是在于“木耕手耨”之阶段。即在于所谓“耨耕”之阶段。 (3) 狩猎及渔捞 《卜辞》由其种类而言,除掉关于祭祀及王者之出入者外,以卜田(狩猎)者为最多。但这个事实,意义并不是说殷代就是狩猎时代。一般人类史上,是否存在有狩猎时代,姑置不论,但由《卜辞》分类而即假定殷代为狩猎时代时,那末,这不能不说是藐视了《卜辞》之性质。《卜辞》是王者占卜之记录,因而,关于田的占卜,大体是关于王者之狩猎者。《卜辞》中卜狩猎的所以占多数,正表示着当时狩猎盛行着为支配者之游乐,而其意义,未必是说狩猎为一般住民主要之食粮获得手段。不过,在某种程度内,无疑的一般住民,恐怕也以狩猎作为着食粮获得之补助手段。渔捞在支配者间,不很通行,据《卜辞》之分类,卜田者百二十三,卜渔者仅七回而已。 狩猎具是弓,矢,网,陷阱等。其时,犬已被利用,马也已被使用为乘御之用。渔具是“梁”及“笱”。 当时,在文化中心地的四周,有多种野兽咆哮着。田猎之主要对象,是鹿、狼、羊、马、豕、兔、雉等。据郭沫若氏所说,狩猎一回所获物之最高记录,鹿为三八四头,豕为一一三匹,狼为四一匹。但是关于虎豹等猛兽之记录,完全没有。 要之,狩猎对于一般住民,不过为补助的食粮获得手段,同时已为“一部分特权阶级间所仪礼化娱乐化”(小岛教授语)了。 (4) 工业生产 殷代之劳动用具,最多是铜器。那个还不能不以石器与木器来补足。因而,工业不能不说是在极幼稚的阶段。 当时之工业生产,第一,是土器制造,这个一部分是已进于工艺化。第二,是铜矿之镕解与铜器之制作。铜在当时是最贵重,主要的用作为武器之制作。第三,如《卜辞》中之能发见“丝”“帛”“衣”等的文字,因此纺织也已经营了。这不消说是家内工作。此外,在家庭中也造酒。最后,如《卜辞》中之能发见“宫”“室”“宅”“家”“舟”“车”等之文字,建筑也已进于某种程度了。 要之,工业除土器制造之一部分,铜器制造及工匠等外,仅止于家内工作之阶段。而且,即令这些是专业化的手工业,但也恐怕是隶属于支配者的。 (5) 交易 殷代交易之发达水准,恐怕还不出于自然产物不同之诸共同体间的交换。这种交易,最初,恐怕是以家畜,兽皮来尽货币之职能的,其次,龟甲贝壳也尽了货币之职能。而当时用作为货币之贝壳,据说是子安贝。这恐怕是殷人与沿海诸种族交易而所得者,或者是使沿海诸种族所贡纳者。最后,因养蚕之发达,而绸帛也用作过为货币。 殷代之交通,以战争为主要之形态。武器是劳动手段中的最发达者。战争频繁的发生着,但当时之战争,是扩张文化,掠夺人类劳动力及财货,同时,是混血而使种族向上之主要的交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