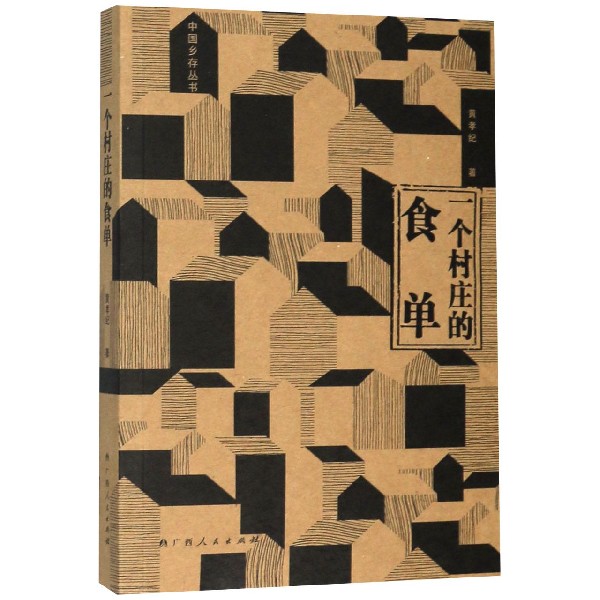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人民
原售价: 48.80
折扣价: 31.30
折扣购买: 一个村庄的食单/中国乡存丛书
ISBN: 9787219108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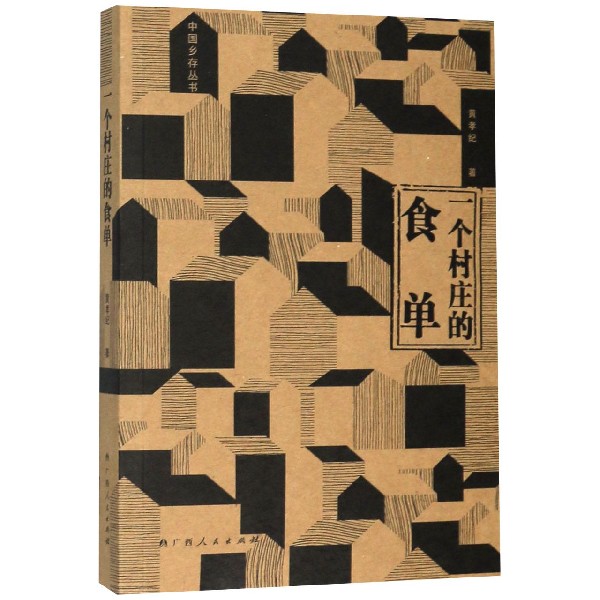
黄孝纪,男,1969年出生于湖南永兴县洋塘乡八公分村。曾为报社记者。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近年致力于散文写作。
鼎罐饭 这辈子注定与鼎罐有缘,才刚出生,就得了个“鼎罐 ”的外号。 母亲告诉我,我大概是1969年农历二月初十子时生的 。那时,在湘南山区八公分村这样一个青砖黑瓦的偏僻村 庄,大概不会有哪家阔气得有一个时钟,因此,我究竟是 哪个时辰来到这个世界的,母亲也拿不准。她只是一遍一 遍地说过,是初九的那个半夜里,鸡叫了头遍,估计是子 时了。后来母亲给我算过许多回八字,请算命先生定时辰 ,也是子时。如此,我的生辰八字就这样定了下来。 我的饭量大得惊人,是母亲说给我听的。在襁褓里, 我就爱吃饭,母亲一口口喂给我吃,我张着贪婪的嘴,像 饥饿的黄口乳燕。同住一个大厅屋的对门老奶奶,是我的 接生婆,笑呵呵地抱着我说:“这个蠢子啊,怕吃得完一 鼎罐饭哩!”老奶奶这金口一开,我从此就有了“鼎罐” 的小名。村里的鼎罐多,可唯独我一人被冠以这个称呼, 男女老幼,无不这样叫我。 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村里家家户户都有鼎罐,大 的、小的,好的、破的,一律黑乎乎的。有的鼎罐,上面 有固定的鼎罐桥,用来在灶口提上提下;有的则是在鼎罐 的两侧耳孔里穿上铁丝做提手;也有的人家,将一口没有 提手的鼎罐埋在灶面下,里面斜通一孔,连接灶膛,用来 温水。 鼎罐煮饭,曾是村人日常三餐最主要的方式,我家自 然也不例外。记忆中,我家煮饭是一个小鼎罐,带铁丝耳 的,底呈锥形,上面是一块小圆铁盖。母亲煮饭时,先洗 净鼎罐,用竹勺从瓦水缸里舀水添上,置于灶口,而后用 手捞盆里淘过的白米,放进鼎罐,盖上盖子。那时,村人 的燃料,主要是柴火,烧炭的时候少,且多在寒冬。其实 ,对于鼎罐煮饭来说,炭火大,火温恒定,反而不好,易 烧焦,锅巴又厚又黑,米饭变黄。倒是柴火煮鼎罐饭,成 为佳配。初时猛火烧煮,火舌熊熊,从灶口周围窜出,舔 着罐体。不久,鼎罐水沸,咕咕有声,渐有热气从铁盖下 冒出,带着白色的米沫,屋子里顿时有了一股米饭的香气 。这时候,柴火要烧得小一点,若是米沫不断溢出来,则 需赶紧揭开盖子,任其热气上冲,待饭水略略平息,方重 新盖上。之后,柴火越烧越小。及至饭水收干,停火煨焐 。这样煮出来的饭,白白亮亮,松松软软,锅巴少而偏金 黄,十分清香可口。 鼎罐饭宜适量煮,最好是三餐三煮,趁热吃。若是剩 饭,则味道要差很多。剩饭也不甚好炒,炒时满锅黏附。 尤其是盛夏,隔夜的鼎罐饭易馊。不过,在我的童年里, 纵是馊了的隔夜饭,母亲也不轻易拿去喂猪。有时她用滚 烫的茶水洗一洗,自己吃了;有时则是洗后晒干,成了干 饭粒。干饭粒坚硬如铁,干锅炒成焦黄,喷香,能当农家 夏日的茶点。 小鼎罐轻巧,霜降后摘油茶时,村人多提了上山煮饭 。干柴山上有的是,灶则往泥土里挖一小坑即成,煮饭的 水自然是山问溪涧的泉水。每当晴朗的中午,绿色的油茶 林里,但见炊烟袅袅,升腾于各处山峦之间。在山上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