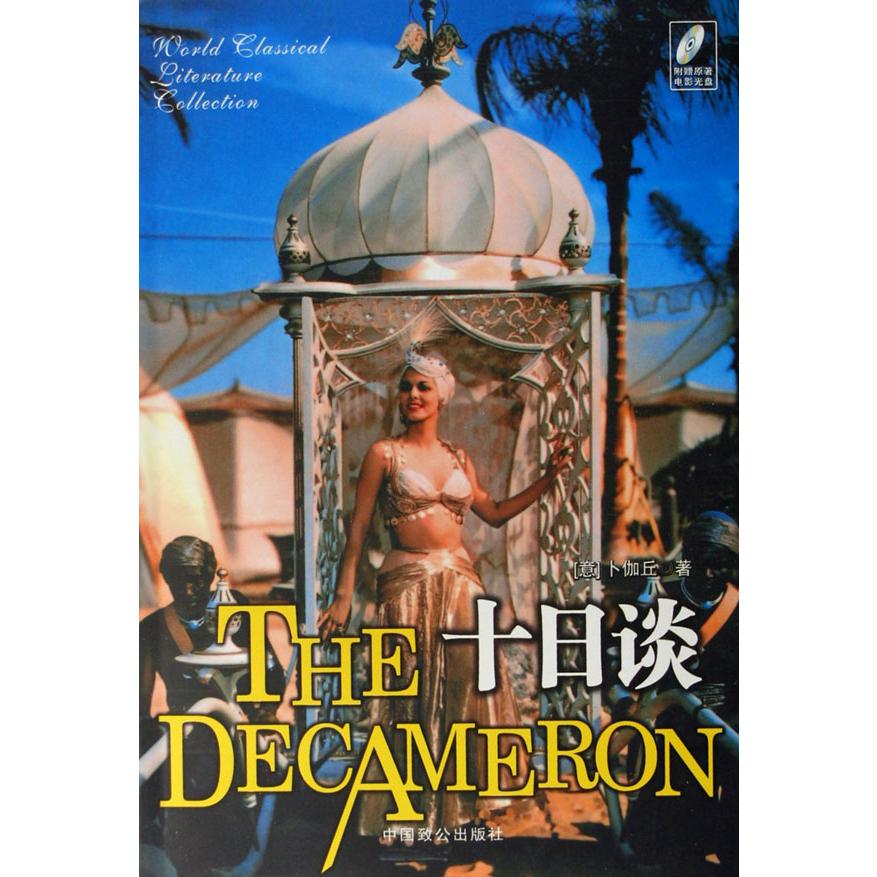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致公
原售价: 28.50
折扣价: 17.10
折扣购买: 十日谈(附光盘)
ISBN: 78017915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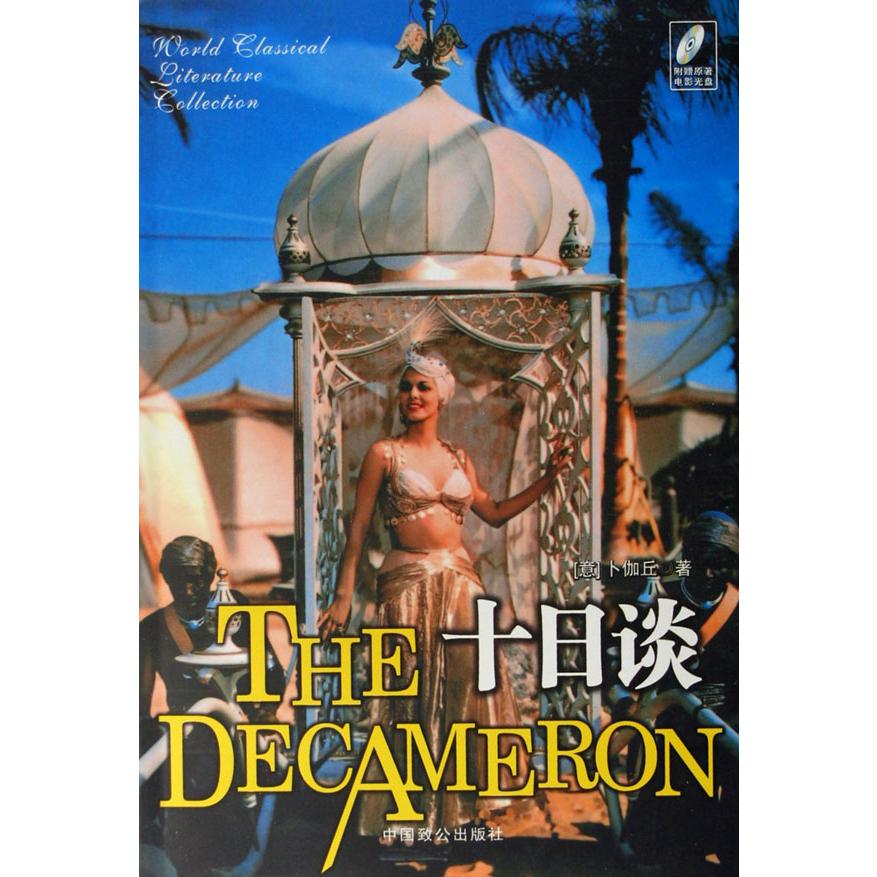
卜伽丘(1313-137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热心研究古籍的人文主义者,通晓希腊文的学者,多产作。著有长篇小说《菲洛柯洛》,史诗《苔塞伊达》、《菲洛特拉托》,牧歌《亚梅托》,长诗《爱情的幻影》、《菲索塔诺的女神》等,其最重要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集《十日谈》。这些作品反映了人文主义的观点及早期人文主义的特点,如提倡复古文化,反对教会的禁欲主义,肯定人有享受现世幸福的权利,歌颂人间的爱情和欢乐等,同时,也表现人文主义思想的狭隘性,把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东西。这正是资本主义萌芽在意识形态方面带来的最初的成果。他与但丁、彼特拉克并称文艺复兴初期的“三杰”。
第一天 《十日谈》的第一天由此开始。作者首先对十个男女集合的缘由做了说 明。他们由潘比妮亚领导,随意讲述故事,以下便是他们所说的故事。 善良的女士们都是富于同情心的,当你们读着这本书时,肯定会认为故 事的开端是太悲惨愁苦了,这正如一场可怕的瘟疫,是一件很不好受的事。 不过请继续往下读。本书的开端虽然凄凉,却好比一座险峻的高山,无限风 光在险峰,攀越的艰苦是必不可少的。俗话说:乐极生悲,而悲到极致,也 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欢乐。 所以开端的凄凉是暂时的,不过占了寥寥几页篇幅罢了;说真话,我真 不愿意累你们叹息、掉泪,可是此外又没有旁的路可通,如果不回顾一下悲 惨的过去,你们将无法理解这些故事,是在怎样的一种情景下产生的;所以 只好在书里写下这样一个开头,让你们体会一下高山后美丽的平原。 公元一三四八年,一场可怕的瘟疫侵袭了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 ——就是那繁华的佛罗伦萨。这场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体的影响,还是威严 的天主对人类的惩罚;它最初发生在东方,然后不断地蔓延开去,不到几年 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计其数;后来竟不幸传播到了西方。大家都束手无策, 城里各处污秽的地方都派人扫除过了,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已经发布了,保 护健康的种种措施也执行了;此外,虔诚的人们还成群结队、零零落落地向 天主一再做祈祷。能做的都做了,可是到了那一年的初春,可怕的病症还是 出现了。 这里的瘟疫与东方的瘟疫不同,东方的瘟疫是鼻孔里一出鲜血,就必死 无疑,而这里染病的男女,先是在鼠蹊间或是在胳肢窝下隆起一个瘤来,到 后来愈长愈大,有时候有一个鸡蛋或苹果那么大。一般人管这瘤叫“疫瘤” ,不消多少时候,这“疫瘤”就蔓延到人体各部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 至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现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时候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 有时候又细又密,不管是什么样子,都是死亡的预兆。 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得了这病就意味着人生的终结。也许这根本是一 种不治之症,也许是由于医师学识浅薄,反正找不出真正的病源,因而也就 拿不出适当的治疗方法来。总而言之,得了这种病而侥幸治愈的人,真是少 得可怜,多数病人都在出现“疫瘤”的三天以内就送了命,而且干净利落地 不带发烧或是其他的症状。 这瘟病的传播速度仿佛干柴靠近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健康的人只要 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确切地说,情况还要严重呢,不要说走 近病人,与病人谈话,会招来病魔;甚至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 西,也会立即染上了病。 这还算不上可怕,比这可怕的事还有呢。要不是我和许多人亲眼目睹, 那么,这种种事情无论谁告诉我,我也不敢信以为真,别说是把它记录下来 了。这一场瘟疫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会传染,就连人类以外的牲畜,只要一接 触到病人、或是病人接触过的什么东西,就染上了病,结果与人一样,过不 了多少时候,就死了,这种情形也是屡见不鲜。有一天,我看到大路上扔着 一堆破烂的衣服,分明是一个染病而死的穷人的遗物,这时候碰巧来了两头 猪,大家知道,猪总是喜欢用鼻子去拱东西的,也正是它们祖宗传下来的坏 毛病让它们倒了大霉。这两头猪用鼻子把那衣服翻了过来,在嘴里乱嚼乱挥 了一番,一会儿工夫,这两头猪就不住地打起滚来,再过了一会儿,就像吃 了毒药似的,两脚一蹬,死在那堆衣服上了。 而活着的人们,每天看到这一幕幕的惨事,心里就充满着恐惧和种种怪 念头;到后来,几乎所有的人都采取了冷酷无情的手段:避不接触病人和病 人用过的一切东西。这样一来,心理上有了一种安全感。 有些人以为与世隔绝高度节制,才能逃过这一场瘟疫。于是他们各自结 了几个伴儿,千辛万苦地找些没有病人的洁净的宅子住下,完全和外界隔绝 起来。吃着最精致的食品,喝着最美的酒,但总是尽力节制,绝不肯有一点 儿过量。他们借音乐和其他的玩意儿来消磨时光,他们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 自己的性情,对外界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形他们完全不闻不问。 也有些人认为对付瘟疫的有效办法惟有纵情欢乐、豪饮狂歌,尽量满足 自己的一切欲望,什么都一笑置之,才是最佳选择。而且他们也当真照着他 们所说的话实行起来,往往夜以继日地尽情纵饮,从这家酒店逛到那家酒店 ,甚至任意闯进人家住宅,为所欲为,这时候往往也没有人来阻拦他们,因 为大家都是活了今天保不住明天,保命都来不及,哪儿还顾得到什么财产不 财产呢。所以大多数的住宅竞成了公共财产,哪一个过路人都可以大模大样 地闯进去,只当是自己的家一般占用着。一时间公共财产倒是增加了不少。 可是,尽管他们这样横冲直撞,对于病人还是避之惟恐不及。如果屋里有病 人,他们是断然不会进去的。 非常时期,浩劫当前,法纪和圣规也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 官员,也都死的死,病的病,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此时的等 级制度倒是销声匿迹了。 大多数人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态度。他们既不像第一种人那样严格节制着 自己的饮食,但是也像第一种人一样适可而止;也不像第二种人那样大吃大 喝、放荡不羁,但也像第二种人一样也满足自己一定的欲望。他们并没有闭 户不出,也到外面去走走,只不过手里总要拿些什么鲜花香草,或是香料之 类,用以消除那充满在空气里的病人、药物和尸体的气味,也借此清神醒脑 。 浩劫时期,也有人有一种更明确和直接的见解。他们认为,要对抗瘟疫 ,只有一个好办法,而且这是惟一的办法,那就是躲开瘟疫。于是,有了这 种想法的男男女女,他们背离自己的城市,丢下了自己的老家、亲人和财产 ,逃到别的地方去——至少也逃到佛罗伦萨的郊外去,仿佛这场瘟疫是天主 降临给那些留居城里的人的,只要一走出城,就逃出了这场灾难。或者说, 他们以为留住在城里的人们末日已到,不久就要全数灭亡了。而自己理所当 然是幸运者。 这些人的见解各有不同,采取的方式也各不相同,而结果却是大致相同 。各地都有好些各色各样的人在自身健康时,立下榜样,教人别去理会那得 病的人,后来自己也病倒了,没人看顾,就这样孤独地断了气。 这并不是胡编乱造,真的,到后来大家你回避我,我回避你;街坊邻舍 ,谁都不管谁;即使亲戚朋友也几乎断绝了往来,难得说句话,也得离得远 远的。这还不算,甚至于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姊妹舍弃兄弟,甚 至妻子舍弃丈夫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最伤心、最叫人难以置信的是连父母都 不肯看顾自己的子女,好像这子女并非他们自己生下来的或者说跟他们压根 儿就没有关系。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