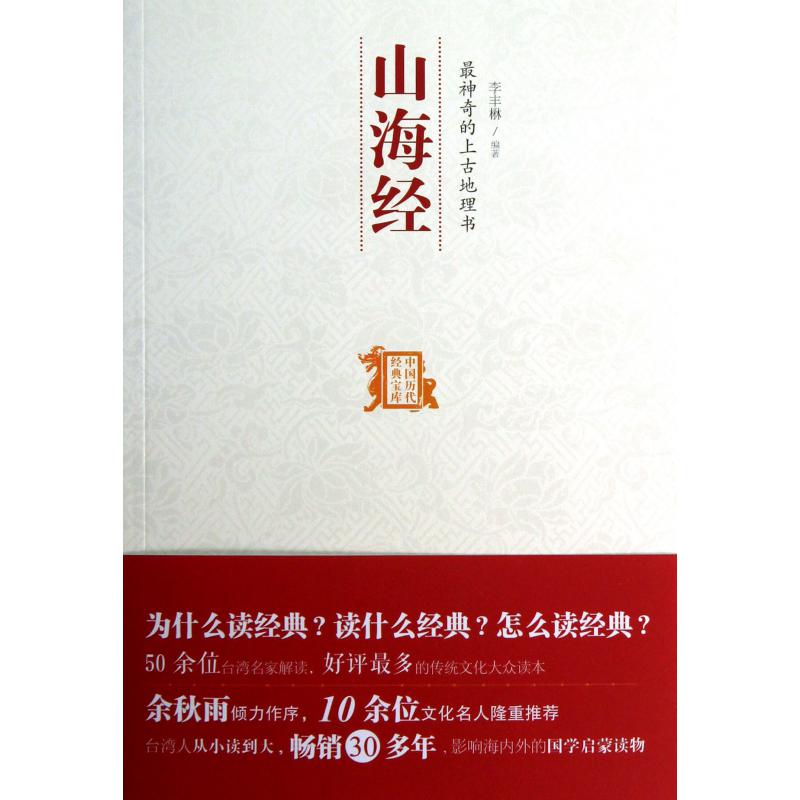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友谊
原售价: 26.8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山海经(最神奇的上古地理书)/中国历代经典宝库
ISBN: 97875057317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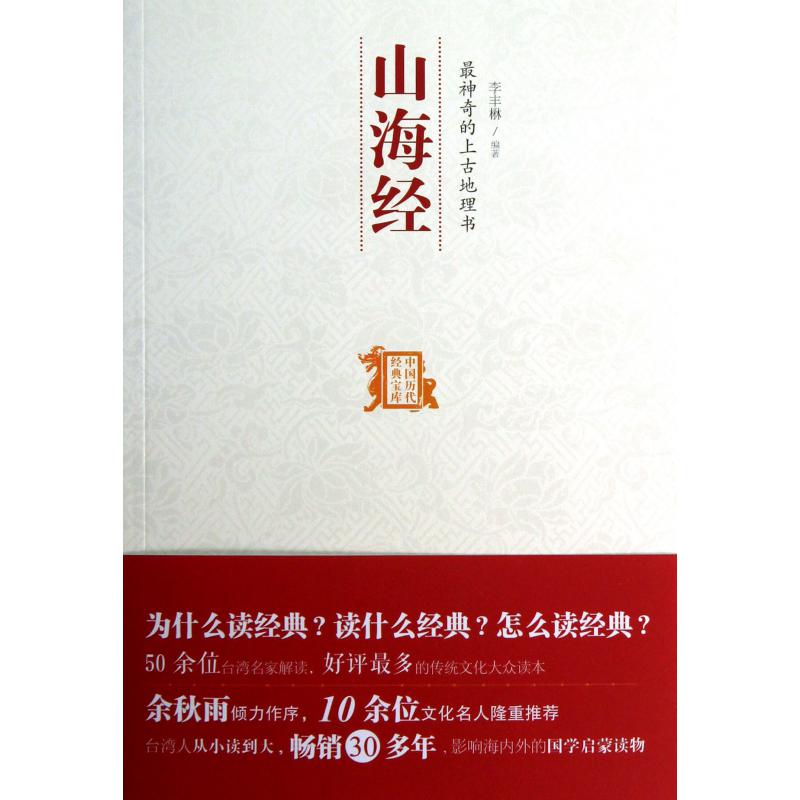
李丰楙,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现任政治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暨宗教研究所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员、中国古典文学学会理事及台湾宗教学会理事。研究领域以中国文学、道教文学、道教文化、华人宗教、身体文化为主。
第一节 《山海经》的编成 《山海经》是一部三万余字、性质复杂的古籍,由《五藏山经》 (《山经》部分)与《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大荒四经》 及较短的《海内经》(《海经》部分)合组而成。它不算是简册繁 重的长篇巨构,但是这五部分的来源、编成以及流传情形,却错综 复杂之极,到了现在还处于众说纷纭的状况。同时,《山海经》这 本曾被司马迁批为荒诞不经的书,也曾被杂厕于书目中的小说类, 而近代研究古代地理的专家学者,却尊称其为最有价值的古地理 书,神话学家也像发现宝藏一样,开始对其进行深入发掘,这真是 一部奇特的古书。 《山海经》为中国最早的人文地理志,是收集古代地方神话 传说最丰富的奇书。但它原始的调查记录者是谁呢?相传其为夏 禹、伯益等所作,刘秀校上《山海经》表文时就主张“山海经者, 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禹乘四载,随山刊木, 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 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后来王充、 赵烨等随从这种说法,但近代学者都觉得难以置信。其实认为是 禹、益所记,只是古人推尊祖师之意,就像《本草经》题为神农所 作。因为禹、益等负责治水工程,涉历山川,书中总要做些纪录; 尤其统一舆图,需要分划经界。诸如此类伟大工作势必引起人类对 山川地理的兴趣,因此后来同一官职的人,基于推崇禹、益的美意, 才题为禹、益所作。 近代研究《山海经》的学者已否定禹、益所作说,纷纷提出 新说:卫挺生说是邹衍为“巨燕”时期的燕昭王所策划的调查探 勘的纪录,蒙文通说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 古籍③,而史景成则认为是楚国史巫之官在国势日衰、臣主共忧患 的局势下,应运起而编纂之书,这些新说多能启发进一步了解《山 海经》的原始型态与编撰过程。《山海经》最初应该是周朝官府所 收藏的地理档案,郝懿行为《山海经》(郭璞注)作了详细的笺疏 以后,认为“周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 之数;土训掌道地图道地慝;夏官职方亦掌天下地图;山师、川师 掌山林川泽,致其珍异;逸师辨其丘陵坟衍逸陉之名物;秋官复有 冥氏、庶氏、冗氏、翨氏、柞氏、薤氏之属,掌攻犬鸟猛兽虫豸草 木之怪□”。周朝官府中有各种各样的职官专门职掌天下舆图的 档案资料,包括了中国境内的山川地理、动植物产及地下矿产、名 山祭典、远方边裔的情状等,这样广博而深入的地理资料,不是邹 衍为燕国训练的探勘队所能完成,也不是南方楚国的史巫能深入各 国、远方及外所去搜集到的。天下土地的地图、九州海外的地域, 只有王官世袭的周朝官府能保存这份珍贵的档案资料。《山海经》, 至少《山经》部分是周朝珍藏的舆图资料:首先《中山经》部分以河、 洛京畿为首,因为那是唐虞夏都城的所在,也是周朝政治的中心, 自然为天下之中,因而纪录时《北山经》、《西山经》自京洛附近 开始向北、向西调查纪录;其次祭祀诸山区图腾神的祭仪,都与周 礼中的祭名、仪式相一致,自然也是由中央职司祭祀的司巫率领巫 师集团担任;再次是远方边裔,当周王室统有天下时,确实需要“任 土作贡”,周朝职司贡职的官员整理各方所贡舆图,才能周知海内 外舆服情形,因为是各地域分由不同职官纪录整理档案资料,才会 有不同文笔、不同方言的歧异现象。当周朝王室衰微时,各国渐有 自己的行政体系,基于政治需要,也需要分任专人职掌纪录地理的 首要工作,经中出现巨燕、大楚以至于竟然有西周等名称,都是职 官各尊视其国的常见现象。因此,原始《山海经》的资料应该是周 王室以及诸侯所纪录的国家档案,其中范围广衍,莫非王土,而独 详于河洛地区,就是京畿为中心的观念;至于神话资料,东、西两 大系俱备,炎、黄两族原发祥于西北,再向东发展,因此保留了早 期西北资料,但东方滨海夷族,帝俊系统的神话资料也是大宗,因 为殷商文化并非在周朝统一之后就完全沦没,还保有部分资料,另 外再加上南方之楚,成为重要一系,也拥有丰富的神话资料。这种 纷然并陈的神话系统实与兼收并蓄的档案及调查资料有密切关系。 今本《山海经》的篇目,是历经多次调整的。汉成帝时尹感 校定的为十三篇:《山经》五篇、《海外》、《内经》八篇;哀帝 时刘秀应是根据三十二篇本重行校定、删汰,改编为十八篇:《山 经》十篇、《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经过删汰),另 有《大荒经》、《海内经》“皆进(或逸)在外”。晋郭璞注解时, 一并注释,成为二十三卷本,后出的郭注十八卷本,《旧唐书·经 籍志》著录时已这样,是另经编排以合十八篇之数的。王梦鸥先生 怀疑,原先《山海经》只有《五藏山经》与《海外四经》两部分, 《海内四经》、《大荒四经》原是前者的另一版本,因为重复的地 方很多,刘歆等将较为残缺部分只作为附录——“皆逸在外”。因 此这种两部组成的结构,可说是先说《五藏山经》而后推广及于《海 外经》,或则先说《海内经》而后推广及于《大荒经》,最末为短 篇的《海内经》,类似这种由内而外的编排方法与邹衍学说的结构 方式有密切关系。 自谓行万里路的司马迁,足迹却未逾于禹贡的九州之外,所 以读到《禹本纪》、《山海经》时,对于昆仑山的有无…… P32-34